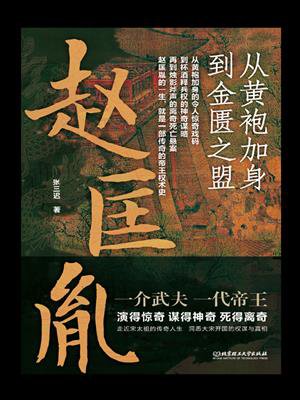第七章
一战成名
赵匡胤终于等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独自率领一队人马攻城拔寨,准备展现自己真正的实力。虽然这队人马只有五千,但已经足够。
涡口位于距离寿州东北约一百五十公里处的涡河和淮河的交汇处,是淮河中游的重要渡口和军事据点。河对面的南岸就是当涂,南唐兵马都监何延锡的一万援军就驻守于此。
第一次独立指挥作战的赵匡胤并不紧张,也没有因为唐军此前的糟糕表现而恃勇轻敌,而是冷静分析形势,定下诱敌深入、设伏歼敌的计策。
三月十七日,赵匡胤派出一百多名骑兵对南唐守军发动佯攻。唐军一看对方只有这么点人,立刻出来迎战。
待敌军追击迫近时,这一小队骑兵就开始掉头逃跑。头脑简单的何延锡果然立即上钩,率全部人马追击,准备消灭这百十来号不知死活的周军。
何延锡一路追到了涡口,眼看就要追上周军,正准备大杀特杀一番,却没想到钻进了赵匡胤所布的口袋阵里。
“杀!”赵匡胤一声令下,事先埋伏好的周军突然四起,杀声震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唐军杀了过去。
唐军猛然遭到伏击,阵脚大乱,被周军围住一顿猛砍,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见大势已去,纷纷举手投降,五十余艘战船也被周军缴获,主帅何延锡在混战中被斩杀。赵匡胤人生中第一场独立指挥的战役,就这样取得完胜。
而这不过是赵匡胤精彩表演的开始。
几天后,柴荣又把肃清寿州东面敌军的任务交给了赵匡胤,命他攻打清流关。
赵匡胤不敢怠慢,率军倍道兼行,很快就杀到了清流关。
清流关乃滁州门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驻守清流关的是南唐老将皇甫晖。
皇甫晖是河北魏州(今河北魏县)人,史书记载他年轻时“骁勇无赖”,是个十足的不安定分子,搞破坏的好手。926年二月,一介小兵皇甫晖先是煽动魏州军士逼迫上司杨仁晸作乱,在对方坚决不从的情况下将其“杀之”;接着又胁迫裨将赵在礼叛乱,制造了著名的“魏州兵变”。
在后唐军队镇压魏州兵变的过程中,皇甫晖故伎重演,胁迫赵在礼一起把领兵前来平叛的李嗣源拉下水,引发了后唐一系列的连锁叛乱,最终导致李存勖兵败身亡。随后,李嗣源即位称帝,皇甫晖也从中受益匪浅,由一名普通军卒一跃成为陈州刺史。
有鉴于此,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给了皇甫晖一句很“高”的评价:“庄宗之祸自晖始。”
不过在十多年后,契丹南下灭晋,时任后晋密州刺史的皇甫晖倒是表现出了一身正气。他不但没有依附契丹,还率本部人马投奔南唐,获得了李璟的重用。
以这位仁兄的闹事经验,率领十万人马,面对寂寂无名的赵匡胤和五千骑兵,怎么也不至于落败吧?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赵匡胤来到清流关后没有盲目强攻,因为他认为敌我兵力悬殊太大,皇甫晖也不是头脑简单的何延锡,想要破敌夺关,必须出奇制胜。
城内的皇甫晖则恰恰相反,他发现周军只有几千人马,主帅还是一个黄毛小子,自己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岂能示弱当缩头乌龟?于是下令打开城门,亲率一万五千部众出城列阵,主动出击,与周军展开激战。
仗一打起来,皇甫晖就忽然发现一个问题:跟自己交战的这股敌军似乎也太少了些,看起来还不到两千人,周军的主力军跑到哪里去了?
正当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出现了——只听背后传来一阵喊杀声,三千多名周军精锐骑兵突然从清流山后疾驰而出,朝皇甫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皇甫晖意识到自己犯了和何延锡同样的错误,中了对方的诱敌之计。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有时人多未必是好事,因为战场狭窄,部队被压缩在一个较小空间内,根本来不及调整阵形,形势十分被动。
皇甫晖试图指挥部队应战,却根本没人理会。唐军被前后包抄夹击,只知对方攻势迅猛,却搞不清周军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被赵匡胤领兵一阵冲击,阵形大乱,大家都只顾四处逃命,完全无力抵抗。
眼看败局已定,皇甫晖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他迅速收拾残兵,一溜烟逃入滁州城,逃命的时候还没忘记断后,命人毁掉护城河桥。
可没想到的是,护城河水根本不足以阻挡对方的脚步。赵匡胤振臂高呼,一马当先,率骑兵强渡护城河,直抵滁州城下。
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一句“环滁皆山也”,足以概括滁州的地理形势。从地理位置看,滁州向东南不到百公里便是长江,长江对面就是南唐国都金陵。如果说清流关是滁州门户,那滁州就是金陵门户。滁州若失守,金陵必定震动,所以李璟才派皇甫晖屯重兵于此,西北援寿州,东南卫京师。
如今,号称“金陵锁钥”的清流关宣告失守,皇甫晖已经退无可退。他若是再退,就要面临被赶到长江里喂鱼的境地了。因此,为今之计只有据城坚守,让周军知难而退。
赵匡胤很清楚,皇甫晖已经吃了一回算计,除非脑子进水,否则他绝不会轻易上当。因此,自己这五千人马面对滁州,根本无计可施。
但令赵匡胤绝对想不到的是,皇甫晖的脑子居然真的进了水。这位以“无赖”著称的沙场老将不服自己被对方用诡计所败,竟然对着城下大喊:“大家各为其主,你让我领兵出城,排好阵列,咱们光明正大地打一仗!”
送上门的肉,焉有不吃之理?赵匡胤哈哈一笑,高声答应。
皇甫晖太不服气了,他只希望能有一次光明正大的机会,让自己好整以暇,从容出击,一雪前耻,以至于完全忽略了兵不厌诈的基本常识。
当皇甫晖率全部主力背城列阵时,赵匡胤确实履行了君子之约,在一旁静静等待。但当唐军刚刚摆好阵形,还没发动攻击时,意外却发生了。
只见原本保持沉默的周军队列中突然杀出一骑,一名将领手抱马颈,身体紧紧伏在马背上,双腿用力夹击马腹,催动战马风驰电掣般向唐军冲了过去,一边冲还一边高喊:“我只取皇甫晖的脑袋,与他人无干!”
众将大吃一惊:这是哪个不要命的?大家定睛一看,此人正是赵匡胤。
影视剧中经常会有孤胆英雄冒着枪林弹雨纵马冲锋的拉风场面。无一例外的是,那些子弹都像长了眼睛一样呼啸而过,绝不往人和马身上招呼。虽然处境万分凶险,但主角每次都有惊无险地取得了上将首级,赢得了胜利。
赵匡胤的这次冲锋不是表演,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场搏杀。但奇怪的是,整个冲锋过程中,唐军方面竟无人放箭阻拦,或许是被这一幕震撼了吧!
由于事发突然,加上冲锋速度极快,赵匡胤转眼就冲到了皇甫晖面前。皇甫晖还没反应过来,就觉眼前一闪,被一剑击中头盔,狼狈地栽下马来。
说书人常讲“说时迟那时快”,战场上的变化也就在电光石火之间。周军见状,大为振奋,立刻发起潮水般的进攻,个个如狼似虎、猛进疾击。唐军见对方主帅如同天将下凡,一招就制服了自己的主帅,顿时胆战心惊,斗志全无,一击即溃。在周军的追击砍杀中,唐军死伤无数,非逃即降。
是役,周军大胜,赵匡胤以五千人马击溃南唐十万大军,生擒皇甫晖、姚凤两位主帅,占领滁州城。
清流关之战和滁州之战让赵匡胤声名鹊起,他在战役中表现出的非凡军事才能更是令人叹服。
面对南唐十万大军,赵匡胤头脑清醒,谋划机智,反应敏锐,出奇制胜。在战斗过程中,他身先士卒,带头冲锋,英勇无比,实在是一名极具天赋的将领,就连手下败将皇甫晖也对他彻底服气,当面向柴荣盛赞赵匡胤的智谋英勇。
攻占滁州后,赵匡胤奉命暂时接手州城军政事务。这天半夜,城外来了一个熟人——侍卫亲军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弘殷。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赵弘殷也参加了此次淮南之战。此番,他带领数千兵马前来滁州,想让儿子赶快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城休息。
没想到的是,赵匡胤竟当众拒绝了父亲。他站在城楼上说:“父子虽至亲,城门王事也,不敢奉命!”
赵匡胤狠心不给老爹开门,是有原因的。
在古代,城门是进城的唯一途径。为保障城池安全,战争期间若没有上级签发的命令或信物,守军是断不能擅自开启城门的。尤其是在夜间,万一被敌军所乘,后果极其严重。因此,“城门王事也”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赵弘殷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也知道儿子的脾气,只好率军在城外安营扎寨,直到第二天一早,赵匡胤才打开城门,迎接父亲进城。
其实,以赵匡胤的身份,加上他和赵弘殷的父子关系,即便打开城门也没什么问题,就算皇帝知道了也不会怪罪。但即便人人都觉得可以破例,赵匡胤依然选择了坚持原则,这才是最难得的。
为人若此,治军若此,何愁三军将士不令行禁止?
除了偶遇父亲,赵匡胤还在滁州遇到了另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一天,城内守军向赵匡胤请令,说捉到了一百多号偷窃军粮的盗贼,依律当斩。赵匡胤正在忙碌之际,没有细问,就直接下了处斩令。
眼看这伙盗贼就要人头落地,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了:“这些人中可能会有无辜百姓,将军不能这样草率处理,还是亲自加以讯问,弄清楚真相后再做处置为好。”
说这话的人时任滁州军事判官,并非赵匡胤的下属,赵匡胤完全可以不予理会,但他觉得对方言之有理,所以还是虚心地接受了意见,亲自讯问这些嫌犯。这一查不要紧,原来所谓的“盗贼”里果然有很多无辜百姓。他们迫于饥饿,不得已铤而走险,偷盗军粮,罪不至死。重新量刑定罪后,不少人免于一死。
五代武将蛮横跋扈,枉法杀人随处可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处斩盗窃军粮的盗贼行为是否合法,根本不会引起关注。但赵匡胤没有滥用生杀大权,这源于他对权力的克制、对百姓的爱惜,以及对生命的尊重,这一点就连柴荣都自叹弗如。在淮南之战中,赵匡胤不仅展现了他的杰出军事才能,更展现出他对人性、对生命的关怀。
那位不知名的滁州军事判官也因为这次劝谏而受到了赵匡胤的尊重,年纪相仿的两人很快就成了亲密的伙伴。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他将成为赵匡胤最重要的参谋助手,他们二人的名字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宋初名相赵普。
在赵匡胤率军连战连捷、横扫唐军的同时,其他部队也纷纷告捷。
一方面,柴荣在探知江北重镇扬州兵力空虚后,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率两万步骑挥师向东,奇兵突袭,一举攻克扬州。几天后,又一鼓作气攻克泰州,乘胜扩大战果。
另一方面,配合后周进攻南唐的武平节度使王逵、吴越王钱俶分别从西南、东南向武昌、常州、宣州等地发动进攻,让南唐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困境。
对南唐来讲,在这三面之敌中,真正的威胁来自江北——寿州被团团包围,朝不保夕,自不必说,连滁州和扬州也先后失陷,这使得被南唐恃为天险的长江防线遭受严重威胁,更让李璟寝食难安。
滁州和扬州同在长江北岸,两地分踞安徽和江苏南端,形成掎角之势。这对掎角所冲方向正是南唐国都金陵,中间仅隔一条长江。虽说以后周水师的实力,渡江直捣金陵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整天处在别人的掎角威胁之下,实在是提心吊胆,觉都睡不好。
为缓解这种令人崩溃的压力,李璟决定求和。他开出了如下筹码:第一,割让寿州、濠州、泗州、楚州、光州、海州六州;第二,赔偿后周军费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罗绮两千匹;第三,自降身价,甘做后周藩属之国,每年进贡价值百万的财物。
又是割地赔款,又是称臣纳贡,就算后世清廷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内容条款也不过如此,足见李璟求和还是拿出了十分的诚意的。而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周军撤出淮南。
柴荣一口回绝:“交出淮南全部十四州,否则一切免谈。”
李璟实在低估了柴荣的胃口。自从决定南征那一天起,柴荣的目标就只有一个——拿下淮南。
李璟愤怒了:“我好歹也是一条汉子,既然谈不拢,那就继续打吧!”
事实证明,天无绝人之路,南唐还没到灭国的时候。很快,李璟就迎来了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来自西南。
准备进攻武昌的王逵还没正式向南唐开战,就先和自己在湖南的老邻居潘叔嗣火拼一场,兵败被杀。南唐西南面的危机解除。
第二个好消息来自东南。
攻击常州的吴越军被南唐将领柴克宏一战击溃,损失惨重,主将吴程孤身逃回吴越。吴越国王钱俶本想借此向后周表表忠心,顺便趁火打劫,没想到遭此大败,自信心受到严重挫伤,再也不敢出兵。因此,南唐的东南面也安全了。
三路敌军已退两路,战场形势的好转让李璟信心倍增。于是,他决定转守为攻,主动出击,狠狠打击一下后周的嚣张气焰,彻底扭转战局。
956年四月,李璟向江北同时挥出两记重拳。
右路拳是陆孟俊率领的一万兵马,主要任务是自东路渡江北上,收复泰州、扬州,夺回金陵东北门户,巩固长江防线。
这路部队的进军出奇地顺利,后周泰州守将没有应战就直接弃城逃窜,陆孟俊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泰州。而当他继续向扬州进发时,驻守扬州的大将韩令坤居然也主动率军弃城。
柴荣闻讯大怒,扬州是江北的重要据点,怎能如此轻易放弃?他立刻派张永德带兵驰援扬州,又命赵匡胤率两千精兵火速前往江北的六合(今南京市六合区),以阻止从扬州方向后撤的周军。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命令韩令坤务必守住扬州。
变幻莫测的战局再次将赵匡胤推到了风口浪尖。但在这重重挑战和风险背后,也隐藏着难得的机遇。
赵匡胤率军赶到六合时,韩令坤已奉命返回扬州。大战在即,为防止韩令坤部再次溃退,赵匡胤当机立断,放出一句狠话:“扬州兵敢有过六合者,断其足!”
这招十分奏效。皇帝下了死命令要守住扬州,自己的发小兼战友也放出了狠话,谁要后撤就在六合砍谁的腿。韩令坤无处可退,只得背水一战。
四月十三日,韩令坤率军击败南唐军于扬州城东,擒南唐主帅陆孟俊,杀之。
赵匡胤在六合用极端方式阻止了周军的溃退,帮助韩令坤守住了扬州城,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李璟的左路重拳正在向他击来。
李璟的左路军足有两万人马,他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将统帅位置交给了自己的亲弟弟齐王李景达,并任命亲信陈觉为监军。
李景达生长在深宫,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从来没有行军打仗的经历,李璟把两万精锐之师的指挥权交给他,实在不知是在求胜还是在求败。
至于监军陈觉,更是声名狼藉,他唯一的特长恐怕就是“窃弄威福”了。除了是李璟的亲信外,陈觉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李璟之所以让他监军,完全是为了防范李景达,因为李景达曾是父亲李昪心中的皇储人选,也是自己皇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这种“无能+小人”的组合,想不打败仗都难。
李景达和陈觉率领的左路军是南唐反击的主力军,他们的任务本来是北上救援寿州,但当大军从瓜洲渡江后,迎面就碰上了还在六合的赵匡胤。
这时的赵匡胤刚刚完成督战任务,麾下只有两千骑兵,而他的对手足有两万之众,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
然而,决定一场战役胜负的不是人数多寡,而是交战双方的将领水平和士兵素质。不幸的是,这对“无能统帅”和“小人监军”碰见了五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
李景达充分吸取了皇甫晖轻敌冒进的教训,没有立刻向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发动进攻。他让大军在距离六合二十里处扎下营寨,设立栅栏,摆出一副严防死守的姿态,一直摆了好几天,这算给了赵匡胤撤退的机会。
但赵匡胤没有选择撤走,他从李景达迟滞不前的奇怪举动中察觉到对方的胆怯和谨慎,敏锐捕捉到了新的战机——或许自己可以冒险一搏,以少胜多。
不过当部将要求主动出击时,赵匡胤却拒绝了。他说出了自己的理由:“敌军摆出防守姿态是因为不了解我们的底细,不敢贸然进攻。如果我们主动攻击,敌军就会发现我们真正的兵力,到时就不会再惧怕,并利用人数优势将我们围歼。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待,等到他们沉不住气主动来攻时,再集中兵力,全力出击,一定可以击败他们。”
敌不动,我不动。面对十数倍于己的敌军,这是一战破敌的唯一良策。
对峙数天后,李景达和陈觉终于摸清了对方底细,决定吃掉这支敌军。四月二十二日,唐军毁弃栅栏,拔营而起,浩浩荡荡地向六合发动进攻。
眼见对方列阵前进,咄咄逼人,赵匡胤没有一丝慌乱——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敌欲动,我先动!没等唐军逼近,赵匡胤当机立断,身先士卒,率领两千骑兵奋勇出击,直插唐军阵中!
周军虽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个体优势明显,士兵们个个骁勇善战,奋不顾身,纵横往来,挡者披靡,气势上完全占据上风,搅得两万唐军乱作一团。反观南唐,刚一开战,李景达和陈觉就慌了神,自顾尚且不暇,更别谈指挥作战了。
南唐拥有两万士兵,却缺乏有效指挥,士兵各自为战,很快便成了一群待宰的羔羊。经过一番鏖战,唐军死伤惨重,被斩杀者近五千,剩下的都被吓破了胆,无心恋战,全都向南溃退,准备渡江逃回老家。
这个时候的唐军完全没了几天前北渡长江的从容,在周军的穷追猛打下,溃兵们乱作一团,争相渡江。由于舟船不足,乱军争来抢去,又是踩踏,又是溺水,再次造成了士兵的大批伤亡。
是役,赵匡胤以两千人马击败两万唐军,斩杀唐军五千人,溺死、伤者不计其数,又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的战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