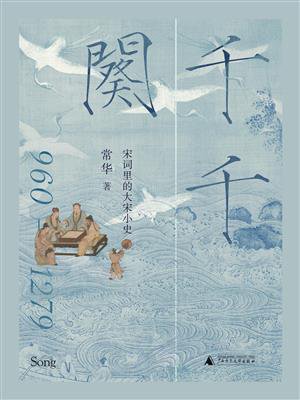权力游戏的局外人
宋宁宗赵扩的悲剧,在于始终不能活出自己。
绍熙五年(1194),对于赵扩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分野。此前,这位宋光宗的次子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君临天下,由于兄长早亡,赵扩便成了光宗唯一的儿子,但这位自幼养在深宫的皇子从未想过自己那么快就会成为一国之君。他的皇祖父孝宗对其疼爱有加,直到他25岁还幽居深宫,未让他有过政务国事的历练,而他的父亲光宗更是受到专横的李皇后的控制,对赵扩没有什么管束。尽管赵扩被封为嘉王,但如何当皇帝、怎样当个好皇帝,光宗也没有给他面授过什么机宜。当然,作为一个在位仅短短五年的南宋皇帝,光宗临御期间的表现也实在乏善可陈,而他的李皇后倒是一个狠角色,据说光宗洗手时发现一宫女双手甚白,便随口夸了几句,结果用膳时,竟发现这个宫女的双手已被李皇后砍下,放在了食盒里。由于李皇后悍妒狠毒,孝宗曾几次要将其废黜,并拒绝认可李皇后之子赵扩为储君,而这也让李皇后与孝宗结下了仇怨。她不仅操控病恹恹的光宗退居深宫,极少临朝听政,而且还怂恿光宗减少去重华宫朝拜孝宗的次数。结果,这位听话的窝囊皇帝还真就照办了,由最初的一月六拜减至一月四拜,再至一月一拜,到了绍熙四年(1193),光宗去重华宫的次数更是骤减到了四次。而这样的报复显然还没有结束,绍熙五年六月,随着孝宗驾崩,已有半年未见过孝宗,即便他病入膏肓也未曾前去探望的光宗,再次做出了让朝臣们认为无视孝道有悖人伦之举,在李皇后的阻拦下,竟然不为孝宗服丧,尽管众臣恸哭恳求,光宗和李皇后也无动于衷。当朝中百官发现这个得了失心疯的皇帝已经完全置孝道人伦于不顾,一场逼宫大戏便开始悄然酝酿。这一年是绍熙五年,史家将这场逼宫大戏称作“绍熙内禅”,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生于深宫长于深宫的嘉王赵扩,还没有做好当太子的准备,就一步跨越上了皇座,成为南宋第四任皇帝。
“绍熙内禅”的幕后操控者有两个人:一个是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另一个是北宋名臣韩琦后裔韩侂胄。宗室出身的赵汝愚曾于乾道元年(1165)擢进士第一,只因为自己是皇室宗亲才屈降第二。他工诗属文,藏书万卷,堪称儒士,在朝中素有声望。和赵汝愚相比,韩侂胄差了点儿,虽说出身名门望族,但他缺乏科举出身,不过是通过恩荫入仕,此外,韩侂胄还和皇室有一层裙带关系,他不仅娶了高宗之妻吴太后的侄女,同时,自己的侄孙女也许配给了当时的嘉王赵扩,有这样一层关系在,韩侂胄虽身居负责进出宫门的閤门司,却是外戚独有的殊荣。绍熙五年六月,当孝宗驾崩,光宗不执丧礼,赵汝愚便与韩侂胄、殿帅郭杲等人密议,决定逼宫,逼光宗禅位,拥立皇子赵扩为皇帝。赵汝愚之所以与韩侂胄密议,就是看准了他能以外戚身份出入慈福宫,与太皇太后吴氏谋议并取得其支持。这个办法很奏效,早对光宗不执丧礼之举看不惯的吴太后于7月垂帘,成为这次宫廷政变最坚强的后盾,当赵汝愚等率文武百官在孝宗灵柩前请求太皇太后吴氏宣示光宗禅位诏,已经老态龙钟的太皇太后吴氏当着众臣工的面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皇帝心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帝位。”
就这样,命运将嘉王赵扩推上了御座,和他的先祖赵匡胤一样,经历了“黄袍加身”的过程。当然,《宋史》中的这两次“黄袍加身”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赵匡胤站在陈桥驿的朝霭中,被众将士披上黄袍,实际是一次有预谋的操作,而当他的后世子孙赵扩被赵汝愚和韩侂胄等人强推上皇位,披上黄袍,这位无心称帝的储嗣一再说的只有五个字:“恐负不孝名。”如果说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开启了一个王朝,那么发生在南宋皇帝赵扩身上的这次“黄袍加身”,实际上带来的是其自身生命的禁锢和一个王朝的阴霾。
阴霾从即位伊始就笼罩在了这位年轻皇帝身上。由于有定策之功,宋宁宗即位之后,即将赵汝愚擢升为右丞相,以独相身份执政;而同样自恃在“绍熙内禅”中颇为卖力的韩侂胄,本以为能做个节度使,却因赵汝愚在宁宗面前一句“外戚不可言功”,官阶只升一级,被授为宜州观察使。韩、赵二人的梁子就此结下,为了将赵汝愚排挤出朝廷,此时尚兼任枢密都承旨的韩侂胄利用了宋代帝王极为看重的台谏制度。有宋以来,朝廷设置的台谏官有纠正皇帝疏失、弹劾百官的权力,刚刚登基的宋宁宗也认为“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然而,这个从一开始即位就处于权力争斗之中的“局外人”,显然缺乏驾驭臣子的睿智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从小就身处幽宫的宁宗宪法不会想到,御史台这块看似一尘不染的净土其实始终就没有真正干净过,尤其是当韩侂胄将自己的心腹耳目安插进来后,更是乌烟瘴气,颠倒黑白。当刘德秀、许及之等人从卑官迅速蹿升至言官之位,他们对举荐自己的韩侂胄感激涕零,纷纷站在了韩氏阵营,而韩侂胄也由此羽翼丰满,“绍熙内禅”刚过去半年,他便牢牢控制了御史台。他迅速赢得了宁宗的信任,即便帝师彭龟年多次就内廷权势的增长对宁宗发出过预警,要求罢免韩侂胄,宁宗也认为“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而随着赵汝愚的支持者纷纷被从要津免职,赵汝愚实际上已是一位落寞的孤臣,这个时候,当被蒙蔽的宋宁宗接过一封封由韩侂胄党羽罗织的赵汝愚贪赃枉法的奏报,再加上一个“宗室不可身居宰执高位”的“理由”,这个倒霉的臣子已经无路可走,在数度贬谪的路上最终暴卒。
如果说宋宁宗在韩侂胄的蒙蔽下保不住一个臣子还是件小事,那么,由一个臣子牵扯出一场文化浩劫就已经让宋宁宗变得很可悲。由于赵汝愚尊奉理学,韩侂胄“恨屋及乌”,他先是将理学宗师朱熹赶出朝堂,随后又假皇帝之口宣布理学为伪学,凡是支持朱子理学的统统被视为逆党,当时的许多文化名流因此惨遭清洗,要么削官流放,要么迫害致死,一度繁荣的理学盛景凋零不堪,而一些举子由于是朱熹的门生,也被挡在了科举取士的门外,枉费了多年的寒窗苦读。
宁宗庆元二年,韩侂胄袭秦桧余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和之,上章论列。刘德秀在省闱,奏请毁除语录。既而,知贡举吏部尚书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令太学及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
这段记录于《宋史》中的文字,让我们看到韩侂胄专权时道学之士被排斥打击的残酷现实,当“稍涉义理,即见黜落”让天下举子们纷纷改弦易辙,根据朝廷之令调整自己的苦读方向,以至于“当时场屋媚时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我们看到,这场被称为“庆元党禁”的文化浩劫,始作俑者是权臣韩侂胄,但发出这道诏令的宋宁宗却因此背上了践踏文化的骂名。
得罪读书人,让宋宁宗成了孤家寡人,而得罪黎庶苍生,则让宋宁宗百口莫辩。在“庆元党禁”之后,韩侂胄已经权势熏天,他“凿山为园,下瞰宗庙,出入宫闱无度”,至于生活用度更是奢侈无比。据说他过生日,百官都要争相献上奇珍异宝,有个叫赵师
 的官员进献了四顶北珠冠,引得韩侂胄妻妾争要,这个赵师
的官员进献了四顶北珠冠,引得韩侂胄妻妾争要,这个赵师
 马上又用十万贯铜钱买了十顶北珠冠。当然,位极人臣锦衣玉食的韩侂胄也有危机感,当他看到“庆元党禁”让他渐失人心,便决定铤而走险,用北上伐金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加分。为了遮蔽自己的野心,他向宋宁宗提议为岳飞平反,追谥“武穆”,又革去秦桧的王爵,改谥“谬丑”,与此同时,他开始厉兵秣马摩拳擦掌准备北伐。韩侂胄的这一系列举动很快令宋廷的主战派士气大振,而宋宁宗的形象也开始在人们的眼中变得可爱起来。
马上又用十万贯铜钱买了十顶北珠冠。当然,位极人臣锦衣玉食的韩侂胄也有危机感,当他看到“庆元党禁”让他渐失人心,便决定铤而走险,用北上伐金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加分。为了遮蔽自己的野心,他向宋宁宗提议为岳飞平反,追谥“武穆”,又革去秦桧的王爵,改谥“谬丑”,与此同时,他开始厉兵秣马摩拳擦掌准备北伐。韩侂胄的这一系列举动很快令宋廷的主战派士气大振,而宋宁宗的形象也开始在人们的眼中变得可爱起来。
然而,宋宁宗知道,从即位那一天起,自己就已注定是韩侂胄手中的一枚棋子,而不是战略决策的有力制定者。综观当时宋金对峙的局势,许多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韩侂胄的北伐必定无功而返,叶适不仅拒绝起草宣战诏书,还上书宋宁宗,认为轻率北伐“至险至危”;武学生华岳上书,认为此时南宋“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认定此次北伐将“师出无功,不战自败”。而最主张北伐的辛弃疾更是对宋金双方战力洞若观火,开禧元年(1205)春,在镇江知府任上的辛弃疾站在北固山上,面对滚滚奔流的长江水,挥笔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善于用典的辛弃疾在这首《永遇乐》中,用当年刘宋文帝草率北伐导致惨败的历史教训警示韩侂胄不要急功近利,仓促出兵,为了更清晰地陈述自己对战局的分析,他还提出了北伐“更须二十年”的慎重主张。然而,包括辛弃疾、叶适等人在内的这些有见地的声音很快就被韩侂胄压了下去,当他得意扬扬地挥舞战旗,号令三军,宋宁宗已在喊杀声中丧失了一个皇帝对时局应有的判断。
事实证明了叶适、辛弃疾等人的正确,这支被韩侂胄仓促组建起来的北伐军由于缺乏有效的训练,没有像样的统兵之将,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开禧二年(1206),身任平章军国事的韩侂胄未做充分准备,便贸然派遣宋军多路出击,命山东、京东招抚使郭倪派兵攻打宿州,建康府都统制李爽率部攻打寿州,江陵府副都统制皇甫斌攻打唐州,江州都统制王大节攻打蔡州。然而,正如拒绝起草宣战诏书的叶适所担心的那样,金军早有准备,看似多点开花的战略布局皆以失败告终,只有镇江副都统制毕再遇连战皆捷,但也无法扭转败局。而杀得兴起的金军则乘胜南下,一路兵锋锐利,恰在此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又叛宋降金,割让了关外四郡,导致宋军雪上加霜。当他们被迫转攻为守,金兵乘势占领了真州、扬州、西路军事重镇和尚原及蜀川门户大散关,这场匆匆挑起的北伐第二年就偃旗息鼓了。
然而,随着宋的战败,金人气焰再起,向宋廷提出了割地赔款、缚送首谋等五个条件。此时,宋宁宗已全无主见,而原来一直站在韩侂胄阵营的礼部侍郎史弥远觉得机会来了,他很快与宁宗的第二任皇后杨氏建立了同盟。出身卑微的杨皇后由于颇有权谋,深为韩侂胄所忌,故在自己的侄孙女韩皇后去世后,力劝宁宗不要立杨氏为皇后,结果杨皇后上位之后,对韩侂胄恨之入骨,当北伐失败消息传来,史弥远又主动找上门来,二人遂一拍即合。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的一天凌晨,据说在畅饮达旦后,韩侂胄醉眼蒙眬地乘着官轿前去参加早朝,结果在皇城墙的六部桥附近被殿前司中军统制夏震率领的数百禁军精锐拦截,他们将韩侂胄五花大绑着拖至皇城墙外的玉津园,当场槌杀,此后史弥远又让人割下韩侂胄首级函装送往金国。对于发生在皇城根的这场政变,宁宗知情却无可奈何,一个权臣说死就死了,还是死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既能看出此时宋廷权力之争的惨烈,同时也看出了宋宁宗的无力,当宋宁宗不胜哀伤道,“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这位羸弱的皇帝实际已经由韩侂胄的傀儡转而成为史弥远的傀儡。嘉定元年(1208),南宋王朝与金朝签订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和议条款为:两国边界不变;宋金两国皇帝以侄伯相称;增岁币予金为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宋纳予金犒师银三百万两。对这纸屈辱的“嘉定和议”,时人刘克庄一首七言绝句在讥讽中充满了悲愤:
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
——刘克庄《戊辰即事》
此后,朝政实际已由史弥远一手操控,在史弥远的操控下,宋宁宗仍旧是一个无法活出自己的窝囊皇帝,当他在57岁病死时,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段历史:这位子嗣早夭的皇帝钦定的养子太子并没有继承大统,取而代之的是由史弥远另立的皇帝赵昀,而在宁宗后期到理宗前期,赵宋王朝成了史弥远的天下。
花似醺容上玉肌。方论时事却嫔妃。芳阴人醉漏声迟。
珠箔半钩风乍暖,雕梁新语燕初飞。斜阳犹送水精卮。
——赵扩《浣溪沙·看杏花》
吟着软词的宋宁宗其实并不是一位声色犬马的皇帝,史载,他“无声色之奉,无游畋之娱,无耽乐饮酒之过,不事奢靡,不殖货利,不行暴虐”。在生活上,他更是节俭力行,据说每到用膳时,他总是命两个小黄门背着“少吃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病”的两个小屏风作为前导。然而,宋宁宗也许不会知道,真正的英主,除了这些,关键一点,是要有审时度势的英气和力挽狂澜的王气,而这些,做了一生傀儡的宋宁宗显然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