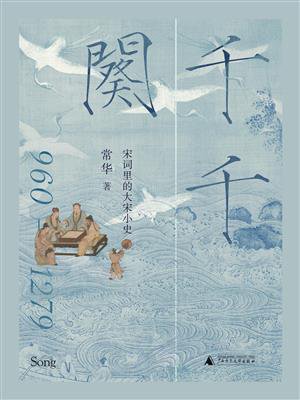牵着皇帝的衣角,孤注一掷
“朕得寇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坐在高高的御座上,宋太宗当着满朝文武对参知政事寇準发出了这样的褒奖。毫无疑问,这是皇帝对臣子至高无上的精神奖励,这样的精神奖励显然要比赏赐良田美宅厚重得多。但是,翻检《宋史》,看一看寇準的宦海生涯,这位社稷之臣真的像魏徵那样慎终如始吗?他所忠心效命的宋王朝又给了他多少施展抱负的机会?
在宋朝相当严格的科举制度下,19岁中进士、33岁即成为参知政事的寇準,堪称宋代官场的奇迹。然而,这样一位多才早慧的臣子并没有一路平坦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从参知政事到宰相,转而到太子太傅、莱国公这样的虚职,以至于最后客死雷州司户参军任上,造成这样生命轨迹的根本原因,是他高傲耿直、刚正不阿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寇準身上,这句话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
《宋史》中有这样一小段文字颇为引人注目:
(準)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
在这段简洁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景:手持笏板的寇準在殿中慷慨陈词,全然不顾及皇帝的感受,当至高无上的皇帝终于按捺不住,怒而起身,寇準竟冒着杀头的危险,硬是将皇帝按在了御座上,直到事情彻底解决方肯罢休。批龙鳞逆圣听者历代均有,但像寇準这般敢于上前揪拽龙袍、喝令皇帝的臣子却不多见,看来,宋太宗能说出“朕得寇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这样的话也确实发自肺腑。
关于寇準刚猛耿直的个性,还有一个例子。淳化二年(991)春耕时节,久旱不得甘霖,而这已经是连续三年大旱了,太宗很是焦虑,遂召集群臣询问执政得失。群臣皆噤若寒蝉,唯独寇準大胆地站了出来,他对太宗说,之所以久旱不雨,其实是量刑失当的表现。前不久,祖吉、王淮两个官员因为贪赃枉法,数额巨大,获罪下狱,然而,真正到最后量刑时,对两人的处理却迥然不同,祖吉被处斩,罚没家产,而比他贪墨更多的王淮却因为是副宰相王沔的弟弟而免于死罪,只是被杖责了几下,继续做官。因为同罪不同罚,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所以用天下大旱来惩罚。对于寇準这番借题发挥的话,史书记载太宗的反应是:“上大悟,明日见沔,切责之。”一直以唐太宗自期的宋太宗对寇準这样的直臣,当然要做出个从谏如流的姿态来,至于此后又以类似“罪己诏”的形式给宰相吕蒙正、副宰相王沔写信,让他们为自己在文德殿前砌一高台,自己在上面求雨,更是做给寇準和群臣看的。这件事虽然最后真的以一场大雨收场,但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宋太宗对寇準的话还是比较在意的。
当然,任何一个皇帝听逆耳忠言的耐性都是有限的,开创贞观盛世的唐太宗都曾经想要杀魏徵以泄愤,更何况无论从气度到胸襟都远不及唐太宗的宋太宗?当生性耿介不懂迂回的寇準一次次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当九五之尊的威严一次次受到挑战,皇帝终于震怒,在太宗一朝,寇準曾先后两度外放,一次外放青州知州,一次外放邓州知州。“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宋史·寇準传》)对于这位“不通人情”的臣子,宋太宗就像碰到了个烫手的山芋,直到他驾崩,也没有让寇準回朝复官。
一个王朝总是在危如累卵时才会意识到诤臣的重要。景德元年(1004),一直被宋朝视为心病的契丹趁新皇帝宋真宗即位未稳,悍然发兵,一路烧杀掳掠,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州城下。在这危急时刻,宋真宗想到了外放的寇準,将他召回,任命他为集贤殿大学士,共商退敌之策。此时,以王钦若为首的一班贪生怕死之辈极力怂恿真宗迁都金陵或成都等地,而刚刚回朝的寇準却铮骨不改,不仅与王钦若等人当廷激辩,直言“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更拿出了当年拽龙袍的劲头,要求宋真宗御驾亲征,以励士气。
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宋史·寇準传》
《宋史》中寇準的这段切谏可谓掷地有声,面对这番无可辩驳的言辞,宋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而当软弱的宋真宗到了澶州地界,看到契丹兵先头部队已与宋军交锋,怕有危险,不愿渡河劳军,仍旧是寇準执意固请,宋真宗方起驾渡河。寇準的冒险坚持换来的是守城将士高昂的士气:“(帝)御北城门楼,(将士)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宋史·寇準传》)
依寇準的想法,宋军宜乘胜追击,继而一举收复当年石敬瑭拱手相让的幽燕之地。然而,根本无心恋战的宋真宗并不想扩大战果,而是以澶州保卫战的胜利作为筹码,急着要和契丹签订城下之盟;此时,契丹也由于长线作战,辎重补给已成问题,正巴不得赶紧捞些好处打道回府。这一次尽管寇準一再苦谏也无济于事了,无奈之下,寇準在盟约最后的条款上将屈辱的岁贡压到了最低,允诺每年向契丹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这便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尽管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的盟约,但“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样的岁贡对于宋朝的国力来说,并未伤筋动骨,而从后来的历史看,这纸盟约确实保持了宋辽之间100多年的和平局面。对于寇準在澶渊之盟中的贡献,仁宗朝的参知政事范仲淹曾给予高度评价:“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身为熙宁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对这位耿介之臣更是英雄相惜,特作《澶州》一诗旌扬寇準之功:
去都二百四十里,
河流中间两城峙。
南城草草不受兵,
北城楼橹如边城。
城中老人为予语,
契丹此地经钞虏。
黄屋亲乘矢石间,
胡马欲踏河冰渡。
天发一矢胡无酋,
河冰亦破沙水流。
欢盟从此至今日,
丞相莱公功第一。
——王安石《澶州》
而宋人陈莹中更是言辞中肯:“当时若无寇準,天下分为南北矣。”可以说,正是寇準这种不畏皇权,敢于“左右天子”的个性,使他成为有宋一代力挽狂澜的社稷再造之臣。
然而,对于这位社稷再造之臣,宋真宗给予他的又是什么呢?还记得那个在兵临城下时劝宋真宗迁都避险的王钦若吗?君子最难防的就是小人,当年在朝堂上寇準曾对其发出“罪可诛也”的厉声呵斥,在澶渊之盟后终于让这个小人找到了报复的机会。王钦若对宋真宗说,在澶渊之盟后“颇矜其功”的寇準,其实一直都在拿皇上做孤注一掷,这种孤注一掷是可怕的,更是不可饶恕的!
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準,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顾准浸衰。
——《宋史·寇準传》
《宋史》中的这段君臣对话,让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形象:一个是妒贤嫉能挟私报复的小人王钦若;一个是面对社稷之臣起了疑心的宋真宗;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险之将至被人暗捅刀子的孤臣寇準。历来刚正之臣少有不是孤臣的,他们逆圣听斥群小的刚直不阿极容易让自己陷入孤立之境,贞观后期的魏徵如此,北宋初年的寇準更是如此。
当王钦若等人的谗言充塞皇帝的耳朵,当寇準耿直的个性触怒圣上威严,等待寇準的,是他生命中又一个寒冷的冬天,就在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準再被罢相,官贬陕州。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寇準《踏莎行》
在北宋初期,寇準的诗文造诣已相当了得,他的七言绝句“比较地不依傍前人,最有韵味”(钱锺书语)。吟诵“高桐深密间幽篁,乳燕声稀夏日长”,我们对应的是《四库提要》的精到点评:“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走进“落日动离魂,江花泣微雨”的诗行,我们听到的是杨慎对其“妙处不减唐人”的诗评……而寇準不仅将缠绵的思绪化作了诗句,更带入到了他的词作之中。在《全宋词》中,寇準的词仅辑录六首,却以特有的清丽在宋初词坛博得一席之地。从寇準留给世人的这六首词作中,我们可发现,这位文名被勋名所掩的臣子,用寥寥可数的词作,勾勒了他沉浮起落的一生。
“四十年来身富贵。游处烟霞,步履如平地。紫府丹台仙籍里,皆知独擅无双美。”在《蝶恋花》的意境里,我们看到的,是寇準前半生仕途的顺遂与心情的畅快。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走进《踏莎行》,我们看到的,则是寇準羁旅行役宦海沉浮的无尽感伤。宋人多以闺怨表达况怨,而寇準的这首闺怨词却表达得克制而含蓄,与五代的浮艳之词做了切割。
“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当寇準以情景交融的笔法写出女主人对远行的夫君渺茫无期的等待,我们便理解了宋人胡仔对寇準“诗思凄婉,盖富于情者”的评价。在北风怒号的外放之路上,这位胸怀社稷却壮志难申的臣子,心中的落寞与悲凉早已被填得满满的,无法释放,更无处消弭,只能化成一阕忧伤的词,徘徊低回,隐入尘烟。
寇準被外放之后,朝中群小当道,被时人称为“五鬼”的王钦若、刘承珪、陈彭年、林特、丁谓一班佞臣争相伪造“天书”,献祥瑞之报,粉饰太平,弄得整个朝堂乌烟瘴气。而宋真宗却一面大兴土木,一面声势浩荡地搞起泰山封禅,在虚无的幻境中,他自欺欺人地做起“帝业永昌”的迷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急于回朝效命的寇準做了一件令他一生都抱憾不已的事情——违心地向当朝皇帝进献“天书”。这种阿谀奉承之举曾最为寇準所不齿,但为了直达圣听,这又好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果然,在各地纷纷进呈的“天书”中,宋真宗终于发现了寇準的名字,他没有想到这位清正之臣也会歌功颂德,高兴之余,马上召寇準回朝委以重任。
然而,以一纸违心的“天书”重回朝中的寇準已经无力推倒群小营造的厚重障壁。就在回朝后不久,真宗病倒,刘皇后开始干政,尽管年幼的赵祯被立为太子,但真正在幕后操控的则是刘皇后,加之“五鬼”祸国,寇準终于按捺不住,大胆进谏。
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预政于内,准请间曰:“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帝然之。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已而谋泄,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宋史·寇準传》
寇準的不入俗流,结果只能有一个:继续被罢官外放。天禧四年(1020),也就是在回朝不足一年时间,寇準先是被罢为太子太傅,后又外放道州,既而再被外放雷州。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寇準《阳关引》
寇準这首化用唐人诗句写就的《阳关引》,被词评家胡仔视为送别词第一。“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时隔千年,我们已无从知晓这首《阳关引》是寇準在真诚地送别友人,还是凭轩感愤之作,但无论是送友也好,自况也罢,《阳关引》的背后,寇準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完成一次送别。从车马繁华的汴京到烟瘴之地的雷州,从三登宰辅的勋臣到贬谪千里的司户参军,走了两个多月方到达贬所的寇準,面对浊浪滔天的琼州海峡,心中暗念着当年写下的“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的诗句,应当会惊讶于自己一语成谶。时年61岁的寇準不曾想到,雷州会成为他最后的外放之地,更是他生命的终结之地,而若干年后,将有一位和他一样仕途坎坷的臣子路过雷州,经历琼州海峡的风吹浪打,一路颠沛流离去往比他更远的儋州。
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
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
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
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
——寇準《病中书》
就在外放雷州的第二年,寇準,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郁郁而终。
《宋史》载,寇準在官贬陕州知州时,曾为一位叫张咏的朋友饯行,临行之际,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曰:“何以教准?”
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
准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
这位友人对寇準可谓了解颇深,在他看来,寇準虽有奇才,但学识仍然不足,而且欠“变通之术”,而正是这种毫无矫饰清正率直的个性,最终导致了寇準悲凉的生命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