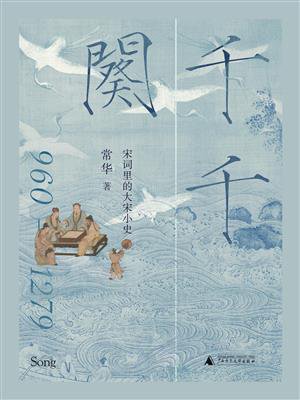用真知作为行吟的词牌
身处吟风弄月的时代,却能矢志不渝地叩响科学之门,北宋沈括,是一个另类的官员,更是一个横跨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学、水利学等诸多学科的科学通才。
梳理沈括的为官履历,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平缓的轨迹。仁宗嘉祐八年(1063)高中进士,神宗时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骨干,熙宁五年(1072)提举司天监,熙宁九年(1076)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元丰五年(1082)因宋军永乐城之战驰援不力为西夏所败,致仕归田。可以说,在20年的宦海生涯中,沈括既没有让我们看到太高的波峰,也没有让我们看到太低的波谷。
然而,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沈括人生的另一条轨迹,便会发现一条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科学之路。这位在政治上并未引人关注的大宋官员,其彪炳史册之处恰恰是在当时被认为奇技淫巧的理科。在奉立德、立功、立言为圭臬的封建中国,能够产生科学家的土壤本身就很贫瘠,而能够出现一位影响后世的卓越科学家就更加难得。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下,沈括却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被誉为“石油之父”,当他看到陕西延州一带居民取流于沙石间的“脂水”燃火为炊,十分兴奋,认为“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并将其命名为“石油”,这个称呼取代了以往的“石漆”“石脂水”“猛火油”等叫法,一直沿用至今;沈括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地磁偏角的人,早在航海家哥伦布远渡大西洋观测到地磁偏角位置的400多年前,沈括就已经发现“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他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更是可圈可点,他创立的隙积数,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而他创立的会圆术,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更为中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和许多官员不同,沈括的“在其位谋其政”渗透进了自己更多的创造性劳动。司天监是宋代专门负责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机构,在担任司天监之职时,沈括治学严谨不徇私情,先后罢免了六名不学无术的旧历官,同时不计出身,破格举荐精通天文历算、布衣出身的卫朴进入司天监,主持修订新历。沈括力主从观测天象入手,以实测结果作为修订历法的根据,据说为了准确观测天象,这位一丝不苟的科学家曾连续三个月每天夜里亲自用“窥管”观测北极星的方位,并将初夜、中夜、后夜所看到的北极星的位置准确地画在地图上,最终测算出了北极星同北极之间的距离。在他的主持下,重新修订的奉元历终于在熙宁八年(1075)颁布施行,此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十二气历”的主张,他以十二气作为一年,一年分四季,每季分孟、仲、季三个月,并且按节气定月份,立春那天算一月一日,惊蛰算二月一日,依此类推,这种历法已经与我们今天使用的阳历十分相似。
作为王安石变法的骨干,沈括和一众文官的最大不同是能够将自己的科学实践精神融入变法的进程之中,正如变法失败后守旧派对沈括的攻讦:“朝廷新政规画,巨细括莫不预。”这虽是一句守旧派射向沈括的“投枪”,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沈括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时,沈括行至镇州和定州时发现:“中山城北园中亦有大池,遂谓之‘海子’……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漫数里,颇类江乡矣。”正是沈括这种积极的作为,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尤其是他在两浙地区提出“宽民力”“毋伤农”的经济主张,更促使沈括关注农业实践和生产技术,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之中。而随着变法的深入,沈括的能力也愈发得到彰显,熙宁七年(1074),他曾受命兼管军器监,正是在这一任上,他提出了“百炼钢”的锻冶之法,即“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而在分析了吐蕃的铁甲制法之后,他更是创造性地提出,“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认为要锻造“柔薄而韧”的铁甲,冷锻之法更佳。由于沈括的钻研精神,使得宋军拥有了坚甲强弓。当这些精良的兵器列装全军,谁能想到,它们,竟然出自一位孜孜不倦善于观察的大宋文官之手。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一方百姓,最典型的事例还是他独出机杼的分层筑堰法。熙宁五年(1072),沈括开始主持汴河的水利建设,汴河是从京都汴梁经淮河入运河,到达江南的唯一水上通道,但由于多年治理不力,淤塞严重,极大影响了流域内的农业灌溉和航运。为了治理汴河,沈括亲自测量了汴河下游从汴梁到泗州淮河岸共840多里河段的地势,在实测过程中,他独创了一种全新的分层筑堰法,即把汴渠分成许多段,分层筑成台阶形的堤堰,引水灌注入内,然后逐级测量各段水面,累计各段水面的差,从而测得汴梁和泗州地势高度相差19丈4尺8寸6分。这种分层筑堰法无疑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创举,仅仅五年时间,汴河便“过尽千帆,斜晖脉脉”,而流域内的引水淤田也达到1.7万多顷。
楼上正临宫外,人间不见仙家。
寒食轻烟薄雾,满城明月梨花。
——沈括《开元乐》
以科学家名世的沈括,很少有人对其文学造诣予以关注。事实上,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沈括也有诗词存世,只是数量不多,这首《开元乐》即是其一。品读沈括的词,我们看不到剪红刻翠,嗅不到红袖添香,和他对科学的求真务实精神一样,沈括在诗词创作上也不喜夸张虚构,浮华造作,同样是用了“开元乐”这个词牌,我们看到其另外两首词也秉持了这种简隽的风格。
“殿后春旗簇仗,楼前御队穿花。一片红云闹处,外人遥认官家。”在平实的表述中,我们看不到华丽的铺排。
“鹳鹊楼头日暖,蓬莱殿里花香。草绿烟迷步辇,天高日近龙床。”在清丽的描摹中,我们看到的是道家的香火。
在沈括留给后世的60余首诗作中,这样的写作原则更是俯拾皆是:
“卷幔夕阳留不住,好风将雨过梅塘。”这是沈括笔下的江南烟雨。
“雨急喧流水,溪深噪乱鸦。”这是沈括眼中的简约山水。
“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这是沈括状写的鄜延气韵。
在诗词中行走,不喜夸张严谨求真的沈括显然另辟蹊径,而也恰恰因为这一点,他常常成为被文人们讥笑诟病的“靶子”。比如,沈括曾说“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再如,沈括评“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这两个例子曾是许多文人对其讥讽的笑料,笑其不懂文学夸张,过度较真其实是一种迂腐。然而,谁也不可否认,这位存词不多的科学家,尽管在文人扎堆的宋代显得是那么独立不群,但正是他的较真,让僵硬的数字翩翩起舞,让吟风弄月的时代呈现出多元的声音。当沈括选择用真知作为自己行吟的词牌,谁又能忽视这位勤思敏行的科学奇才的存在呢?
元丰五年(1082),对于沈括而言,是其政治生涯的终点。就在这一年,为抵御西夏军,给事中徐禧决定以逸待劳,在距西夏都城银州25里的永乐川筑城。永乐城建好后,西夏举全国之兵围困这座沙洲小城,他们切断了宋军的补给线,断绝了通向城中的水道,使一座刚刚建成的新城顿时成为一座死城。此时,守卫米脂的沈括欲率军驰援,但得报正有一支西夏军杀向绥德,危及关中,便“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结果永乐城陷,徐禧战死,而沈括则以“始议城永乐,既又措置应敌俱乖方”的罪名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基本上就宣告了沈括政治生命的终结,元祐三年(1088),就在贬官六年之后,经皇帝恩准,他在润州的梦溪园致仕归田。
离开了政治的羁绊,沈括更加自由,他开始潜心著述,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科学活动,并广泛搜集记述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最终完成了一部旷世奇书《梦溪笔谈》。“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惟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在这部几乎包罗万象的巨著中,我们看到的是沈括在浩瀚的自然科学领域的信然独步,是他在多项学科中的苦心孤诣。《梦溪笔谈》共计二十六卷,再加上《补笔谈》三卷和《续笔谈》一卷,合计三十卷,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数学、地质、地理、制图、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建筑、冶金、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录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过程,从而使这项惠泽后世的发明有了可以传承的文字载体。而身为科学家,不存门户之见,能将默默无闻的印刷技工毕昇抬升到发明家的序列之中,更能看出沈括的虚怀若谷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尽澳中水,船乃笐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梦溪笔谈》中的这段文字,体现了沈括的创作态度和研究方法。文中提到的这位聪明的太监,其实想出的是一个两全之法,龙船腹部需要维修,又不能在水下施工,怎么办?这个黄姓太监想出一个办法,挖一可容龙船的大澳,在大澳底部竖起若干立柱,架上大梁,然后引水入澳,船便浮于水中,再把水排出去,船就落在了横梁上,工人们便可修缮船腹,等修复完毕,再将水重新注入,撤去梁柱,并在大澳上方建屋,就成了藏船之室,不至于在阳光下暴晒干裂。和这则修龙船的故事相类似,沈括还收录了一则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丁谓复建宫室的办法。《梦溪笔谈》载:
祥符中,禁中火。时丁晋公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排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宫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北宋真宗朝的丁谓人品很差,但脑子却很灵光,皇宫着火,丁谓任修葺使主持修复宫室,他想出个一举三得之法:在宫外凿街衢以取土,继而引汴水入沟堑,将建筑材料从水路运至宫中,待新宫建成,又将废墟的建筑垃圾填入沟堑,复成街衢,遂“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事实上,诸如修龙船、造宫室这类奇思妙想在《梦溪笔谈》中还有很多,它们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也彰显了沈括这位北宋通才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他注重科学实践,在《梦溪笔谈》中,他曾言:
古今言刻漏者数十家,悉皆疏缪。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于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
正是这样充满独立思索的科学实践,让沈括研制改进的漏壶在时间测定上变得更加精准。他善于观察推演,认为“观古人者,当求其意,不徒视其迹”,说到底,就是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他曾去过太行一带,在那里,他看到山崖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由此,他推演得出结论:“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他更尊重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正是这种“有常有变”的唯物主义立场,让这位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可以跳出所谓的五行灾异之说,以一种尊重自然运行规律的态度,一丝不苟地进行科学研究……
《梦溪笔谈》前后共创作七年,身处润州梦溪园的沈括曾说,在这部书中,“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抛却世事纷杂,不记录人之短长,事之毁誉,己之荣辱,而专注一心地将其打造成一部充满科学探索精神的百科全书,这正是历经近千年的时光之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仍历久弥新、烛照后世的主因。这部《梦溪笔谈》,不仅国内学者将其作为研究中国科学史的重要依据,外国学者对它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同样评价甚高。日本著名数学家三上义夫赞道:“沈括这样的人物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唯有中国出了这个人。”“日本的数学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沈括。”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则说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他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据《梦溪笔谈》载,当时沈括为了研究光的直线传播现象,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曾做过一个小孔成像的实验。他在纸窗上开了一个小孔,使窗外的飞鸟和楼塔的影子成倒像于室内的纸屏之上,根据实验结果,他形象地指出了物、孔、像三者之间的直线关系。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也许不会知道,通过《梦溪笔谈》这个孔洞,他呈现给后人的,同样是一个丰富而特别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