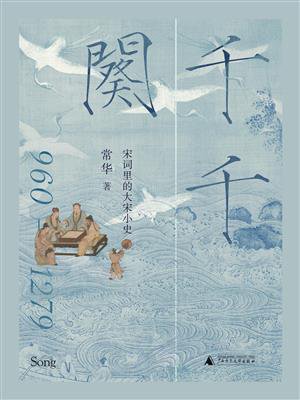血路与退路
放眼两宋,忠臣难得,而忠直之臣能申大志以报国者,更不多见。
提到靖康之耻,人们想到的更多是徽、钦二帝的昏庸无能,但如果我们仔细回望那个让赵宋皇族蒙难的历史断片,便会发现,在杀气腾腾的金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却有如松柏般矗立,他,就是时任兵部侍郎的宋代名臣李纲。
李纲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在宣和元年(1119)。史载,这年六月,汴京发生水灾,黄河洪峰过境时,水位高达十丈以上,一时间,“京城之西,大水渺漫如江湖,漕运不通;畿甸之间,悉罹其患,无敢言其灾异者”。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水灾,宋徽宗竟荒唐地找人以“厌胜”(古代一种巫术)之法退水,满朝上下无一人发出质疑之声。见此情景,时任国史编修的李纲不顾从六品的低微身份,连上两书,不仅直言徽宗应“寅畏天戒”“博询众谋”,要下罪己诏,同时提出了“治其源,折其势,固河防,恤民隐,省烦费,广储蓄”等六项治防水患措施。一个从六品的官员竟胆敢将大灾异和天谴联系在一起,又是让皇帝下罪己诏又是影射皇帝大兴土木空耗国力,当然让徽宗十分恼火,很快便以“挟奸卖直”之罪,将李纲贬为承务郎,监南剑沙县税务。沙县为闽中古城,与李纲的祖籍福建邵武相距不远,初到贬所,李纲不仅没有被贬谪的落寞,反而为能吃到当地味美多汁的荔枝而倍感惬意,“不烦传送之劳,以资口腹之适,快平生之素愿,饱珍味而无斁”,当李纲在《荔枝赋》中抒发自己啖食荔枝的快乐,我相信,这位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太学的京官,实际是在以一种生命的达观看待自己首次因言获罪的境遇。
忠耿之臣的特点就是永远不会绕弯子。时间走到宣和七年(1125),就在这年冬天,金军大举南侵,步步进逼宋都汴梁。社稷危难,徽宗手足无措,朝中大臣更是一片议和之声。就在此时,担任朝中太常少卿的李纲再次挺身而出。如果说六年前的水灾让李纲看到了一个王朝的溃堤之患,那么六年之后,李纲已经从汹汹而来的“兵灾”中看到了大厦将倾的危险。仍然是“狷介”得难以讨喜的性子,仍然是没什么话语权却又不吐不快的态度,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李纲的劝谏更有了一层“逼君就范”的味道,他用匕首在自己的胳膊上划开了一道口子,蘸着鲜血写下了一封措辞激越的血书。
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
这封血书,是李纲随着一道颇具战略眼光的“御戎五策”奏书一同献上的,在这封谏书中,李纲直言不讳,几乎是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劝徽宗马上禅位,速立新君以提振士气。在李纲看来,大敌当前,大宋王朝太需要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天子了,而淫奢怯懦的徽宗显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这时,必须效仿唐朝故事,像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奔蜀之际肃宗灵武即位那样,以一个全新的国君面孔重拾王朝的信心。
李纲的这封血书,绝对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呈上去的,自古皇位继承之事本身就是君臣之间的敏感话题,况且李纲的这封血书显然不是和徽宗探讨,而是直接逼宫,让徽宗赶紧交出皇权。然而令所有朝臣都没有想到的是,徽宗看到李纲的血书,不仅没治李纲谋逆之罪,反而没打任何折扣就同意了。其实,此时43岁正值春秋鼎盛的徽宗比谁都清楚,兵临城下的皇位更像一个烫手山芋,与其天天听着金兵的马蹄声坐立不安,不如赶紧找个人给自己当挡箭牌,而这个当口,李纲的血谏正好给自己一个台阶。很快,这位并不算老的艺术家皇帝就将皇位禅让给了25岁的儿子赵桓,自己则忙不迭地当起了太上皇,带着后宫妃嫔和一众旧臣仓皇逃离汴京。
新皇帝钦宗即位,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气象,这位在李纲眼中有恭俭之德可守宗社的新天子即位伊始,就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兼亲征行营使,委以防卫京都的重任。看到钦宗能积极应战,李纲十分兴奋,马上便发动军民,严密布防,加固城堞。靖康元年(1126)正月,凶悍的金兵开始向汴梁城发起猛攻,在飞矢如蝗的进攻中,整座汴梁城都能感觉到这支金兵铁骑所带来的阵阵杀气,但让金兵困惑的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一触即溃的疲弱之师,而是一面打不透撞不碎的铜墙铁壁。在连续十昼夜的激战中,李纲身先士卒不畏矢石,始终在城头督战,并屡挫从城沟来袭的金兵。最终,远程奔袭的金兵补给不足,死伤惨重,被迫退去。汴梁保卫战,是孱弱的宋朝为数不多的胜仗,而李纲是这场战役卓越的军事指挥者。
然而,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很快就化为乌有。一场汴梁保卫战,鼓舞了广大军民的士气,却驱不走朝堂的颓靡之气。此时的宋钦宗,早已被金兵的喊杀声搅乱了神经,他优柔寡断,一直都在战与和之间徘徊,最终令宋廷失去了乘胜追击的战机;而面对朝中大臣们不绝于耳的议和之声,宋钦宗不仅没有保持一个皇帝应有的威严,反而唯唯诺诺,首鼠两端,成了一个失败的胜利者。早在金兵昼夜攻城之际,钦宗就已如坐针毡,一些主张弃城逃跑的大臣遂撺掇钦宗不要再和金兵硬碰硬。见此情景,李纲力谏钦宗,并对打算逃跑的钦宗晓以利害:“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愿以死守,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敌兵已逼,知乘舆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这个说话不会绕弯子的直臣对钦宗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所有人就打算据城死守了,你既然想逃走,我们也没办法护卫你,万一被敌兵追上,你的身家性命可就堪忧啊!钦宗听此一言,也就放弃了逃跑之念,他对李纲道:“朕今为卿留。治兵御敌之事,专责之卿,勿令有疏虞。”看看,这就是曾被李纲认为可守宗社的新君,一句“朕今为卿留”,让我们仿佛觉得钦宗能留下来纯粹是给扶自己上位的臣子一个面子,殊不知,李纲的据城死守给的又是谁的面子!有这样一个软骨头的皇帝在,接下来的发展轨迹自然是可想而知,在反反复复的拉锯战中,钦宗再也不想硬撑危局了,最终倒向了投降派一边。即便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猛击登闻鼓,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也无济于事,在痛快答应金兵苛刻的议和条件的同时,钦宗不惜自毁长城以示其诚,守城有功的李纲不仅未得任何封赏,反被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罢官,一直贬到了比福建沙县更偏远的重庆。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就在汴梁保卫战胜利不到十个月,金兵卷土重来,宋钦宗在外无御敌之将,内无首辅之臣的情况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遂发出一道急诏封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令他火速赴京勤王。然而,已经走到湘江边的李纲又怎么可能来得及救火呢?就在李纲日夜兼程北返到中途的时候,汴京城破,钦宗和他那位太上皇父亲一起,成为远徙荒蛮的囚徒,而“靖康”,也由此成为宋人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耻辱年号。
汴京城破后,赵构在应天府匆匆即位,是为宋高宗。作为一个怎么也轮不到当皇帝的九皇子,赵构为了稳固岌岌可危的帝位,即位之后,马上任用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对于这个在战乱中草草组建的南宋朝廷,前朝老臣李纲同样不改其忠贞本色,甫一入相,便代表主战派向高宗上陈十议,奏议直接提出反对和议、收复失地的主张。在李纲看来,“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李纲上陈的这十条奏议堪称是对南宋朝廷的精准献策,弱国无外交,没有强盛的国力,就不可能有与金人对峙的筹码,将永远改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以守为策,整饬军政力量,稳定经济以稳住民心,无疑至关重要。
立足未稳的高宗对李纲言听计从,短短几十天时间,李纲的十议主张便得以顺利推行,在惩办张邦昌、莫俦等卖国贼后,李纲开始有条不紊地整饬废弛的朝纲。在他的力荐下,张所、傅亮、宗泽等抗金志士相继被重用,使匡复中原收复失地成为上下共识,与此同时,采取寓兵于农策略,“仍创骁胜、壮捷、忠勇、义成、龙武、虎威、折冲、果毅、定难、靖边凡十号,每号四军,每军二千五”,迅速集结起军事力量。为了更有效地扩大抗金的有生力量,李纲又上奏高宗选派将领,经略两河,增援义军,一时间,“两河响应,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皆附之”。当两河地区腾踏起收复失地的滚滚黄尘,当石州、陕州、绛州相继重归宋廷,李纲,这个在以文驭武的时代挺身而出的战时宰相,用自己强健的军事人格为新生的政权赢得了可以立足的空间。
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彰显出卓越的才能,在一系列经济政策上,李纲更是出手不凡。为了让这个新生政权在风雨飘摇之中立足,李纲殚精竭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政策。当他看到,“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新生的南宋政权随时有倾覆之危,遂“命都水使者陈求道等措置,凡二十余日,而水复旧,纲运沓来,间拨入京师,米价始平”(《李纲行状中》)。形势扭转后,李纲开始大力整饬南宋的经济秩序,他认为中央对地方的盘剥是造成民力疲弱的主因:“夫民犹鱼也,财犹水也,鱼恃水以生,民恃财以养,水日汲而至于涸则鱼亡,财日取而至于匮则民散。故善养鱼者,蓄之于陂池深渺之间;善养民者,临之以宽厚简易之政。”(《乞减上供数留州县养兵禁加耗以宽民力札子》)在这样的执政理念下,李纲大刀阔斧,施行了一系列缓解地方财政的措施。可以说,正是这位南宋首任宰相的呕心沥血,才使得南宋朝廷在肇建之初,得以保持了财政的稳定。对此,朱熹评价甚高:“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李纲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臣,最终难逃被废黜的命运。当南宋政权稍微稳定,宋高宗想到的不是收复失地,而是议和与迁都。而在李纲的人生信条里,只有血路,绝无退路,面对徽、钦二帝如此,面对高宗,李纲更是不改初衷。听闻迁都江南,李纲曾数次上书,力陈迁都之弊,极力主张挥师北伐。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况尝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
历史跨越900年,当我们再回头审视这段充满激情的文字,不能不为李纲的忠耿与洞见所折服。这位历经三朝的臣子,好像使命就是要做宋王朝的一堵墙,每当皇帝想要撤退逃跑,他便不由分说地堵住皇帝的退路。
然而,一心偏安的宋高宗早已不是刚刚即位的宋高宗,他对李纲的任用,与其说是量才而用,不如说是小朝廷初建时的权宜之计,他要稳住臣民的情绪,也要做出迎回徽、钦二帝的姿态,而当这样的价值已经失去,李纲的奏议即便再具真知灼见,也会被束之高阁。建炎元年(1127)八月,相任上才77天的李纲被罢职了。“纲罢而招抚、经制二司皆废,车驾遂东幸,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金兵益炽,关辅残毁,而中原盗贼蜂起矣。”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
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李纲《苏武令》
这首《苏武令》,为李纲被罢官时所作。在此后的宦海生涯里,这位始终不给自己留退路的臣子被一贬再贬,最后竟被贬谪到了海南岛上的万安军,而这处贬所,竟然比当年苏轼的贬所还要远!尽管此后不久李纲便被高宗赦免,准予放还,居处自便,但这位老臣的心已如同死灰。当他一路颠簸从海南回到故乡福建邵武,当曾经的一腔激情被冲荡得气息奄奄,李纲郁闷成疾,不久便病逝。“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对这位涕泗满襟的老英雄而言,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境。
李纲为官洁身自好,两袖清风,据传在他邀人过生日的请柬上,都要特意注明“主人清茶待客,贺客勿带礼品”字样,然而有一次过生日,李纲却破了个例。据说有一次李纲回乡探亲,正赶上大雨,乡间小路泥泞难行,当地村民苦不堪言。看到此景,李纲有心为百姓修一条路,但苦于囊中羞涩,就在这时,他忽然想到过几天就是自己的生日了,于是便马上写起了请柬,这一次,李纲在请柬后只写了“主人清茶待客”字样,当友人收到请柬,都以为这位老臣终于想通了,于是纷纷带着金银珠宝玉器前来祝贺,李纲都一一笑纳。事后,当一条平坦的乡间道路修整完毕,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条路是李纲变卖了他们送的礼物修成的。对上披肝沥胆对下宅心仁厚的李纲,一直都在努力为国家社稷铺设一条通途,而回望他的人生轨迹,我们看到的却是崎岖坎坷,充满了报国无门的血泪和壮志难酬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