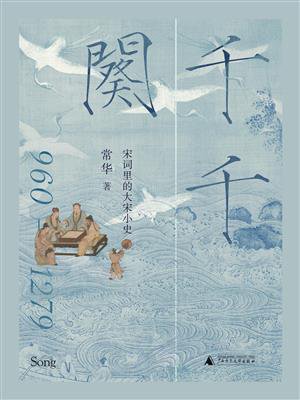“秽冢”下的权相
因为嫌恶一个人的品行,致使一个叫“桧”的汉字永远不再被人作为名字使用;因为不齿一个人的操守,纵然他写得一手好字,也不能与颜柳欧赵一样自成一家;还是因为痛恨其丑恶的灵魂,他被铸成了一尊黑色的跪像,千载而下,人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唾弃……这个被人们深恶痛绝的人是谁?他,就是南宋祸国巨蠹秦桧。
秦桧是作为臭名昭著的南宋投降派的代表被写入史册的,这个前后两次担任南宋宰相的奸佞之臣,其实并不是从一开始入仕就走投降路线,相反,在靖康之难前后,他甚至是主战派的代表,并在士人中颇有声望。作为出身寒微的徽宗朝进士,秦桧早年曾做过私塾先生,但自视甚高的他并未满足于此,“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当他写下这行诗句的时候,已经踏上了赶考之路。政和五年(1115),秦桧以二十六岁的风华之年一举高中,不久又中词学兼茂科,成为这一年科场中五位“文学之士”中的一员。跻身士林后,诗才书艺兼备的秦桧便开始向着他的梦想迈进。他写得一手好字,师法黄、米,又独树一帜。经游定夫和胡安国等人举荐,至靖康之难前,秦桧已官至太学学正。
“不宜示怯,以自蹙削”,这是靖康元年金人兵临汴梁城下时秦桧在《上钦宗论边机三事》中的文字。当时,金要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钦宗执意求和,秦桧坚决主战,反对割让三镇。及汴梁失守,金欲挟宋百官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担任御史中丞的秦桧又一次上书反对。此时的秦桧,尚以主战派的正面形象出现在史书之中,也正因如此,当靖康之难发生时,这个在金人心中挂了号的主战派也就成了一名重要的战俘,和徽、钦二帝,公卿大臣、妃嫔媵嫱一起,被裹挟其中,驱掳北上。
在“北狩”的浩荡人群中,徽、钦二帝涕泗横流,神情黯然。这两个亡国之君,使“靖康”变成了一个充满耻辱的年号,而所有的被俘者也和他们一起,开始颠沛流离的囚徒生活。亡国奴的命运自然无从选择,这群囚徒不仅遭受金人的凌辱,他们的生命也危在旦夕。然而,就在这群人中,秦桧却是一个例外,金朝统治者不仅专门宴请秦桧,还请京都王公贵戚的姬妾为他侍酒,并让他做了金国贵族挞懒的帐下幕僚。一个俘虏为什么能受到如此礼遇呢?说到底,是金朝统治者看到了秦桧的价值。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和徽、钦二帝被掳至燕山后,秦桧曾代徽宗给完颜宗翰致信一封,内中极尽卑词,表示愿意子子孙孙奉金正朔,并向金纳贡;为了打通关节,秦桧还厚赂了完颜宗翰。有关秦桧在金国的记载,充满了迷雾,很多过程与细节也都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秦桧正是通过这样一封替徽宗转呈的“卖身契”,成功地博得了金国贵族的好感。这个在靖康之难前还意志坚决的主战派,也正是在金人攻城的喊杀声和一路被俘北上的风雪中,逐渐消弭了意志,丧失了气节,可悲地成了一个变节者。在金人眼中,这个变节者显然比众多唯唯诺诺的北宋降官更有利用价值,尤其是在他被金太宗赐给金国贵族挞懒后,挞懒更是将他视为身边谋士,任命他为“参谋军事”。在攻打淮东之际,挞懒对秦桧言听计从,面对楚州军民的英勇反抗,写得一手绝妙好词的秦桧亲笔写下了一封劝降书。正是这封劝降书,让秦桧彻底从曾经的主战派蜕变成为奴颜婢膝的投降派。当楚州军民最终粮尽援绝,在城破之日,纷纷“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回应那封被撕得粉碎的劝降书。
攻下楚州后,挞懒对秦桧更加信任了,金国统治者对这个“有头脑”的北宋降臣也更加重视了,尤其是当秦桧献上“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策略,更令金国统治者看到了这枚棋子的价值。所谓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实际上就是将南宋北方领土拱手割让给金国,实行南北分治。基于秦桧这样的“政治智慧”,金国统治者认为,若将刚刚成立的南宋政权置于亡国之境,秦桧,无疑是最佳的内奸人选,“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
事实证明,秦桧没有“辜负”金人对他的厚望。在金国没待多久,秦桧便杀了“金人监己者”(《宋史·奸臣传》),弃舟南归了。关于秦桧到底是“纵归”还是“逃归”,学界曾有一些争论。由于传世的史料没有留下太多的证据,这种学术争论亦属正常,但如果我们置身当时宋金对峙的时代,又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在汴京众君臣都成为阶下囚的时候,秦桧作为一个降臣,怎么可能带着家眷和大量金银细软取道涟水军水寨,穿行2800里,安然返回南宋行都临安?邓广铭先生曾说,“女真贵族阴遣汉奸秦桧归南宋”,王曾瑜先生认为“判断秦桧是奸细,大致是没有冤枉他的”,而漆侠先生更是明确指出,“秦桧是女真贵族豢养的、并被派到南宋的一个内奸”。当这些严谨治学的宋史专家拨开历史迷雾,对这个千年前的宋人作出定评,我们相信史家的判断,更相信历史的眼睛。
事实上,关于秦桧的顺利南归,南宋王朝的君臣们也颇多质疑。“朝士多谓桧与(何)㮚、(孙)傅、(司马)朴同拘,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宋史·奸臣传》)从南宋朝野上下对秦桧南归的质疑之声,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双双充满怀疑的眼睛。然而,秦桧还是用自己当年在靖康之难中的慷慨形象实现了自救,最终,“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
随着怀疑被解除,宋高宗对这位千里迢迢“舍身归宋”的“忠臣”开始格外垂青,他曾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深感秦桧如“苏武之在匈奴,常持汉节”,得秦桧犹得“一佳士也”(《金佗续编》)。由于得到宋高宗的赏识,秦桧很快官拜右仆射,爬上了权力的高位。
那么,这个南宋权相给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交出的又是一份怎样的“政绩”呢?《宋史·奸臣传》是这样写的:“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如果说宋高宗赵构在建立南宋政权之初,还在战与和之间摇摆,那么秦桧的“回归”,则彻底将南宋政权推向了议和投降的轨道。尽管刚即相位不久,秦桧因抛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投降政策而招致众怒,甚至高宗也认为“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将秦桧罢去相位,但很快,根本无意恢复只求偏安的宋高宗便认可了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将其官复原职,秦桧由此再次拜相。此后三年间,随着宋军抵抗与金国势颓,这位于忙乱中建国的皇帝不仅没将形势逆转之功记在奋力抗金的南宋军民头上,反认为这得益于秦桧提出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策。
重掌权柄之后,秦桧植党营私、排除异己便再无顾忌,而作为一个被女真贵族豢养的奸细,其投降主义的路线更是毫无掩饰地推行开来。此时,作为一个在靖康之难中的“受益者”,宋高宗在朝野上下自然要制造孝悌的假象,绍兴八年(1138),就在秦桧再次拜相之际,高宗在朝堂“动情”地说道:“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有了高宗这层铺垫,善于察言观色的秦桧不失时机地和高宗形成应和:“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心,两得之矣!”当这对南宋君臣站在孝道的制高点上,将“屈己议和”变成囿于道德层面的不得已,又将群臣的忠和皇帝的孝实现道德上的绑架,宋金议和已不可避免。尽管有一些大臣提出反对之声,但高宗一句“朕独委卿”,众臣只能徒唤奈何。金国的“诏谕”到了,秦桧忙不迭地替高宗在金使面前代行接受诏书的跪拜之礼,而随后屈辱的议和条件是:宋向金称臣,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送还徽宗梓宫以及亲族。在这个金国贵族代理人的操纵下,宋高宗以迎回徽宗梓宫及生母韦太后为幌子,奴颜婢膝地向金人讨得了一时苟安。而此刻的朝堂,已成为被秦桧左右的朝堂,当朝中一些像李光、胡铨、赵鼎这样的忠直之臣纷纷上书请斩秦桧以谢天下,秦桧一党极尽构陷栽赃之能,将这些大臣全部贬黜。“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当朱熹声色俱厉地给秦桧下了这句按语,他痛感到,此时的南宋王朝,已经被这个祸国巨蠹啃噬得不成样子。
秦桧最为人所唾弃的,是他对抗金名将岳飞的迫害。绍兴十年(1140),就在宋金议和不到一年的时间,金撕毁和约,完颜宗弼再次挥师南下,而身为南宋主战派的代表,岳飞高擎着高宗手书的“精忠岳飞”的大旗,成为金兵最忌惮的对手。在宋金双方的数次交锋中,岳飞率领他的岳家军一路攻势如虹,所向披靡,战颍州,攻蔡州,克郾城,战功赫赫。然而,这位高呼“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将领,可以躲过明晃晃的刀枪,却难防背后射来的冷箭。就在岳飞攻城拔寨,光复在望之时,秦桧却怂恿宋高宗道,时“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三朝北盟会编》)。宋高宗在秦桧的撺掇下,连下十二道金牌催岳飞班师回朝,这位一心收复失地的臣子只能仰天长啸,拭一把壮志难酬的英雄泪,败于垂成之际;而在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后,心狠手辣的秦桧更是不择手段,给岳飞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最终将其残忍杀害。
岳飞死后,秦桧的卖国求荣变本加厉,他不仅向金国百般示好,大肆推行其投降政策,同时竭民膏血,卖官鬻爵,其积蓄财富足可敌国,而经他举荐的官军都“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当抗金防线在秦桧的手中迅速坍塌,南宋王朝已再无统兵御敌之将,只能任人宰割。
腊残春早。正帘幕护寒,楼台清晓。宝运当千,佳辰余五,嵩岳诞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庙。尽总道,是文章孔孟,勋庸周召。
师表。方眷遇,鱼水君臣,须信从来少。玉带金鱼,朱颜绿鬓,占断世间荣耀。篆刻鼎彝将遍,整顿乾坤都了。愿岁岁,见柳梢青浅,梅英红小。
——康与之《喜迁莺·丞相生日》
这首《喜迁莺》,出自秦桧门下“十客”之一的康与之之手。这个无行文人因为攀附秦桧,得以官运亨通。在日常的谀颂之作中,康与之就极尽逢迎之能,及至秦桧生日,他更要用“生花妙笔”吹嘘这位权倾朝野的“恩公”。在秦桧把持朝政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像康与之这样的“文丐”不胜枚举,当“文章孔孟,勋庸周召”这类肉麻的颂词对应起秦桧的“功德”,当祝寿之词“篇什之富,烂然如云,至于汗牛充宇,不可纪极”,南宋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秦桧搅得乌烟瘴气。
秦桧之佞,不仅在其祸国殃民,更在其对历史的疯狂篡改。这位“词学兼茂,才华卓绝”的“文学之士”,将自己的文采用到了对国史的任意涂抹上。他深知自己恶名昭著,不能见容于后世,遂命其子秦熺负责编修国史和高宗在位以来的日历,他隐瞒了自己变节投敌的事实,为自己做了大量粉饰,同时,对岳飞的诸多战功则刀削斧砍,大肆篡改,致使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不仅如此,秦桧还严禁私人修史,凡是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之处,统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秦桧对历史的疯狂篡改,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岳家军战功战果记录的严重缺失,以至于后来当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议赐“武穆”谥号时,竟“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秦桧对史实的删削、隐毁,更给后世学者研究宋史带来了巨大障碍,很多历史真相已经被彻底尘封,成为一道道难以解开的谜题。
据说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对其恩宠不减,特在其墓前立碑,然而,虽“丰碑屹立”,却无人愿为其镌一字,更无人愿为其撰写碑文。后宋将孟珙率军与金兵作战,回朝经过秦桧墓时,特意在其墓前屯军,并命军士粪溺其上,时人遂称秦桧墓为“秽冢”。自南宋开始,民间便通过炸制一种捏成人形的面食来表达愤怒,名之为“油炸桧”,此后,“油炸桧”逐渐演变为人们今天吃的油条。当一个人的品行达到人神共愤的程度,秦桧不会想到,即便他篡改了历史,仍旧难逃历史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