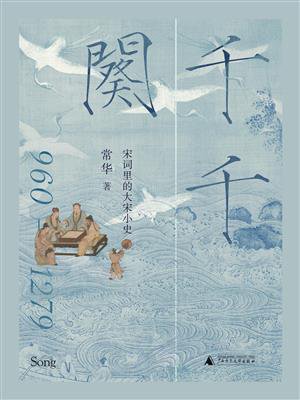序
品读宋词,走近宋人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早在《诗经》出现之前,我们的先民们在华夏大地上就已经开始用诗歌记录他们的生活,而当周朝的采诗官们巡游各地,采集民间歌谣,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这些散落民间的经典便以文字的形式固定成永恒。由此,在风、雅、颂的脉脉流韵中,我们一路吟着“关关雎鸠”“呦呦鹿鸣”,走进《楚辞》的天空,走进《古诗十九首》的意象与张力,走进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走进自由奔放的唐诗,走进清雄婉约的宋词……走进诗词里的中国,我们收获的,是炽烈燃烧的文明之火,是打开中国历史、政治、文学、军事以及民俗民风的钥匙,是探寻中国文人心路历程的通关密码。
作为大盛于宋的文学形式,宋词与唐诗一起,共同耸峙起中国文学史上两座巍峨高峰,成为泱泱诗国的象征。宋词的兴盛,得益于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诚如王国维所云:“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当然,宋词能成为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更离不开唐诗的繁盛。大唐王朝近300年的历史,让唐诗成为上至公卿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钟爱的抒情方式,而当这种深入人心的抒情方式与宫廷燕乐相遇,也便逐渐过渡为“依曲拍为句”的制辞形式。正因如此,在琵琶等各种乐器共同构成的乐阵中,写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刘禹锡,开始在作品中呈现出“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
 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的全新样貌,这是唐代文人“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的集体变奏,也是词体得以确立的重要阶段,当张志和的《渔歌子》、韦应物的《调笑令》、刘禹锡的《潇湘神》、白居易的《长相思》,共同构成这些诗人洋洋诗篇背后的另一道风景,我们发现,诗与词,恰如江河入海,交融,互通,一路澎湃。
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的全新样貌,这是唐代文人“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的集体变奏,也是词体得以确立的重要阶段,当张志和的《渔歌子》、韦应物的《调笑令》、刘禹锡的《潇湘神》、白居易的《长相思》,共同构成这些诗人洋洋诗篇背后的另一道风景,我们发现,诗与词,恰如江河入海,交融,互通,一路澎湃。
由此,宋词的成熟与鼎盛也便水到渠成。经历过大唐的肇始、五代的丰富,穿越过花间词的金粉香艳、南唐词的深幽文雅,进入到宴饮无歇弦歌不绝的宋代,词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已经成为宋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当我们在宋词的低吟浅唱中一路行走,便会发现,品读宋词去理解宋人、感悟宋人,是一个多么便捷的方式,又是一种多么直观的体验!
是的,这就是宋词的魅力!“花底忽闻敲两桨。逡巡女伴来寻访。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只有读到这样的词句,我们才会看到,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是如何在努力摈弃花间派词人的铺金缀玉,以效仿和吸收民歌的方式形成其词作的语近情深;“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默诵这样的词句,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文辞纯浑,有西汉风”的司马光的形象,看到一位“不通时变”的臣子,如何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投向历史的深处;而沉浸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生命交响之中,我们相信,苏东坡这位被流放到天涯海角最终病逝于归途的北宋诗文大家,其实一直都在叩问命运,只是叩问的方式有些特别,一路绝尘,不闻鞭响,只听得阵阵鼓声……
当然,我们还要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辛稼轩一起,擦拭那柄壮志未酬的利剑;和写出“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贺方回一起,感受江南的梅雨;和吟诵着“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三变一起,共同喝光一壶浊酒。最后,我们还要追上李清照那艘为夫鸣冤的快船,问一问这位中国第一女词人,当她将“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融入《渔家傲》的韵脚,是否看到了前方乌云蔽日,大浪滔天……
感谢宋词!让我们得以和宋人形成精神的对视和心灵的对话!感谢宋词!让我们得以在国运昌明的今天,以多元的视角和不断的求索,完成一次说走就走的穿越宋朝之旅。走进三百余年两宋史,它的轨迹,恰如一串词牌:始于“破阵子”,兴于“清平乐”,衰于“雨霖铃”,终于“如梦令”;而走进《清明上河图》这幅北宋长卷风俗画,物阜民丰的背后,伴随着清明时节的哀声阵阵,浮华喧嚣的终点,是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悲……
当然,我只是一名历史爱好者,专业的考据和研究自知力有不逮,但我更愿意亦文亦史,文史兼顾地走进宋朝三百余年时空。循着宋词的足迹,我愿意用历史随笔的方式,去面对大宋君臣,体悟什么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去描摹那些远去的文人背影,千年之后,仍盼望“一尊还酹江月”,去融入那段滚滚红尘,领略“东风夜放花千树”。宋词,宋史,宋人,在时间长河里,我愿乘一只不系之舟,享受书写的自由。
最后,我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将本书看作是了解宋词的一个小小窗口,每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都有着自己的理解,这本书权当是一种进入的方式。对宋词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价值的再发现,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引擎,为此,我愿抛砖引玉,接受广大读者朋友的批评和指教,同时,面对未来,我的选择仍旧是:不敢懈怠,继续行走!
是为序。
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