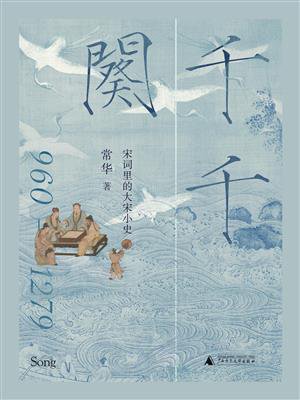无为有为之间
秦始皇以降,第一个庙号为“仁”的皇帝是宋朝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
说起宋仁宗赵祯,人们并不陌生,作为“狸猫换太子”的主角,他的形象随着戏曲、笔记小说等多种艺术形式早已深入民间,有很高的知名度。“狸猫换太子”演绎的是一出宋室宫闱遗案:赵祯的生母本是一位李姓妃子,在和宋真宗有过一夜缠绵后,遂珠胎暗结,这件事让刘皇后知道,不仅妒火中烧,因为刘后不能生育,而连夭五子的宋真宗又急于立储,因此,当李妃有孕之事传入刘皇后的耳朵,她就意识到了自己皇后地位的危机。很快,工于心计的刘皇后就想了一条毒计,她将李妃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诬说李妃生的是个妖孽,结果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后来这个被偷梁换柱的婴儿当了皇帝,是为仁宗,在包拯的彻查下,终于真相大白,仁宗迎回生母,一直垂帘听政的刘皇后畏罪自杀。
其实,撇开这段宫闱秘闻不谈,单说说这位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宋仁宗在位42年——整个北宋,共历九帝167年,仁宗一朝就占了四分之一的时间。这42年间,边事太平,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鼎盛气象。比起开国初的太祖太宗,仁宗算是一位稳稳当当的守成之君,但守成能守到42年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苏轼语),也颇为难得,而他执政的一个重要特点——“仁”,成了他耀眼的标识。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当编修《宋史》的史家们用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境界“仁”字来评价这位宋朝皇帝,宋仁宗赵祯实际已经享受到一份旷古未有的殊荣。
对赵祯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有史家的过誉之处,但也看出人们对他的尊敬。那么,仁宗之“仁”究竟体现在何处呢?首先还是体现在他对臣子的宽容仁厚上。要做到宽仁,对于一个皇帝而言并非易事,而对于批龙鳞、逆圣听的大臣,皇帝有生杀予夺大权,“宽仁”,其实是对皇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宋仁宗却是一个出了名的怕大臣的皇帝,有三个例子体现得颇为充分。

宋仁宗
一是包拯斥张尧佐事。在戏剧文学作品中,包拯一直都是以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形象示人的。这个“包青天”不仅不畏权贵,在皇帝面前也是据理力争,不让寸步。据说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包拯指陈三司使张尧佐不作为,要仁宗撤掉其职务,而张尧佐是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面对包拯的奏折,仁宗最后改任张尧佐为淮康军节度使、宣徽南院使,也算是对张贵妃有个交代。然而,包拯却不依不饶,认为仁宗有开启“外戚干政”的危险,带着七名谏官和仁宗死磕到底,不仅连续上书,而且在退朝后还留班不退,言辞激烈处,包拯的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脸上,仁宗虽然没被唾沫星子惹恼,但还是对着以包拯为首的几个谏官说了句:“节度使粗官,何用争?”不想包拯言辞更为激烈:“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就这样,仁宗这场朝堂公议到底也没说服包拯等人,最终张尧佐也没做成节度使和宣徽使。“汝只知要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当退朝之后的仁宗见到急切等待结果的张贵妃,对她说出这番无奈之语,我们看到的仁宗,表面上是被臣子们折了面子,但能做到折了面子而不龙颜震怒的皇帝,又有几个呢?
还有一个例子也和谏官有关。话说这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便唤来梳头太监给他梳头。这梳头太监见仁宗手里还拿着一份奏折,便问收到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奏折,仁宗说,这是谏官让他减少宫女和侍从的,这太监于是便道:“大臣们家里有歌儿舞女,一朝晋升还要增加,他们怎么还盯着陛下这点宫人侍从,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仁宗并未搭话,接着梳头太监又道:“这些谏官之言,陛下打算采纳吗?”仁宗道:“谏官建议,朕当然要听。”这梳头太监听了,仗着自己是皇帝身边之人,竟不满地说道:“如果陛下采纳谏官之言,那么就请将我作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一听,立刻头也不梳了,站起来就招呼主管太监过来,当即清点名册,将29名宫人和这个干涉朝政的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觉得仁宗这样做有点过,毕竟梳头太监是多年亲信,但仁宗认为,这个梳头太监让自己拒绝谏官忠言,那就是在挑拨君臣关系,这种人坚决不能留。为了不得罪大臣,而把身边亲信太监轰出宫门,仁宗对大臣的“怕”由此可见一斑。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载:“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可以说,北宋的台谏体系是由宋仁宗一手扶持起来的,正是在仁宗朝,谏院成了一个独立机构,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而其职能则从规谏君主扩大到了监督百官,职能不断强化,用欧阳修《上范司谏书》的话讲,就是“谏官虽卑,与宰相等”,甚至到了可以与宰相相提并论的地步,而这些可广泛参与国事的谏官在仁宗一朝由于“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有学者统计,仁宗朝任谏官的67人中,有40人都得到了升迁,像范仲淹、韩琦、富弼等知名谏官,更是曾经出任宰辅要职。当然,强化台谏体系的宋仁宗在力倡谏诤之风的同时,也势必会给自己的帝王生涯套上紧箍圈,如前所述,妃子们的枕边风会立马被谏官们的唾沫星子压住,谏官呈上一份奏折,仁宗的后宫就得没商量地裁员,更重要的是,广有四海的仁宗平时想有个赏赐,都得偷偷摸摸。史载,有一天宫里做道场,仁宗看得兴起,当即赏赐给每个和尚一匹紫绸,出宫之前,仁宗再三叮嘱他们要将紫绸藏于怀中,个中原因,就是怕谏官将此事记录在案,拿来说事。
可以说,正是仁宗对大臣们的这种“怕”成就了他的宽仁政治。据南宋陈亮《中兴论》载,有人曾劝仁宗要拿出皇帝的威仪,独断专行,仁宗却说:“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在仁宗看来,皇帝一言九鼎,说出的话作出的决定不能轻易更改,但臣子办错事相对容易改,所以还是要注重廷议。事实上,正是这种与臣子们商量着来的做法,让仁宗朝呈现出由强势君主乾纲独断到君臣共治的清平图景,在他执政的42年间,名臣云集,英才辈出。苏轼曾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这并非溢美之词,打开仁宗朝的名臣卷册,我们可以看到一串响当当的名字,他们之中,有锐意改革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有明察秋毫为民请命的包拯,有学富五车纵横写史的司马光,有跃马横刀冲锋陷阵的狄青……宋仁宗的仁政,给了这些臣子施展抱负的舞台,而也正是这些名字,撑起了宋王朝的黄金时代。
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魏泰《东轩笔录》
这段宋人笔记中的文字,体现了仁宗之“仁”的另一面,那就是律己悯人。因为担心随从因服务不到位而受到责罚,即使口渴难耐,也要“忍渴而归”,这种对属下细致入微的体恤,好像很难与九五之尊的皇帝挂上钩,但无论官方正史也好,民间野史也罢,仁宗类似这样的故事,还真不少。
据说有一次,仁宗处理奏章一直到深夜,饥肠辘辘,很想喝一碗羊肉汤,但想了想还是忍住没说出来。第二天上朝,大臣们看到仁宗气色不佳,以为他昨夜在后宫御幸过度,都委婉地劝他要保重龙体,仁宗听后笑着解释道,其实自己差的是一碗热羊汤,想到祖宗未开此先例,一旦开了这个头,以后御厨们可就有得忙了,必定会每晚宰羊,以备皇帝不时之需,积年累月,所宰之羊将数不可计,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而造成宫中这种无谓的奢侈浪费,正因如此,他才愿忍下一时之饥。
与这个例子形成呼应的,是仁宗拒吃蛤蜊一事。一年初秋,有官员敬献蛤蜊给仁宗,仁宗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大臣回答说是从远道运来。又问多少钱,回答说共两万八千钱,仁宗立刻变色道:“朕常常跟你们说要节俭,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二万八千钱,朕吃不下!”仁宗面对这份美味珍馐,最终未动一箸。
作为一位13岁即位,经历过刘太后11年垂帘听政,直至24岁才亲政的皇帝,宋仁宗在史家小说家的笔下,已经将“仁民爱物”做到了极致:他寝宫的被子,由于很久未换,竟会洗到由明黄变为暗黄;他对服饰不求奢华,甚至能补则补,以至于影响到六宫及朝臣,“当时不唯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而他在位时颁布的不得进诸瑞物的诏令,更能看出仁宗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百姓的体恤。当然,这些故事逸闻也许不乏史家、小说家们的渲染、夸张甚至杜撰,但我们又必须发出这样的疑问:类似的故事,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其他皇帝身上?而仁宗的故事又为什么独此一份,成为不可复制的“孤本”?
毫无疑问,作为仁宗之“仁”最令人赞叹的,还是他对文人的宽待。从6岁起,仁宗便就学于宋真宗为众皇子设立的资善堂,自幼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使得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飞白体自成一家,堪称“儒者皇帝”,而生于仁宗朝的文人显然是封建时代最幸福的文人,这份幸福,正得益于宋仁宗的儒学修养和仁厚胸襟。《渑水燕谈录》载,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科考试,依据道听途说,写下了“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的过激之言,试后苏辙认为自己抨击圣上,言语失当,一定会落榜,而初考官也准备以跑题为由,将苏辙的试卷甩至一边。然而让这位巴蜀举子没想到的是,仁宗看过此论之后竟大赞苏辙敢于直言,说:“朕设制举,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如此直言,特与科名。”不久便授予苏辙商州军事推官一职。
和苏辙的这个故事异曲同工的,是另一位岁数较大的巴蜀老秀才。这位老秀才也许是久考不中,想发发牢骚,竟然写了“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样的诗句献给成都知府,当时就把他吓得不轻!这分明是反诗啊,又要“烧栈阁”,又要“一乾坤”,这不明摆着要犯上作乱吗?成都知府自然不由分说,直接将这位老秀才绑了,将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处置。不想仁宗看到奏报后,竟莞尔一笑,认为这位老秀才不过是“急于仕宦而为之”,不但没有问罪,反而给了他一个司户参军的官职。
这两个例子,反映出的正是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由于这份宽容,使得仁宗在位期间,文人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局面,42年间,没有一起文字狱,有的只是文人气性的放旷和舒张。程颐、程颢兄弟因为这股自由的空气,得以将理学广泛播扬;而唐宋八大家中,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是闪耀在仁宗朝的星斗;就连打着皇帝旗号“奉旨填词”的柳永,也没有因讽刺仁宗获罪,相反,在文风自由的环境中,柳永的个性更加狂放,最终成为“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民间填词高手。
缵重明。端拱保凝命。广大孝休德,永锡四海有庆。觚坛寓礼正典名。幔室雅奏,彩仗崇制定。五位仿古甚盛。蒿宫光符辰星。高秋嘉时款芎灵。交累圣。上下来顾,寅畏歆纯诚。三阶平。金气肃,转和景。翠葆御双观,巽风兑泽布令。脂茶刬荡墨索清。远迩向附,动植咸遂性。表里穆悦,庶政醇
 ,熙然胥庭。唐舜华封祝,如南山寿永。愿今广怀宁延,昌基扃。
,熙然胥庭。唐舜华封祝,如南山寿永。愿今广怀宁延,昌基扃。
——赵祯《合宫歌·皇祐二年飨明堂》
仁宗的仁政,最终赢得的是民心。“缵重明。端拱保凝命。广大孝休德,永锡四海有庆。”当宋仁宗在吟着《合宫歌》的时候,自己绝不会想到,在他驾崩之日,“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敌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将仁宗所赐御衣“葬为衣冠冢”;而当金兵占领中原后,尽管曾大肆盗掘宋陵,但慑于仁宗之名,“独昭陵如故”。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宋仁宗并不是一位最出色的皇帝,在其统治后期,冗官、冗费现象已渐成王朝的沉疴,而史家、小说家们对他大为称道的“仁”,也存在仁而无断、仁而无矩的弊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仁厚之君,造就了一段长达42年的和谐与繁华,为深受诟病的宋代皇帝们赢得了一点荣光,赢得了后世人们的一些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