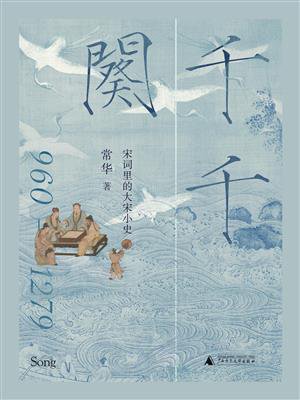变革风暴里的孤家寡人
两宋18代皇帝大多碌碌无为,真正可圈可点的并不多,除太祖、太宗、仁宗外,值得一说的可能就剩下宋神宗赵顼了。这位只活了37岁的皇帝,曾经在朝野上下轰轰烈烈地掀起过一场变革风暴。他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也正是这样一股劲头,让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驾崩,19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史载,赵顼从小便谦谨好学,“动止皆有常度,而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内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及长,受封为淮阳郡王、颍王,更是与名士韩维“论天下事,语及功名”。然而,这位锐意求治的宋王朝第六任皇帝即位伊始,不得不面对祖宗留给他的巨大财政危机。此时,宋王朝的气脉已经运行百年,早已显现出疲态,连年的岁贡令国库空虚,仁宗的葬礼费用刚消耗掉巨额的财力,英宗的突然驾崩又让财政雪上加霜。而庞大臃肿的官僚体系更让朝廷不堪重负,宋太祖赵匡胤定鼎之初,全国官员约5000人,到了神宗朝,已达2.4万多人,官俸总支出已是宋初的80倍,再加上逾百万的军队所产生的庞大军费,宋神宗刚刚君临天下,就必须面对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大沉疴。
年少气盛的宋神宗赵顼决意掀起一场改革弊政的风暴。为此,他先是找到了宰相韩琦,这位三朝元老当年曾在仁宗朝雷厉风行地发起过一场庆历新政。然而,年轻皇帝的治世雄心并没有得到热烈的回应,神宗即位不久,思想已趋保守的韩琦就称病坚辞相位,出判相州;接下来,神宗又找来了另一位三朝元老富弼,热情澎湃地向他讨教富国强兵之策,可是和韩琦一样,这位老者也早已不复当年和韩琦等人一起参与庆历新政时的锐气,他颤巍巍地对这位少年天子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宋史·富弼传》)这些位高权重的老臣投给宋神宗的,是老态龙钟的背影和一盆浇熄热情的冷水。
这就是宋神宗赵顼在即位之初所面对的朝堂,因循守旧的臣僚们都在明哲保身,根本无意革除积弊,对心怀壮志的宋神宗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孤独的处境。然而,宋神宗在孤独的行走中,还是发现了一个人,他,就是王安石。早在仁宗朝,颇富治国韬略的王安石就曾经写过一篇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宋王朝内部的诸多危机,并针对这些危机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略。这是一篇言辞激切的谏言,尽管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却让当时的皇孙赵顼记在了心里。等到赵顼即位,当他失望地面对着满朝文武,王安石的名字再次震响在耳畔。他先是将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六个月后,便将王安石调入京师,任命为翰林学士,早已等不及的神宗很快便召其“越次入对”,话题直指改革。此时,47岁的王安石面对20岁的新皇帝,力主其效法尧舜推行改革,并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从吏治、科举、农业、财政、军事、教育等方面提出诸多改革方案,令神宗大为赞赏,旋即将王安石擢升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着手变法事宜。对于王安石的火箭式提拔,朝中众臣颇多微词,当时的参知政事唐介更是以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拒绝与其同事。然而,即便周遭都是反对的声音,年轻的宋神宗也从未动摇过对这位“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臣子的信任,他将反对之声抛弃一边,同时,对王安石言听计从,视其为“师臣”,关系俨然超出了君臣之谊。在宋神宗看来,即便整个朝堂都喑哑无声也没有关系,他只要有一个王安石就够了。这一年是熙宁二年(1069),在风雨声中,血气方刚的宋神宗和踌躇满志的王安石上路了。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很悲壮。
事实证明,王安石的到来,令宋神宗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作为大宋王朝的首席执行官,王安石的确有着过人的政治才能,在他的主持下,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保马等诸项新法相继出台。随着新法的陆续施行,宋王朝的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然而,王安石执拗的性格也让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树立起了太多的敌人。史载,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朝中人称“拗相公”,这样一种性格的人主持变法,当然很难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以至于后来许多中间派都倒向了守旧派。北宋政坛的三朝元老曾公亮当时曾坚信王安石是“治国之才”,没少在神宗面前举荐王安石,及至王安石荣升相位,曾公亮更是认为“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而随着变法的深入,这位年届古稀的老臣已经因无法与王安石达成政见上的一致而产生分歧,最终请求致仕还乡。神宗还是颍王时,担任王府记室参军的韩维每当讲经被称赞,他都会说“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对王安石后来被神宗重用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当变法大幕拉开,韩维却无法与王安石形成政治上的契合,转而成为坚决的守旧派。
而随着新法的施行,朝中守旧势力和宗室外戚的利益已经被触及,他们不仅向朝廷上书抵制新法,围攻王安石,更煽动两宫皇太后教训新皇帝“祖宗法度不宜轻改”。面对整个朝堂的一片呵责之声,宋神宗没有动摇自己改革的初衷,他曾当着太皇太后的面对王安石褒奖有加,认为“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当这位“拗相公”有时丝毫不顾及九五之尊的颜面,“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神宗竟能马上“改容为之欣纳”“一切屈己听之”。被财政赤字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神宗太需要用一场雷霆万钧的改革来摆脱危机了,而在他身边有太多看热闹甚至干脆躺平的臣子,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即便王安石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也必须毫不动摇地用他做开路先锋。青苗法实施过程中,针对朝中两派的争论,神宗曾一度动摇,但他最终顶住了压力,力挺王安石;募役法规定,乡户如不去官府当差,可缴纳“免纳钱”,这种做法本是给乡户多一个选择,却因执行走样而招致非议,御史杨绘、刘挚纷纷向神宗指陈“募役法十害”,结果神宗细询王安石,认为是一项好政策,命杨、刘二人当面认错;熙宁三年(1070)至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曾五次请辞相位,以一种近乎要挟的态度让神宗为自己撑腰,每一次神宗都不得不降手诏逊谢……对于王安石这位改革旗手,神宗始终在以“师臣”相待,既然是“师臣”,就要给他更多的空间,让他心无旁骛,放手一搏。
刘安世《元城语录》记载:“得君(王安石)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而已。”事实上,在熙宁变法这段时间,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已是相互依存的君臣关系,一个是孤臣,一个是孤君,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支撑着熙宁变法的节奏。为了推行新法,神宗力排众议,一如既往地信任王安石,给了王安石更多的权力,就在将他任命为宰相的同时,对皇命唯命是从的“三旨相公”王珪也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王氏父子一时风光无两;不仅如此,为了扫除变法路上的层层障碍,神宗先后罢退了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
 、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依靠皇权的推动,熙宁变法进入高潮,王安石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一系列变法措施的推行中,看似正一步步地实现,但宋神宗心里明白,为了变法,为了王安石,他已经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一大批年纪较长的重臣,如欧阳修、司马光、王陶、范镇、吕诲、富弼等人,已经相继走下权力巅峰。皇帝固然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支持,当变法进行两年之后,他的身边仍旧只有王安石这样一个可用的臣子,宋神宗已经感到了莫大的孤独与悲凉。
、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依靠皇权的推动,熙宁变法进入高潮,王安石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一系列变法措施的推行中,看似正一步步地实现,但宋神宗心里明白,为了变法,为了王安石,他已经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一大批年纪较长的重臣,如欧阳修、司马光、王陶、范镇、吕诲、富弼等人,已经相继走下权力巅峰。皇帝固然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支持,当变法进行两年之后,他的身边仍旧只有王安石这样一个可用的臣子,宋神宗已经感到了莫大的孤独与悲凉。
宋神宗第一次对自己力推的改革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源自一幅《流民图》。此前,各地反常的天象早已成为守旧派借题发挥的谶词,他们将河北大风、华山崩裂这些不祥之兆归咎于变法,对此,宋神宗并不以为然,可当熙宁七年(1074)的大旱之年,一个叫郑侠的官员献上这幅《流民图》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心里再也无法平静。“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的郑侠,早前曾是王安石非常器重的得力助手,但二人最终因政治上的分歧而形同陌路。熙宁七年,当时已被王安石贬为监门小吏的郑侠不堪民苦,为民请命,画了这幅《流民图》,并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黜新法。人微言轻的郑侠自然被挡在閤门之外,他遂假称秘密紧急边报,发马递直送银台司,呈给神宗皇帝,疏中称:
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呈现在神宗面前的《流民图》,是一幅充满了饥饿和死亡的图画,画中的流民骨瘦如柴,因干旱导致颗粒无收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卖儿鬻女。事实上,在看到这幅《流民图》之前,神宗已经看到一些来自灾区的奏报,由于久旱不雨,赤地千里,导致百姓疲羸困厄,身无完衣,而各地官吏不顾百姓死活,仍然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对于这些奏报,神宗当时还认为是有人借题发挥,但当郑侠这幅《流民图》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他已经不能不怀疑起熙宁变法的初衷,一心要改善民生的宋神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在大旱之年竟毫无成效。史书记下了神宗看这幅令他触目惊心的《流民图》时的一系列反应:“反复览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就在第二天,他在朝堂上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安石乱天下”,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看过《流民图》的反应言犹在耳,再加上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大臣对王安石的口诛笔伐,终于让神宗无法再给这位“师臣”任何庇护,他不得不接受王安石的辞职。尽管第二年二月王安石便回京复职,但熙宁九年(1076),由于爱子王雱英年早逝,加之旧派势力不断对他施压,这位锐意改革的老臣终于被压垮,他再次向宋神宗递交了辞呈,从此退居金陵,再也不问政治。空荡荡的朝堂之上,宋神宗目送着这位疲惫的臣子远去,他已经隐约感到冬天的来临。
西母池边宴罢,赠南枝、步玉霄。绪风和扇,冰华发秀,雪质孤高。汉陂呈练影,问是谁、独立江皋。便凝望、壶中珪璧,天下琼瑶。
清标。曾陪胜赏,坐忘愁、解使尘销。况双成与乳丹点染,都付香梢。寿妆酥冷,郢韵佩举,麝卷云绡。乐逍遥。凤凰台畔,取次忆吹箫。
——赵顼《瑶台第一层》

宋神宗
对于“瑶台第一层”这个词牌,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武才人出庆寿宫,裕陵得之。会教坊献新声,为作词,号《瑶台第一层》。”东晋王嘉在《拾遗记·昆仑山》中,则描述瑶台道:“(昆仑山)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少年时代便博览群书的神宗,用这个词牌进一步丰富着自己对道教理想中的神仙境界的想象,但同时,也用一句“汉陂呈练影,问是谁、独立江皋”表达内心的那份孤独。就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的第二年,宋神宗将年号改为元丰,他向天下颁布了《寄禄格》,旨在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如果说熙宁变法还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如一的联袂出演,那么到了元丰改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宋神宗一个人的改革。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在元丰改制中,本来旨在使顶层设计更加简洁的对三省行政事务的严格划分,却反而降低了行政效率,以至于神宗差点要重新采用旧制。为了尽早显现变法的成效,又不致引起朝野的更多争论,宋神宗在前十年的变法基础上,开始转向强化军兵保甲的改革,旨在对外提高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同时改变守旧派对变法的排斥状态。然而,文官带兵的传统是宋王朝百年羸弱的主因,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急于雪耻以节省“岁贡”的宋神宗以为历经改革,宋军已成铁军,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结果由于深入腹地各军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西夏横山地区,不料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征讨西夏,共计折损军兵数十万人。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神宗听到永乐城陷的消息后,“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900多年过去,当我们翻到这一页史册,仍能听见这个心忧社稷的皇帝那响彻朝堂的哭声。这是无助的哭声,宋神宗的富国强兵之举,换来的是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无奈的哭声,十几年旨在为百姓带来福祉的变法,最后却惹怒苍生,以致民怨沸腾;这是无望的哭声,变法形成了新旧两派对立的阵营,旧派是一堵难以撼动的高墙,而所谓的新派却与自己离心离德,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元丰八年(1085),就在宋神宗当廷痛哭三年之后,这位一心想成为尧舜之君的皇帝终于一病不起,驾鹤西去,年仅38岁。
据野史记载,宋神宗在执政之余,还颇通望闻问切之道,《说郛》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有内侍病肿,太医言不治。帝为诊之曰:阴虽衰阳未竭,犹可疗也。令食蒜煮团鱼而愈。”精通医术的宋神宗可以治愈内侍的重病,但面对身染沉疴的大宋江山,却回天乏术,尽管他开出了一剂药方,但这剂药方实在缺少太多的药引,直到他赍志而殁,也改变不了宋王朝病入膏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