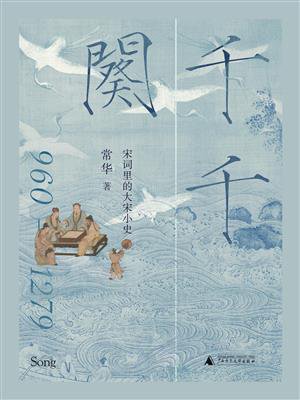匆匆而过的接棒者
两宋皇帝中,如果不算四岁被抬上龙椅的恭帝赵㬎和八岁就被大臣背着投海而死的赵昺,宋钦宗赵桓可以说是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从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匆匆即位,到靖康二年(1127)初被金兵远掳金国,他的在位时间仅有短短一年零两个月。而对于这位倒霉的皇帝,我们似乎只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评价他。
说宋钦宗是不幸的,许多人可能会打个问号:皇帝贵为天子,口体之养无所不用其极,何来不幸?但了解一下宋钦宗即位的时代背景,我们便可以看出,宋钦宗其实更像是一个被推进北宋王朝这间破败老屋的“挡风”皇帝。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兵大举南下,终日风流放浪的宋徽宗被越来越近的铁蹄声吓得魂飞魄散,慌忙举行禅让礼,将自己25岁的儿子赵桓推上了皇位,自己做起了太上皇。显然,在这个时候即位的宋钦宗没有一点可以笑起来的资本,一方面,他的浪荡父亲交给他的是一个被掏空的家底,军队毫无斗志,百姓苦不堪言,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另一方面,则是金兵一路杀伐掳掠。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此时的北宋皇位已经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没有半点吸引力。
作为一个匆匆即位的接棒者,嫡长子赵桓其实并不是徽宗眼中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任何一个封建帝王在立储时都希望立一个和自己在性情禀赋上相似的皇子,书画家皇帝宋徽宗最中意的人选也是“学造渊深”的嘉王赵楷。和他父亲一样,赵楷“禀资秀拔,为学精到”“多士推服,性极嗜画”,深得徽宗钟爱。政和八年(1118)三月,徽宗为了在人前显示这位皇子的才华,特诏“嘉王楷令赴集英殿试”,考官心领神会,赵楷当廷唱名第一,获得满足的徽宗当然要谦让一番,降诏“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为榜首”。和赵楷的受宠相比,赵桓显然难得父皇的垂青,徽宗的艺术基因在他身上没有传承到一分,“声技音乐一无所好”,至于徽宗的好色崇道,赵桓也不感兴趣,不仅“不迩声色”,而且看到徽宗大兴土木,崇道抑佛,甚至还在大殿之上和他争了个面红耳赤。朝臣们都是会察言观色的,已当了十年太子的赵桓因为和当朝皇帝在性格禀赋上迥然有别,身边的支持者自然也不会有受宠的嘉王赵楷多,在皇位继承的逻辑里,赵桓这个储君其实过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宋钦宗
然而,历史却让赵桓于狼烟骤起之际登上了御座。北宋皇帝都有一个心结,那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徽宗同样也希望用一场漂亮的收复之役为自己镀上一层金。机会出现在政和五年(1115)。这一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这让徽宗看到了灭辽的希望,他和群臣想出了一个“以夷制夷”之策,特派人走海路绕开辽国和金国签订了“海上之盟”,寄望形成宋金同盟一举灭掉辽国。而后来事态的发展显然不是这个以“天下一人”花押名世的皇帝所希望看到的:在风驰电掣的金军面前,辽军节节败退,而说好的宋军对辽军的围追堵截却总是跑风漏气,不仅没有和金军形成呼应之势,反而将自己在军事上的劣势给“盟友”金国探了个底儿掉。由此,结果便可想而知,在辽国被金国灭掉之后,这个于冰天雪地间建立起来的王朝抖抖肩头的落雪,转而就扑向了门户洞开武备废弛的中原大宋王朝。当女真人浩荡的铁蹄直抵黄河岸边,与宋都汴京的路程仅有七日之遥,自顾不暇的宋徽宗早已顾不上什么更立储君,他要做的,是带着一干近臣迅速逃往相对安全的镇江府(今江苏省镇江市),虽然此前在李纲等大臣的坚持下,他万分不舍地行了禅让礼,自己做起太上皇,但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让一个当了十年储君的儿子出来给自己扛雷顶包,怎么说也还是划算的。
就这样,并不被徽宗看好的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显然,这位在大厦将倾之际穿上龙袍的皇帝,接过的是一份糟糕透顶的政治资产。早在金兵南下之前,出知定州的张舜民就曾针对宋军武备废弛的状况上疏发出过预警:“今日河朔之势,正如陕西宝元、康定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仓促,不可枝梧。边臣若预为振举,则谓之张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旧宴安,号为无事,则纲目日见颓废,有不胜举之忧。”“又为将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惟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这样涣散的队伍,在金兵的铁蹄下当然不堪一击,而更加让新皇帝不知所措的,是一班主和派的煽风点火,危言耸听,尤其是曾做过十四年太子宫僚的耿南仲,更是让还未行登基大典就面对金军兵临城下危局的宋钦宗陷入恐慌之中。《历代名臣奏议》对在钦宗即位后担任尚书左丞的耿南仲评价极低,言其“沮渡河万全之战,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镇,明日截黄河,自谓和议可必无患,凡战守之具,若无事于切切然者”。而对这位跟随自己时间最长,在自己储君之位动摇之际也没“变节”的臣子,钦宗显然“信如蓍龟,敷奏之语,盖未尝不从”。这个倒霉的接续者,等着当皇帝等了足足有十年时间,但真正坐在了这个烫屁股的御座上,尽管号称“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他却恨不得马上结束这场当皇帝的噩梦。
在历史上,总是英雄与小人并存,忠臣与奸佞同在,而越是在乱世,这样的两极对比也就越明显。此时,在宋钦宗面前的朝堂,虽说充斥着类似耿南仲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但也不乏像李纲、种师道这样为国家兴亡甘愿赴汤蹈火的忠直之臣,正是这两位主战派的坚持,让本已垂头丧气的宋钦宗又重新打起了精神,决定坚守汴京。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钦宗下诏:“祖宗典训具存,纲纪修明,朕当与执政大臣共遵成宪。”并下令“应亲征合行事件,令有司并依真宗皇帝幸澶渊故事,疾速检举施行”。这纸诏令对于守城官兵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鼓舞,面对城下的金兵,尚书右丞李纲大义凛然,精心组织防卫,率领众将士坚壁清野,在汴京保卫战中没有让金兵讨到一丝便宜,而外围策应的老将种师道,更是赤胆忠心。看到汴京保卫战取得初步胜利,钦宗长舒了一口气,王朝危如累卵时,他视皇位如同针毡,随着危机的暂时解除,他又仿佛找到了当皇帝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的一个最大表征就是疑心。毫无疑问,李纲和种师道都是不可多得的宋廷脊梁,然而,这样的脊梁对于皇帝而言,在外患凸显之际,是其重要的倚仗,而随着外患消退,他们的存在则成为皇帝的心头之患,历代皇帝都走不出臣子们功高震主的危机感,刚刚定下心神改元的新皇帝更不能不对有退敌之功的臣子心存戒备。就在汴京保卫战初步取得胜利之后,被钦宗任命为亲征行营使的李纲为了更好地调动兵马应对金兵南侵,曾提出要求行营使司取得高于三省、枢密院的军事指挥权。正是这一要求,让钦宗对李纲产生了疑心,他不仅没有答应其请求,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其兵权,李纲只能节制城内兵马,而城外的勤王之师则由种师道节制,同时又任命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行营使司和宣抚司分别向钦宗负责,二者互不统属。
分权制衡向来是皇帝的驭臣之术,但大敌当前的这套驭臣之术显然影响了军政效率,而更加要命的是,优柔寡断的宋钦宗开始在可耻的投降主义和冒险的机会主义之间左右摇摆。劳师远征的金军担心夜长梦多,向宋廷提出了议和的条件,即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处战略要地,同时还要增加岁贡,这样的条件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一时间宋廷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交锋激烈,钦宗无心恋战,已决定妥协。就在此时,大批勤王的宋军从西北策援而来,钦宗这才重又兴奋起来,然而,这个兴奋过头的皇帝很快就使出了一个昏招,那就是“劫寨之谋”。
其实,所谓“劫寨之谋”不过是钦宗主导的一次蹩脚的偷袭。眼见勤王之师日增,几天前还心惊胆战的钦宗仿佛被打了鸡血,尤其是新任命的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提出的偷袭金营、生擒敌首的建议,更让他头脑一热,想都没想就拨给了这个曾在种师道手下号称“小太尉”的姚平仲七千精锐。尽管李纲和种师道都极力反对,认为此举与自杀无异,但钦宗却一意孤行,还是决定派姚平仲前去劫寨。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行事张扬的姚平仲根本就没将劫寨做得秘而不宣,反倒大张旗鼓,毫不掩饰,结果金营早已探得消息,七千劫寨精锐有去无回,劫寨不仅成了闹剧,还成了金人要挟的借口。面对气势汹汹的金兵,钦宗不仅罔顾主战派乘机击敌的上奏和陈东等一众太学生的集体请愿,同意了金人割地、增岁贡的要求,同时还罢免了李纲、种师道的职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当汴京之围以屈辱的方式得到化解,这位坐了御座仅几个月的皇帝望着因太学生集体请愿而被贬被杀的“六贼”背影和李纲、种师道两位守城主帅的落寞神情,发出了这样一道御批。900多年后,这道冰冷的御批仍令人周身寒彻。事实上,学着当皇帝的宋钦宗始终不得要领,当深重的疑心让他在一年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26位身边宰执,当一次次的割地求和最终变成难以填满的沟壑,当意在灭宋的金兵再次席卷而来,内无共谋之臣、外无可用之将的宋钦宗已无半点招架之力。
由此,靖康之耻注定让宋钦宗成为北宋王朝最后一个接棒者。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攻破汴京,一心以为拱手称臣就可保富贵的宋钦宗,在被金主骗至金营之后,很快就被关进了一间四处漏风的小屋,成了一个可怜的人质。为了满足金主“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的无理要求,惊慌失措的宋廷和入城的金兵一起,开始了对汴京掘地三尺的搜刮,一时间,哭声相闻,火光四起,呼啸的北风卷带着漫天大雪,流离失所冻饿而死的百姓不计其数。然而,尽管宋廷对金主百般讨好,仍不能摆脱亡国的厄运,靖康二年(1127)二月,钦宗被金主废为庶人,不久,太上皇徽宗也被押至金营。当钦宗的龙袍被金兵强行剥掉,透过史书的墨迹,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位短命皇帝无望的泪光,一年零两个月,北宋积贫积弱的国运虽不是他一人的昏聩无能所致,但历史还是让他成了一个断送江山社稷的罪人。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
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
——赵桓《西江月》
当《西江月》的韵律和风声一同响起,宋钦宗已经和他的父亲一起,被掳到金国,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执政的懦弱和壮士忠臣的可贵。然而,这份悔悟为时已晚,史载,这位亡国之君在北狩途中受尽了金兵的凌辱,日暮宿营时,金兵“絷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其逃跑;翻山越岭,他则被缚于马背之上,饱受颠簸之苦;到了金上京宗庙,更是经历了屈辱的献俘之仪。后来的野史笔记曾详细记录下了金天会六年(1128)八月二十四日献俘之仪的凄惨:
黎明,虏兵数千汹汹入逼至庙,肉袒于庙门外。二帝、二后但去袍服,余均袒裼,披羊裘及腰,絷毡条于手。……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朱后归第自缢,苏,仍投水薨。
南宋初年,宋廷对这段屈辱的“靖康耻”极为忌讳,曾多次下诏禁止私人修史,遍焚有关靖康年间的笔记小说,同时,为了掩饰这段皇室丑闻,还特将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年龄虚增十岁。但作为靖康耻的核心当事人,对于赵桓而言,自己宠爱的朱皇后决绝赴死的一幕已不可能从他的记忆里删除,那些在北狩路上被凌辱、被蹂躏、被强嫁的妃嫔宫女同样也成为这个短命皇帝后半生难以走出的噩梦。
是夕,宿树林下,月色微明,闻番人吹笛声,呜咽如哭,盖奚国兵后队也。帝与太上太后闻之曰:“与化成乐何如?”时太上口占一词曰:“玉京曾忆旧京华,万里帝王家。琼楼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少帝唱其词,复和之曰:“宸传二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天坼地,忍听琵琶。如今塞外多离索,迤逦绕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歌不成曲,三人大哭而止。
这段记录于宋人笔记《南烬纪闻》中的文字,充斥着徽、钦二帝这对亡国父子的悲凉与无奈。身处苦寒之地,怅望漫天飞雪,赵桓还寄望着他的弟弟赵构能够打马杀来救自己脱离苦海,甚而至于在韦太后同徽宗灵柩归宋时,钦宗还声泪俱下地请求韦太后转告高宗,如能归宋,他不会去与其争皇帝,只求当个太乙宫主足矣。然而,这最终是一个杳不可及的梦,偏居江南的新皇帝此时正在重演着割地求和的老套路,在虚无的靡靡之音中,他怎么可能请回一个和自己争夺皇位的对手?
关于宋钦宗死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中风而死,另一说则甚为惨烈。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曾命钦宗和一班大臣比赛马球,因长期困禁加上心情沉郁,让他染上了严重的风疾,再加之不善骑术,比赛一开始,他便一头从马上栽下,被后面的乱马践踏成了一堆肉泥。其实,这位可悲的末代皇帝早在被金人掳掠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那个在金国苟活了近30年的阶下囚,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