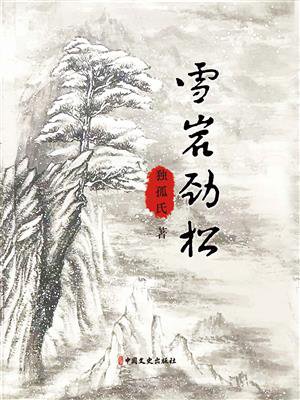第七章
十年离别两茫茫
考场相逢徒感伤
会议开了五天。那天上午一散会,我就立即赶回学校,投入紧张的教学中去了。那时候,教书还真不像现在这样急功近利,总是重过程落实、基础夯实,务求学生基本技能学扎实。不像今天这种教法,上新课如发射火箭,上复习课一题千练。那时,也没啥复习资料可做,也不开什么研讨会、座谈会、吹风会,更没有培训机构雪片儿似的外出考察通知、论坛邀请。那是“真教育”,靠的是“硬功夫”。
新课上到4月底才结束。上新课倒轻松,可一进入复习,我就成了“大忙人”了。我一人包揽了两门应考科目:语文、政治。语文教材两年共四册,政治上下两册,在两个月内复习完毕,迎战中考。这六十天一千四百四十个小时八万六千四百分钟,分分秒秒都是那么的金贵,不!比金子更宝贵呢,因为这不仅是检验我是否称职,更重要的是这一考关乎几十个青少年的前途和未来。
我那时给学生复习分两步走:第一步,把学生学过的知识分成若干条块复习,又叫纵向复习,比如语文,分成语法(包括造句、修改病句)、词语释义、拼音、改错别字、记叙文、散文、小说、古文……复习一类,过关测试一类,并美其名曰过关题。这类复习一般在5月完成,到了6月就开始拉网复习,这是第二步,即以教材册次为单位进行复习,然后进行“期末考试”,我把这种复习叫横向复习。一纵一横,漏网之鱼可就小而少了。
这种应试教育,在当时是剜肉补疮的“良药”,到了1983年,我在自我反思中认识到了我教学中的失误。此为后话。
初中毕业兼升学考试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那时,国民经济还在恢复中,不仅教育教学设备设施落后,而且交通闭塞,老百姓兜里也没几个钱,所以学生参加中考,哪有钱住旅舍住宾馆呢!中考考场设在区中学。于是,我事先找了熟人——当时一区中学的肖校长,借了两间空教室,一间住男生,一间住女生。住宿找到了,可又在哪里吃饭呢?一时间没了主意,就在我束手无策之时,管小勇的妈妈焦秀明对我说,她有一个亲戚就在区中学附近,我们可以在她亲戚家煮饭吃,后来又传来更好的消息,她那亲戚还答应义务为考生煮饭弄菜。万事俱备了,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考试头一天,全班学生有的背着米,有的扛着柴,有的背着干谷草,还有人扛着竹席……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区中学走去。尽管这一行人活像逃荒要饭的难民,但是一个个精神焕发,自信满满,一路上笑语不断。
到了区中学,带领学生在水泥地上铺好了临时住宿地,我也选了靠墙角处摊开了竹席。接着又带着学生去管小勇亲戚家用餐,用完餐带领学生回到临时住处,已是晚上八点钟了。大多数学生躺下就呼呼大睡,可疲惫不堪的我,却不敢躺下,因为有睡不着的学生需要我劝慰。
我光着脚——不敢穿鞋子,怕惊醒了学生,小心翼翼地在水泥楼板上来回走着,时不时俯下身子静静地听他们细细的鼾声。在女同学住处,我发现了两个女同学佯装熟睡实际却侧着头在暗中流泪的。我把她们悄悄地带出了住处,在走廊另一头的一间没人住的空屋子里,我使尽浑身解数安抚她们,劝慰她们,并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们:“……考起了高中,那当然好,没考起,也没什么,我不也是一个连初中都没上完的人吗?命运的方向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劝慰了好半天,两个女同学都笑了,其中一个说:“纪老师,你放心,我们回去睡了,这次保证考完才回家,不管考得好不好!”我将她们送回“宿舍”。
我回到地铺上又坐了一会儿,再一次巡视了一次,才和衣躺下。
第二天早饭后,我把学生送进考室,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监考了。
预备铃一响,我领起试卷迈着八字步踱进了教室,虽然我还是一个民办教师,但第一次踏进如此庄重严肃的考场,真有点忘乎所以,不免有点飘飘然的感觉。铃声响了二遍,该是服务员送草稿纸、备用墨水来了。
“元初,这是草稿纸和备用墨水,有啥需要的,招呼一声,我会立即送来的。”我抬头一看,不由得傻眼了。
“哎呀,咋是你嘞!卢姐!”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
“你什么时候当上教师的?”
“比你早!顶替我妈。”
“哦,公办教师,了不得!”我调侃了一句,掩盖自己的窘态。
“我才疏学浅,有啥了不起的哟。哪像有些人吃粉笔灰还没一年,就红透了半边天。”说完,她转身走了,因为发试卷的铃声再次响了。我只好收心敛神,发试卷,监考……
可是,任我如何暗自叮嘱自己别分神,要专心致志监考,但就是魂难守舍,脑海老是浮现出十年前那一幕幕令我永铭五内的往事……好不容易熬到考试终场的铃声响了,我收好试卷,正准备去考务室密封试卷,卢姐走了进来问:“你昨晚住哪?”
“和学生一起睡楼板!”
“你身体这么差,哼!滚楼板。”她恨恨地说了一句,剜了我一眼,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拿着,住我寝室吧,我今晚上到王老师家去住。”
“卢姐,谢谢了,我还是和学生一起滚楼板吧。我怕他们晚上睡不好,明天考不好!”
“还滚楼板,你不要命啦!”
“啪”的一声,她把钥匙拍在讲桌上,回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剜了我一眼说:“谁也不会黏上你的。放心去睡吧。”我彻底被弄糊涂了!身边来来去去的考生发出的嘈杂声提醒我该干什么了。
我慌慌张张地来到考务室,依规依矩地把试卷装订好,贴上密封笺,急匆匆地找到班上的学生,带他们去吃完饭,又把他们带回临时住地休息。
下午,我把学生送进考场,又回到自己的岗位,整个下午,我再也没见到卢姐的身影。当天晚上,我衣袋那把小小钥匙真是让我为难极了。不去睡吧,拂了她的好意;撂下学生不管去床上睡,我睡得放心,睡得安稳吗?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让常本英、牛玉学、陶文芳她们几个女同学去睡。
我守护着学生全部进入甜蜜梦乡后,摊在只铺了一张竹席的水泥地板上,辗转反侧,难以入梦……卢姐今天的语气眼神透着满满的怨气!这是为什么?十年前不是她叫三姐写的那封恩断情绝的信吗?重逢时,我不计前嫌,她为何倒反而一副气冲斗牛的样子……难道其中有什么误会?
好了,不想了!下定决心不想了,可是尘封的往事总是一个劲儿地如潮水般往上涌……深夜长谈,竹林幽会……谁能忘却呢?
眼紧闭,头痛欲裂,总想睡,但就是睡不着,没法子,干脆睁大眼瞪着天花板!哪知道这样过了一阵子,我反倒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又是一天的考试,下午三点半考试结束了,我叫班上纪检组组长常本英、班长隆华带领学生回家了,没人关注学生归家途中是否安全。若是放在今天,谁像当年的我那样做,我非扣他奖金一万元,并给记过处分不可!
学生走后,当官的把我们留下来聚一聚,那时能聚餐喝酒就是天大的喜事美事。太阳快落山了,晚餐开始,两间大教室,临时改作餐厅,两张课桌一拼就成了餐桌,凳子不够,有的也懒得去找,八九个围站成一圈就狼吞虎咽起来。每个人脸放红光,激情飞扬,一边吃喝一边大声喧哗:有讲学校工作的,有讲家事的……总之,家事国事天下事,胡侃;东风西风南北风,乱吹。喧嚣不已的是“高阳酒徒们”,猜子的猜子,喊拳的喊拳,放刁的放刁,耍赖的耍赖,闹声雷动!
我理所当然地被挟裹进了“酒囊”堆里。郁闷了两天的我,此时的心情依然如浓云满天——阴森而沉闷。我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没有感受到暑热气息,心里依然是冰天雪地般酷冷,昨天的重逢又勾出了我那段剪不断理还乱,既苦涩又甜蜜的回忆。十年前那段恋情是那样刻骨铭心,而我眼下的婚姻又是这样苦痛而闹心!张兴老师找我喊拳,我摇了摇头;吕善述老师喊我猜子,我摆了摆手。我腔不开气不出,愁云满面喝闷酒。
“哪个是纪元初?”突然一女高音传来。
“那里。”不知谁应道。
“好,我跟他是一个大队的,却还不认识他呢,听说他兄弟酒量不错,今天想来会会他。”话音还没落,一个高挑个子、白皙脸、蛾眉隆鼻的少妇来到了我桌前。几杯酒下肚的我此时已进入半酣状态,进入半酣状态的酒徒是既亢奋而又大胆的!她走到我身边爽朗地笑道:“老弟,我也姓纪,老家与你家隔一条小溪沟,可是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哟。来,今晚上我姐弟俩一醉方休,如何?”已进入亢奋状态的我回了几句,撸了撸衬衫袖子,就和她一杯又一杯地喝了起来。不一会儿,我俩就喝得满脸红霞飞,接着就“三桃园呀,五金魁呀”地喊起拳来了……
太阳已落到山背后去了,但天边那抹红霞还不忍离去,经东关火烧坝,爬上观音岩那长长的石梯,走到快要翻过莲花坡坳口的时候,酒精已烤得我头昏脑涨,脚下轻飘飘的,东歪西倒,三四米宽的路也不够我走。不知何故,我一下子就跑到了悬崖边。我赶紧伸手抱住一棵硕大的梧桐树,跌下悬崖的势头被刹住了,酒意也被吓醒了一半!但我最后的劲儿也用完了,无力地侧着身子瘫坐在大树根下,一只脚悬在崖边。这悬崖少说也有十多米深啊!俗话说得好,“酒醉心明白”。尽管此时我连说话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但我心里还是明白的。我吃力地脱下刚买不久、已满是汗渍的白色衬衫,歇了歇,又抹下手表,把表放在衬衫上,心想:看来我今天死定了,这表、这衣服留给妻女换点钱吧!
我坐在树下,昏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在蒙眬中,我似乎听到有几个人在说话:“喂,你看这树下还有点财喜啊……”
“财喜,你敢要?”
“咋不敢?”
“哎呀,这不是纪眼镜嘛!”
我很想睁开眼开口回应他们,但就是开不了口,也睁不开眼。迷迷糊糊的我感觉到有人把我背到背上——我昏睡过去了。待我醒来时,已躺在了会议室的长条椅上了,耳边只听到头顶上的大吊扇呼呼地响着,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口干舌燥,头痛欲裂。我挣扎着起来,准备找水喝,这时,表兄端了一大碗白糖水进来,我迫不及待地端过来就咕噜咕噜地往肚子里灌。一碗灌下去,我心里好受多了,似乎又有了活力。
“我咋在你这里?”
“你呀,还是那种喝起酒来就拼命的德行!今晚上要不是莲花桥的龙惠泽他们看川戏回来,把你背到我这里,我看你摔死在岩下还不知咋个死的哩!”
“好多了,我回学校去了。”我站起来,说完就走出了大门。这时酒劲消退了许多,但走起路来,脚下还是有点飘。
回到学校已是深夜十一点了,暑气已消退了许多,毕业班的常本英等几个同学还在学校,等候我的归来。那一夜真令我铭感五内,终生难忘。
我回家了一趟,把与卢姐重逢一事如实和妻子说了。妻子笑了笑,说:“你咋不去她床上睡呢,人家多心疼你啊!”
“我们两个清白如水,谁像你……”话没说完,我就打住了,因我是个死要面子活遭罪的主儿。
两天后,上级通知我去参加中考阅卷。阅卷,这种“劳动”是对一个民办教师的认可和信任,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阅卷组第一次会议,区文教干事王乾俊就宣布我为语文阅卷复查组组长。这是一份信任,也是一份荣誉,但在我心灵深处,我感到是一种压力,因为这个“组长”要承担重大的责任。阅卷前两天,我们组还较轻松,因作文改得慢一点,所以复查组清闲些。到了第三天,已批阅完传到复查组的卷子就多起来了。整个上午我厕所也没去一趟,整整复查了四百五十份卷子。
在复查到第十五本试卷时,我发现这一本试卷的阅卷老师对作文评分标准把握不准:不看作文结构是否完整,内容是否具体而丰富,凡是写得朴实一点的作文,一律定为C等;有几篇辞藻稍微华丽一点,但空洞无物的作文,竟然被评了29.5分(那时是100分制,作文满分为30分)。更为“奇葩”的是,有一份试卷作文没有写完,仅是字写得好一点,开头一段的套话写得多一点,也给了25分。
一个阅卷小组五个人,两人改作文,其余的改散题,因为没有阅读题,最难改的是问答题,而最好改却总是改不好的是作文。因为同一篇作文,同一个人批改,读第一次与读第二次,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篇作文见仁见智就情有可原了。
但是,一篇作文能被评为上等还是评为下等,其界限还是如鸿沟般分明的。这篇作文写的是一个人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上一名教师,就刻苦自学。有个部分非常动人,大意是:夏夜饕蚊如麻,他为抵挡蚊子侵袭,不顾炎热穿上长衣长裤,并用橡皮筋扎紧衣裤口子,戴上自制的头套,只露出两个鼻孔呼吸、两只眼睛看书。一两个小时下来,浑身犹如从大海里刚捞起来,全身湿透了且汗臭味四溢。另一个打动人的部分是写病中看书:他斜倚在床头的栏杆上,身下垫着一个大枕头,通红的脸上汗流如注。很显然,他正在发着高烧,可他手里却捧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在吟诵着……
就凭这两段,这个毕业生的作文也不可能评个下等,得分在10分以下。按阅卷场相关规定,复查组不得在有错误的试卷上改分,只能将阅错了的试卷交回原阅卷组改正。当阅卷组不改正或与复查组意见不一致时,复查组可报请阅卷场领导小组同意后直接更改。
我拿着这份试卷找到阅卷教师——阅这张卷子的是一位公办教师。我拿着试卷走到他面前,毕恭毕敬地说道:“刘老师,请你老人家把这个作文再复查一遍,斟酌斟酌吧!”
他抬起头发花白的头,伸出左手中指,弯曲着左手食指,十分优雅地把眼镜架往上推了推,鄙夷地瞥了我一眼,不无讥讽地说:“纪大组长,有啥指教?”
“指教倒不敢当,请教一二还是十分必要的!”我按捺住性子,装作没听懂他的挖苦。
谁知没待我把话说完,他竟然说道:“你知道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是啥意思吗?你今年多大了?教几年民办了?”他把“民办”二字咬得很重,声音拖得老长老长。
我被他的无礼激怒了!就把那本试卷啪的一声拍在这个老师面前,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你知道六十耳顺是啥意思吗?谅你也不懂!你要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得等到投胎转世才行。闲篇不扯,请你这个老教师,对照作文打分参考指南,把改错了的改过来!”
这是他未曾料到的回应!
我的几句话噎得他瞠目结舌,气得他的脸色由紫变白。
甩下几句话,气愤至极的我扬长而去。两小时后,我叫组里的一位老师去取回那本试卷,试卷上的错误依旧未改一处。我知道如果这样作罢,就会使一些学生名落孙山,而另一些庸才则榜上有名。这绝不是我的私事!
于是,我走到这个老师面前,拿起那份试卷就往阅卷场领导小组临时办公室走去。我找到区文教干事、阅卷领导小组组长王乾俊,把事情大致经过说了一遍。说是“大致”,是因为我隐去了那个自以为是的老头对我的侮辱和轻蔑。
“你做得对,刘老师这个人本事不大架子大,学历不高心气高。我批准你们把他批改的作文重新评改,我相信你纪元初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的问题我会处理的。”我心里虽高兴,但又觉得压力倍增,领导的信任就等于责任,有责任就有压力。
当天,我们小组复查了刘老师阅过的十本试卷共三百人的作文,改评的就达八十五份,差点占到三分之一。为了减少误判,我们五人分为两组,一组、二组各自二人,各评各的分,由剩下的一人把两组的评分加起来除以二的得分即该作文的最后得分。
卷阅完后,开总结会。区委分管教育的杨委员和王乾俊干事都表扬了我,对我秉持公道、认真严肃而又有创造性的工作态度大加赞扬,并号召大家向我学习,当然也严肃地批评了刘老师。
时隔不久,刘老师从中学调到一所偏僻的村小教小学,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