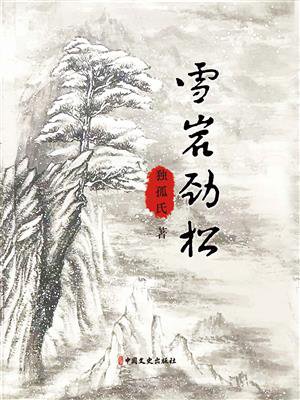第三章
屠龙自有心中剑
打虎原凭梦里猷
老先生走后,我就立即召开了班委会,决定暂停早晚自习一星期。每天下午放学后,我由一名熟悉该区域路径的班干部带路,走村串户,与家长们面对面地交流。我与家长的心通了,对他们面临的困难了解了,解决困难的方案也浮出了水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家长的面对面交流,他们明白了我对孩子们的真心真情,我的设想赢得了家长的支持和尊重。
那时农村缺电少煤油,就连我这个老师也没有手电筒。没有月亮或雨夜家访时,只好打着麻秆、干竹竿或柏木皮火把。但这样的火把,燃烧很快,烟雾又大,这就要求我既要跑得快且要踩得稳。如果跑慢了,火把一旦烧完了,我就得摸黑在高低不平且弯来拐去的田间小路上走了。可是我一个近视得近于盲的人,也得在小路上“跑步前进”啊!其难度可想而知了。这时我信奉的“事到万难须大胆”又发挥作用了。每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就不管面前的路高低直弯,不管有水无水,凭着直觉走。这样走绝大多数的时候是走对了的,当然,被摔得鼻青脸肿的时候也是有的。
通过家访,我逐步得到了家长的深度认可和高度赞许,反对我的声音逐渐减弱了,直到后来消失殆尽。
一个多月后,我班上的早晚自习已成了风雨无阻的常态了。每到下晚自习时,我总是站在操场边看着学生打着电筒、举着火把回家的壮观场面:几条小路上满是火光,一串一串的,像一条条闪光的长龙,越走越远,亮光越来越分散,在黝黑的夜幕下散开来,犹如满天星斗……
第二个学期,转校来我班的学生越来越多了。邻近几个大队的好几个学生也转来我班读书了。我了解到他们离校很远,上早晚自习,花在路上的时间,少则一个小时,多的两个小时。
于是我下定决心,排除困难,组建班上的师生伙食团,接着又开始组织离校远的学生住校。我把办公室腾出来,安上三张木床,一张睡三四个女同学,可住下十一二个女生。有几个男同学从家里搬来了床,也住下了。其间还发生了两个有趣的故事。
在学生还没住校前,我就把两个喜欢的男生留下来和我一起住。一张大木床,可睡三四个人。我和四岁的女儿睡一头,睡另一头的是我班上一个最小的又是最聪明的男学生——小华。一天早上,我起床叠被子,一看,傻眼了,床席上一大摊尿渍。我气极了,认定是小女夜里偷懒不起床,尿到床上了。我把女儿叫来,一顿训斥。女儿死活不认账,我正准备修理她,女儿委屈地一边哭,一边指着床上那摊尿渍说:“爸爸,你看,你看,那是在华哥哥睡的那头哦!”我一看,哎呀,原来是那个傻小子干的。后来,霞儿一见到那小子就喊“尿班长”。
20世纪80年代初,石桌子换成了木桌子,晚上学生们把几十张木桌拼成了一张“大床”,我和学生都睡在这“床”上。为了不被蚊子轮番叮咬,他们用衣服把头包裹起来,只留下两个鼻孔出气。一天夜里,在睡梦中,我被挨着我睡的邓伟一伸脚踹下了“床”,摔在地上。那小子也被惊醒过来,他一边把我从地上扶起来,还一边打趣说:“老师,你咋睡了个‘月亮落土’呢!”
学生伙食团初创时,没有锅没有灶,我再三恳求妻子多给我留下几块钱用于伙食团的“基本建设”。
为了表示我的清白,也为了让家长明白,学生伙食团由学生选出团长、保管、“会计”,实施学生自治。学生把从家里拿来的米交给伙食团长(保管往往由团长兼任)过秤,由“会计”记上账。就餐的头一天,由“会计”统计第二天的就餐人数及就餐的饭量标准,再由团长把米称给炊事员。
饭做好后,由团长根据学生自己登记的用餐标准,把饭分给学生。最先量米分饭都用秤称,很费时,学生有意见,他们打趣地说:“排前面的吃了都拉出来了,后面排队的还没轮上。”后来学生们一商量,创新出一个法子来:米改成量筒量,一两、二两的各做了一个量筒。用量筒量,简便易行——那时学校没有秤,每顿称米分饭都要去农家院子借秤,怪麻烦的。分饭也不再用秤了,改成用小碗量,通过先后几次测试,测定了一两米、二两米量饭用的饭碗,就用这两个饭碗分饭。比如你吃三两米的饭,那么就量一中碗,再加上一小碗;你吃四两米的饭,就两中碗。
当时,只有我一个民办班住校,班上的一切经费全靠自筹,所以没有经济实力给学生准备菜。学生的菜都是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泡菜、辣椒酱,没有汤,最好的汤就是米汤里撒大把盐,弄成的盐米汤。学生每次带来的菜,就要吃十天半月——冰箱冰柜这些现代化的奢侈品,那时还没听说过呢!
那时伙食团唯一要开支的是买引火柴和煤的钱。这钱是我和学生按就餐的次数均摊的。最先请的炊事员是紧邻学校农家院子的管婆婆。管婆婆娘家姓汪,她老人家生有二女二男,其时四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自立门户了。管婆婆给我和学生煮饭不要报酬,只求学生吃剩的饭和淘米的、洗锅的泔水归她,她把这些废物拿回家去喂猪。
我这人大半生中遇到了许多善人恩人,管婆婆就是其中的一个。老人家心地十分善良,对我也十分关照。
那时,我一个月只有二十来元工资,每到五号领工资那天,妻子就到中心校找到总务申中陆,除给我父女二人留下五元的生活费外,其余的她全领走了。我那时烟瘾大,每天一包八分钱的劣质香烟——“经济牌”,买烟就花去二元四,还要喝酒,称盐打油,所以根本就没钱割肉买菜了。我和小女吃一次肉真比登天还难。2015年,大外孙女蔡珮出嫁时,我到湖北麻城女儿家去做客,当谈到那时我父女二人经常吃辣椒酱下饭时,女儿红着眼睛说:“爸,有辣椒酱下饭还好哇,你忘了吗?我们吃盐米汤泡饭可不计其数啊!”在这艰苦的几年中,管婆婆没少帮过我,经常给我带来咸菜、泡菜,还时不时地给我弄来猪油或一小块猪肉。这些当然都是她老人家背着她儿子、儿媳干的哟。
在我这一生中,最喜欢的就是读书。我自以为读书不少,可从一任教开始,就尝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滋味。
在任教生涯中,我遇到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不是科班出身——从没读过师范,对怎么备课可是一无所知,只能四处求人指教。向红星小学的同仁请教吧,但这里初中语文教师只有我一个。
于是我备好课就步行四五公里,到中心校找人请教。我首先选择的是方老师,这个老师矮矮的个子,似乎没看见过他长胡子。鼻梁上老架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轻言轻语,从不高声大气,一副十分和善的样子。我找他“问道”的原因:一、他是受排挤的,一定不会排挤我。二、他和善。善者会以助人为乐。
可当我走到中心校找到他时,他正在看书。我走到他身旁,毕恭毕敬地叫道:“方老师,你好!我想请你帮我看看我写的教案,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教一二。”
他抬起头,望了望我,又望了望他手中那本翻开的教案,轻言细语地说:“纪老师,你是青年才俊呢,这课备得很好,比我都还备得好哩。”一说完,低头看他的书去了。口气中、神情上明显流露出的是讥讽。但从他的话语中,我又挑不出一点不是来。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我沮丧极了,决定去找一个教了几年民办初中语文的教师吕福求助。这次倒还好,他接过我的备课本,装模作样地翻了翻,微笑着说:“好,很好!我向你老弟学习!”这两句话真噎得我差点背过气去了。
本来我想去找张老师问问,可听说他父亲病了,请假回老家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只好悻悻地回到学校。这时刚下第一节晚自习,我回到办公室——大队新修的一间办公室(原来的办公室腾出来做了女生寝室)。新修了两间教室,竣工后,我请示了生产大队领导,把其中一间教室一分为二,一半做了学生伙食团,一半做了我的办公室兼寝室。顺便在此补白一下,那些叫嚷着三个月把我赶出红星小学的领导,在“收未录生”事件后,都一致向我伸出了大拇指,所以凡是我向他们请示汇报工作,只要他们力所能及的,他们都会同意、支持的。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我回到办公室,翻出教材、教学参考书,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决心走一条自己的路,不管那些这样那样的规矩,我潜意识中的“狂妄”,又一次冒出嫩芽来。我不管你什么备课方法,只要学生听懂了,成绩好了就行。
我悟出一个“理”来,备课也应分为虚实两个方面,虚的就是教学重点、教学难点,因为这些是任何一本教学参考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可又实实在在的都没用的。我之所以说这些是虚的没用的,是因为,编教参书的专家们不可能了解全国每所学校的校情,每个班的班情,那么他们编的参考书就只有参考的价值,绝不能悉数搬过来就用。
在我看来,备课应做到“三实”:一是教师钻研教材必须落到实处,也就是要找出哪些是学生自学能懂的;哪些非要教师讲了学生才能懂的;哪些是老师讲了,学生也弄不懂的。这就是备学情,也可以套用现在一些时髦的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一切为了学生”“以学生为主体”……第二个实,那就是教材后的作业要落实。不管你的课备得多好,到头来学生连课后的作业也完成不了,学生能学到什么呢?第三是要落实学生的学法。学生不能一生一世身边都带着一个老师吧,所以学生必须学会逐渐丢掉教师这根拐杖的本领,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当教师的既要授人以鱼,也要授之以渔。授人以鱼是近期目的,是治标的手段;而授之以渔才是终极目的,也可以说这才是教育教学的本质任务,套用当今一些学者金光闪闪的时髦语言来说:“教就是为了不教。”
基于以上认识,从那时起,我就按照自己对教材的理解来备课了,第一,在备课前,我会认真熟读教材,若是古文古诗或好的散文,我会先背诵。备课的重点我放在两个环节:一是整体把握,比如一篇课文,我准备几课时授完,哪一课时实现哪些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是什么。第二,那就是教学的步骤,我的教学步骤是十分细致的,细致到什么时候讲什么话,什么时候提问,学生答不起问时又如何启发,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学生练或者讨论,甚至连预习题的设置、作业的纠错我都会一一预设好。再后来,我连哪个环节用多少分钟也在备课时予以考虑了。在那个时候,我十分注意抓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和练习,比如组词、造句、扩句、缩句……
备课这一拦路虎终于被我打掉了。但更大更凶恶的龙潭虎穴在等着我,那就是当年语文教材中的语法、修辞等知识。比如词,从音节划分为单音节、多音节;从构词方式来分,可分为单纯词、合成词,合成词中又分并列式、动补式、动宾式……;按感情色彩划分,又是什么褒义、贬义、中性……还有什么反义词、同义词、近义词。
“词”的常识闹灵醒了,又要讲句子了,从语言表达又得分陈述句、祈使句、判断句、感叹句,从动词谓语与主语的关系又得分主动句、被动句,从句子构成来划分还得分单句、复句。在教单句时,除了讲清句子的主、谓、宾、定、状、补这些成分外,还要讲什么省略句、独词句;复句,除了要弄清复句的并列、选择、总分、转折、因果、递进、条件等关系外,还要教会学生判断多重复句之间的关系。在那时的升学考试,语文100分,而以上这些知识最少也要占20分,甚至有一年达到了25分。
这真是准备把每个初中生都培养成现代语法大家。
前几年,什么语文、地理、历史、自然、数学、物理、化学……都没系统地学习过。可现在,似乎学生这个虚弱的群体得大补特补,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得学。
这些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还有古代汉语语法等一大堆学问,一时间可把我这个“半文盲”弄得不知所措了。
在遇到拦路虎时,我不止一次地默默地念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战略上,我那时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要重视“敌人”。我知道这样说有人是非常不高兴的,但我写我的心里话,别人不高兴与我何干?我那时的“敌人”也好,困难也罢,那就是一大堆我自己从没涉猎过甚至听也没听说过的知识。
藐视这些困难就是不被吓倒;重视这些困难,就必须尽快学会,熟练地掌握并运用这些知识,以便斗困难而胜之。
于是,我决心边学边教,边教边学。可是,手里没有有关现代汉语语法的书,想学也无从学起。后来听人说双江师范大学函授部编写了《现代汉语语法》,我急不可待地托人买来了这本没有封面封底的书。这本书除了前言外,近三百页。可惜后来的几次搬家,那“救命稻草”竟被我弄丢了。再后来,一个朋友的丈夫,从纳溪监狱里给她邮回来了《古代汉语知识》《现代汉语语法》《形式逻辑学》《现代汉语修辞》《浅说病句修改》。这些书,朋友说放在她那里用不上,就统统地送给了我。我如获至宝。
买到重师大《现代汉语语法》的当晚,我就通宵夜战,看了四十七页,并将其中的要点一一地背诵默写。事后,我每天挤出时间:一边吃饭一边看此书,一边大便一边看此书,一边走路一边看此书……总之,我白天看,晚上也看,除了备课上课不看之外,我都在看《现代汉语语法》。我不仅看,而且还把重要的例句背下来,作为讲课的例句。比如形容词一般不能充当句子的主语和宾语,若要充当宾语和主语,它的谓语必须是判断词“是”或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
如:一、红是这类花的主色调。二、他喜欢这种红。三、优秀不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就在我奋笔疾书的同时,这一串熟悉的例句就会自然而然地跳出记忆的闸门,挥之不去,争跃于笔端。
我这个人从不死读书,读死书。在读的过程中,常常是一边读一边总结事物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性,并加以概括,形成“纪氏口诀”。比如在给学生讲名词的分类时,我就编出了一些好记、易判别的顺口溜式的口诀:“名词表名称,‘不’字来区分,前面能加不,就不是名称(抽象名词,如:科学、民主之类除外)。动词表动作,能带着了过……;形容词多得很,能加‘不’,也能加‘很’,加‘不’表否定,加‘很’表程度……”
总之,我千方百计地交钥匙,认真地去授之以渔,用眼下时髦的语言叫作“以人为本,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我用了七个白天黑夜攻下了这个龙潭。接着,我又攻下《古代汉语知识》《现代汉语修辞》这两个虎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