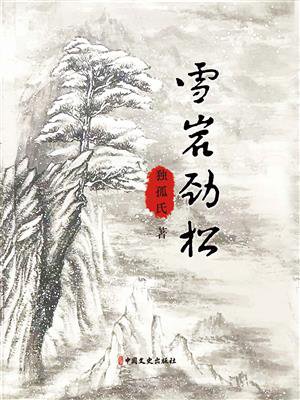第四章
且看朝霞红岭上
休听蓬雀噪檐前
我在后来十余年(语法知识考试在学生升学考试中占重要一席,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语文教学中,每当讲到现代汉语语法及修辞或古代汉语时,我都会自豪地两手空空地进教室,既不带教材,也不带备课本,挥洒自如地讲课,我讲得精彩而接地气,学生学得扎实而又有创意。与此同时,我要求我的学生学以致用,用学过的语法知识检查、修改自己的作文。
这些知识,我在任教以前是从没接触过的,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但我清楚地知道,能否站稳三尺讲台,关键在于我是否有上刀山下火海的意志和胆魄。前面几关均已攻破,此关不过就将功败垂成。
在学习中,我坚持熟读中理解,理解中记忆,在记忆理解中创新。我坚持先学好、理解好再教给学生,在教给学生时必须有创新。我坚决反对“拿来”“借来”知识,而主张“偷来”知识,因为“拿来”“借来”的不需要动脑筋,不需要根据班情、学情加以改造,而是照本宣科即可。若是“偷来”的知识,则必须改头换面、加工更新、修修补补。这个改头换面、加工更新、修修补补的过程就必须研究教材,研究班情和学情,进行符合客观实际的创新,就是现在说的“内化于心”。例如学生在学习修辞时,对借喻与暗喻、借代,排比与对偶,设问与反问,这些修辞手法常常会混为一谈,于是我就找出其区别点加以简析:比如任何借喻都可改成明喻,而借代却不能改成明喻;排比必须具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分句,而对偶则只有两个分句,排比个别词可以重复出现,而对偶两个分句间的主要词词性相同,而意义相近或相反,一般不允许词重复出现(那时弄不清楚平仄相对这一概念)。
一番“日夜兼程”,我终于“过五关斩六将”,夺得了学习的“阶段性胜利”,掌握了教语法修辞的主动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1月中旬全区九所初中三十多个初中一年级班的统一进行的半期考试时,红星小学初中一年级班的语文、政治独占鳌头,郑杉教的数学居全区第二。这样的成绩引来了一些老师赞许的目光,当然也招来了非议和质疑,一时间谣言满天飞,如:“纪眼镜早就把考题捅了出来。”“考试时,有人看到纪眼镜递了答案进考场。”“他把优生和差生交叉编考号,要求一个优生必须把正确答案递给差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不久,这些流言蜚语也传到区文教办公室的领导和区里分管领导耳朵里去了。于是当下一年1月底全区期末考试时,对监考、阅卷等流程做出了近于苛刻的规定。
其后一周,就是考试、阅卷、统分等繁忙而又紧张的工作。在阴冷的隆冬,我心里始终是朝阳一片,但是从来就吝啬笑意的我,那几天就更没向谁挤出过一丝半毫的笑意。
分数统计完了,我们班学生语文成绩平均分、及格率、优生率均居全区同年级三十多个初中班之首,班人平均、优生率、及格率都比第二名高一大截。
公布分数名次那天,主席台上下一片愕然。因为一个低学历的“流浪汉”击败了一大群自以为“饱读诗书”的“夫子”。
我击败了“夫子”们,既带来“名誉”,也招来了忌恨。
那是初夏的一天,时任副班长的龙芬有两天没来上学了,于是我决定下午放学后去她家了解情况。她家住双溪大队,要翻过红星五队的一个高坡才能到。为了不影响学生上晚自习,放学后,我把学习委员和语文科代表叫到办公室做了周密的安排,并再三叮嘱他们一定要维持好上课秩序。一切安排妥帖后,我才叫上搭档理科教师吕善述一同前去。
找到龙芬家,已是傍晚时分了,她父母还在地里干活,而龙芬穿着一条蓝布围腰,正端着一大盆猪食去喂猪。我看着这个十二三岁的瘦弱女孩干如此繁重的劳动,鼻子酸酸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她一见到我和吕老师,满脸喜悦地叫道:“纪老师、吕老师,快请到堂屋坐,我倒了潲就来。”我俩刚一坐下,龙芬就从厨房里端来半面盆温水,找来面巾,说:“老师,擦把汗吧,大热天的,你们辛苦了。”多懂事的孩子哦,我心里暗暗赞道。这时她脸上的喜色早已褪尽,而笼罩在脸上的全是惶恐与不安。
“这两天你咋不来念书?”我望着她问。
“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还小。家里活没人干……爸不让我读书了!”话还没说完,她的眼泪就如泉水般地涌了出来。
“不要哭嘛!我们今天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我保证能说服你父亲,让你重返课堂。”我信心满满地对她说。
“没用的,我爸说,姑娘家,读再多的书也没用,长大了都是别人家的人,只要弟弟把书读好就行了。”
“咋这么说呢?”一向语言不多的吕老师也开口了。
“你爸他们在哪里干活,我们找他去!”
“在那边的高坡上,路不好走,我去叫他们回来好些!”话一说完,也没等我点头,她就一溜烟地小跑去了。
她和她父母从地里回来时,天已经黑了,我先是耐心开导她父母。龙芬的妈背着她丈夫望着我眨了眨眼,又朝她丈夫努了努嘴,她的意思我全明白,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她丈夫身上。
我耐心地从各个方面开导学生的老爸,吕老师也时不时地从旁帮腔,但这个做父亲的就是那么一套歪理:“我家人多劳力少,女儿大一点,可以回家帮着干些活儿了。再说女娃儿读那么多书有啥子用?……”
一个多小时就在磨嘴皮子中过去了,一点松动的口气也没有,这可让我的火一下子蹿了上来。我呼地一下子站起来怒斥道:“解放二十多年了,你还满脑壳的封建残余思想,那些疾风暴雨也没把你头脑的封建堡垒摧垮吗?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觉悟咋连一般群众也不如?我懒得再和你嚼舌头了,你还是共产党员,又是生产队长。明天我找你们大队姚支书去,让他来给你脑壳里打扫一下清洁,如还不行,我就请公社领导给你打扫清洁……”
你还莫说,我这一通火发出去后,他一下子就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他的大眼睛转了几转,狡黠地笑着说:“纪老师,你莫冒火,也莫把这个事儿搞那么大好不好?我明天就叫大妹崽来读书就是了。”
“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就是沉不住气。动不动就发火。对不起,对不起!”我看目的已达到,立即道歉,准备走人。
他们一家老小却非要留我们吃了晚饭才走,我却说学校还有学生在上晚自习,要立即回校。好不容易才逃脱他们的“围追堵截”,所以连火把也没准备就往回走了。
我和吕老师逃跑似的来到龙芬家对面的山前。翻山两条路,一条是宽一点、缓一点的路,好走一些,但要多绕远路;另一条路窄一点、陡一点,可要近一些。吕老师担心我视力不好,坚持走那条绕远的路,我则坚持要走近的这条。
我对吕老师说:“你说我视力不好,今晚上我两个就一较高下,看谁走得快。”说话时,我俩已上山了。我为了显示自己的“神勇”,不顾天黑这个现实,一个劲儿地快走。
“小心,这儿路很……”吕老师的“窄”字还没说出口,我两脚一踏空,一下子掉进了一个废弃的砖瓦窑里。跟在我身后的吕老师一听我在窑里发出的“哎哟”的呻吟声,忙问:“纪老师,你摔伤没有?”
“不知道!”我有气无力地回应道,只觉得手脚不听使唤,背上肋间一阵阵钝痛。
吕老师急忙对着龙家院子一阵大吼:“小龙,小龙,快叫你爸爸拿架长楼梯来啊!”这一阵大吼,打破了山村夜间的静谧,引发了四周护家犬的狂吠。
不大一会儿,小龙和她的父母打着火把,扛着毛竹楼梯来了。她父亲放下楼梯,和吕老师一前一后下到砖瓦窑的石炉桥上。他俩争着要背我,结果小龙的父亲抢先把横躺在炉桥上的我小心翼翼地背了起来,一手反过背来,搂住我的屁股,一手扶着楼梯,往上爬去。爬上砖瓦窑后,他坚持不放我下来——其实就是放我下来,我也站不起,走不动的。
小龙的母亲一再抱怨说:“就是你这个老车夫不准芬妹子去读书。要不,纪老师会受伤吗?”我和吕老师再三劝她母女俩回去了。她们往回走后,吕老师在前打着火把,小龙的爸爸背着我在后面走着。伏在他背上的我,此时除了感激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把我背回学校,小龙的父亲致歉再三后就走了。我睡在床上觉得肋间、背部热乎乎地痛。吕老师站在我床前一个劲地问:“骨头摔断没有?”
“可能没有吧,翻身动弹没加剧痛感,应该是只伤到软组织了!”
“那就好,那就好!”
第二天,我写了几味草药名字,请吕老师到山上去给我挖回来,再打上半斤白酒,然后把草药切碎捣成泥状,调上白酒,敷在痛处,一天换三次药。不知是我的伤不重,还是草药药力强,抑或两种可能兼而有之吧,三天后,我身上的疼痛消减了大半,能起床上课了。
我伤好了后,还留下一段永生难忘的花絮。在我伤好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中心校通知开会。那时的校长、书记二人,性格各异。书记古板正直,并小有才气,非师范生;而校长则三教九流似乎都略知一二,且书法还不错,尤其精于打牌,划拳喝酒。两人心有千千结,但面子上又不得不表现得和气团结,于是他们总是找机会实施指桑骂槐、敲山震虎之计。那天开会,校长长篇大论地讲了一番之后,轮到书记讲话了,他借题发挥地说:“……有些老师下班上班也不分,总是爱喝酒。喝酒也就罢了,有的还滥酒!前几天,纪元初老师喝醉了酒,摔在瓦窑子里,造成很不好的……”
没等他把“影响”两个字吐出来,我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哈哈大笑,会场上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射向了我,我昂首挺胸地大声调侃道:“书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酒龄已有十八年了,从来没喝过一滴烂酒,也不知道哪里有烂酒卖!我喝的最差劲的酒就是红苕干酒。你哪里痒就挠哪里嘛,千万不要拿我这个基层教师来撒气!……”我这一席话,赢得许多钦佩、赞许和同情的目光。
书记被我呛得面红耳赤,瞠目结舌,老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劝你少喝酒,可是为你好啊!”
“我不需要你这种假惺惺的好心。”我忍不住又呛了他一句,气得他脸发白,手发抖。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其他几个教初中的教师,对我因妒而生恨,在支书面前有鼻子有眼且成功地造了一次谣。
这次家访以及家访后所衍生出的书记“谏言”的情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现聊以记下,以正视听。
初战告捷真让我这个凡夫俗子高兴了好一阵。乘初战告捷之余威,在发放成绩册那天,我口头表扬了许多学生及家长,要求学生回家去征求家长意见,再补八天课——直到腊月二十八才放假,正月初六开始上课行不行,同时郑重宣布不收学生一分钱补课费。愿意补课的第二天上午八点到校,不愿来的不强求。
第二天一大早,不但全班到齐,还新来六个学生。原来中心校公办班有四个学生,决心下学期转学过来,双溪民办班有两个学生转学过来,怕来晚了我不收,当然,跟着来的还有这几个学生的家长。这样,原来坐两个学生的石桌子,就只好坐上了三个,没有凳子,由学生从家里搬小木方凳挤在两个小石方凳中间。
那年春节,我吃上了肉和白米干饭。更为重要的是,我信心满满、惬意满满的,真有如坐春风的感觉——或许这叫“小人得志”吧。
正月初五,我就担着吃的穿的赶往学校:担子一头是大米,大米上放着一包换洗衣物,几样蔬菜;另一头则是红苕,因为那时大米金贵。一到校放下担子,我就把过春节这几天备完的语文课再次检查了一遍,又开始备政治课《社会发展简史》了。
初六开学那天真是忧喜参半:喜的是报名交费时,没有一个家长不是眉开眼笑的。他们一见到我总是如是说:“纪老师,我家娃儿能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真是运气好!”“纪老师,我这死妹崽交给你,我们放心!”
俗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一向自诩厌恶吹捧的我听到家长们七嘴八舌的赞扬,口里一再谦虚辞让,但心里还是暗中涌动着几许甜甜的欣慰和扬扬自得。不过,这种情绪没持续到中午,就被一股忧愤弥盖过去了。
“老师,管忠和龚昌元不来上学了。”班长小华还没走进办公室就叫嚷了起来。
“为什么?”
“他们俩要转学去县城。”我一听,不由得一惊,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副班长,一个是少先队大队长,成绩也在班上的前几名,这一转学若引起了骨牌效应咋个收场?我可是新手上路啊!当时农村初中与城里初中学制不同,城里的读三年,农村的读两年。这种政策上的差别,是两名优生家长通过关系让学生转学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这个老师学历太低,难入两个孩子家长的法眼吧!想到这里,一股悲凉之气顿时塞满了心田。
不过后来,这两位家长竟然成了我的粉丝,并常和我一起推杯换盏。
我走出办公室来到教室,一个胖嘟嘟、粉团团的女孩子就站在我面前叫了声:“纪老师,我想来你这里复学。”
“你叫啥名字?”
“龚运学。”
“哦,这里学习条件不好啊,石桌、石凳,还得三个人坐一桌!”
“我知道,我家长也知道。这些都没关系,只要你收下我。”面对这个求学若渴的农家少女,我真找不出半点拒绝的理由来。
当天下午,一个中等个子、瘦瘦的、小脸、头上有少许几根白发的老者,带着一个黧黑圆脸、大眼的姑娘来到我办公室。一进门,老者就自报家门:“我叫常兴田,住在学校斜对面的胜利一队,小女叫常本英,想投到纪老师门下复习,万望收下为幸。”……就这样,今天两个,明天一个,到真正开学——正月十五时,我班上已从原来的六十一人变成了六十七人了(转走了两人去县城,转来和复学的八人)。
新年新气象:喜——忧——喜,总的看来有些差强人意吧。开学没几天,妻子就把四岁的女儿送来学校:“我要干农活,没法照顾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