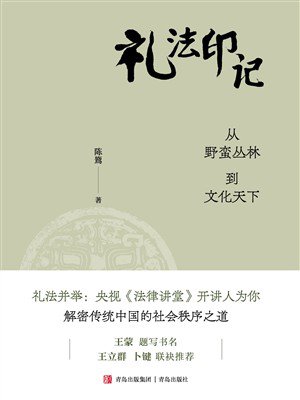第一章
牧野之战
毋庸讳言,文明脱胎于野蛮。人类文明的历史无不书写在鲜血铺展的背景之上,中华文明也不例外。
翻开中国的历史,公元前1046年春天的那个甲子日的清晨是那样的特别。中华文明似乎就在那一年那一天的那一刻,懵懂中被一通隆隆的战鼓声敲醒了。
那一天,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牧野之战。这场战斗只进行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却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中华文明的走向。
那么,牧野之战是怎么发生的?它又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和文明的走向呢?
一、血流漂杵
公元前1046年,经过几代人战略性累世经营,一个蓄势已久的西部邦国周终于捕捉到一次难得的战机,对它的世仇——掌控天下近600年的商王朝发起了决战。
这一年的初春,周的国君周武王率领周军,从丰镐(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出发,经过崤函古道,到达位于今天河南省西北部的孟津。他在这里会同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邦国,聚集了四万五千人的军队,再渡过黄河,迅疾推进,抵达了商王朝都城朝歌附近的牧野(今河南省淇县以南、新乡以北一带)。
周联军的突然到来,让朝歌城里的商纣王帝辛措手不及。此时商朝的军队主力正在征讨东夷,于是商纣王仓促组织起大批奴隶和战俘,连同国都的守备军队一起,开赴牧野来迎战周的联军。《史记》记载纣王出动的兵力有七十万,也有别的文献记载说是十七万。不管哪种说法,从人数上,商军大大地超过了周的联军。然而周的军队显然更加精锐,士气也更加高昂。姜太公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且冲乱了商军阵脚,然后周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将对方的阵形彻底冲垮。商军最前沿的大概正是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军队。他们不仅无心恋战,而且纷纷倒戈,同周军一起冲向后面纣王率领的守备部队,商军大败。战败的商纣王撤回到朝歌城里,在他的宫苑鹿台穿上玉衣,自焚而死。战胜的周武王赶到鹿台,砍下商纣王的头颅并悬挂到旗杆上示众。历时近600年之久的商王朝就此灭亡了。
《尚书·武成》中这样记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就是说:甲子日这天的清晨,商纣王率领他如林的军队来到牧野会战。他的军队不是周军的对手,前面的士卒反戈向后面攻击,商军大败,血流之多,竟然将军中的木杵漂了起来。
这段短短的记录,却留给了我们重要的信息。
首先,这个日子很特别,它是甲子日。
中国古人用天干地支来纪年、纪月、纪日和纪时,就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按顺序两两配对,进行纪年、纪月、纪日和纪时。这样,10与12的最小公倍数60就是一个轮回,周而复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六十甲子。古代的中国人认为“六十伊始,甲子为开首”,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所以,中国人觉得凡是大事的开始,用甲子日这一天最为吉利。
那么周选择在这一天开战,就具有特别的意味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利簋”。利簋的腹内底部有4行33字的铭文,里面不仅提到了武王征商,还提到了就是在甲子日这一天。这是武王征商最直接的证据。利簋也被称为“武王征商簋”,出土文物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武王在甲子日这一天伐纣是确凿无疑的。
其次,这一天商纣王率领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只是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其中很多人都是奴隶和战俘。这些人不愿意为纣王卖命,还反过来帮周联军的忙。比如其中有一部分羌族的奴隶就向商军当中同族的官兵们喊话,呼吁大家投降,结果导致了商军临阵倒戈。
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给周帮忙的,不仅是这些阵前倒戈的奴隶和战俘,还有相当一批商的王室贵胄和官员。战前就有一批官员跑到周那边告密去了,《史记·周本记》就记载说:“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战斗开始之后,纣王的亲哥哥微子启也在阵前主动投降了周。
最后,“血流漂杵”则描述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战场鲜血横流,或许还伴着天降的雨水,竟然将军中的木杵(也有说是盾牌或者其他器物的)都漂起来了,可见死者之多与场面之惨烈。按照另一部古书《逸周书》中的说法,这一战周人杀了商军十几万人。后世有好事者概算了一下,在一个小的区域内杀死十几万人,“血流漂杵”是可能的。何况当时正是雨季,雨水和着血水漂起杵来,就更有条件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和《逸周书》的记载真伪难辨,但战国时代的孟子是看到过《尚书》的。孟子在其中就看到了这句“血流漂杵”,大不以为然。他有一句名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由此事而发出的议论。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其中的《武成》篇,不过取信它的两三条罢了。仁道的人天下无敌,极其仁道的周武王去讨伐极不仁道的商纣王,怎么会流那么多血,还让木杵都漂起来呢?
孟子的不信很可能源于儒家倡导仁政。他要让“仁者无敌”的思想确立起来,所以凭着臆断就否定了《尚书》的这个记载,认为周武王这样至仁的人讨伐商纣王这样至不仁的人,商王朝这边的人也都应该一呼百应、全面倒戈,怎么还需要杀这么多人呢?何况杀这么多人也显得周武王太不仁慈了。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写“血流漂杵”,只写了商军前列的士卒倒戈,与周联军一起往回打,商纣王就败了。感觉上,好像王师所至,兵不血刃,摧枯拉朽就结束了战斗。
本人觉得孟子的这个说法恐怕靠不住。首先,《尚书·武成》是胜利的周人记录的,他们一定也会本能地自我维护,这样残酷的场景,他们没必要无中生有;其次,古书惜墨如金,其中的每一句话都会携带重要信息,《尚书》中直接形容这场战争场面的话语只有这一句,它应该是最精到的描述。
如果按照孟子和后世儒家的说法,商军几乎毫不抵抗,纷纷对仁义的周武王望风归降了。可如果真是这样,战争结束后为什么还会发生武庚叛乱?商的遗民为什么还会聚集到纣王的儿子身边起来反抗周呢?还有战后两个著名的贤人叔齐和伯夷,竟然耻食周粟,宁肯饿死在首阳山上,临死还作歌唱道:“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倘若没有发生惨烈的杀戮战争,“以暴易暴”从何说起?
即便按照明代王夫之折中的说法,古代“漂”与“飘”可以通用,可能是“血流飘杵”——也就是战场上砍杀出来的鲜血在风雨中飘洒到盾牌上,也显得有点和风细雨了。
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腐朽的统治者是不会自动离开历史舞台的。革命是要流血的。何况,牧野之战是两个世仇国家之间的大决战,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斗争,也是两种文化制度的大博弈!尽管周是闪电袭击,商来不及准备,但是这场战争也打得相当惨烈。“血流漂杵”也应该是牧野之战的真实写照。
然而,周本来是商分封的诸侯,甚至是商非常倚重的方伯,两者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是姻亲关系。那么周与商是如何走到了无法调和,只能用这场残酷的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地步的呢?
二、前因后果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首先是两个世仇政权之间的大决战。
要了解周和商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可以先来看看周人的发展历史。
据《史记》记载,五帝之一的帝喾的元配夫人姜原外出时踩到一个野人的足迹怀孕,而生下周的先祖弃。这个记载有点绕,说白了就是周的先祖名叫弃,他是帝喾的元配夫人姜原生的,但他似乎不是帝喾的孩子,而是姜原与一个“野人”的孩子。弃后来又被叫作后稷,被赐予姬姓。后稷非常贤德能干,负责掌管农业,奠定了周这个氏族的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业经济。后稷的后代中,有两代比较贤能的部族首领,一个叫公刘,一个叫古公亶父。特别是古公亶父,为了回避戎狄的侵扰,他带着族人从黄河中游的豳(今陕西省旬邑县西)南迁到渭水之滨、岐山脚下,找到了更加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地方,并且在那里迅速地壮大起来。
《诗经·绵》中就唱道:“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文中的“水浒”是指渭水之滨。因为这里是周人寻找到的生机之地,从此“水浒”一词就成了一个典故,指生机之地。因此后世写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小说取名叫《水浒传》而没有叫《梁山传》,其寓意就可想而知了。
古公亶父对周的进一步兴旺充满了期待,因此,他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直接看中了孙子辈中的人物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事实证明他也没有看错。昌是亶父的小儿子季历的长子,亶父就把国君的位子传给了季历。而亶父的长子太伯和次子虞仲在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以后,就主动离开周去了南方,并且断发文身,自毁形象,以示彻底地离开了周这个邦国,让季历和昌相继继位了。
《史记》对季历的记载非常简单,几乎看不到他的经历和作为。然而《竹书纪年》记载,季历在位的时候曾经帮助商王朝征讨敌国,屡建功勋,却因为影响越来越大而引起了商王文丁的忌惮,后被杀害。文丁杀害季历的理由是说季历杀害了文丁的父亲,也就是商王武乙。
其实,商王武乙的死是个历史悬案。《史记》记载说他死于雷劈,也有人说他死于与神职人员的斗争。武乙死于神职人员之手,这是有一定可能的。本来商是鬼神信仰,神职人员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但是到了商的后期,王(权)与神权之间形成对立,王与神职人员明争暗斗,鬼神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地位。有一个“武乙射天”的故事,说商王武乙让人缝制了一个大皮囊,灌满了兽血挂到榆树上,对人们说这就是天神,然后一箭射中皮囊,鲜血四溢,皮囊也从树上掉了下来。围观的商人看到武乙这样对待神,都惊恐万状。武乙这么做,就是要打击神权势力,所以他与神职人员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也有人猜测说武乙当时也开始疑忌季历做大,武乙率军逼近周,却不明不白地死了,季历也脱不了干系。不管武乙之死的真相如何,商王文丁杀了季历是事实。周与商自此结下了仇恨。
季历死后,周文王昌继位了。商王朝这边,文丁也死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这位帝乙就是后面商纣王的父亲。由于东方夷族对商王朝的威胁太大了,为了缓和与周的矛盾,避免腹背受敌,商王帝乙又将自己的女儿——也有说是妹妹的——嫁给了昌。《周易》当中就有“帝乙归妹”的记载。《诗经·大雅·大明》中也有“文王初载,天作之合”的记载。成语“天作之合”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发明出来以粉饰商周联姻的。
但是好景不长,帝乙死后,帝辛——也就是商纣王继位了。姬昌贤德智慧,周的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崇国的国君崇侯虎就给商纣王进言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史记·周本纪》)意思是说:姬昌不断地做好事积功德,诸侯的心都向着他了,这事儿可是对您不好。纣王就把姬昌囚禁到羑里,现在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边还有一个羑里城的遗址。姬昌的手下一看大事不好,赶紧带着美女和珍宝去贿赂纣王。这纣王一见美女和珍宝,笑逐颜开,就把姬昌给放了,还说出给他进谗言的人是崇侯虎,把崇侯虎也给卖了。这个历史细节与后来项羽在鸿门宴放了刘邦,还出卖了向他告密的曹无伤何其相似。
但是《史记》的这一段记录实在过于简单了。实际上,商纣王这个人很不简单。在日益腐朽没落的商王朝贵族集团当中,他是个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得罪了统治集团内部很多人。历史上为他翻案的人很多,毛泽东就曾评价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史记》上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可见纣王很聪明,也很勇敢。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上,商纣王很可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昏庸。他当时面对的主要威胁来自东夷,之所以没有杀掉周文王,是担心周人反抗,使自己陷入东西两线作战。另外,纣王轻易地就囚禁了周文王,说明这个时候的周还没有足以与商王朝摊牌的资本。所以,符合逻辑的推理应该是:在东夷为主要威胁的情况下,商纣王既不愿意看到周继续做强做大,要对周文王进行敲打和防范,同时也不能彻底与周撕破脸皮,以免导致腹背受敌。而周文王对纣王的心思也一定是心知肚明,但是他对纣王的帝王之术又无可奈何,只能假做臣服,隐忍不发,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商周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表面上是君臣、实际上是仇敌的尴尬局面。仇恨的结,就在这样的猫玩老鼠的博弈中越结越深。
还有个传说说周文王的嫡长子伯邑考在周文王被囚禁的时候,也被商纣王给烹杀了,并且纣王让周文王吃了伯邑考的肉做的羹。但是这个故事的真伪难辨。如果说是真的,那就进一步加深了周对商的仇恨。
周文王回到周以后,更加速了复仇灭商的步伐,但是他还没有完成大业就去世了。他的次子发继位,这就是周武王。
周文王有两个儿子很厉害,一个是武王发,一个是四儿子周公旦。周文王去世后,武王发在四弟周公旦和军师姜子牙(也是周武王的岳父)等人的辅佐之下,继续着先人的宏图大业。今天的考古发现,周人当时学习从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传来的新技术,并且加以改进,制造和运用了先进的战车,使得自身的军事技术有很多地方已经超过了商。
随着实力的增强,周王武开始悄悄寻求灭商的战机。
武王九年(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在文王的墓地为文王举行了祭祀,然后东进到孟津进行阅兵。据说有八百多个诸侯虽然没有接到邀请但闻讯带着军队赶到孟津来会师。诸侯们都说:“可以讨伐纣了。”武王却说:“你们不知道上天的旨意,尚不能伐纣。”于是前来汇合的各国军队又各自撤回了。这一次,周测试了自己的号召力和天下诸侯对商纣王的态度,也进行了一次演习,熟悉了灭商的进军路线。但是武王一定有比那些诸侯们更准确的情报,说明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没有贸然行动。
这个时期,周不断地派间谍到商刺探军情,同时还有从商王朝跑过来的官员密报,让周准确得知商的情形。这一年,商的大军正在东征夷族,都城朝歌形同空城。而且就在这一年,周闹了饥荒,农业没有收成,农夫们也愿意出去作战,去夺取粮食活下去。于是,周武王、姜太公果断决策,武王在即位十年之后,用一场牧野之战终于革了商王朝的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开启了长达近800年的周代。
周的这种战略性的累世经营,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所以今天看到一些西方人惊呼中国“五年计划”厉害的时候,我常常会笑——他们还没看明白,中国共产党的伟业其实也是一个战略性的累世经营的成果。这应该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续。
实际上,周在灭商的时候,相对于商来讲依然还是个小邦,整体实力上比商还有很大差距。那么,小邦周为什么能灭了大邑商呢?难道就是一场战争这么简单吗?
三、天道人心
中国上古史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经过“帝王之别”,进入夏商周三代。
夏王朝大概是在组织先民抗击水患和开展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商王朝依靠先进的青铜技术和发达的商业而兴盛。周则依靠农业文明走向强盛。
从目前已见的出土文物来看,商王朝的青铜器十分壮观,甲骨文的藏量也非常丰富。商的粮食拥有量也应该不低,在保证食用的基础上,还有相当的盈余可以用来酿酒。周武王攻下朝歌之后,从纣王的宫苑里搜出了大量的珍宝玉器。几百年来,商王朝东征西讨,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即便到了周武王战胜商纣王的时候,在这些方面周与商还是不可匹敌的。
然而周就这样以弱胜强,取而代之了。原因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导致商王朝一朝崩溃的原因,是商有根本性的“四败”。
一败于骄奢淫逸——整个贵族阶层腐化堕落,不思进取,纵情于物质享乐和感官刺激。他们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为长夜之饮,这也是成语“酒池肉林”的来历。纵情享乐带来的就是不思进取,一个王朝到了不思进取的地步,也必然要衰落。
二败于信仰崩溃——整个社会失去了凝聚力。商王朝统治者本来是鬼神信仰,他们宣扬上帝,也就是他们自己死去的先王,宣称君权神授。而到了后期,王权与神权对立,王与神职人员明争暗斗,鬼神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地位,贵族们甚至去偷祭神的供品来享用。到这时候他们再宣扬鬼神和上帝,还有谁会跟着信呢?
三败于族群撕裂——王朝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导致族群撕裂。比如,商纣王的亲叔叔比干和箕子都是王朝的高官,因为意见不同或者是权力斗争,比干被杀害,箕子被囚禁。王室成员和纣王的关系非常紧张,甚至很多人都直接参与了给王朝掘墓和拆台。
四败于人民反抗——奴隶和下层百姓不堪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商王朝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很多奴隶还要被杀死了殉葬,惨无人道。大批的奴隶都是商王朝四方征战俘获的,这些人对商王朝怀着国仇家恨,视商朝统治者如仇寇,因而反抗和倒戈。
而反观周呢?在我看来,周虽然总体实力不如商,但它却有关键性的“三胜”。
一胜于天道人心——周人看到了天命与人心的关系,认识到了天命其实是由人心来体会和表达的。于是他们提倡“以德配天”“以德治国”,主观上施展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客观上也顺应人心,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比如,周文王向纣王“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自愿向商纣王奉献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纣王废除残酷的炮烙的刑罚。周因此而大得天下人心。此外,针对商纣王招诱其他小国逃亡的奴隶而为其他小国所怨恨,周文王就定出一条“有亡(奴隶逃亡)荒(大)阅(搜索)”的法律,明确说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他人藏匿,从而大得天下诸侯之心。
由于周重视天道人心,就使得两个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虽然物质上强而精神上没落;一个虽然物质上稍弱而精神文化上光明。两个文明相比较,让天下人看清了道与无道、仁与不仁,分清了光明与黑暗。因而,周与商之间的斗争,又绝不仅仅是两个世仇政权之间的博弈。周革商命,还有着深层次的道义支撑,是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
二胜于视野宏阔——周人的战略显然长于商。在与商的长期博弈中,周早已开始着眼大局,悄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长江、汉水和汝水三个流域,教化那里的蛮夷,称之为南国或召南,逐渐对商王朝形成政治合围之势。文王晚年时,周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到周武王时,又不断地将周的政治中心向东移,逼近商王朝都城朝歌,为最后的决战做好了准备。
三胜于其命维新——周人在哲学思想上也比商人先进。《史记》上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的核心观念就是“变”。周人深刻地认识到: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使得周人既具备了面对困境时的乐观精神,也具备了身处顺境时的忧患意识。而且面对永恒变化的世界,周人给出了积极正确的应变之策,那就是“创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这个意思。而周的创新又绝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更是道的层面的创新,是基于对人心和人性的深刻认知与敬畏以及深刻的忧患意识而进行的创新。
一种新的有利于社会和谐,甚至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与制度就这样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