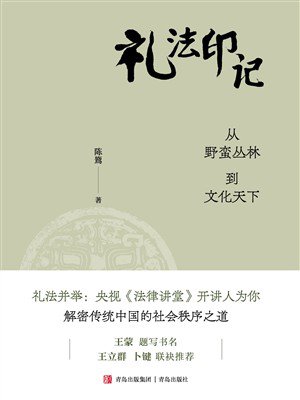第二章
天道人心
《尚书·虞书·大禹谟》中有一段政治名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据说这十六个字是尧把帝位禅让给舜,后来舜又把帝位禅让给禹时,代际之间所做的政治交代。意思是说:人心变化莫测,天道中正但需要细致入微地去察知,执政要精准地把握和坚守天道,最后使人心与天道和合,执中而行,天下方能大治。这句话教导后世帝王,执政需从认识人心、知道“人心惟危”开始,要察知天道并不忘初心、坚守如一,追求人心与天道的合一。在儒家看来,这十六字几乎是圣帝明王对整个后世中国的政治遗言。
武王伐纣,周革殷命,单看最后的战争,从公元前1047年底周联军在孟津会师起兵,到次年二月甲子日牧野一战定乾坤,一场灭国之战、改朝换代之战,历时仅三十余天就结束了。它的速战速决,它的以小博大、以少胜多,都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于这场战争的到来及其结果,估计商王朝统治者完全没有料到,天下邦国也都莫名其妙,就连胜利者周武王和周公旦们恐怕也感到不可思议。尽管周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渴望已久,且已经为之筹划了几代,但他们千筹万算恐怕也没有算到,这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了。
可贵的是,战争的胜利者没有忘乎所以。周人清醒地认识到了牧野之战的胜利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取代商王朝、重塑天下秩序的道路路阻且长。
原因何在?恰在“人心惟危”!
一、夜不能眠的战胜者
牧野之战结束后,周武王占领了商都朝歌,但是商的贵族阶级仍然保存了很强的实力。为了加强对这里的控制,周武王将商的京畿之地分割为邶、鄘、卫三国,将邶国封给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而鄘和卫两国,则分别交给了自己的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来管理。这三国合称为“三监”。当然“三监”还有别的说法,比如说是:管叔监管卫、蔡叔监管鄘、霍叔监管邶,他们从三个方面来监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也就是监视以武庚为代表的商的遗民。
随后,周武王又派兵征讨那些还不臣服于周的商朝诸侯。历史记载说,周迅速征服了99个诸侯国,还有600多个国家望风归顺了。
如此安顿了商都朝歌,招抚了商王朝的诸侯们之后,周武王还师西归,在都城镐京举行了盛大的典礼,正式宣告了周王朝的建立。
周武王完成了改朝换代大业,实现了几代周人的夙愿,他本应该高兴才对。然而,此时此刻的他却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史记·周本纪》记载:
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hé)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xiǎng)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fěi)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bìn)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周武王回到周,晚上却睡不着觉。四弟周公旦来看他,问道:“您为什么睡不着觉呢?”周武王说:“我告诉你啊,因为上天不肯享用殷的祭祀,贤德的人被逐放了,而小人却在朝野得势。上天不保佑殷,我们周才成就了王业。过去上天保佑殷的时候,他们任用了很多有名的贤人,使得殷的事业虽然不太昭显,但也没有很快就灭亡。今天,我们周还没有确定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我哪里有工夫睡觉呢?”
从周武王这段简短的对答中,我们就能看到,他深刻反思了殷商兴衰的原因。关于殷商过去的兴盛,他恳切地指出了其任用贤人的正确。关于殷商的衰败,他先说的是“天不飨殷”,也就是说,上天不肯享用殷的祭祀,而接着把问题落脚在人,就是贤德之人被逐放,小人却在朝野得势。周武王深刻地认识到:殷商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正在于人心的得失。
不仅如此,他还清醒地认识到,周还没有确定得到上天的保佑。用他表述殷商得失的逻辑,实际上他想说的是:周还没有赢得天下人心。这就是周武王夜不能寐的原因。
那应该怎么办呢?
周武王在不眠之夜,深入地思考了对策。他接着对弟弟周公旦说:
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lào lài),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luò ruì)延于伊汭(yī ruì),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
——《史记·周本纪》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周武王是一个多么深谋远虑的人!他认为,要获得上天的保佑,让天下民众都依从天子的朝廷,首先要全面搜捕那些不顺从天命的恶人,让他们跟商纣王一样接受惩罚。就是说周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进行彻底的肃反,把那些绝不顺从的死顽分子全部找出来,彻底清除。他们是新政权最大的危害。
接着他说:“我们还要日夜辛苦操劳,招揽贤人,以安定我们西部的国土。我只有办好各种事情,直到道德教化施达于四方,并且发扬光大。”他明确了认真扎实做好实事的重要性,明确了人才的重要性,明确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表明一定要让天下民众认识到周的仁德,从而以德服人。
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设想,那就是在东边营建一个陪都,以那里为中心,来扼控殷商旧有的势力范围,或许还有更远的东夷,可以说他的这一构想奠定了“中国”的雏形。他说:“从洛水河湾一直延伸到伊水河湾,那一带地势平阔宜居,但没有固守的城池,那里是夏代的居住地。我站在那里,往南边能望到龙门山,往北边能望到太行山(也可能是指衡山),回头能看到黄河,还能遥望到洛水和伊水的两岸,那里离天子的镐京也不太远。”后来周公旦完全按照周武王的设想,建成了东都洛邑,使之成为周王朝掌控天下的战略中心所在,也成为中国古人心中的天下之“中”。出土文物西周青铜器“何尊”上,就铭记了周建造洛邑这件事。其中有一句特别有名的铭文——“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
周武王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夜不成寐地思考的对策,实际就是从三个层次来收拾天下人心巩固政权:
一,对死顽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彻底清除祸患;
二,对天下民众,通过办好实事、任用贤才和思想教化来赢得民心;
三,对各路诸侯,通过营建洛邑,从地理、心理、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个角度来造势,夯实政权,予以镇服。
然而,收服人心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夺取了政权的周武王和周公旦,又面临着怎样的局面呢?
二、人心惟危
周武王深邃而宏大的思考,为周王朝擘画了政治蓝图和政治路线,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然而,收拾人心谈何容易?夜不能寐、日夜操劳,终于让周武王积劳成疾。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在灭亡商朝的第二年,天下还没有安定,周武王就生病了,感觉很不好,群臣都很害怕。
周公旦非常担忧社稷。他亲自去向先王们祷告。史官替他宣读的祷告词上说:
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
——《史记·鲁周公世家》
意思是说:“你们的长孙武王发积劳成疾,如果你们在天有灵,就让我来顶替武王发承受病魔吧。我比武王灵巧能干,多才多艺,能来天上侍奉鬼神。而武王发刚刚被上天授命,葆有天下,天下百姓没有不敬畏他的。因而他在世上,就能安定你们的子孙。请不要毁掉了上天赐给周的天命,只有这样,先王你们的灵魂,也才能永远地有所归依。”
历史记载说,周公祷告之后,占卜的结果非常好。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好了。
但是过了不久,武王还是死了。
作为战神和政治领袖,周武王的死给刚刚改朝换代、尚没有安定的天下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王公贵族、天下诸侯,各怀心思,觊觎政权之心俟机萌发了。周王朝刚刚获得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思乱就在眼前。
问题首先出现在周王室的内部。《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武王死了,儿子成王继位。这个时候成王还年幼。因为担心天下反叛,周公旦就暂时摄政,代行王权。管叔和一群众兄弟,首先不干了,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怀疑周公要抢班夺权。
这里面领头的人,很可能就是管叔。周文王的儿子当中,长子伯邑考早亡,武王发排行老二,管叔鲜排行老三,周公旦是老四。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古代传位原则,管叔一定觉得接替武王位置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老四周公旦。至于其他的兄弟,是要因此而起来维护管叔还是各有想法,就不得而知了。
“人心惟危”,这时就充分显现了。众兄弟觊觎权力,钩心斗角。面对危局,不肖之子考虑的不是顾全大局、齐心协力地来维护这个岌岌可危的王朝政权,而是对贤能者造谣中伤,想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还有商王朝的贵族和遗民们,他们本来就没有从心底顺服周朝,看到武王一死、周王室内讧,就觉得有机可乘。于是,他们迅速地聚集到纣王之子武庚的旗下,开始了复辟叛乱。
原来与周像友军一样长期与商王朝势不两立的世仇淮夷部族,此刻也举起了反周的大旗。大概他们觉得,多年以来,正是他们在与商王朝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斗争,牧野之战的时候也正是他们吸引了商军的主力,突然间却让周人乘虚而入获取了战果,实在心有不甘。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此刻的淮夷,居然又与曾经的敌人武庚站到了一起。
更让周王室难以接受的是,本来派去监视武庚和商朝遗民的管叔、蔡叔,这个时候居然也与武庚联合起来,和淮夷一起发动了叛乱。而其他诸侯,许多则处于观望之中,没有几家是省油的灯。
周革殷命,宣称天命归周,这是周人自己的说法,天下人还没有认同——至少武庚所代表的商朝遗民和淮夷这两大势力就很不认同,而周家的管叔、蔡叔之流,也来挖自家的墙角。天下秩序未定,各方面的人都从牧野之战的惊讶和蒙圈中醒来了,大家都定下神来,要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捞回或者是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利益。
人心惟危,内忧外患,叛乱频起,给刚刚建立的周王朝提出了新的历史难题。
三、平叛与吐哺
周公旦摄政,他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沉稳与果敢,成为周王朝政权的中流砥柱。
他首先从王朝核心成员的思想工作做起,与他们“谈心”。《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周公先去找王朝的核心成员太公望——也就是灭商的大功臣姜子牙——和召公奭(shì),跟他们交心。他说,自己之所以不避嫌而来代理国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王室,那样就没法向先王们交代了。先王们为天下之业忧劳了很久,现在刚刚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又年幼,自己是为了稳定周朝的大业才这样做的。
周公旦的恳切,说服了王朝的核心官员们。于是,周公旦获得了成王的命令,兴师平叛。
但是平叛东征必然要大动干戈,王朝内部、各路诸侯和各级官员的思想并不统一,甚至很多人都反对。大家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内部还不安定,出兵困难重重;二是要讨伐的反叛者管叔和蔡叔是王室的重要成员,是很多诸侯的长辈。于是周公又发布了晓喻各路诸侯及官员们的《大诰》,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
《大诰》是以周成王的名义发布的,说了三个方面的意思:
其一,王朝正面临着灾难,可能比诸侯和官员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殷商遗民想要复辟,天下很多诸侯都响应他们。管叔和蔡叔还助纣为虐,领头反叛。这怎么了得啊?如果不面对和及时处理,将可能让先王开创的基业毁于一旦。大家要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继承先王遗志,巩固王朝大业;
其二,周公用周文王留下的龟甲进行了占卜,得到的结果是吉兆,说明上天和先王也肯定了平叛的正确性,说明平叛是可行的。在那样一个迷信上天、迷信先王、迷信占卜的时代,这样的做法能够极大地坚定人们的信心;
其三,种田要除去杂草,治国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对于靠农业立国兴邦的周王朝上下,也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这篇《大诰》凝聚了周王朝各路诸侯和各级官员的人心,发挥了很好的战争动员作用。
于是,平叛东征开始了。战争打得很惨烈,整整持续了三年。
周公首先平定了“三监”的叛乱,诛杀了管叔和武庚,流放了蔡叔,再一次镇服了殷商的遗民。然后,他把周武王同父同母的小弟弟康叔封在卫国,以震慑商民。他还把商纣王的大哥、主动投降了周的微子启封到了宋国,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让他带去一些商的贵族,奉行殷商的祭祀。这样,就进一步把商的贵族和平民进行了分割。
这个微子启在商王朝影响很大。他是商纣王帝辛的庶兄,他们同父同母的兄弟一共有三个,微子启是长兄,中衍是老二,商纣王帝辛最小。微子启的母亲生下微子启和中衍的时侯身份还是妾,后来成了商王帝乙的正妻,又生了个小儿子。父母本来想立长子子启为太子,但是太史依据法典认为,应该首先考虑立正妻的儿子做太子。商王的继承人就没有选择长子子启,而是选择了嫡子帝辛也就是商纣王。这时周公利用微子启的影响力,让他带着一些商的贵族去到宋国,并奉行殷商的祭祀,也是对殷商遗民的一个安抚。
平定武庚和管蔡叛乱之后,周公乘胜东进,平定了淮夷及其东部一些地区,一举灭掉了东部反叛闹得很凶的奄国(今山东省曲阜市一带),还有其他五十多个国家,用三年时间彻底完成了平叛。天下诸侯都归顺了周王朝。当初武王克商,只是打碎了商王朝的核心,经过周公东征,周才彻底扫清了殷商的外围势力,不仅如此,还荡平了商朝也未曾征服的东夷。
东征的战果来之不易,战斗极其残酷激烈。《诗经·豳风》中记录了东征战士们的心情: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都砍出了缺口,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已是幸运了。他们思念家乡,期待解甲归田。
但这场征战是值得的。东征以后,周王朝再也不是征战之前的那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了。周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一个西起六盘山、东到大海(山东半岛)、南达淮河及长江中游、北至燕山山脉的泱泱“大国”,准确地说是一个泱泱大王朝了。
平叛和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落实周武王当年的宏大构想,经过占卜,周公在成王五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发布了起建洛邑的命令。这一天,与牧野之战的那天一样,也是个甲子日。
周对洛邑的建设进行了认真规划。他们在洛水以北、瀍水的东西两边各筑起一座城池,合称为洛邑。西面的那座城池是周天子的王城,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考宫、路寝、明堂等这“五宫”。东面的一座叫成周,周把殷商遗民中的一些顽固分子——也称为顽民——移居到这里,进行集中监管和教化。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珍藏着一件西周的青铜器,叫作何尊。何尊上面有122个字的铭文,里面就记载着周成王五年周公旦营建成周洛邑这件事情。其中有一句特别有名的铭文——“宅兹中国”,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两个字最早的文物见证。
至此,洛阳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周则完成了周武王居天下之“中”而掌控天下的设想。
当年,战胜商纣王的周武王忧心忡忡,夜不能寐。那么此刻,完成了荡平天下、掌控天下大业的周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曾经告诫将代表自己前往鲁国封地的儿子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意思是说:“我作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对天下人而言,地位也不低了。而我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握着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停下来,以便及时地接待贤能的士人,就是这样,我还担心失去天下贤士。你到了鲁国一定要谨慎,不可以凭着国家的势力傲慢地对待他人。”可见,赢得天下人心是周公始终致力的事情。
我想,无论在随武王伐纣的征战中,还是在平定叛乱的东征之战中,还是战争之余的政务工作中,周公旦与周武王一样,他从兄弟们的钩心斗角、殷商遗民的伺机复辟、东方夷族的不满,以及王朝内部上下思想不一当中,都深刻地认识到了“人心惟危”,认识到了赢得人心的重要性。
而面对刚刚打下来的天下,首先要安抚、镇服和赢得的,就是王朝功臣、王室贵胄和前朝贵族们的人心。对这些人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好王室与他们的关系,从而确保天下的安定,这是王朝赢得天下人心需要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