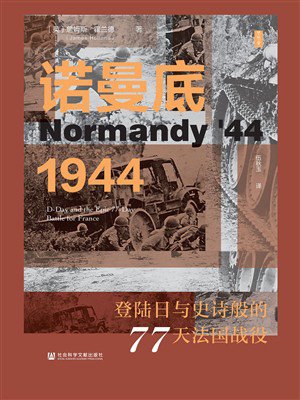第7章
空中力量
“敌人持续对塞纳河、瓦兹河上的桥梁发起集中空袭,还不时轰炸了埃涅河上的桥梁,”德国B集团军群的参谋在每周情况报告中写道,“空袭还集中在敦刻尔克和迪耶普之间以及科唐坦北部的海岸防御工事上。盟军继续破坏铁路运输,对编组站……和机车发动了袭击。”
空军上将泰德和盟军的空军指挥官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过去九个星期的军事行动感到满意。单是针对法国的袭击目标,他们就投下了大约19.7万吨炸弹,相比之下,在整整七个月的闪电战中,纳粹德国空军在伦敦只投下了18000吨炸弹。尽管盟军对运输计划和石油计划争论不已,但事实上,盟军空军已经利用重型战略部队、中型战术轰炸机和战斗机等军队对众多不同的目标进行了打击,包括编组站、石油工厂、纳粹德国空军的基地、沿海雷达站、V-1和V-2飞弹的发射指挥站以及沿海炮台。盟军飞机的飞行次数超过了20多万架次。6月3日,纳粹德国空军在一份报告中称:“巴黎的长途交通已经被有计划地切断了,塞纳河下游最重要的桥梁也相继遭到摧毁。”报告继续说,只有尽最大努力,才能让军事交通和其他基本交通保持畅通。“目前,德军几乎不可能通过铁路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而且按照目前的攻击强度,情况仍将如此。”一旦登陆行动开始,盟军的进攻强度肯定不会减弱。相反,盟军将进行更加猛烈的轰炸,特别是在盟军空军无须再对登陆地点保密的时候。
不过,凡事都有代价。1944年3月,712名法国平民死于盟军的空袭;4月有5144人,5月有9893人——虽然没有一些人担心的那么多,但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悲惨数字。从4月1日到6月5日,盟军有12000名机组人员死亡和失踪,损失了大约2000架飞机。毫无疑问,战略空军的损失最为惨重——美国第8航空队损失了763架轰炸机,英国王家空军的轰炸机司令部损失了523架。一些人对自己的生存概率越来越抱有一种宿命论的态度,其中就有杜鲁门·“施密提”·史密斯(Truman “Smitty” Smith)中尉。他是第550轰炸机中队的B-17飞行堡垒轰炸机的副驾驶员。第550轰炸机中队隶属于第385轰炸机大队,这个大队驻扎在大阿什菲尔德(Great Ashfield),位于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的萨福克(Suffolk)镇以东。
在愚人节那天,史密斯和欧内斯特·“穆恩”·鲍曼(Ernest “Moon” Baumann)中尉的其余机组成员抵达了大阿什菲尔德,他们都希望这个日子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史密斯认为,这10名机组成员是一个兼容并蓄、物以类聚的群体,他希望这个群体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各自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为生存战斗而发挥的力量之和。史密斯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庞卡城,他一直都对飞行很感兴趣。在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攒下了4美元,并把钱花在了第一节飞行课上。甚至在16岁时,他就已经能够单独飞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经常去庞卡城的空军基地,感受那里的气氛,打扫飞机,坐在飞机的座椅上。后来,在1941年当地成立民间航空巡逻队时,他设法提供帮助、排忧解难。第二年,他高中毕业,之后,他很自然地决定当一名空军。他赢得了梦寐以求的职位,开始训练,并于1943年10月实现了抱负。而后,他被任命为B-25中型轰炸机的“临时”副驾驶,随时待命加入机组。之后,他被派往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Tampa),加入了“穆恩”·鲍曼的机组。他们在佛罗里达募集了一架崭新的堡垒轰炸机,并驾驶它飞越大西洋。虽然B-17看起来要比B-25大得多,但史密斯很快就适应了,这主要是因为鲍曼很宽容。“事实上,”史密斯说,“整个机组都很随意,很有幽默感,是我在服役期间遇到的最不像军人的队伍。”
不管怎样,他们在最初的10次任务中幸存下来,然后又挺过了两次,现在迎来了他们的第13次任务,也就是5月20日对位于亚琛(Aachen)的编组站发动袭击。史密斯确信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任务:在他们看来,13这个数字似乎非常不吉利。一些机组成员把13称为“12-B”,但对史密斯来说,这没有任何用处。他写道:“我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感觉,第13次任务真的是我的最后一次任务了。这迟早会发生。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这个职业就是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据我所知,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毕业生来接班了,这就是原因所在。”他试图表现出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至少他去过伦敦,也风流快活过了——但在这次任务之前,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自以为注定会失败的信念。那天早上,他甚至拒绝起床。“我不去”,他对其他人说。之后,他非常不情愿地改变了主意。
很多时候,预言最终都变成了现实,但史密斯和其他机组成员成功返回,并在6月2日前连续完成了4项任务:他们对位于德国西部科尼格斯博恩(Königsborn)的铁路编组站发动袭击;5月29日,对莱比锡飞机工厂发动空袭,这是一场针对V-1飞弹基地的行动,也就是所谓的“无球(NO BALL)”行动;30日,袭击了法国的瓦滕斯特拉古(Watten-Stracourt);31日,对位于德国鲁尔山谷的哈姆编组站发动袭击。“这是连续执行的第4个任务,”史密斯说,“但这种单调的活动越来越不合我的胃口。”他算出每次任务能拿到10.67美元,并发现美国陆军航空军的报酬超过了理应得到的回报。无论如何,机组人员再次成功返回,这意味着,他只需要再执行7次任务,便可以结束战斗之旅了。两天后,他们开始了第19次任务,目标是袭击更多的编组站,这次是埃奎赫恩(Équihen),它位于法国北部城市布洛涅的南边。805架B-17和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中的一架击中了加来海峡,包括“无球”行动的64个目标和编组站。这是一次势不可挡、彻底无情的袭击。
为了达到规定的任务数量,美国第9航空队中型轰炸机的机组成员面临着非常紧张的态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需要更频繁地飞行,执行更加短程的任务。例如,第391轰炸机大队在5月27日执行了2次飞行任务,28日又执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4次飞行任务。他们必须在登陆日前达到目标,时间是如此紧迫,以至于他们的飞行架次将会达到一个非常极端的水平。
与第391轰炸机大队一起飞行的还有乔·博伊兰(Joe Boylan)中尉和他的机组成员。博伊兰22岁,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Waterbury)镇。他的童年过得非常艰辛:家里经济拮据,母亲在他12岁时死于癌症。挣扎度日的父亲开始酗酒。尽管如此,他还是明智地鼓励儿子进入纽约的一所好高中,这让博伊兰能够参加并通过空军飞行员培训考试。长期以来,年幼的乔都对这个考试寄予厚望。后来,他表现出色,并希望能够驾驶类似P-38的多引擎战斗机,他曾被派去接受关于多引擎战斗机的训练。最终,他工作称职,并被授予了一项任务,他的职责是向第573轰炸机中队进行报告。第573轰炸机中队隶属于第391轰炸机大队,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麦克迪尔机场集结,他将在那里驾驶B-26掠夺者轰炸机。
博伊兰听说过一些关于掠夺者轰炸机的不好的事情,这种轰炸机在起飞或着陆时发生事故的概率很高,因此有了“寡妇制造者”的名声。然而,到了1944年,这些早期问题大多得到了解决,它已经成了一种高度可靠、强大的中型轰炸机,时速达到了近300英里,而且非常敏捷。与B-17不同的是,它有一个三轮车起落架,这样一来,飞行员便可以在地面上获得很好的能见度;而且事实证明,只要启动正确,它就很容易起飞。博伊兰说:“一旦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学会了驾驶它,那么它就很难被击落。”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B-26掠夺者轰炸机大队的伤亡率是非常低的。到达英国后,博伊兰听说了重型轰炸机机组的损失,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在第9航空队驾驶B-26掠夺者轰炸机。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免于不幸,正如博伊兰在5月28日亲眼见到的那样,那是他离开伦敦一段时间后的第一次任务。那天早上,他们的目标是里勒(Risle)河上的一座桥梁。里勒河的流淌方向大致与勒阿弗尔东南部的塞纳河平行。天气不太好,所以引导员为他们引路。尽管盟军曾警告他们可能会遇到高射炮,但散布在法国村庄的高射炮一般没有安装枪炮瞄准雷达,所以准确度不是很高。博伊兰和机组的6名成员满心期待着这将是一次“容易执行的常规飞行任务”。
石桥位于里勒河畔格洛斯莱(Grosley-sur-Risle)的一个小村庄。31架掠夺者轰炸机将负责袭击这个目标,其中的大多数都携带一枚1000磅的炸弹。在平安飞越海岸线后,他们继续前进,云层逐渐变薄,他们可以看到诺曼底东部乡村的一块块田地。在离目标不远的地方,高射炮开始攻击他们,炮弹碎片在他们的周围噼啪作响,天空中弥漫着烟雾。博伊兰的编队在高空飞行,他鸟瞰着诺曼底的地形和他下面的飞机。
“我们的一架飞机被击中了!”机首的投弹手比利·罗斯(Billy Rose)中尉喊道。
“谁驾驶的?”博伊兰问道。
罗斯不确定是谁驾驶的,但那架飞机被直接击中,垂直落下,引擎也在着火。接着,右舷机翼脱落了。罗斯数了数降落伞。“有一个降落伞!又有一个!”
他们继续飞行,在引导员发出的照明弹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桥梁,并按计划击中了它。目标周围根本没有高射炮。
在安全返回位于麦奇格林(Matching Green)——坐落在埃塞克斯郡的哈洛附近——的基地后,他们才得知被击落的飞机是鲍勃·古德森(Bob Goodson)中尉驾驶的。听到这个消息时,博伊兰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副驾驶鲍勃·克拉克(Bob Clark)和投弹手罗斯·泰勒(Ross Taylor)都是他的好朋友。几天前,他们还一起在伦敦度假。
*
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德国的雷达站。大量的情报组织(包括噪音调查局和通讯研究机构等专业组织)合作绘制了一幅图像,清晰显示了加来和瑟堡之间的92个雷达装置。当远程雷达遭到轰炸时,其中的一些雷达装置也会受到干扰。针对这些雷达的行动从5月10日开始,就在四年前的这一天,德国对西欧发起进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空袭不是由轰炸机部队实施的,而是由对地进攻的单引擎飞机执行,这些飞机装备有炸弹、加农炮和火箭弹。这是因为盟军认为摧毁雷达装置的最佳方法是从较低的水平进行倾斜打击——这只能使用前射导弹来实现。
最适合执行这项任务的盟军机器是“霍克台风”,这是一种飞行时速超过400英里的强力飞机,装备有4门20毫米的加农炮,还能携带两枚500磅的炸弹。它还可以在每个机翼下面配备4枚RP-3空对地火箭弹。它的翼幅超过41英尺,配备有24活塞、2200马力的纳皮尔军刀发动机。发动机罩下有一个巨大的、异常吓人的球根状进气口,看起来就像一头愤怒的西班牙公牛要冲上去一样。盟军最初打算用“霍克台风”取代“飓风”。“霍克台风”的样子就是实际看到的样子:一架巨大、凶狠、强大的对地攻击战斗机,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置信。
康宁厄姆的第2战术空军有18个台风战斗机中队,其中包括第123联队的第609中队。这是战前驻扎在约克郡西区的一个辅助中队——他们被称为“周末飞行员”——大多数成员都是年轻富有的绅士。但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们已经发展成为一支高度专业、多国人员参与的队伍。它是第一个在不列颠战役中取得100场胜利的中队,即便在那时,它就已经吸引了美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到了1944年,它成了比利时飞行员的向往之地。队伍中还有三名新西兰人、三名加拿大人、一名阿根廷人,以及一名来自柏林的德国犹太人克劳斯·“肯”·亚当(Klaus “Ken” Adam)。亚当是一名空军中士。1934年,他和家人一起逃离了德国。
他们在关键时刻逃走。亚当的父亲曾在首都经营一家高档体育用品商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是一名被授予勋章的骑兵军官。由于拒绝接受纳粹的威胁,亚当先生在1933年被捕,他感到非常震惊。通过关系,他在48小时后获释,但他在巴黎学习的长子彼得(Peter)敦促家人离开。“他生活在德国以外的国家,”亚当说,“那里的媒体对纳粹怀有敌意,他能看到发生了什么。”
先是孩子们被送到英国,然后父母也跟着去了。克劳斯最初在蒙哥马利的母校圣保罗学校上学,后来去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建筑。那个时候,他努力融入英国,接纳英国人的习性,尽管他的德国口音导致他把自己的名字“克劳斯”发成了“肯”。他也非常渴望在战争到来时尽自己的一份力,并多次试图加入英国王家空军。1941年末,他终于被英国王家空军录取,并在加拿大接受训练。1943年10月,他被派往第609中队。然而,没有人叫他“肯”;在中队里,人们总叫他“海涅”
 ,他不得不接受这个叫法。虽然人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但他仍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并被弥漫在中队里的同志情谊和团队精神所打动。新飞行员受到热烈欢迎和精心栽培,他们的战斗技能得到了充分磨炼。
,他不得不接受这个叫法。虽然人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但他仍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并被弥漫在中队里的同志情谊和团队精神所打动。新飞行员受到热烈欢迎和精心栽培,他们的战斗技能得到了充分磨炼。
到了1944年春,亚当已经成为第609中队的正式成员。该中队一直作为战斗机中队独立作战。但是,到了2月底,他们重新接受训练,成了一支火箭弹射击部队。随后,他们被分配到第84大队的第123联队,隶属于第2战术空军。现在,他们驻扎在朴次茅斯附近的索尼岛(Thorney Island),成了空中炮兵,任务是对法国北部的目标进行常规的地面攻击。5月初,一连串的任务接踵而至:5月2日,他们袭击了瑟堡附近的一座公路桥;第二天,该中队向亚眠附近的铁路棚发射了近100枚火箭弹。5月7日,他们的目标是航运运河及另一座桥梁。
四天后,也就是5月11日,他们开始了摧毁敌人雷达的行动,袭击了勒阿弗尔附近位于费康(Fécamp)的雷达站。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在他们实施空袭前,美国的轰炸机中队以及其他台风战斗机中队已经进行了打击。“我们是最后一个实施空袭的,”亚当说,“当台风战斗机进入目标领域时,德军的高射炮对准了我们。”此外,他们还奉命从内陆和海上进行攻击。第609中队的前四架飞机排成纵队,一架接一架进行攻击;有两架被迅速击落,第三架遭到重创。亚当飞在后面,惊恐地看着空军上尉伍德的台风战斗机突然起火,撞到了空军中士基斯·亚当斯(Keith Adams)的台风战斗机,把后者的左翼撕出一条长达2.6英尺的裂口,然后坠向地面。在意识到它们成了德军坐待攻击的目标后,亚当立刻偏离了纵向编队,从不同的角度发起攻击。这个决定可能救了他的命。亚当在航空日志中写道:“朱尼尔·索斯曼(Junior Soesman)被击中,然后跳伞了,但他没有爬上救生艇。伍迪也被击中了。他的飞机着了火,撞上了亚当斯的飞机,然后在房子上坠毁爆炸。这该死的运气。”正如亚当记录的那样,八架飞机损失了三架,还有两名飞行员丧生,“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十二天后,他们袭击了诺曼底海岸和三个雷达站:佩斯角峰雷达站、迪斯戴尔芬克(Distelfink)雷达站——它位于杜夫尔,是诺曼底海岸最大的雷达基地——和位于勒阿弗尔北部的圣瓦莱里(Saint-Valéry)雷达站。第二天,他们袭击了位于阿格角(Cap de la Hague)的雷达站,阿格角在科唐坦半岛的西北端。执行这次袭击任务的只有四个人,亚当是其中的一员。“他们非常完美地轰炸了目标”,这是中队记录簿上的评价。
台风战斗机的确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但到了6月3日,盟军认为,战略空军也应该参与打击关键设施。那天的晚些时候,以及在6月4日和5日,重型轰炸机炸毁了法国北部海岸的雷达基地,包括迪斯戴尔芬克雷达站。截至登陆日,沿海的92个雷达站中有76个停运,包括安装了特别精确的Mammut型雷达和Wassermann型雷达的雷达站。在计划的登陆前线沿岸,没有一个雷达站还在工作。此外,盟军还执行了干扰措施,这导致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整个德国雷达系统的工作效率只有5%。盟军的空中力量和无线电技术还掐灭了德国的许多防御照明装置。
*
在登陆前的最后几天,相互矛盾的情报和解释困扰着德国守军。无情的轰炸、低空扫射和头顶上方航空发动机的轰鸣声让他们遭受了损失,而恶劣的天气也让他们无法对盟军的意图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德国在西部设立了非常少的气象站,因此,虽然天气预报员从大西洋沿岸和北极圈收集了大量气象资料,但他们从大西洋获得的报告比盟军的还要少。不过,他们已经观察到了横扫英国并向欧洲大陆移动的低锋面,而且在6月的第一周,天气似乎非常不稳定、变幻莫测。马克斯将军也反复研究了盟军以前的登陆行动,意识到月亮和潮汐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至关重要。此时,他估计,下一次月亮和潮汐都满足登陆要求的时间是6月20日前后。根据马克斯的天气趋势报告,正在刮起的风、月亮和潮汐都表明盟军至少要在两周后才会登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埃尔温·隆美尔元帅觉得可以在6月4日星期日离开拉罗什盖恩,亲自到贝格霍夫去见希特勒,恳求再派两个装甲师到法国,以及再次请求希特勒向他授予装甲师的战术控制权。他仍然相信德国可以阻止盟军;不过,他也完全相信,只有当装甲师在诺曼底和加来海峡之间的前线附近集结时,才能阻止盟军,尽管他仍然预感到盟军将在第十五集团军驻守的区域登陆,也就是从塞纳河河口到加来海峡、比利时及荷兰海岸的地区。要是他没有直接控制权——那么他就无法迅速、果断、自由地调动装甲部队——他担心德军很快就会失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促使隆美尔在此时动身:在去贝格霍夫的途中,他可以回到自己位于赫尔林根(Herrlingen)的家,就在乌尔姆(Ulm)附近,6月6日星期二是他心爱的妻子露西的50岁生日。他甚至还在前一天去巴黎给她买了一双新鞋。
然而,在其他地方,不同的情报组织接收到了不同的讯号。6月1日,一名法国的游击队指挥官被第352步兵师抓获。在审讯期间,他告诉他们,盟军随时都有可能登陆。抵抗组织的成员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但他们一直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警报。对克莱斯将军来说,这足以让全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但现在是1944年,而不是1940年,没有上级的授权,他不能这么做。马克斯将军也不能这样做,他同意克莱斯的看法,认为全面戒备是最明智的做法。然而,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克莱斯能够进行戒备,是因为德军在那一周安排了军事演习。他让自己的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要是上级问起来,他就说他们正在进行演习,这是本周演习活动的一部分。结果,6月5日星期一,第352步兵师成了诺曼底唯一一个全面戒备的部队。
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德国人真正了解盟军的意图。多亏了一位在土耳其的德国间谍艾利萨·巴兹纳(Elyesa Bazna)——又名“西塞罗(Cicero)”,他是英国驻安卡拉大使的贴身男仆——他们才知道登陆行动的代号是“霸王行动”,但这没有什么用。5月27日,希特勒自信地告诉日本大使,盟军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他们在挪威、丹麦、法国西南部和法国地中海实施了声东击西的行动;之后,他们将在诺曼底或布列塔尼建立一个桥头堡,然后穿过加来海峡建立真正的第二前线。当然,这只是胡扯。希特勒是在两头下注,给自己留条后路,这表现出他对军事计划和行动的无知。毕竟,盟军怎么可能想到发起诸如此类的两栖作战行动呢?
6月5日星期一下午,西线总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情报汇总,情报表明最有可能的登陆地点是荷兰的斯海尔德河河口(Scheldt Estuary)和诺曼底之间的某个地方。报告说:“敌人试图在这个地区的哪个地方登陆,目前还不清楚。”报告总结道:“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登陆。”
事实上,在拉罗什盖恩,没有人为即将到来的登陆作好了准备。隆美尔不在的时候,由汉斯·斯派达尔将军负责。海军上将鲁格冒着雨,开车去视察西线海军集团军群,并狠狠地训斥了他们一顿。当时位于布列塔尼的第2扫雷艇舰队被派往勒阿弗尔,途中遭到盟军空军的猛烈攻击,除一艘外,其他的都被炸毁。在鲁格看来,扫雷艇的遭遇让人无法理解,因为其中的很多舰艇都是S艇——速度非常快的鱼雷艇——和机动扫雷艇,它们都是低轮廓的小型船只。此外,它们都是木制的,不太容易被英国雷达探测到。
在严厉地训斥了他们后,鲁格回到拉罗什盖恩吃晚餐。在鲁格看来,吃晚餐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斯派达尔还邀请了他的姐夫霍斯特(Horst)医生和作家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鲁格不知道的是,他们都是谋反者,正在密谋推翻希特勒和这个政权。斯派达尔接到具体指示,试图招揽隆美尔,尽管到目前为止进展还不太顺利。身体康复后的隆美尔似乎又一次被元首俘虏了,而且充满了斗志;5月13日,他甚至要求希特勒尽早使用V-1飞弹对英国发动攻势,以破坏盟军的登陆计划。即将到来的战斗,是他一心想要打赢的一场战役。
事实上,荣格甚至起草了一份和平宣言,一旦希特勒政权被消灭,他们就会大规模发行这份宣言。它宣称,他们信仰的是一个统一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在这里,民主、宽容和社会正义的理念将被放到最前面。然而,他们没有在餐桌上讨论这些事情,尽管当隆美尔不在场的时候,他们总会开玩笑地说希特勒是“来自贝格霍夫的混蛋”。鲁格认为大家的讨论“非常活跃”。他们喝了很多酒。
他们不知道,登陆舰队已经穿过了英吉利海峡,当这伙人在午夜散去时,盟军近25000名空降兵中的第一支队伍已经准备好登陆法国。
这个时刻终于来了。那是1944年6月6日星期二,诺曼底登陆日。

美国第18步兵团和第115步兵团的登陆艇正在接近奥马哈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