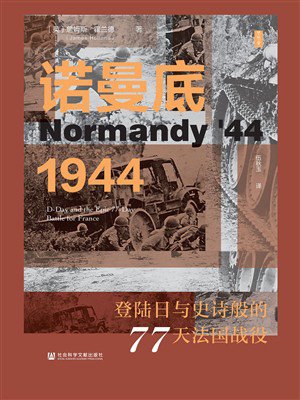第9章
登陆日:最初的几个小时
6月5日晚上9点15分,在位于蓬托德梅尔的比弗莱瑞城堡的一间后屋里,罗伯特·勒布朗和他最信任的苏尔库夫游击队的五名中尉再次聚集在一台收音机的周围。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他们听到了一条消息,“战斗的时刻即将来临”,这是他们事先说好的暗号,表明他们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他们把音量调得很低,此刻轮到这个小组的第2分队的队长勒内(René)来听。他弯着腰,把耳朵紧贴在收音机上。
“开始行动吧!”他突然叫了起来,“他们说,‘骰子在垫子上’。”
勒布朗感到自己的心几乎要跳起来了。是这样的吗?他们听到的消息应该是“骰子被扔在垫子上”。这个消息是否正确?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之前说好的消息?又或者这是一个圈套?他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分钟。不过,这群人中还有其他人在收听其他电台。晚上10点,另一个成员贝斯勒(Beslier)出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浑身大汗淋漓。他也听到了这个消息,而且还听到了下一条消息,那是登陆的讯号:“Il fait chaud en Suez”(苏伊士很热)。勒布朗仍然心存疑虑,这真的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时刻吗?这时,勒菲弗尔(Lefèvre)夫人急匆匆地走进来,证实她也听到了这两则消息。
“这一次,我不再犹豫,”勒布朗在日记中写道,“我等了这么久的时刻,我的兄弟们盼了15个月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登陆!!”他环顾四周,看到部下的眼睛里洋溢着喜悦。之后,他命令他们立刻收拾行李和装备。勒布朗还对部下发布了其他命令。阿拉索前往鲁托村去接保罗,赛朋和贝左要把他们在杀死维奥莱特·莫里斯后藏在附近农场的雪铁龙汽车带回拉皮尔维戴尔(La Pilvédière)——这是他们在几英里外的劳奈酒庄(Château de Launay)备好的总部,那天晚上,盟军将在那里空投补给。通常情况下,如果他们分散开来,那么他们会更加安全,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勒布朗需要他的部下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勒布朗还发出了警报信息:最迟要在两个小时内告知所有分队的指挥官时间到了,应该让士兵们作好准备。另一个叫普罗斯珀的士兵负责征购手推车和货车,罗杰负责征购卡车,并拜访杂货商博斯克特,以便获取食物。
正如勒布朗预料的那样,这一切花了几个小时,但到了午夜,他们差不多准备就绪。贝斯勒奉命切断了电话线,现在,是时候攻击当地的战地宪兵(也就是德国国防军的军事警察)了。“我充分利用了货车到来前的几分钟,”勒布朗潦草地写道,“去和我的妻子道别。我亲吻了我的孩子。”他非常担心小女儿克劳丁(Claudine),因为她正在发烧,但职责在召唤着他。那天晚上,他不得不参加战斗,去为法国而战。
*
与此同时,滑翔机飞行在大约6000英尺的高空,它们搭载着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第2营的士兵,正在向诺曼底海岸靠近。按照英国的双重夏令时
 计算,那时是午夜刚过几分钟。在第一架滑翔机“粉笔91”的驾驶舱里,飞行员吉姆·沃尔沃克(Jim Wallwork)和副驾驶员约翰·安斯沃斯(John Ainsworth)正在作准备。
计算,那时是午夜刚过几分钟。在第一架滑翔机“粉笔91”的驾驶舱里,飞行员吉姆·沃尔沃克(Jim Wallwork)和副驾驶员约翰·安斯沃斯(John Ainsworth)正在作准备。
沃尔沃克对安斯沃思说:“离解开牵引绳
 还有2分钟。”之后,从牵引他们的哈利法克斯牵引机那里,他得到了风速、高度和航向的详细信息。
还有2分钟。”之后,从牵引他们的哈利法克斯牵引机那里,他得到了风速、高度和航向的详细信息。
“准备解开牵引绳!”他向身后的人喊道。紧接着,霍华德少校让士兵们停止讲话和唱歌,之后传来“砰”的一声,牵引绳被解开了,滑翔机稍稍摇晃了一下,然后陡然下降,舱内鸦雀无声。滑翔机在大约1000英尺的高度开始平稳飞行,坐在霍华德旁边的排长“登”·布拉里奇中尉解开了安全带,把装备递给了霍华德少校,然后小心翼翼地倾身向前,打开了舱门。于是,舱门便升到了顶部。他身后的另一个士兵也做了同样的举动。当空气呼啸着穿过木制的霍莎滑翔机时,士兵们可以看到法国的风景从他们的脚下掠过,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安心的熟悉感。凉爽的空气中弥漫着夜间乡村的清香,下面的一道银光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航线上。
突然一个右转弯,接着又是一个,霍华德喊道:“手挽手!”于是,他们双手交叉在胸前,两只手分别抓住左右两边的战友的手,这是在相互鼓劲。就是这样。这是让人心跳停止的时刻,但随后,丹尼斯·爱德华兹感觉到一阵轻微的抖动和颠簸,之后是一个更响亮的嘎吱声,滑翔机稍稍反弹了一下,然后再次着陆,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颠簸着快速向前行驶,不时摩擦、剐蹭地面,在黑暗中擦出一片火花,同时右轮飞了出去。紧接着,一声巨响,爱德华兹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同时扔向了几个方向。他的视线变暗了,当视线恢复时,他发现滑翔机停了下来。接下来是片刻的沉默。现在是午夜刚过16分钟。有那么一瞬间,他怀疑他们是不是都死了,但随后他们开始骚动起来,解开了安全带,艰难地从黑暗的舱内爬出来。舱门已经扭曲变形、破碎不堪,爱德华兹看着身旁舱门的残骸,然后和其他人一起用枪托砸开了出口。
过了一会儿,他和战友们都出来了。他抬起头,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平旋桥,在夜空的映衬下呈现出银色。这就是横跨卡昂运河的贝努维尔桥(Bénouville Bridge),代号“飞马”。他们几近完美地着陆了,滑翔机的机头距离桥梁不到40码,正好在运河岸边一排树木的右侧,触到了铁丝网的边缘,这真是一个奇迹。一名军官喊道:“来吧,小伙子们,就是它了!”爱德华兹和其他人一起向前冲去,一边开火,一边投掷手榴弹,一边大声喊叫。桥梁旁边的一门大炮和地堡被磷弹炸毁,之后,敌人的一架机关枪从远处开火。士兵们立刻还击,不一会儿,他们就上了桥。爱德华兹跟在布拉里奇的后面。这时,又有一拨机关枪吧嗒吧嗒地向他们猛烈开火。突然间,布拉里奇倒下了,但爱德华兹和其他人继续向前冲。他们喊叫着、射击着、投掷着手榴弹,尽管他看到自己的手榴弹掉进了运河里。他说:“虽然我的手榴弹只杀死了几条鱼,但它们发出了很大的一声巨响。德军确确实实跑了,他们四处逃散。”他们按照计划完好无损地占领了这座桥梁,而且只用了一两分钟。在上年7月西西里岛战役的惨败之后,这是目前为止最顺利的一场战役。“我觉得终于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兴奋,又有点不敢相信——当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占领了这座桥梁时,我体会到的就是这种感觉。”
当时,德军只安排了第736步兵团的11名军士——1名下士和10名士兵——守卫桥梁,他们不是被杀,就是逃跑。布拉里奇中尉的颈部中弹,这是致命的一枪;不幸的是,他在英国的家里还有一个大肚的妻子。与此同时,另外两架滑翔机(粉笔92和粉笔93)也以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准确度降落了。尽管风很大,士兵们仍然蜂拥而出,来到桥梁上。很快,工兵在桥上发现了爆破室,但里面是空的。在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快速搜查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棚子里发现了炸药;德军没有把它们放在桥上,这是因为东部军——由波兰和苏联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存在语言障碍,之前由于命令被误解过早地炸毁了桥梁,德军害怕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当然,他们也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会遭到袭击。
与此同时,霍华德少校和无线电通讯员泰德·塔潘登(Ted Tappenden)准下士正试图与攻击奥恩河桥梁[代号“霍萨(HORSA)”]的士兵们联系。前两架滑翔机大约在0点35分时着陆,第三架则完全失联,此时下落不明。尽管如此,工兵西里尔·拉金(Cyril Larkin)和他的孪生兄弟克劳德(Claude)还是非常迅速地夺取了桥梁,拆除了空的爆破室。
截至那时,6架双引擎的阿尔伯马尔运输机空投了60位来自第22独立伞兵连的探路者。他们携带有照明灯和尤里卡信标,肩上背负着一个重大的任务:让即将在午夜前抵达的空降部队的主力辨别出着陆区。然而,这一切并不像期望的那样顺利,因为他们的行装太重了。这减缓了他们从飞机上跳下来的速度,使得他们飘下来的时候比原计划的还要分散。此外,着陆区K的探路者被空投到了着陆区N,并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也突显出在导航设备有限和风力强劲的情况下进行空投是极其困难的。
*
在英国,通常习惯在白天工作的美国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机组人员被从床上叫醒。英国王家空军的轰炸机司令部将在清晨轰炸法国海岸的据点和炮台,随后,将会有一拨又一拨的轰炸机从黎明时分开始轰炸,一直持续到进攻时辰前的10分钟。出于安全考虑,在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全面批准后,投弹手被告知将炸弹的投放时间推迟30秒,以确保他们不会击中海上的进攻部队。
在剑桥郡的巴辛伯恩(Bassingbourn)——这里是第91轰炸机大队的驻地——机组人员在0点30分被叫醒。
“1点吃早饭,2点听取作战指示”,叫他们起床的人用疲倦的声音说道。
“上帝保佑”,伯特·斯泰尔斯(Bert Stiles)中尉低声说道。他已经完全厌倦了战争,而且只睡了半个小时。斯泰尔斯23岁,但看上去更年轻,是一架名叫“时光匆匆”的空中堡垒轰炸机的副驾驶。正驾驶兼机长是山姆·牛顿(Sam Newton)中尉。他也是23岁,在科罗拉多学院念书时,他和斯泰尔斯都是兄弟会的成员。纯粹是因为偶然的机会,他们在美国陆军航空军位于盐湖城温多弗的训练基地又相遇了,并设法说服领导让他们在同一个机组。虽然在地面上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但一到了空中,斯泰尔斯就有些担心了,因为他们不太默契,实际上还惹恼了对方。4月19日(也就是到达巴辛伯恩后的第四天),他们执行了第一次任务,目标是纳粹德国空军位于德国埃施韦格(Eschwege)的装配工厂。
“你害怕吗?”斯泰尔斯在出发前问牛顿。
“我是山姆,当然不怕了”,牛顿回答道。他在那次飞行和随后的几次飞行中似乎一直保持着镇静。作为机组成员,他们可能有些合不来,但他们还是一同保持冷静,继续执行任务。
6月6日上午,在从床上爬起来时,全体机组成员都在嘟嘟囔囔地抱怨。
“也许今天就是登陆日”,斯泰尔斯说道。但没有人笑,甚至没有人回答。这句话说过太多次了,但从来没有变成现实。然而,他们一到食堂,公共关系专员麦克(Mac)就告诉斯泰尔斯今天的确是登陆日。突然间,这一切似乎开始成真。
“今天是登陆日,”斯泰尔斯回答道,“我向上帝发誓。”
*
身在巴辛伯恩的斯泰尔斯和战友们不知道的是,在诺曼底西部,美国的探路者正在空降到拟定的第101空降师的三个着陆区;一个小时后的凌晨1点21分,探路者将空降到第82空降师的着陆区。三架飞机正飞向各个着陆区,第101空降师的三个着陆区的代号分别为A、C和D,前两个着陆区位于犹他海滩的后面,第3个位于卡朗唐以北3英里。每架飞机都运载了两个尤里卡无线电信标、Holophane照明灯和13名探路者。它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科唐坦半岛,尽管有一架飞机因引擎故障不得不迫降。在快到着陆区时,其余的飞机撞上了一大团从西海岸飘来的低云,导致队形解散,而德军发射的零星的高射炮使情况变得更糟。不过,通过Gee导航系统,他们还是到达了着陆区。午夜0点16分,第一批探路者跳伞降落。那些需要降落在着陆区A的探路者空降在距离目标以北1英里的地方;需要降落在着陆区D的探路者相当准确地着陆;需要降落在着陆区C的探路者偏离了目标几英里。现在,他们展开了一场比赛,希望能赶到正确的地方,及时设置好照明灯和尤里卡信标。
在东翼的桥梁上,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士兵已经向前行进到拟定的据点。现在,他们正在等待第7空降营的增援部队,盟军承诺说,在他们空降的那一刻,这些增援部队就会立刻向他们进发。第二天早上,特勤突击旅在剑滩的东部边缘登陆,随后,急匆匆地向他们赶去。不过,他们首先要通过无线电与探路者进行联系。占领卡昂运河桥梁的行动代号是“火腿”,占领奥恩河桥梁的行动代号是“果酱”。塔潘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D4,D4,火腿加果酱,火腿加果酱”。最后,他失去了耐心,朝着无线电对讲机喊道:“他妈的火腿加果酱!”但是,没有人回答。塔潘登不知道的是,探路者的无线电操作员已经在跳伞时身亡;他的讯号是发给一个死人的。
凌晨1点50分,可以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在1英里外的着陆区,照明弹被点燃了。位于奥恩河东侧的是朗维尔(Ranville)村,其远处,在布雷维尔山脊前,有一大片开阔的农田。这是一个理想的着陆区,正因为如此,5月的时候,隆美尔曾视察了这个山脊,下令立刻在整个地带播种“芦笋”——防止空降的柱子。现在,伞兵正在那里降落,在照明弹的照耀下,桥上的人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降落伞。因此,德军向空中发射了曳光弹。
第一个跳伞的是一名年轻的排长,这天距离他的25岁生日只有五天。宣战的时候,理查德·托德(Richard Todd)中尉还是一名有抱负的演员。1940年春,在征召士兵时,他离开了邓迪保留剧目剧院,被派驻到国王嫡系约克郡轻步兵团。随后,他接受了军官训练,进入了战斗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实弹训练。之后,他在冰岛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北极练兵。在经历了这么久的战争后,他都平安地活了下来。最终,他作为第42步兵师的联络官回到了英国。他感到越来越无聊,一直在寻找解脱的机会,他多次尝试加入突击队或伞兵团,但都没有成功。1943年的某一天,当他在索尔斯堡平原向“温迪”·盖尔将军送信时,他被召进了第6空降师。托德非常高兴。后来,机缘巧合,第6空降师的一名上校和他闲聊说自己正在寻找一些军官。托德说:“命运把我直接引向了负责第6空降师的所有军官职位的那个人。”事情过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在领头的运输机上指挥着一群伞兵,这使他成了空降任务中的第一个跳伞员。
在从英格兰南部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飞向诺曼底的旅程中,托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在准备跳伞前的几分钟,他才被空投员摇醒。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背着沉重的装备,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把伞包上的拉绳扣到机舱内的滑轨上,在跳出机舱后,拉绳就会将降落伞从伞包内拽出来。舱口打开了,托德站在舱口上方,俯视着白色的浪花消失在海岸线上。红灯亮了,他看见一道道黄色和橙色的光,像流星一样从容不迫地划过天空。他意识到,这就是曳光弹。一分钟后,绿灯亮了,空投员又向他扔了一个充气保护囊,他从距离地面大约600英尺的地方跳了下去。他还有10秒钟的时间着陆,当降落伞的伞盖打开时,他拉开了开伞索,放开了腿袋
 ,并用另一只手抓住绳子。他顺滑而下,灼烧感刺痛了他的皮肤。
,并用另一只手抓住绳子。他顺滑而下,灼烧感刺痛了他的皮肤。
“见鬼!”他痛苦地叫道。周围的噪音很大:飞机在头顶上方嗡嗡作响,机关枪吧嗒吧嗒地响个不停,枪炮轰鸣。片刻之后,他重重地落在一片玉米地里。他迅速扔掉背带和腿袋的绳索,蹲下来清点装备。四周没有一个人,他也看不见特定的标记物——朗维尔教堂,这让他觉得自己可能空降得有点早。突然,一架燃烧的飞机坠落下来,明亮地划过天空,但他没有时间多想这件事;他需要行动起来。他朝树林走去。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他很快就听到了英国人的声音。在一片空地上,他发现了理查德·派恩-科芬(Richard Pine-Coffin)上校。科芬是托德所在的第7伞兵营的指挥官,该营隶属于第5伞兵旅。他们的任务是前往桥梁,增援霍华德少校的部队,其他两个营负责占领朗维尔,确保着陆区和周边地区的安全。詹姆斯·希尔准将领导的第3旅的各个营将摧毁迪沃河上的桥梁,占领德军在梅维尔的炮台。
这就是当时的计划。不过,和以往的空降行动一样,这个计划正在瓦解,而且是迅速瓦解。总的来说,第5伞兵旅的降落是相当成功的:着陆区N靠近朗维尔,位于内陆几英里处,这让机组人员和部队在飞机上弄清了他们的方位;这里距离运河和河流很近,容易找到,而且探路者也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盟军成功空投了2000多人和702个集装箱。希尔准将指挥的第3旅几乎同时到达,但他的大部分人马却分散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混乱,是因为着陆区K的探路者降落到了着陆区N,并且太晚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着陆区V的探路者遇到了轰炸机司令部派遣的几百架兰卡斯特轰炸机,它们本来打算在午夜0点30分轰炸梅维尔炮台。这些战略轰炸机需要在能见度有限、狂风大作的夜晚行动,而且瞄准的是一个很小的目标,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因此,它们超出航线2400码,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差一点歼灭了着陆区V的探路者,发生这种情况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它们还撞碎了尤里卡信标,这是一套无线电测向装置,可以向前往这个着陆区的领头运输机发送方向脉冲。更糟糕的是,这些意外情况产生的烟雾飘过了整个地区,把大部分区域都给遮蔽了。在运输第9伞兵营和加拿大第1伞兵营的71架飞机中,只有17架进行了稍微准确的空投。此外,着陆区V的东部地区已经被大水淹没,很多人降落在浸满水的地面上。“先生们,虽然你们受过良好的训练,虽然你们秩序井然,但是,即使遇到了混乱的场面,也不要气馁,”希尔准将曾经这样警告他的部下,“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他说得没错,但他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迅速地从混乱中理清头绪,并完成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
*
科尼利厄斯·陶伯中尉刚刚从库尔瑟勒(距离卡昂运河以西大约10英里)进入内陆。午夜时分,在检查完一个新的地堡后,他回到兵营,随即听到头顶上方传来飞机的嗡嗡声,大多数都是低空飞行。他认为这不像是空袭。此时,天空中飘着毛毛雨,云层掠过月亮,他停下来仔细看了看,竟然能看清飞机的形状。高射炮在开火,曳光弹直冲云霄。这是登陆吗?陶伯和同事们都不确定,但是,如果这是他们最后的平静之夜,他们认为不妨好好利用一下。于是,他们开了一瓶白兰地,一同享受着美酒。
贝伦格雷维尔(Bellengreville)是卡昂东南部的一个村庄,距离英军的着陆区以南只有几英里。汉斯·冯·卢克少校坐在贝伦格雷维尔的一间陈设简陋的房子里。午夜约0点20分,他听到了飞机的声音,这些飞机飞得很低。他有些闷闷不乐;作为一个行动派,他怀念过去的日子,那时,他们在法国和北非横冲直撞。坐着等待盟军登陆并不符合他的作风。他还没有睡,正在四处走动,因为他在等待第2营报告说他们在特罗阿恩(Troarn)附近的夜间演习结束了。此时,大批盟军飞机正从上空飞过——除此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东西。几分钟后,他的副官通过野战电话告诉他,伞兵和滑翔机正在空降。
“所有部队立刻进入戒备状态,”冯·卢克毫不犹豫地命令道,“通知各师。”尽管上级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他仍然对副官说,必要时,第2营应当立刻投入战斗,并且应把俘虏直接送到他那里。然后,他前往指挥部。在那里,他得知第2营已经在行动了,还得知虽然第5连一直在训练,但都不是实弹训练,这让他非常担心。更让他恼火的是,他发现福希廷格尔少将远在巴黎。
在盟军发动重大进攻时,德国的高级指挥官竟然缺席,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阿拉曼战役开始时,隆美尔在德国,现在他又不在前线。在1944年5月盟军发动占领罗马的“王冠(DIADEM)”行动之前,德国第十集团军的指挥官海因里希·冯·维廷霍夫(Heinrich von Vietinghoff)上将和部队的高级指挥官弗里德林·冯·辛格尔-艾特林(Fridolin von Senger und Etterlin)中将已经回到了德国。西线总司令部的情报总监威廉·迈耶-德特林(Wilhelm Meyer-Detring)上校此刻也不在前线。这至少可以说是太疏忽了。
在其他地方,德军只是慢慢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盟军曾希望实现全方位的战术突袭,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好像确实做到了。当然,德军发现的各种各样的讯号和收集的情报图片显示,盟军正在开展某些行动——冯·伦德施泰特的情报人员破解了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抵抗运动的代码——但是,如果B集团军群和西线总司令部的高级将领选择忽略它们,那么即使破解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情报图片表明,盟军很可能会先发动转移注意力的突袭并进行登陆,因此,高级指挥官们不想过于迅速地采取应对措施,以防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都敏锐地意识到,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任何意见,实际上都是希特勒对形势的看法。
然而,当第3旅的一名英国伞兵散乱地降落在指挥部的屋顶上时,第711步兵师的指挥官约瑟夫·赖歇特(Josef Reichert)少将很快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什么转移注意力的行动。当时,他和高级参谋们正在深夜里玩纸牌。尽管赖歇特和他的师隶属于汉斯·冯·扎尔穆特上将的第十五集团军,他还是立刻给马克斯将军打了电话。当时是凌晨1点11分。之后,第七集团军的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多尔曼上将获悉了这一情况,并在凌晨1点30分下令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凌晨1点35分,伞兵在科唐坦半岛降落的消息也被传达给了驻扎在拉罗什盖恩的B集团军群。
然而,斯派达尔(隆美尔的参谋长)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告诉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甚至没有告诉隆美尔,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喝醉了,或者至少可以说他喝了很多酒。当然,喝大量的葡萄酒和烈酒与清醒果断地采取行动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然而,在战争爆发近五年后,任何一位德国高级指挥官都应该知道,就空降部队的本质特点而言,他们都是轻装上阵的,最适合进行简短而迅速的作战行动,盟军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增援部队——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增援部队实际上只能从海上到达。即使这是一次转移注意力的行动——如果德国人理智地考虑过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不太可能——增援部队也有可能很快就会登陆诺曼底海滩。就像隆美尔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灌输的那样,德军需要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但是,没有元首的明确授权,他们无法命令任何一个装甲师开赴前线。既然如此,如果希特勒越早知道、越早发出命令,那么情况也就会越好。然而,斯派达尔保持沉默。他甚至没有给他在赫尔林根的上司隆美尔打电话。
然而,在巴黎,西线海军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海军少将卡尔·霍夫曼(Karl Hoffmann)没有丝毫的疑虑。凌晨1点50分,他向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报告说盟军已经开始登陆。10分钟后,冯·伦德施泰特获悉了这个消息,暂时让第21装甲师——他只能调动第21装甲师——处于2级戒备状态,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90分钟内准备好行动。说得客气点,这样的回应其实很敷衍。另外,马克斯将军和第七集团军的参谋长马克斯·彭塞尔(Max Pemsel)少将意识到这是空降袭击。在过去的几周里,彭塞尔越来越相信,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他认为情报图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德军原计划在6月6日举行军事演习,内容关于如何应对空降部队对科唐坦的袭击,指挥官们预定在布列塔尼的雷恩开会。然而,彭塞尔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要求他们在黎明前不要出发——以防盟军抵达。并不是所有人都听从了他的命令,其中就有经验丰富的第91空降步兵师的指挥官威廉·法利(Wilhelm Falley)中将。他仍然前往雷恩,但他中途被拦住了,并被责令返回。
*
在诺曼底,美军正在进行空降突袭。讽刺的是,如果他们前一天晚上出发前往科唐坦,那么他们本来可以赶上更加晴朗的天气,尽管那时东侧天空的云层较多。诺曼底下了一场雨,5日凌晨3点前后,东部地区的雨停了。英国调整了空降时间,如果英国坚持在5日进行空降,那么天气可能会更好,而且他们现在也不用冒着小高压脊可能会消散的风险了。事实上,夜晚的时候,高压脊已经有所发展,使得天晴的时间要比最初预期的长。
无论如何,推迟空降的决定肯定无助于美国的空降突袭。凌晨1点刚过,433架C-47运输机搭载着第101空降师的大约6900名伞兵向科唐坦海岸靠近,这个庞大队伍的各个联队均采用V形编队——三个V形编队一起飞行,每个编队有36架飞机。随后是52架滑翔机,主要运载吉普车、反坦克炮和其他武器。这个庞大的部队在1500英尺的高空飞过海岸,然后减速到每小时110英里,接着下降到约600英尺,这是空降的最佳速度和高度。如果飞得太高,伞兵就会在空中停留太长时间,那样一来,他们就非常容易暴露,也非常容易遭到袭击;如果飞得太低,那么伞兵的降落伞就没有机会打开;如果飞机的速度太快,伞兵就会偏离轨道,降落的准确性就会大大降低。然而,虽然美军制定了复杂精细的计划,却没有人想到提前派一架侦察机去查看科唐坦的实际天气情况——英军也没有想到要侦察天气情况,尽管他们基本上都化险为夷。此外,美军也没有在恶劣的天气下进行任何特别的夜间训练;除了5月份的演习,第101空降师已经有七个多星期没有进行任何训练了。
第506伞降步兵团的第2营正在空中飞行,他们作为第12梯队,编号为46~81。靠近第67号飞机舱口的是迪克·温特斯(Dick Winters)中尉,他是E连1排的指挥官,E连的绰号是“轻松连(Easy Company)”。温特斯26岁,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毕业于一所学院的商科专业,拥有高级学位。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并拥有很好的运动天赋。他自愿参加了一场他根本不想参加的战争,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展现出了作为军人和领导者的天赋——尽管他和第101空降师的所有人一样还没有尝过战斗的滋味。
在他们准备跳伞前,飞行员提前20分钟呼叫机组组长,组长打开了舱门。温特斯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外瞥了一眼。天空中挂着一轮满月,虽然低垂,却仍发出皎洁的光辉,足以让他看清周围的一切。整个天空似乎布满了飞机,但是,当他们飞过海岸时,这个平静而又令人敬畏的景象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他们撞上了一堵云墙,他们在一瞬间发现了探路者,但这堵云墙却一直没有消散。突然,飞行员们什么也看不见了。然而,由于他们仍然排着紧密的队形,因此发生碰撞的风险是巨大的。每个梯队的大多数飞机都依靠领头的飞机进行导航,但现在,它们看不见领头的飞机,都是在盲飞。一些飞行员惊慌失措,有的爬升到更高的地方,有的降到更低的地方,有的加快速度,有的减慢速度。
在内陆10~12英里处,云层逐渐变薄,并且分散成很多小云。在飞越海岸时,飞机意外遭遇了高射炮的攻击,温特斯感到非常惊讶。现在,他看到红色、蓝色、绿色的曳光弹向他冲来,这些曳光弹纵横交错,照亮了整个天空。虽然一些飞机仍然隐隐约约地保持着队形,但飞越海岸时那种平静的凝聚力已经消失了。突然,他们旁边的一架C-47被击中:温特斯看到曳光弹径直地穿过那架飞机,并从顶部飞了出去。这时,远处的一团云挡住了他的视线。温特斯没有看见的是,那架被击中的飞机翻了个身,然后坠落到地面,并发生了爆炸,机上所有人全部阵亡,包括E连的连长托马斯·米汉(Thomas Meehan)中尉。
第67号飞机的驾驶员正在加快速度,以躲避敌人的火力。温特斯向下看,因为紧张,他的体内开始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他搜寻着地面,希望找到地标和着陆区的标志。他命令大家站起来,让他们把伞包上的拉绳扣到机舱内的滑轨上。然后,他再一次向打开的舱门瞥了一眼。曳光弹越来越近,最后击中了机尾,飞机开始摇晃,一些人踉踉跄跄地跌倒。温特斯回头瞥了一眼调度员,当绿灯亮起时,他喊道:“跳!”就在这时,一枚20毫米口径的炮弹击中了飞机。他跳了下去,但这时飞机的时速接近150英里,而不是110英里。由于飞机以这样的速度飞行,这给跳跃造成了冲击,导致他的腿袋和其他大部分装备都被扯掉了。
不一会儿,他就降落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肩膀和腿严重受伤,但他还活着。尽管如此,他的处境并不好。他知道自己错过了着陆区,但不太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他没有武器,他的武器在跳伞的过程中丢失了。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害怕。他知道自己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而后,他发现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写道:“虽然我一直担心自己能否达标,但现在是检验这几个月的训练成果的时刻了。”
很快,另一名来自总部连(而非E连)的士兵加入了温特斯的队伍。在绕过德军的一支机枪部队后,他们继续前进,并使用军队向他们发放的在廉价商店购买的蟋蟀哨设法与所在排的其他人联系。在仔细查看地图后,温特斯意识到他们正在接近圣梅尔埃格利斯——事实上,他们可以看到一座房子里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这个小镇。他们位于着陆区西北方向约4英里处,虽然不是很理想,但初步看来,也不算太糟糕。
*
凌晨2点,在距离卡朗唐不远的一个农舍(这是第12连的总部)里,马丁·波佩尔(Martin Pöppel)中尉被叫醒,并被告知第6伞降猎兵团已经处于全面戒备状态。这是该地区唯一的伞兵团,它的三个营被分散安排在不同的地方——第1营驻扎在圣玛丽迪蒙(Sainte-Marie-du-Mont),第2营驻扎在圣梅尔埃格利斯,第3营驻扎在卡朗唐。他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对周围的乡村进行了彻底调查,那里大部分都是经过开垦的沼泽地,周围交错着密密麻麻的灌木篱墙或“波卡基”。他们意识到,这些都是很高的土墙,缠绕着树木和茂密的灌木根。因此,他们充分利用这些天然的防御工事,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和定期演习,等待着盟军舰队抵达法国海岸的那一天——他们知道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第6伞降猎兵团是近期组建的兵团,它由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组成,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有战斗经验的伞兵。其余的都是狂热的志愿兵,平均年龄只有17岁半,仅仅接受了四个月的训练。尽管时间很短,但他们的训练还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他们遵守纪律,又拥有丰富的经验,这确保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了诺曼底最优秀的德国军队之一。他们还是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每个步枪大队(每个大队10人)配有2挺MG42机枪,而不是普通的机枪。重武器连配有12挺重型迫击炮和重型机枪,比一般的连都多。在车辆上,他们只有70辆卡车来运输这个4600人的兵团。这些卡车既有德国制造的,也有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制造的,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搜罗来的。由于缺乏备件和所需的大量零件,维修卡车简直是一场噩梦。5月底,弗里德里希·冯·德·海德特(Friedrich von der Heydte)上校曾报告说:“虽然该兵团是用于地面战斗的,但是,只有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地面作战,因为它没有足够的重型反坦克武器和机动运输工具。”
波佩尔几乎在伞兵战斗过的所有地方打过仗,从挪威和低地国家到克里特岛的激战,从东线到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一路走来,他赢得了一等铁十字勋章和二等铁十字勋章,很早就被晋升为上级猎兵,然后晋升为中尉;现在,德军把他从第1伞降猎兵师调来,并让他拥有了自己的连。虽然年仅24岁,非常年轻,但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纪律严明的军官了,德国国防军越来越依赖这类军官。
此刻,他和连队总部的工作人员匆忙赶往观察哨,在等待了解更多情况的时候,他们枪上的保险栓松脱了。他凝视着外面的夜色。虽然风越来越大了,可月亮还是不时地出现,照亮了乡村。偶尔会有一两个枪声响起,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规模的攻击。然而,更多的盟军伞兵正在赶来:第82空降师的另外6420名伞兵也在路上。
*
在第101空降师的行动开始大约半小时后,也就是凌晨1点51分,第82空降师(也就是所谓的“全美国人”师)开始进行伞降。第101空降师遇到的任何问题,对第82空降师来说都变得更加糟糕,因为盟军已经扰动了马蜂窝,此时地面上的德军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高度警惕。云层没有消散。马克·亚历山大中校乘坐的是领头的C-47运输机,他坐在飞机后部敞开的舱门处。当他们越过英吉利海峡时,他俯视着大海,看到了被奶油般的月光照亮的几百艘船舰,那个景象令人生畏。然后,他们抵达了诺曼底海岸,并一直停留在云层中,直到红灯亮起。他非常确定飞机已经开始爬升,他担心会跳到比他们飞得低的C-47运输机的航路上。红灯亮了,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他们把伞包上的拉绳扣到机舱内的滑轨上,一些人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亚历山大觉得他们肯定已经飞过了着陆区。突然,绿灯亮了,他跳了下去。由于速度过快,降落伞打开时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迅速地降落在一片树林的一小块空地上,除了卡宾枪的枪托碰到了他的下巴外,他没有受什么伤。令人惊讶的是,整个小组的降落距离靠得很近,没过多久,18个人都收拾好装备,去和亚历山大会合。第505伞降步兵团的着陆区在圣梅尔埃格利斯的西北方,亚历山大估计他们在向北约2.5英里处降落。情况还不算最糟——对第82空降师的许多人来说,的确是这样。
另外两个着陆区位于梅德列(Merderet)河对岸的西部和西南部,也就是隆美尔下令放水淹没的地区。由于很多C-47运输机的飞行员为了躲避云层和高射炮加快了飞行速度,这意味着,这些飞机已经大幅超过了指定的着陆区。离梅德列最近的着陆区T,是第507伞降步兵团降落的地方,然而,很多伞兵降落到了被水淹没的地区。虽然大多数地方只有一两英尺深,但这足以淹死许多背着沉重装备的伞兵。
*
与此同时,在东面,位于飞马桥西侧的丹尼斯·爱德华兹和他的七人小组已经占领了沿着运河运行的单轨电车旁的据点。在不远的地方,防空警报开始响起。其他人已经解放了与贝努维尔桥同在一侧的有轨电车酒吧(Buffet du Tramway);它是盟军从纳粹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第一栋法国建筑。酒吧的主人乔治斯·龚德瑞(Georges Gondrée)立刻从花园里挖出了他深藏的99瓶香槟,把它们送给了霍华德少校和他的部下。这是一个备受赞誉的举动,不过,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这些人确保龚德瑞先生和他的家人继续获得解放。
就在离奥恩河的朗维尔一侧不远的地方,包括理查德·托德中尉在内的大约50人聚集在河边陡峭的悬崖上。他们在某个预先约定的地点会面,并围绕在派恩·科芬上校的周围。一名号手不断地吹响号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现在把视线转到桥上,霍华德吹起了他的便士哨,并用莫尔斯电码吹出了“耶!胜利!”的调子。很快,第5伞兵旅的旅长奈杰尔·波依特(Nigel Poett)准将出现了,他让霍华德坚持住,并保证援军马上就到了。然后,他再次消失,继续去集结他的部下。
由于德军在两座桥的两端都修建了防御工事,霍华德便把一些士兵从霍萨桥带回运河边。布拉里奇中尉(他和霍华德在同一个连,他们是好朋友)被送到临时救护站,这个救护站搭建在位于两座桥梁之间的一架滑翔机的残骸上,但他很快就去世了。他的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此刻,可以听到枪声从朗维尔方向传来。不久,德国巡逻队抵达霍萨桥,并向盟军开火。德军很快便被消灭了,然而,守卫霍萨桥的盟军发现,他们误杀了三名早前被俘的盟军伞兵。
此刻,可以听到枪声从朗维尔方向传来。不久,德国巡逻队抵达霍萨桥,并向盟军开火。德军很快便被消灭了,然而,守卫霍萨桥的盟军发现,他们误杀了三名早前被俘的盟军伞兵。
在那之后不久,一辆德国高级人员乘坐的专车从同一个方向向盟军疾驰而来,汽车穿过外面的防御工事,经过大桥。在那里,它遭到了盟军的火力扫射,然后急转弯,冲到了路边。从车里跳出来的三个人被打死了,另一个腿部受了伤。他是第736步兵团的团长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少校。他没有视察、监督士兵,而是和当地的一名法国女士待在一起。他失血过多,失去那座桥梁让他蒙羞受辱、心烦意乱,于是,他请求盟军枪毙他。相反,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这让他安静下来,并促使他用更乐观的态度看待目前的形势。
凌晨2点刚过,可以听到西边的贝努维尔村传来坦克的轰隆声。德军第716步兵师的装甲歼击连正哐啷哐啷地向运河上的大桥驶来。丹尼斯·爱德华兹一直在拼命地掘壕固守,这时,他停下手里的活儿,出神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第一辆坦克停了下来,几名乘员走了出来,与跟在后面的步兵交谈,看起来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时,从霍萨桥过来的“韦格”·桑顿(“Wagger” Thornton)中士跑上前去,当距离足够近时,他冷静地使用步兵用反坦克发射器(PIAT)——这是一种便携式反坦克武器,通常因为太笨重而不太受欢迎——朝他们开火。这一次,发射器发挥了作用。只听见“嘣”的一声,一两分钟后,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烈火熊熊,”爱德华兹说,“橙色、红色和黄色的巨大火焰照亮了大桥。”德军急忙撤退。桑顿的这一枪不仅使大桥免于被占领,也为盟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凌晨3点前后,托德中尉和第7伞兵营的150多名伞兵终于到达了大桥。当他们穿过两座桥梁之间的堤道时,托德发现了被他击毙的第一个德国士兵。这具尸体没有腿,但托德可以听到哼哼声。他猜想这是体内产生的气体,于是从旁边走了过去,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惊慌害怕。他是营队的助理副官,在龚德瑞的酒吧,上级指示他沿着运河向北到达一个叫作勒波特的小村庄,并告诉他建立一个防御前哨。他召集了十几个人,带领他们走了大约半英里,来到运河旁的一座圆锥形小山上,俯瞰着一个白垩岩采石场。他原本希望,夜幕降临的时候,会有更多第7伞兵营的士兵抵达临时据点(这个据点搭建在两座桥梁的两端),但此时托德和他的部队相当孤立,并与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
守卫桥梁的盟军士兵只能等待——等待敌人,等待突击部队,等待未知的命运。
*
与此同时,在东边,凌晨2点,罗伯特·勒布朗终于坐上卡车离开了蓬托德梅尔,前往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总部——拉皮尔维戴尔。到目前为止,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盟军成功袭击了德国的战地宪兵,3名德国士兵被杀,但其余的人在攻击发生时已经离开。在前往新总部的途中,勒布朗带上了更多的食物,最重要的是,还有25升燃料。最后,在拉皮尔维戴尔,他遇到了目前在他麾下效力的3个宪兵,并等着头顶上传来飞机的声音。没过多久,他们就听到一架飞机在附近盘旋——而且是在约定的时间。“不会有错,”勒布朗写道,“快,快,我们发信号吧!”他和3个宪兵拿起电灯,急忙冲到外面。他们跑到着陆区,打开了照明灯。每个人都很兴奋——的确是这样!他们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然而,赛朋和贝左还没有带着雪铁龙汽车回来,这让他很担心。之后,在凌晨3点15分,他们没有看到飘浮落下的金属罐,而是听到了哨声和爆炸声。他们没有收到武器,反而遭到了4枚炸弹的攻击。“所幸没有人伤亡,”勒布朗潦草地写道,“但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然而,无论是敌人的轰炸机还是友军的误射炮火,他们都不能再冒险使用拉皮尔维戴尔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再次转移,这一次转移到了附近树林边上的一个小农场。
*
此时,诺曼底沿岸的德国军队已经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在内陆的临时营地里,汉斯·海因兹少尉刚刚上床睡觉,很快便睡着了。这时,他被叫醒,匆忙赶到科勒维尔附近的一个观察哨,科勒维尔位于奥马哈海滩的东端。他本人不相信这只是虚惊一场,所以他非常担心。然而,地面上的士兵显然很恐慌。在62号抵抗力量据点,二等兵弗朗茨·戈克尔结束了前半夜的执勤,此刻在地堡里熟睡。他和战友们睡的是用铁链搭成的架子床,铁链的两端固定在墙上,每个竖排都有三张床。睡在上面的是一位35岁的士兵,他最近把所有的牙齿都拔掉了,还戴了一副假牙,睡觉时,他都会把假牙泡在一杯水里。睡在下面的是一个18岁的士兵,他小时候失去了一只眼睛,被替换成了玻璃义眼。
“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站在地堡入口的一个同志喊道,“你们最好快点!”当戈克尔和其他人揉了揉眼睛,迅速清醒过来时,一个二级下士喊道:“小伙子们,盟军真的登陆了!”几分钟后,戈克尔和战友们分别回到了各自的岗位,并架好了机枪和步枪。但是,当他们凝视着漆黑的夜空时,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心想,这会不会又是虚惊一场。戈克尔写道:“我们穿着轻便的制服,携带着武器,瑟瑟发抖地站着。”炊事员给他们送来了热的红酒,他们把这个叫作“生命的灵魂”。
沿着海岸往东,陶伯中尉从他的兵营急匆匆地走了30分钟才到达位于库尔瑟勒的地堡。装甲歼击连的炮手已经准备好了,地堡里操作3辆“歌利亚”的5名士兵也准备好了。“歌利亚”是一种小型遥控履带车,装有炸药和足以行驶一公里的汽油。在适宜的时候,德军将把每辆“歌利亚”送进一个伪装的混凝土隧道,然后开到海滩上。德军通过地堡里的一个观察孔和从观察孔里伸出去的潜望镜观察形势。现在是凌晨3点,他和部下所能做的就是在黑暗中、在寒冷的地堡里焦急地等待。他们启动了“歌利亚”,以测试引擎能否正常运作。这时,浓厚的烟雾弥漫在空中,刺痛了他的眼睛。他试图保持冷静,但他禁不住想到,如果盟军登陆,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此外,尽力让部下保持士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要么是40多岁的老家伙,要么还是十几岁的少年。
过了一会儿,汉斯·海因兹少尉站在观察哨上,这个观察哨建在悬崖上,大致位于奥马哈海滩的中点,他认为这真的又是虚惊一场。海上升起了薄雾,在很远的东方,第一道灰色的晨曦已经跳出了地平线。在向他的顶头上司格里姆(Grimme)上尉进行报告前,他把双筒望远镜放在眼前又扫视了一遍。他看到远处地平线上有个东西:一个桅顶。然后他发现了另一个,接着又有一个。几分钟内,地平线上似乎都是桅顶。海因兹擦了擦镜片,又看了一遍。这次确定无疑了:在海上和靠近海岸的地方,出现了一支真正庞大的无敌舰队。他迅速写下一条信息,并交给了勤务兵。“成千上万艘船舰向我们驶来,”他写道,“盟军就要登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