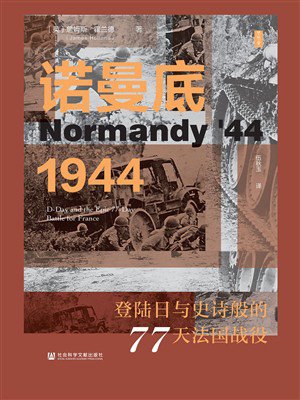第2章
制空权
1944年5月22日星期一,第61战斗机中队的16架P-47雷电战斗机在沉着冷静的弗朗西斯·“加比”·加布雷斯基(Francis “Gabby” Gabreski,昵称“加比”)
 中校的带领下,飞快地冲向德国北部城市不来梅。不久前,第61战斗机中队——它隶属于“胡伯”·泽姆克(“Hub” Zemke)
中校的带领下,飞快地冲向德国北部城市不来梅。不久前,第61战斗机中队——它隶属于“胡伯”·泽姆克(“Hub” Zemke)
 上校指挥的第56战斗机大队——帮助护送近300架B-17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对波罗的海的基尔港口发动袭击,不过,它们的护送任务已经结束了,现在,它们的职责是在德国北部的上空进行袭击,击落它们看到的任何敌机,特别是摧毁地面上的铁路机车。这次密集的火车粉碎行动于前一天开始,代号为“查塔努加酷酷(CHATTANOOGA CHOO CHOO)”,取自一首著名的歌曲。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一个欢快的叮当声,然而,袭击铁路机车却是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实际上,德国的铁路网——帝国铁路——是把德国的战事工作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铁路运送到不断衰败的帝国的:原材料、武器、劳动力、军队、食物,还有被送往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越多的铁路调度场被毁,越多的机车遭到轰炸,越多的铁路桥被破坏、线路被切断,德军的调动就会变得越发困难。在登陆前,盟军最担心的是西线的10个装甲师发起集中反击。这个所谓的“运输计划”的目的是,尽可能让德军难以将所有重要部队和其他增援部队运送到诺曼底。
上校指挥的第56战斗机大队——帮助护送近300架B-17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对波罗的海的基尔港口发动袭击,不过,它们的护送任务已经结束了,现在,它们的职责是在德国北部的上空进行袭击,击落它们看到的任何敌机,特别是摧毁地面上的铁路机车。这次密集的火车粉碎行动于前一天开始,代号为“查塔努加酷酷(CHATTANOOGA CHOO CHOO)”,取自一首著名的歌曲。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一个欢快的叮当声,然而,袭击铁路机车却是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实际上,德国的铁路网——帝国铁路——是把德国的战事工作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铁路运送到不断衰败的帝国的:原材料、武器、劳动力、军队、食物,还有被送往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越多的铁路调度场被毁,越多的机车遭到轰炸,越多的铁路桥被破坏、线路被切断,德军的调动就会变得越发困难。在登陆前,盟军最担心的是西线的10个装甲师发起集中反击。这个所谓的“运输计划”的目的是,尽可能让德军难以将所有重要部队和其他增援部队运送到诺曼底。
就在那一天,“胡伯”·泽姆克引入了一种新战术,被人们称为“泽姆克扇形”。他将战斗机大队分成3个中队,每个中队驾驶16架飞机,4架为一组。为了在回程时充分利用这些飞机,他命令它们在3个不同的区域上空飞行,而不是一起返回基地。于是,第62战斗机中队被派往帕德博恩(Paderborn)地区进行搜寻,第63战斗机中队被派往汉诺威(Hanover),而加布雷斯基的战斗机中队则急速飞往西南方向的不来梅。
在不来梅东部大约20英里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几辆铁路机车。在晴朗的天气里,它们喷出的白色蒸汽云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于是,加布雷斯基命令埃文·麦克明(Evan McMinn)的黄色飞机冲下去袭击它们,剩余的12架雷电战斗机则盘旋埋伏在大约15000英尺
 的高空。然而,就在它们刚开始盘旋时,加布雷斯基发现了下面有一个伪装得不太好的空军基地。过了一会儿,无线电对讲机里传来麦克明的声音,他说他看到了一些福克-沃尔夫190战斗机正在起飞。
的高空。然而,就在它们刚开始盘旋时,加布雷斯基发现了下面有一个伪装得不太好的空军基地。过了一会儿,无线电对讲机里传来麦克明的声音,他说他看到了一些福克-沃尔夫190战斗机正在起飞。
当加布雷斯基带领中队向下俯冲时,他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兴奋之情。雷电战斗机是一种大型战斗机,在俯冲速度方面无人能敌。它配备有点50口径
 的机枪,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能够承受炮弹的打击,并且高度灵活。更重要的是,就飞行技能而言,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与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不在一个层次。以新加入中队的飞行员为例,大多数人的飞行时间是德国同行的三倍多,而且由于拥有大量的燃料,每个中队都有很多冗余的飞行员——通常超过50人,以便在每次执行任务时都能有16架飞机飞行——所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起练习和磨炼技能。由于德国长期缺乏燃料,新加入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往往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才有机会飞行。因此,大多数德国飞机被迅速击落。
的机枪,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能够承受炮弹的打击,并且高度灵活。更重要的是,就飞行技能而言,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与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不在一个层次。以新加入中队的飞行员为例,大多数人的飞行时间是德国同行的三倍多,而且由于拥有大量的燃料,每个中队都有很多冗余的飞行员——通常超过50人,以便在每次执行任务时都能有16架飞机飞行——所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起练习和磨炼技能。由于德国长期缺乏燃料,新加入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往往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才有机会飞行。因此,大多数德国飞机被迅速击落。
这将是许多福克-沃尔夫190战斗机的命运。当加布雷斯基和飞行员冲向它们时,他看见大约有16架飞机排成一行散开。此刻,敌军战斗机已经飞到可以转身作战的高度,但它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一切,而是以固定的队形继续飞行,使自己成了P-47战斗机的诱人目标。加布雷斯基选中一架飞机,朝它开火,他看见子弹打在德军飞机的机身和机翼上。这架飞机翻转坠落,然后燃烧起来。现在,加布雷斯基跟在第二架飞机的后面,向它逼近,再次开火。这一次,飞机的座舱罩被打飞,片刻之后,飞行员跳伞了。回头看时,加布雷斯基看到两架190战斗机正在追踪他。他设法爬升,然后掉头,甩掉了它们。然而,这时他看见中队的一架飞机起火,另一架冒出一股浓烟,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爬升回到12000英尺的高空,命令中队的飞行员在敌人机场的上空重新集结。很快,他集结了6架雷电战斗机,他们发现下方有大约20架福克-沃尔夫战斗机。突然间,德国战斗机的高射炮手向自己一方的战斗机开火。一些飞机发射了绿色识别信号弹,但敌机的编队还是被打乱了。
加布雷斯基毫不犹豫地带领飞行员冲下去,急速跟在6架德国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后面。过了一会儿,他击落了当天的第三架飞机,但随后看到另一架福克-沃尔夫战斗机从左侧偷偷靠近他。他将控制杆向下猛拉到腹部位置,收油门,他的雷电战斗机便向下落,几乎达到失速的程度,这样一来,追踪他的飞机别无选择,只能从他的上方飞过。突然间,加布雷斯基出现在追踪者的后面,但他的弹药不足,而且还有5架梅塞施密特109战斗机跟在他的后面,他认为是时候掉头逃跑了。他命令中队的飞行员飞回去,他们便迅速向西飞行,不料碰见一架福克-沃尔夫战斗机在云层里飞进飞出。加布雷斯基加速跟在后面,利用最后的弹药把它从空中击落,这是他一天内击落的第三架飞机,另有1架未被证实。
那一天,加布雷斯基和中队的飞行员总共击落了13架飞机,另有1架未被证实,重创2架,中队损失了2架。尽管机舱上有上百个弹孔,飞行员乔尔·波普尔韦尔(Joel Popplewell)仍成功地驾驶雷电战斗机返回了英国。当时,加布雷斯基是美国第8航空队的王牌之一,他认为这是他执行过的最艰难的任务之一,但它证明了,在西线,美国的日间战斗机比纳粹德国空军更具有绝对优势。距离登陆还有两个多星期,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天,泽姆克的战斗机大队也进行了同样出色的狩猎行动:有6辆铁路机车被摧毁,7辆受损,18艘驳船被炸毁。“查塔努加酷酷”进展顺利。
更值得欢呼的事情发生了。不到一周后,也就是5月28日星期天,一场历时五个月的争夺西北欧空中优势的战斗达到了高潮。对于登陆,掌握制空权是不容商议的前提条件。自去年夏天以来,这一直都是盟军的战事领导人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1943年的夏秋之际,尽管人数有所增加,经验有所提高,助航设备有所改进,美国第8航空队和英国王家空军的后方指挥部仍竭力取得更大的进步。英国王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总司令、空军上将阿瑟·哈里斯爵士坚持认为,使用越来越多的重型轰炸机对德国城市进行夜间轰炸,足以让纳粹德国空军,乃至整个纳粹德国屈服。几个月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说法越来越误导人。首先,纳粹德国空军最终建立了一个日益有效和协调的防空系统。其次,他们召回了大部分的纳粹德国空军,以保卫德意志帝国,同时大幅增加了飞机的产量。空中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夜间战斗机来迎接哈里斯的轰炸机。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专业指导,将组织严密的情报机构、地面控制和雷达结合起来,以便对付英国的轰炸机。虽然轰炸机司令部继续对德国造成大范围的破坏,但这不足以使德国投降,而且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轰炸机的飞行员也会遇袭身亡。
美国开始在白天轰炸德国,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更加精确地轰炸目标,从而更有效率。为此,他们开发了全副武装的四引擎轰炸机,能够以防御严密的编队飞行;但很快,在吃了一番苦头后,他们认识到,仅有轰炸机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轰炸机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和英国的轰炸机司令部一样,美国空军也受到了打击。
1943年下半年,在危机四伏的那几个月里,美国人尤其意识到,他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获得空中优势,这是他们进行战略轰炸的首要任务。早在1943年1月,他们就在“零秒战区(POINTBLANK)”指示中同意了这项任务,并在同年6月初正式确定了这项任务。之所以要比纳粹德国空军更具优势,原因有二:如果沿途不再遭到敌方战斗机的拦截,那么战略轰炸将会更加有效;在盟军跨越英吉利海峡进行登陆之前,获得空中优势,不仅对登陆海滩,而且对获得整个西欧的制空权来说,都是一致认同的先决条件。空中力量对“霸王行动”的策划而言至关重要,也被正确地视为赢得地面战的关键。
事实上,就连希特勒也明白在登陆前线拥有空中优势的重要性;正因如此,1940年,即便当时他没有考虑过跨越英吉利海峡出兵,但他仍然让纳粹德国空军试图摧毁英国王家空军。不管怎样,对于“霸王行动”来说,在登陆前线获得空中优势至关重要,这样一来,盟军就可以在不受空中干扰的情况下登陆,而且在更远的内陆地区也需要空中优势。这是因为盟军意识到,尽管英国集结了数百万的兵力以及大量的武器和补给,但航运和港口的状况限制了在登陆日和此后登陆诺曼底的士兵和物资的数量。如果德军想要抓住机会把盟军赶回大海,那么德军就需要尽可能快地动用所有机动力量,发动一次协调反击。情报显示,德国在西线部署了10个装甲师和机动师,因此,对盟军来说,尽可能延缓、拖延和阻碍这些部队到达诺曼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法国抵抗运动扮演了关键角色,但空军将承担最为困难的工作,他们将在登陆日前的九个星期和登陆日后的几天(或几周)里,袭击桥梁、机车、铁路和任何行驶的车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动将由战术空军执行,也就是那些专门为支持地面行动而创建的部队。这些轰炸机速度更快,体积更小,安装有两个引擎,在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的支援下,它们可以在低空飞行。然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在低空飞行,必须确保空中没有敌机。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获得空中优势才会对盟军如此重要。没有空中优势,“霸王行动”就不可能成功。
然而,直到最近,这似乎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1943年秋,盟军面临的困境是如何摧毁纳粹德国空军,因为单靠轰炸显然无法达到目的,这主要是因为敌人的大多数工厂都位于德意志帝国的腹地,日间轰炸机,甚至夜间轰炸机都无法有效地抵达那里。当时,盟军迫切需要大量的远程战斗机。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意识到解决方案实际上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英国王家空军曾有机会制造远程喷火战斗机,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主要是因为轰炸机司令部继续进行夜间轰炸,而且利-马洛里,甚至是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 Portal)爵士漫不经心、缺乏远见。不过,在去年,美国制造的P-51野马战斗机就配备了劳斯莱斯生产的梅林61引擎,而不是原来的艾利森引擎,这使得战斗机的性能得到了惊人的改善,并且极大地节省了燃油。虽然这种战斗机增加了额外的燃料箱和可抛弃的副油箱,但对它的速度和灵活性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知不觉间,盟军拥有了一架航程近1500英里的战斗机,能够轻松地往返柏林。这是一项力挽狂澜的变革。然而,不幸的是,直到1943年夏,美国空军司令才意识到P-51野马战斗机的潜力。
那年秋天,盟军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制造足够多的野马战斗机,这样一来,局势便可以迅速发生决定性的转变。1943年11月,第一批完整的P-51B野马战斗机大队(即第354战斗机大队)抵达英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开始了第一次飞行任务。到了1月,第二批野马战斗机大队抵达;接下来,第三批以及已经成为传奇的第四批战斗机大队将在2月底取代雷电战斗机大队。3月和4月,还会有更多的野马战斗机大队抵达。
11月底,就在秋季危机最为严重时,盟军发布了一项新的指示——“论证行动(ARGUMENT)”。它旨在对纳粹德国空军和敌人的飞机制造工业发起全面的集中进攻,但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恶劣的天气像裹尸布一样笼罩着英国和欧洲,使进攻受阻。为了让“论证行动”取得成功,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高压天气,但直到1944年2月的第三周,天气才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在这个所谓的“关键周”,盟军屡次轰炸了纳粹德国空军的主要工厂,并尽其所能地将德国的战斗机引到空中。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战,尽管对德国飞机制造工业的破坏并不像最初希望的那样惨重,但“关键周”的真正胜利是打击了德国飞行员。仅在1944年2月,德国就损失了各种飞机共2605架,这个数字令人吃惊。德国完全承受不起这样的损耗;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逐渐减少,而新来的小伙子们还没怎么训练就上了战场,然后被击毙。到了3月和4月,有更多的飞机被击落。德国仍然每月生产数千架战斗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飞行员有效飞行和战斗的能力正在逐渐下降。就像纳粹德国的其他组织力量一样,纳粹德国空军也到了穷途末路。
与此同时,美国第8航空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经验丰富的骨干飞行员(例如“加比”·加布雷斯基)的保护。加布雷斯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城,他的父亲是一位波兰移民。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他便决定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天生的飞行员,差点儿被开除。在得到赦免后,他勉强过关,并被派往珍珠港。1941年12月,当日本袭击珍珠港时,他仍在那里,但后来他成功获得批准,被调往英格兰,并被调到英国王家空军。在那里,他曾短暂地加入第315中队,也就是波兰喷火战斗机中队。在美国第8航空队于1942年初抵达英国后,他被调回美国陆军航空军,并加入了第56战斗机大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那时起,他便成了美国第8航空队的王牌之一,不仅成了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还成了一名天生的领袖。正是在加布雷斯基等人的领导下,第8战斗机司令部在力量、信心和技能方面得到了迅速提升。
然而,随着“关键周”的结束,以及“霸王行动”的迅速到来,对于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应当如何使用派驻英国的美国第8航空队以及英国王家空军的轰炸机司令部,盟军进行了广泛讨论,甚至出现了恐慌。这两个都是“战略空军”,它们的创建、成立和训练都独立于任何其他部队。然而,自从1943年12月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霸王行动”的盟军最高司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到1944年4月,必须启动战略空军,以便直接为“霸王行动”提供支援。这引起了战略空军指挥官的深切担忧,尤其是美国战略空军总司令“图伊”·斯帕茨将军,以及轰炸机司令部的总司令、空军上将阿瑟·哈里斯爵士。两人都执着地致力于战略轰炸,并且都是相当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自从1942年初接管轰炸机司令部以来,哈里斯几乎完全自主地指挥自己的部队,他不喜欢让同僚或上级告诉他应该轰炸什么、在什么时间以及在哪个地方轰炸。确切地说,他更喜欢的做法是听取别人的建议,然后根据他认为最适合自己和参谋作出决定的一系列考虑事项,对目标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美国陆军航空军,斯帕茨仅次于亨利·“哈普”·阿诺德(Henry “Hap” Arnold)。到了1944年初,他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受到高度重视,对空军力量有了深刻的思考。他常带着一种聪敏睿智而又具有权威的从容神态。1940年,他作为第一个美国高级飞行员访问英国,赢得了极大的尊重。之后,他担任美国第8航空队的指挥官,随后在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战役中获得了地中海战区的关键指挥权。1月,他回到英国,成为欧洲战区级别最高的美国飞行员,指挥美国第8航空队和美国第15航空队。
对于如何最好地利用“战略空军”来支援“霸王行动”,哈里斯和斯帕茨意见不一。哈里斯认为继续打击德国城市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他的部队,而斯帕茨认为集中打击德国的燃料来源最有可能使德国的战事工作受阻,进而为盟军的登陆提供帮助。在所谓的“石油计划”中,斯帕茨的目标是合成燃料工厂以及罗马尼亚的普洛耶斯蒂(Ploesti),它是德国人获取石油的唯一油井。斯帕茨估计,这种持续的攻击将摧毁其80%的产量和60%的炼油产能。但斯帕茨不太确定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长时间。
另外,盟军副总司令、空军上将亚瑟·泰德(Arthur Tedder)爵士赞成运输计划,这个计划将袭击铁路、调度场和桥梁。这个计划概述的很多工作都将留给战术空军,因为他们拥有更小、更快的中型双引擎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可以在低空飞行,并打击较小的目标。重型轰炸机的袭击目标是法国和德国的主要城市的大型铁路调度场。盟军对哈里斯的轰炸机部队以所需的精确度打击目标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为此,哈里斯提出了抗议。就在一年前,这种情况还可能存在,但到了1944年春,由于导航技术的改进和标示战术的提高,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举个例子,1943年5月,第617中队摧毁了德国水坝,发挥了先驱性的带头作用,他们使用非常快速的蚊式战斗机在低空投放标示信号弹。
对于如何最好地利用盟军的重型轰炸机部队,人们争论不休,但事实上,关于目标优先顺序的意见分歧要次于涉及指挥系统的问题。实际上,所有的争论都与控制权有关,更具体地说,哈里斯,尤其是斯帕茨不愿接受空军中将特莱弗德·利-马洛里爵士的直接指挥,他们都不太喜欢他,更不愿把他尊为空军总司令。
利-马洛里是去年夏天被任命为“霸王行动”的第一批关键指挥官之一。从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之前挑选出来的一些指挥官已经被撤换掉了,但盟军远征军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继续任职。他是声明远扬的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的弟弟,1924年,马洛里在试图登顶珠峰的途中英勇丧生。利-马洛里是英国王家空军的职业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指挥过8个中队,也是致力于英美军队合作的第一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指挥过英国王家空军的军事合作学院。
在1940年的不列颠战役
 中,利-马洛里负责指挥英国王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第12战斗机大队;后来,他又在英国东南部获得了第11战斗机大队的关键指挥权;随后,他被提升为战斗机司令部的总司令。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他开始对盟军进行游说,以便让自己为即将到来的登陆获得联合空军的指挥权。1943年春,联合参谋部的成员、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爵士认为,就空中方面来说,在登陆日和此后建立滩头阵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持空中优势。英国和美国一致认为空军总司令应当从战斗机司令中选出,鉴于这个合乎逻辑的理由,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军队合作背景,盟军便让利-马洛里担任空军总司令。
中,利-马洛里负责指挥英国王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第12战斗机大队;后来,他又在英国东南部获得了第11战斗机大队的关键指挥权;随后,他被提升为战斗机司令部的总司令。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他开始对盟军进行游说,以便让自己为即将到来的登陆获得联合空军的指挥权。1943年春,联合参谋部的成员、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爵士认为,就空中方面来说,在登陆日和此后建立滩头阵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持空中优势。英国和美国一致认为空军总司令应当从战斗机司令中选出,鉴于这个合乎逻辑的理由,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军队合作背景,盟军便让利-马洛里担任空军总司令。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利-马洛里的自负、野心和讨好上司的本事也在这项任命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作为战斗机司令部的头头,他的总部位于伦敦郊区,距离唐宁街、航空部和陆军部只有一箭之遥。此外,1940年10月,波特尔成了空军参谋长,之后一直驻扎在伦敦,他对北非和地中海战区的战术空军的快速发展没有什么经验,也不太了解。而驻扎在英国的战斗机部队的司令利-马洛里便主动找上门,极力游说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
在被任命的时候,利-马洛里一直与美国友好合作,还使用短程战斗机为美国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护航。然而,到了1944年初,随着斯帕茨在英国担任美国战略空军的总司令,盟军开始对利-马洛里的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认为他不太善于团队合作,有点咄咄逼人,尤其是对同事和下属,而且倔得像一头骡子。在对他的战时生涯进行仔细考察后,盟军也产生了严重的担忧。他提出了“大编队”战术,即在不列颠战役快结束时集结四五个战斗机中队。尽管这个战术在心理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在战术上却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中队的集结时间要长于纳粹德国空军到达伦敦的时间,因此,在敌人到达目标之前拦截敌人的愿望便落空了。此外,他明知有些人提出的主张是错误的,但他放任不理,并一再削弱战斗机司令部的第一指挥官、空军上将休·道丁(Hugh Dowding)的权威,还策划了针对英国王家空军第11战斗机大队司令、空军少将基斯·帕克(Keith Park)的阴谋。这两人都被革职了,成了利-马洛里职业发展的垫脚石。随后,作为第11战斗机大队的指挥官和战斗机司令部的总司令,他私自聚藏了75个战斗机中队,导致盟军无法有效地在法国和西北欧使用战斗机进行作战。1942年春,他非常不情愿地最终同意向马耳他和北非派遣喷火战斗机,在那里,这些战斗机迅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要是他在1941年派遣这些战斗机,那么战果就会大不相同。即使在那时,他仍然顽固地拒绝向海外派遣新的台风战斗机和暴风战斗机,因此,没有一架这样的战斗机在意大利作战。
他也没有力促提高喷火战斗机的远程能力,如果他有这种意向和远见,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解决问题,改进喷火战斗机的远程能力。相反,派去法国的大量喷火战斗机只能执行短程任务,收效甚微,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德国空军非常狡猾,拒绝配合它们的空中飞行游戏。英国和美国幸运地拥有一些真正有才华且充满活力的空军指挥官,他们屡次证明自己是战术敏锐、有魅力、出色的盟军成员。遗憾的是,利-马洛里不属于这一类。
1943年夏,利-马洛里逐步开始担任“霸王行动”的盟军空军司令;8月,他是第一批获得正式批准以担任关键职位的人士之一。至少可以这样说,这项任命为时过早。12月,空军上将亚瑟·泰德爵士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副司令,直接听命于艾森豪威尔。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当然,这也反映了空中力量在登陆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泰德曾是盟军地中海空军司令部的总司令,在那里,他多次证明了自己的技能、远见、作战能力和机敏。更重要的是,他与艾森豪威尔的共事卓有成效,两人相处融洽;对于“霸王行动”来说,现在不是建立新关系的时候,而是要依靠已经建立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由于艾森豪威尔是美国人,那么他的副手应当是英国人。没有人对泰德的任命表示反对。
目前,盟军有两支战术空军用于协助登陆,他们直接受控于利-马洛里,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第一支是由刘易斯·布里尔顿(Lewis Brereton)中将领导的美国陆军航空军的第9航空队,布里尔顿也拥有在地中海指挥作战的经验。人们对他的整体能力存在疑问,但对于第9航空队战斗机司令部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指挥官埃尔伍德·“皮特”·克萨达(Elwood “Pete” Quesada)准将,人们却没有疑问。另一支是英国王家空军新成立的第2战术空军,把这支空军交给空军中将亚瑟·康宁厄姆(Arthur Coningham)爵士指挥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康宁厄姆是一位坚韧而又同样富有魅力的新西兰人,绰号“玛丽(Mary)”,据说这个名字派生于“毛利(Maori)”。很难想象一个如此富有男子气概的人会起这样一个不太合适的名字,但康宁厄姆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当然,他被人们广为所知的就是这个名字。
在盟军发展战术空中力量方面,康宁厄姆发挥了巨大作用。1941年秋,他接管了英国王家空军的北非沙漠空军,在泰德(他当时担任英国王家空军中东战区总司令)的积极支持下,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设想出为第八集团军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想法,从而帮助他们在沙漠中作战,他认为自己的部队应支援地面作战,但不应直接受控于陆军。他提议说,他的总部和第八集团军的战术总部应当并驾齐驱,和睦共事;不过,陆军可以提出具体的目标要求,但最终决定应当交给空军司令作出。关于这一点,他得到了泰德和丘吉尔的支持。
在得力助手兼参谋长、空军准将汤米·艾尔姆赫斯特(Tommy Elmhirst)的配合下,康宁厄姆也对沙漠空军的作战能力进行了磨炼,取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成果。他的中队能够在不同的空军基地以惊人的效率和灵活性向前或向后飞行,从而能够高效地保持队形。可以说,在1942年6月21日的加萨拉(Gazala)惨败和托布鲁克(Tobruk)战败后,正是沙漠空军挽救了第八集团军,使其免遭全军覆没。当第八集团军的残部撤退到埃及和阿拉曼战线时,沙漠空军没有放过追击残部的德国部队——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他们不分昼夜,连续不停地发起进攻,阻止了德军的前进,这不仅让第八集团军得以逃脱,也为他们在阿拉曼战线加强防御争取了时间。
在阿拉姆哈勒法(Alam Halfa)和阿拉曼战线赢得地面战的过程中,以及在第八集团军一路追击隆美尔的部队一直追到突尼斯时,沙漠空军的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炼。在那里,康宁厄姆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北非战术空军的指挥官,美国的拉里·库特(Larry Kuter)准将担任他的副手。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共同创立了战术空军学说,直到今天,这个学说仍然适用于近距离的空中支援。训练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低空飞行和俯冲轰炸技术是这个学说的一部分,不过,最重要的是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之间的通讯方法,这在本质上需要地面车辆中的陆军前进观察员与英国王家空军的地面控制员和无线电操作员协同配合。
在突尼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战术空中力量成了地面进攻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康宁厄姆、艾尔姆赫斯特和库特都推动发展这种力量,其他明智的空军指挥官[例如吉米·杜立特(Jimmy Doolittle)、“皮特”·克萨达等]也是如此。通过提高将地面部队的临时打击请求传递给空军的速度,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在作战和战术上都得到了不断改善。
因此,凭借开创性的见解、经验以及与泰德的长期合作,“玛丽”·康宁厄姆应指挥第2战术空军,这是非常合理的。“‘玛丽’·康宁厄姆头脑清醒、很有逻辑,”“皮特”·克萨达说,“在甄选人才时,最容易选的人就是他了。”布里尔顿将军也和泰德很熟,他拥有在中东战区作战的经验,这足以确保他能够继续指挥第9航空队,尤其是在克萨达担任第9航空队战斗机司令部指挥官的情况下。这些战斗机凭借其速度、敏捷性和不断增强的火力,在1944年成了地面攻击支援的关键部分,并将任何潜在的敌方战斗机——主要的防御飞机——挡在了外围。
虽然这意味着战术空军拥有坚定、强大的领导力,但对于战略空军的角色和指挥系统,以及他们在支援行动中扮演的确切角色,盟军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3月25日,在一次轰炸政策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会上,大家同意由泰德负责协调战略部队的行动,而利-马洛里将负责协调战术计划,这两人都将接受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这个措辞最终在4月7日得到了联合参谋部的批准。
艾森豪威尔受够了与战略轰炸机和空军指挥系统的作用有关的争吵和分歧,他私下威胁说,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那么他将辞职。3月25日,这两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不过需要获得参谋部的最终批准。艾森豪威尔支持运输计划,而不是斯帕茨的石油计划,因为很显然,运输计划为他的登陆部队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帮助。斯帕茨承认,攻击合成燃料工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果;而且,根据内容更加宽泛的“零秒战区”指示(该指示要求继续打击纳粹德国空军),斯帕茨没有理由不命令他的日间轰炸部队攻击这些目标和调度场。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石油计划是可以与运输计划并行不悖的。但事实上,斯帕茨还是很满意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在3月25日的会议后,地中海盟军空军总司令艾拉·埃克(Ira Eaker)中将与斯帕茨共进晚餐,埃克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老朋友和同事如此高兴。他向“哈普”·阿诺德汇报说:“英国和美国的战略空军不会受控于利-马洛里。运输计划优于石油计划,但‘图伊’对此并没有感到很不高兴,因为所有人都坚定地同意,打击德国空军将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然而,尽管战略空军现在似乎有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但大家还是感到深深的担忧,因为虽然有充分的理由使用重型轰炸机来炸毁调度场,但它们靠近市中心,这意味着平民——包括盟军计划解放的法国公民——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个过程中被杀或受伤。虽然近几个月来轰炸的精确度大大提高,但仍不足以避免从属伤害。轰炸法国人的做法让盟军的许多战事领导人难以安心,尤其是丘吉尔和他的内阁,他们对这个计划很慎重。4月3日,首相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考虑到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行为,会使盟军空军招到人们的极大仇恨。”
艾森豪威尔与泰德进行了讨论。两天后,艾森豪威尔答复说,利用势不可挡的空中力量是我们决定发起登陆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他写道:“我和我的军事顾问相信,轰炸这些中心将增加我们在关键战役中的获胜机会。”他还说,他认为平民伤亡的估算数字(大约高达16万)是严重夸大的。“现在,法国人民成了奴隶,”他对丘吉尔说道,“只有‘霸王行动’取得成功才能解放他们。较之于任何人,这次行动的成功对法国人来说更加意义重大。”盟军将竭尽全力避免伤亡,不过,他强烈地认为,如果任何行动能够显著提高登陆的成功机会,那么忽视这些行动就是“愚蠢至极”。1944年4月初,虽然盟军拥有巨大的物资优势,但从英国南部到诺曼底的跨海峡登陆行动,看起来仍是一项极其困难和艰难的行动。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作为整个行动的最高军官,“霸王行动”还没有达到探囊可得的程度。他肩上背负的责任重担是难以想象的。
*
4月19日,艾森豪威尔向斯帕茨授予了轰炸石油目标的直接权力,而美国第8航空队和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轰炸机袭击了调度场,甚至轰炸了塞纳河和默兹河上的桥梁。与此同时,战术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继续在法国和低地国家摧毁桥梁和铁路,并在发现敌人的任何活动迹象时进行打击。在广袤的西欧地区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既有助于支援“霸王行动”,也可以让敌人猜不透登陆的真正目的地。
4月19日,艾森豪威尔还同意将V-1飞弹和V-2火箭
 发射场作为更优先的打击目标。这些都是纳粹科学家研发的复仇武器。盟军知道这些武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将目标对准了位于波罗的海海岸的试验基地佩讷明德(Peenemünde)。自去年5月以来,他们一直都在监视正在法国北部建造的V-1飞弹和V-2火箭的发射场。“十字弓行动(Operation CROSSBOW)”
发射场作为更优先的打击目标。这些都是纳粹科学家研发的复仇武器。盟军知道这些武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将目标对准了位于波罗的海海岸的试验基地佩讷明德(Peenemünde)。自去年5月以来,他们一直都在监视正在法国北部建造的V-1飞弹和V-2火箭的发射场。“十字弓行动(Operation CROSSBOW)”
 于去年11月开始,专门针对这些似乎是为了直接攻击英国而建造的发射场。攻击英国已经算是够糟糕的了,不过,人们还担心,一旦盟军开始登陆,这些发射场将会转头对准诺曼底。英国人非常担心发射场可能造成的破坏,因此请求艾森豪威尔将摧毁它们排在其他空袭目标(“霸王行动”紧急要求摧毁的目标则除外)的前面。现在,他答应了这个请求。
于去年11月开始,专门针对这些似乎是为了直接攻击英国而建造的发射场。攻击英国已经算是够糟糕的了,不过,人们还担心,一旦盟军开始登陆,这些发射场将会转头对准诺曼底。英国人非常担心发射场可能造成的破坏,因此请求艾森豪威尔将摧毁它们排在其他空袭目标(“霸王行动”紧急要求摧毁的目标则除外)的前面。现在,他答应了这个请求。
与此同时,轰炸机司令部有力地反驳了哈里斯之前对缺乏准确性的担忧。5月19~20日夜,轰炸机司令部同时轰炸了布洛涅、奥尔良、亚眠、图尔和勒芒的铁路调度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20日,美国第8航空队对奥利、兰斯、列日和布鲁塞尔进行了狠狠打击。21日,也就是“查塔努加酷酷”行动的第一天,美国第8航空队声称摧毁了91辆铁路机车。5月22~23日,轰炸机再次袭击了勒芒和奥尔良。5月25日,美国第8航空队袭击了法国塞纳河沿岸的桥梁和敌人的空军基地。5月27~28日,亚琛遭到轰炸机司令部的猛烈袭击,其调度场遭到严重破坏,通过这条主干道的所有交通都停止了。袭击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进行着。
对于纳粹德国空军来说,这确实是黑暗的日子。他们曾作为先锋部队,带领德国在闪电战中取得耀眼夺目的胜利;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仓库,里面存放着大量日益落后的战斗机,他们既没有充足的燃料,也没有受过足够训练的飞行员。德意志帝国的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仍担任总司令,但他的前途早已黯淡,他对希特勒的影响力也在直线下降。不管怎么说,他更像一个称职的商人和马基雅维利
仍担任总司令,但他的前途早已黯淡,他对希特勒的影响力也在直线下降。不管怎么说,他更像一个称职的商人和马基雅维利
 式的政治家,而不是空军司令;和希特勒一样,他不断地改变计划和战术。
式的政治家,而不是空军司令;和希特勒一样,他不断地改变计划和战术。
在很大程度上,纳粹德国空军是由戈林的第二把手艾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元帅和空军总参谋部管理,尽管日常作战任务交由一些年轻能干的指挥官负责。虽然混乱局面在日益加剧,虽然希特勒提出了越来越不可能达到的要求,但这些指挥官仍拼命地想要力挽狂澜。4月21日,在一次关于补给和采购的会议上,年仅32岁的空军上将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了一名功勋卓著的王牌飞行员——警告说,盟军不仅取得了优势,而且几乎获得了制空权。他报告说:“如今,我们的1架战斗机要对付7架,而且美国人的战斗机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敌人的每次突袭都会使我们损失大约50架战斗机。局势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会撑不住的。”必须采取行动,他敦促米尔希和采购团队抓紧时间,尽快让振奋人心的梅塞施密特262战斗机投入使用。他认为,只有这种神奇的武器才能扭转空战的局面。
数量不断增加的美国日间战斗机让加兰德的战斗机飞行员应付不过来了:配备副油箱的雷电战斗机飞过欧洲西北部,野马战斗机则深入德意志帝国。22岁的沃尔夫冈·费希尔(Wolfgang Fischer)少尉是与盟军的大规模编队作战的人员之一,他是第2战斗机联队第3大队的福克-沃尔夫190战斗机的飞行员。他来自小镇瓦尔德图恩(Waldthurn),这个镇子坐落在巴伐利亚州古老的上普法尔茨森林(Upper Palatinate Forest)地区。1939年底,他加入了纳粹德国空军。虽然他最初没有被选中参与飞行训练,而是成了一名“执行一般任务的空军士兵”。在费希尔看来,这是最低级的职务。事实上,他在气象部门工作,负责破译盟军的天气报告,但他继续争取飞行员培训资格。1942年2月,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然而,直到两年多以后,他才最终被调到前线的一个战斗机中队,他先是重新接受训练,成了一名夜间战斗机的飞行员;然后被指派为临时教员。他写道:“这是一条漫长的、有时令人费解的道路。但现在,那条路终于被我甩在身后了。”不管过去的日子多么令人沮丧,较之于大多数刚被派往前线的战斗机飞行员,这么长时间的学徒生涯必定让他拥有了更多机会。现在,鲜有人能够像费希尔那样获得盲飞
 证书,或者在他们的飞行日志上达到费希尔那样的飞行时数。
证书,或者在他们的飞行日志上达到费希尔那样的飞行时数。
最初,他在意大利——纳粹德国空军的最后几支部队仍驻扎在那里——加入了第2战斗机联队第4大队。他驾驶着梅塞施密特109 G-6战斗机,和战友们被告知将飞往法国南部,但途中,他们遭遇了一些美国的P-39眼镜蛇战斗机,费希尔被击落。他跳伞逃脱,安全着地,然后被迫乘火车前往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在那里,他被调到第2战斗机联队第3大队,这个大队驾驶的是福克-沃尔夫战斗机,而不是109战斗机。5月1日,I集团军群被派往巴黎西北部的科尔梅耶(Cormeilles)。在将这里作为新的基地后,他们可以每天从空军基地飞向更往西的地方,通常每天飞行两到三架次,主要是为了袭击盟军的战斗轰炸机(德国人称为“Jagdbomber”或“Jabos”)。
一个星期后,德军又调派了两三支中队,这次是调到巴黎西北部博韦(Beauvais)附近的布瓦西勒布瓦(Boissy-le-Bois)。他们驻扎在一个豪华的小城堡里。如果不是因为长期弥漫着紧张和恐惧的气氛,费希尔可能会喜欢这里。每天早上,坐在送他们去空军基地的公共汽车上,他都忍不住去想第二天还会剩下谁。只有在空军基地的扩音器命令他们匆忙起飞时,他才会放下心头的恐惧。然后,地勤人员就会赶紧收回伪装网,把网从树上扯下来,费希尔就会爬上飞机,进入驾驶舱,开始行动。那时,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飞行上,他的头脑开始清醒过来。
5月25日星期四,是执行日常任务的日子,他和战友们正在飞行。他们紧急出动,意图拦截正在逼近的敌方轰炸机编队。他们向上爬升,发现眼前大约有120架B-24解放者轰炸机,在四个不同的区间飞行,周围至少有50架P-38闪电战斗机。费希尔的中队只有5架飞机。他们保持队形,继续前进,一头冲过B-24战斗机的外围。他们声称,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架轰炸机受损,开始脱离队形。尽管如此,德国的战斗机飞行员继续飞行,然后攻击一些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P-38战斗机。中队的队长沃尔特沙伊德(Walterscheid)少尉击落了两架飞机,费希尔击中第三架。“它的飞行员立刻跳伞,就像一个包得不是很严实的包裹从我的机翼下面翻滚落下”,费希尔说道。
然而,费希尔的一位战友遇到了麻烦。“开始行进!”费希尔通过无线电对讲机朝他喊道。“开始行进!”但这没有用。此时,更多架P-38战斗机聚集在他们周围。追踪者从他的驾驶舱前呼啸而过,他把操纵杆向前推,以几近垂直的角度俯冲下去。没有一个美国飞行员跟在他的后面,这让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飞回空军基地,并安全着陆,但是,只有另外两架飞机和他一起返回。几个小时后,他们在燃烧着的福克-沃尔夫战斗机的残骸中发现了另外两名飞行员的尸体。
在认识到以这种小规模的编队作战无法取得很大的成效后,5月的下半月,加兰德将军和第1战斗机师的指挥官“贝波”·施密德(“Beppo” Schmid)少将开始派遣由50~150架战斗机组成的大型编队,以便拦截盟军的轰炸机。这意味着,他们一次只能攻击一个编队,但这是对抗成群结队的美国战斗机的唯一方式,因为第8战斗机司令部在每次轰炸时通常派出多达600架战斗机。
5月28日星期天,就在登陆日的一个多星期前,美国第8航空队派出了850多架轰炸机,对关键的石油目标进行了两次空袭,这些目标主要位于德国东部的马格德堡(Magdeburg)和洛伊纳(Leuna)附近。在被派去护送它们的697架战斗机中,有56架是第354战斗机大队的P-51野马战斗机。虽然第354战斗机大队与第8航空队一起飞行,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从第9航空队借来的,并在登陆开始后重新回归第9战斗机司令部。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一直都在与纳粹德国空军较量,并且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王牌飞行员。
其中包括24岁的迪克·特纳(Dick Turner),他是第356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刚刚被提升为少校,正在领导着整个中队。他采用的方法与泽姆克上校的相类似,即把中队分成三队,由他们护送第3轰炸师的空中堡垒轰炸机,去轰炸位于马格德堡-罗滕湖(Magdeburg-Rothensee)的布拉贝格(Brabag)合成燃料工厂。于是,两队在轰炸机编队的北侧进行掩护,他的分队则在南侧飞行。下午2点前后,特纳将自己的红色飞机开到了30000英尺,以便进行高空掩护,而其他三个分队保持在22000英尺的高空。特纳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轰炸机编队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它们划过天空,留下一片航迹云。
他没有看到敌人的任何踪迹,但是,当大批德国战斗机从北面直接攻击第354战斗机大队的另外两个中队时,他突然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听到了令人激动的消息。他很清楚自己和中队不能放弃南面,于是,他们一边继续飞行,一边听着战友们陆续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兴奋地汇报战果。他后来说:“对于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来说,没有什么比只能听别人汇报附近的空中行动,但自己无法参与更加折磨人了。”
最后,战斗结束了,轰炸机击中了目标。但是,就在特纳准备返航时,他的僚机驾驶员发现了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一架敌机正朝他们飞来。这时,特纳命令他的中队进行拦截。当他们靠近这架飞机时,他对它的奇怪形状感到惊讶不已。无疑,这架飞机和他以前见过的任何战斗机都不太一样。它可能是纳粹德国空军的新型喷气式飞机或火箭飞机,也可能是当年4月开始服役的Me262喷气式飞机。不管怎么说,他的4架飞机都在盯着这架奇特的飞机。就在这时,它突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俯冲下来,然后绝尘而去,尽管野马战斗机的真实飞行速度超过了每小时400英里,但Me262在他们抓住机会追赶之前消失不见了。
特纳安全地返回英国,落地后,他仍在思考刚才在马格德堡上空的所见所闻。他发现,不仅第354战斗机大队,就连整个第8航空队也在这一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仅仅损失了9架飞机,美军击落和重创了78架敌机,18名德国飞行员被杀或失踪。更重要的是,最后一周的飞行表明,地面上被击毁的每架飞机都距离诺曼底海滩至少500英里。这意味着,纳粹德国空军的大部分战斗机部队已经被成功地赶回德意志帝国,无法插手干扰诺曼底登陆。盟军将在诺曼底的海滩和树篱发动更为广泛的战役,而空中之战便是这些战役的一部分。盟军取得胜利的关键踏脚石已经铺就。
对纳粹德国空军来说,5月28日是黑暗的一天。他们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接着,传来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加兰德和施密德等战斗机领机知道他们损失惨重,也明白他们失去了太多的飞行员,而且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程度。他们唯一的希望在于研发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型飞机,尤其是Me262喷气式飞机。但现在,就连这个希望似乎也被夺走了。5月23日,在伯格霍夫(Berghof)召开的会议上,元首发现米尔希一直在开发Me262喷气式战斗机。此前,希特勒曾要求把它建造成轰炸机。当他得知自己被愚弄时,他气疯了。对于希特勒的无理要求,米尔希也很生气,但他不是元首。5月28日(星期日)晚,消息传到了加兰德和施密德那里:一直以来,他们都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Me262战斗机上,但希特勒却下令从他们的辖区撤走Me262战斗机。“就德意志帝国的战斗机和防御来说,我们在喷气式战斗机上看到了力挽狂澜的希望,”加兰德说道,“但现在,我们不得不埋葬所有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