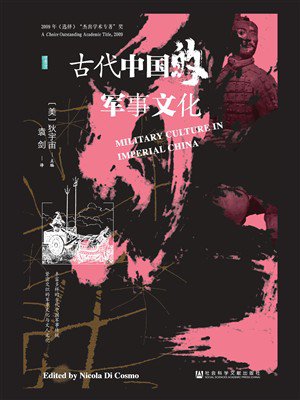第二章
军事预言
正如成千上万的甲骨所揭示的那样,占卜和商朝有着紧密的联系,各种各样的事项都要寻求肯定或祝福,尤其是战争。
 周朝继续用占卜来确定军事行动的吉凶,春秋时期,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蓍草,这种占卜方式最终被编入《易经》。
[1]
此后,对梦、预兆和异象的解释越来越多地补充了这些庄重的、高度仪式化的做法,在地位较低的人中间,尤其如此。
周朝继续用占卜来确定军事行动的吉凶,春秋时期,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蓍草,这种占卜方式最终被编入《易经》。
[1]
此后,对梦、预兆和异象的解释越来越多地补充了这些庄重的、高度仪式化的做法,在地位较低的人中间,尤其如此。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及吉凶的原始解释体系开始发展起来,
 在远征或进攻之前,人们仍然认为应该进行占卜以确定成功的可能性。
[2]
因此,战国中期的《六韬》规定,指挥机构应包括“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
[3]
在远征或进攻之前,人们仍然认为应该进行占卜以确定成功的可能性。
[2]
因此,战国中期的《六韬》规定,指挥机构应包括“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
[3]
此外,人类的恐惧加上权威操纵和宗派宣传,助长了人们对预兆和迹象的广泛信仰。墨子利用它们来进行论证,包括夏朝在内的三个传奇王朝的先祖在驱逐他们邪恶的前任之前,已经有天象预示:“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
 冲突开始时,出现了一个人面鸟身的神灵,夏朝开国君主禹才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
冲突开始时,出现了一个人面鸟身的神灵,夏朝开国君主禹才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
尽管汉武帝统治时期儒学在名义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且对占卜的质疑也时常可见,但汉代可以被视为占卜的鼎盛时期。特别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共鸣与回应,以及刘向在《说苑》中的表述,为越来越多的征兆信仰、四季和谐、占卜活动、新发展起来的《易经》与《易林》的使用方法提供了概念和理论基础。在种种方法中,官方强调五行、气、天体、历法体系,采用具有预测用途的体系来规范行政、仪式和农业活动,准确预测日食,从而化解其潜在的邪恶意义。
虽然怀疑的声音持续高涨,韩非子在《饰邪》中甚至用军事的例子来否认占卜的功效,但《史记》中关于占卜的内容引用了被普遍接受的历史先例,并重申了它的重要性:“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在汉代以后动荡的几个世纪中,部分由于玄学的推动和道教及佛教的最终兴起,无数占卜方法以及需要晦涩技巧、复杂观察和广泛知识的系统化预言信仰发展起来,包括扬雄神秘的《太玄经》、各种寺庙体系、高度复杂的历书和《灵棋经》。
 与日益增加的天文知识和详细记录相一致,以星相学为基础的预测系统对不稳定的行为、不寻常的结合和逆行运动日加强调,尽管有些仍然是纯理论的,甚至是虚构的。要闻和异象不仅被记录下来,而且被收到王朝的文献记载中,尤其是那些与五行有关的著述。然而,汉代以后,这些记载变得更为潦草,甚至在闻名遐迩的传记中相关事件也很少被提及。此外,从唐代开始,云与气的预言基本上局限于军事著作。
与日益增加的天文知识和详细记录相一致,以星相学为基础的预测系统对不稳定的行为、不寻常的结合和逆行运动日加强调,尽管有些仍然是纯理论的,甚至是虚构的。要闻和异象不仅被记录下来,而且被收到王朝的文献记载中,尤其是那些与五行有关的著述。然而,汉代以后,这些记载变得更为潦草,甚至在闻名遐迩的传记中相关事件也很少被提及。此外,从唐代开始,云与气的预言基本上局限于军事著作。
在军事领域,许多个体信仰被组织成一个独立的系统,专注于一个或另一个现象的表现。战国晚期《尉缭子·武议》中的一段训诫语显示了其多重性:“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
在庞大的中国军事文献——一个军事理论、战略和方法的知识库中,同样有大量关于宗教信仰管理、经济学和工艺史的材料,主要内容是各种占卜和预言体系。《太白阴经》是战国后第一部涵盖这些不同材料的文本,全书十卷中它们占了四卷篇幅;在宋代《虎钤经》长达430页的现代版本中,它们约占45%的篇幅;11世纪中叶由皇室主持编纂的军事知识百科全书《武经总要》总计2340页,它们在其中约占15%的篇幅;而在明朝末年完成的《武备志》十卷中,它们同样占四卷的篇幅。
最重要的系统是以星相学为基础的,尽管历法计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汉代已经出现的一些观点——在60年周期内的某些日期具有不利于人类的意义,或强调月亮盈亏及其与阴的活动的相关性——在几个世纪中迅速增加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类似的,五行作用的方式和复杂的《易经》衍生物也出现了,那些引人注目且容易看到的现象,如彩虹、风、彗星、流星、日食、雨和干旱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然而,最便利的可使用的做法是观察到被称为“气”的虚无物质,无论是其微妙的表现形式,还是其更显而易见的不断发展的形式如雾、汽、云、烟,都指示着当前和未来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