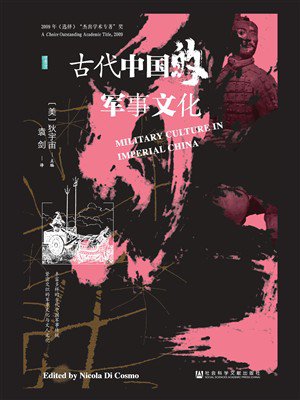气的观念和实践
气的性质和观念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尽管汉代在阴阳五行的范畴内对它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它被简单地理解为生命的“呼吸”或生命的本质,同时又有许多内涵,在不同的语境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包括作为普遍的形而上学的组成部分。民间传说“气”最初描绘的是从蒸饭中短暂升起的一缕水蒸气,它早期成了军队“精神”或活力的代名词。在《孙子兵法》的最初表述之后,气的运用迅速成为军事心理的焦点,致力于使自己的军队获得最大的成就,同时削弱敌人,使其容易受到巧妙运用战略力量带来的伤害。 [4]
《左传》中虽有一段描写春秋时期的将领操纵敌人的气的文字,但战国中期的《六韬》最早提出了气的分类,这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常被收录在后来的《武经七书》中:
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气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气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气出而东,城不可攻;城之气出而复入,城主逃北;
城之气出而覆我军之上,军必病;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用兵长久。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辅。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根据汉代的信仰,朝廷只有在初春阳气初起时才对来年进行占卜:“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
 那天早晨的风向会提供一系列的预兆,其中之一预示着军队的调动。
那天早晨的风向会提供一系列的预兆,其中之一预示着军队的调动。
《史记·律书》部分详细描述了一个基于六阳律的预言系统,它与季节性的气的最初变化相呼应。
 甚至连武王都认为他的行动与季节性的气相协调:“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
甚至连武王都认为他的行动与季节性的气相协调:“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
更重要的是,《史记·天官书》中的一段简短文字构成了云气预言的第一处文献记载。除了一些与周边民族有关的现象外,其影响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而且段落的大部分后来被纳入军事概略当中: [5]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余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
云气有兽居上者,胜。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恒山之北,气下黑下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徒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抟。前卑而后高者,疾;前方而后高者,兑;后兑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后卑者,不止而反。

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
气来卑而循车通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余里见。气来高丈余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
稍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
阵云如立垣。杼云类杼。轴云抟两端兑。杓云如绳者,居前互天,其半半天。其蛪者类阙旗故。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合斗其直。
这一小节继续描述与各种“蛮夷”和地区相关联的气,其原则是“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最后,它还告诫人们要观察任何进入城邑的“气息”,这是一种将气的观察与对城邑“精神”或活力的潜意识感知相结合的方法。
汉代竹简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习俗记载,包括本纪、志、方士传记等都保存了大量复杂且惊人的占卜实例,包括气的表现。
[6]
最著名的可能出现在东汉复兴的初期,据载,王莽派遣的两支共42万人的军队在昆阳包围了一支规模很小的汉军。自信不疑的将领们不时发起攻击,甚至拒绝对手投降:

昼有云气如坏山,堕军上,军人皆厌,所谓营头之星也。占曰:“营头之所堕,其下覆军,流血三千里。”是时光武将兵数千人赴救昆阳,奔击二公兵,并力猋发,号呼声动天地,虎豹惊怖败振。会天大风,飞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乱败,自相贼,就死者数万人。竞赴滍水,死者委积,滍水为之不流。……营头之变,覆军流血之应也。
随后,太白星进入太微,这是一个天文事件,准确地预示了继位者的军队进入王莽的宫殿,以及王莽随后被杀。令人惊讶的是,也许是为了强调云气的预测价值,《天文志》从未提及前一天晚上有颗流星落进了辽阔的官军营地,戏剧性地预示着他们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