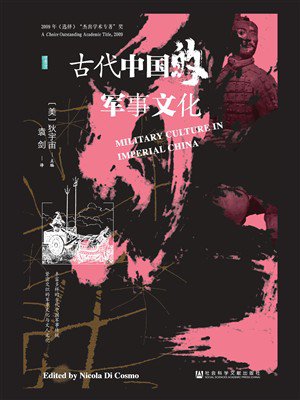历史背景
在秦朝建立(前221年)到王莽称帝(9年)的两个半世纪里,战争的概念及其目的与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战国诸侯为增强国力,以牺牲邻国为代价开疆拓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择手段,依靠说服、诡计、欺诈或使用武力。 [2] 他们的目的相对有限;他们的战术可能受到仪式考量的限制,就像服从战礼一样。王国的防卫可能会推进有限规模的城墙防御建设。 [3]
公元前4世纪,当诸侯中的一个开始攻伐邻国,并将其吞并后,更大的目标被提上议程。从一些当时所记录的报告中,我们或许可以明显看出战略思维的迹象。尽管这些报告的真实性不一定被认可,但它们可能揭示了政治和军事概念更为广泛的方面,这些概念设想的是长期目标,而不是眼前的利益。幕僚们可以建议君主着眼长远,谋划击败近在咫尺的敌人,或者选择攻击一个遥远的王国,而这个王国的沦陷能让那些位置更近的轻易投降。他们可能会制订战役计划,以在对敌人发动进攻之前获取经济资源或阻止敌人获得这些资源。这类蓄意的企图也许可以从一系列行动中看出,例如,秦国在消灭南方的楚国之前,首先试图控制巴蜀与西方的资源和交通线。 [4]
秦朝内部的起义伴随着漫长而混乱的战争,秦朝之前各国统治阶级的冒充者纷纷涌现,技艺娴熟的军队领袖日益崛起,刘邦和项羽的较量如火如荼。战争的进程和进行取决于领袖及其追随者的成败或忠诚的转移,而不是通过压倒一切的计划来打败对手并重建一个帝国。同样,在公元前202年之后,新皇帝不得不发起的军事行动有时是针对昔日支持者的,从本质上讲,这些战役是零星的,都是由可能或至少被认为会挑战刘邦权威的局部行动引起的;真正的危险在于其他族群,如匈奴可能会被引诱加入对新帝国的进攻。这种类型的战争,例如针对韩王信、韩信、卢绾、臧荼、陈豨的战争,可能是刘邦在紧急情况下为防止进一步的威胁而故意挑起的。他的计划建立在对新帝国所处局势的成熟考虑和战略评估基础之上。
高祖建立的帝国在两个方面受到威胁,每一个都可能需要用武力来解决。一方面,中原的大片地区都被皇帝的近亲所控制,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并可能会对皇帝的权威提出异议。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会要求继承皇位。另一方面,无法保证与居住在北方土地上的非汉群体保持和平关系;居住在北方王国和领地之外的骑兵或士兵很可能会闯入中原地域,对那里的民众、土地和财产造成伤害。
对抗诸侯王潜在不同政见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直到公元前141年武帝登基后,皇帝才动手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诸侯们的王国被分割成更小的王国,分别归属他们的儿子;或者,他们的部分领地被接管,作为直接隶属中央政府的郡。就这样,公元前143年,一条由中央控制的走廊或领地通道在东方诸国之间被开辟出来,从而削弱了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使之完全暴露在长安朝廷官员的势力之下。
然而有一次,为了维持帝国的完整,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变得十分必要,因为七位诸侯王联合发动反对景帝中央政府的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前154年)。周亚夫(前143年卒)率领汉朝军队平叛,他的反击表明他是一个战术高手。为了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他选择切断主要诸侯国吴国和楚国之间的补给线。他不顾皇帝的压力,拒绝派兵去帮助一直忠心耿耿的梁王,而选择了保留战斗力,来对付他的主要对手。景帝把护驾之功归于周亚夫。到公元前108年,诸侯国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对汉帝国安全的另一个威胁来自北方。这个问题确实引起了特别的反应,即秦朝通过持续驻军,构筑整体统一的防线。在汉代早期,朝廷希望建立覆盖北方和东部诸郡的弧形区,作为缓冲,保护内地,免受对财产、定居点和农田的袭击,并防止这些袭击渗透到汉朝的中心地带。这种希望或意图带有其自身的危险,正如高祖在臧荼(前202年的燕王)和卢绾(继臧荼之后的燕王)转投匈奴时所看到的那样。在汉军参与对抗这些敌人时,他们的行动和计划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比如匈奴接近长安城时(前166年)的情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汉朝朝廷能够以一种基于对问题和形势需要之评估的前瞻性政策,来应对这些危险。
所幸的是,公元前135年的一次观念交锋流传了下来。根据一些人的结论,多年来,匈奴的敌对活动有所缓和,汉朝和匈奴似乎都渴望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朝廷里的一些人不接受中原没有受到掠夺的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朝廷里的一些人不接受中原没有受到掠夺的说法。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她可能对公共决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她倾向于自由放任政策,而不是积极进取政策,很可能她的死引发了一种反应。记录在案的观念交锋,是在匈奴要求缔结条约(和亲)之后进行的;
 众所周知,这样的条约附带着汉朝政府必须满足的一些条件和支应的开销。
众所周知,这样的条约附带着汉朝政府必须满足的一些条件和支应的开销。

王恢 [5] 是燕国(今河北北部)人,公元前136年,他被任命为出使的负责人(大行令),他当时反对接受这一命令,因为他相信匈奴肯定会很快破坏协议;他建议派遣一支部队进攻他们。韩安国 [6] 在中央政府任职,他在公元前135年做到了御史大夫的高位。他建议王恢接受朝廷的命令,因为军事手段不太可能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
次年,没有官职的聂壹提出了伏击匈奴的建议。皇帝似乎被这个想法吸引住了。王恢支持这一建议,他认为,与以前相比,如今汉朝可以支配更强大的力量发动进攻,以震慑匈奴并阻止他们进一步的敌对活动。韩安国回应说,高祖曾在平城被匈奴军队包围(前200年),之后辗转逃归,他不但没有耽于愤怒,反而把帝国利益放在第一位,采取了绥靖政策;同样,文帝也签订了友好条约。
对于这些说法,王恢回复说,高祖的先例并不一定适用于此时已变化的情况。与以前不同的是,汉人现在在边疆地区伤亡巨大,采取进攻是正确的。韩安国对此不以为然。他强调,朝廷不应轻率采取这种行动。在遥远的过去,人们认为不值得牺牲民众的利益来占领如此遥远的土地或俘虏远方的民众。匈奴是一个勇敢的族群,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前进。作为牧民或猎人,他们没有永久的居住地,而且很难被管理。如果边疆农业发展中断,而非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受阻碍,那将是一个奇怪且不平衡的结果。
王恢接着列举了过去秦国抓住机会扩大疆域的例子。匈奴可以被武力压服,但不能以道德理想为基础来培养;可以用汉朝所能调动的一小部分兵力来击败他们。韩安国对在离本土这么远的地方发动战争能够取得成功,表示严重怀疑。
然而,王恢的话最终被采纳,他认为韩安国的观点无关紧要。他反驳说,自己并不是主张远征深入匈奴的居住地,而是建议把他们引诱到汉朝所挑选的有部队驻扎的地方,俘虏他们的首领。王恢的建议占了上风,他随后试图在马邑诱捕单于,但这次军事行动最终失败了。
可是,到了公元前120年,新的情况出现了。汉朝政府正以新的力量和决心治理帝国,一方面是因为消除了对于皇帝的内部威胁,另一方面是因为朝廷正试图协调经济实践。 [7] 汉朝从秦朝继承下来的长城防御工事,得到了在公元前127年形成的朔方和五原两个郡周围建立的新防线的加强。有了新获得的力量,汉朝就有可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深入中原以外的地域,这可以从卫青和霍去病所领导的坚决抵抗进犯者的行动(前124~前119年)中看出来。大约从公元前110年起,郡的建立成为向遥远西部延伸的基础,其中就包括敦煌。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