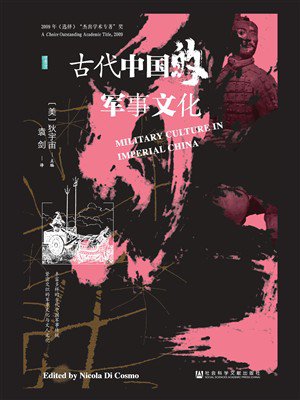军人管理
除了从公元前110年起极力扩展的西北防线之外,长安城设有两支部队,称为北军和南军。南军是由服役不超过一年的应征兵组成的。相比之下,北军则毫无疑问是专业的士兵;在武帝统治期间,北军由五个特别命名的校尉指挥。 [24]
西汉初期,帝国统辖不超过15个郡,这些郡位于长安城的南边、北边和西南方向,并稍向山东半岛东北部延伸。帝国其余区域也许是更大的一部分,以10个诸侯国的形式,托付给皇帝的近亲管理。随着各方面的探索性进展和某种程度的重组,到1~2世纪,共有83个郡或类似的单位,其中20个小王国作为飞地而存在。
郡的控制权掌握在两位高级官员手中,即守或公元前148年起的太守,以及都尉,
 他们的职位被列为级别很高的秩二千石。
[25]
太守的一名下属官员负责武器和马匹,但是,都尉被特别任命为太守的助理,负责军事任务和管理武装的应征入伍者。总的来说,他负责维护安全;在西北部,则包括部署防御工事。
他们的职位被列为级别很高的秩二千石。
[25]
太守的一名下属官员负责武器和马匹,但是,都尉被特别任命为太守的助理,负责军事任务和管理武装的应征入伍者。总的来说,他负责维护安全;在西北部,则包括部署防御工事。
西北防线是由战国时期的局部防御工事发展而来的,在秦始皇时期形成了统一的防御体系。在武帝统治时期(前141~前87年),防御体系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和加强,起初是在朔方郡和五原郡(前127年)建立了防御工事,后来又扩展到敦煌。
 很明显,从大致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年,这些防线是以高度系统化的方式被控制或整合的。在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个郡中,校尉控制着大约三个被称为“候官”的单位或连队,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名称,如“殄北”、“居延”或“广地”。
[26]
在候官的指挥下,一个连队大约有4~6个部,其中可能有10个燧;在他们(燧长)的领导下有2~4个燧卒。
[27]
据初步估计,总共需要3250名勤务兵来守卫帝国西北边陲从敦煌到朔方长达1000公里的防线。
[28]
除了以这种方式戍守的人外,还有总部的参谋和骑兵。目前还没有办法估计从防线上如居延等地区被派去从事农业工作(田卒)的义务兵人数;他们的职责是为朝廷在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建立的农业定居点工作;这些定居点大概会为驻军提供粮食。
很明显,从大致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年,这些防线是以高度系统化的方式被控制或整合的。在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个郡中,校尉控制着大约三个被称为“候官”的单位或连队,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名称,如“殄北”、“居延”或“广地”。
[26]
在候官的指挥下,一个连队大约有4~6个部,其中可能有10个燧;在他们(燧长)的领导下有2~4个燧卒。
[27]
据初步估计,总共需要3250名勤务兵来守卫帝国西北边陲从敦煌到朔方长达1000公里的防线。
[28]
除了以这种方式戍守的人外,还有总部的参谋和骑兵。目前还没有办法估计从防线上如居延等地区被派去从事农业工作(田卒)的义务兵人数;他们的职责是为朝廷在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建立的农业定居点工作;这些定居点大概会为驻军提供粮食。
防线由一系列的指挥所和瞭望塔组成,呈方形,并用堤道相连接。指挥所会提供维持传信系统(利用旗帜、烟筒或燃烧的火炬)所需的仓库并对设备进行安置和存储。这些建筑用晒干的砖块和稻草捆交错搭建;墙壁上可旋转的小木孔可以让射手在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下瞄准,以达到精确瞄准的目的。他们所装备的弩有各种不同的强度,根据装载所需的压力来确定。在扳机上标记的精确刻度使弩手能将箭发射到估计的距离。指挥所的外围被埋入了向上的尖刺,以防止敌人或野兽突然靠近。再往外一点,一片平滑的沙丘会让掠夺者或其他人在夜间从附近经过的举动暴露无遗。堤道将站点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受保护的通道,能够保证部队和其他旅客的安全。
在甘肃发现的文献残片 [29] 揭示了驻军执行任务的方式。仅能判断出来的是:他们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可以说具有专业水平,而且充分注意营房和瞭望塔的维修和保养;观察和报告敌人的动向;定期编写收发信号和通信的日志;遵守时间表;控制进入线路;检查设备和武器;维护常规信号;精确计算。他们的特殊技能之一是通过传“檄”来安排急件速递;这是一种特殊形状的长木条,刨得很平整,可以用来书写信息,上面还有一个凹槽,可以绑在骑马信使的马背上。 [30]
从西北防线发出的例行报告残片表明了军队的管理和控制方式。 [31] 并非所有这些报告都能测定年代,有些能追溯到公元前97年,有些则可能追溯到公元104年。它们涉及通信、军人的活动、军需问题、军人的警觉状态以及他们的设备状况,其中还有一部分历法和法令。
这些防线的成功维系有赖于纪律,发动进攻也是如此,但我们没有关于将领如何保持部下服从、如何防止兵员因叛逃而减少以及如何使他们保持战斗力的常规信息。不同的问题将影响到将领的这些职责,对于在周边防线的高级军官、从一个地区或营地到另一个地区的军队的军官以及那些积极参加战役的军官来说尤为如此。这里有一些提示。当周亚夫指挥抵御匈奴的战役时(前158年),他的军官们已经准备好去要求坚持某些预防性规则和程序,甚至要求皇帝本人(文帝)遵守这些规则。其他的将领就没有这么严格。
 武帝统治初期的两名军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公元前134年起,长乐卫尉、车骑将军程不识严格遵守军事规则和军事程序,剥夺了士兵们的闲暇时间;他同时代的未央卫尉、骁骑将军——李广,则以一种轻松的态度,不坚持这样的事情,这使他赢得了部下的喜爱。
武帝统治初期的两名军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公元前134年起,长乐卫尉、车骑将军程不识严格遵守军事规则和军事程序,剥夺了士兵们的闲暇时间;他同时代的未央卫尉、骁骑将军——李广,则以一种轻松的态度,不坚持这样的事情,这使他赢得了部下的喜爱。
 据闻,大约在公元前166年,西汉大臣冯唐向文帝提出了一项申诉,大意是文官在某些细节上过于严格,例如,在上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时,拒绝给予人们应有的奖赏。
[32]
据闻,大约在公元前166年,西汉大臣冯唐向文帝提出了一项申诉,大意是文官在某些细节上过于严格,例如,在上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时,拒绝给予人们应有的奖赏。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