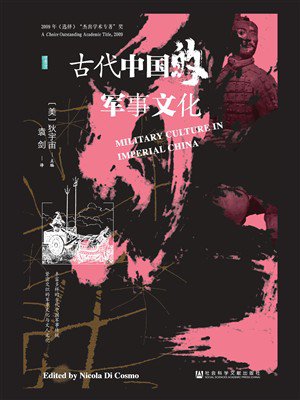战略辩论与权力的事实
我们已经讨论过主要战略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光武帝和他的儿子明帝在廷议上进行了严肃的辩论,而章帝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他们。然而,代汉和帝摄政的年轻的窦太后出于家族的政治利益,决定发动摧毁北单于的战役,并在强烈反对声中一意孤行。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协商,即使89~92年的战役取得了成功,却在大草原上留下了权力真空,为鲜卑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是一个重大错误。边疆的理想状态是:一个非汉人统治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掌权,他的命令在自己的疆域内得到服从,但他也能和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或者容易屈服于中原的权威,使他不得不制止自己的臣民制造麻烦或扰乱边疆。通过消灭北单于,汉朝除掉了一个潜在的威胁,但发现又要面临鲜卑的不断壮大,而南匈奴则被新的事务压垮。总之,汉朝消灭了一个弱小的、几乎是卑躬屈膝的敌人,让一个不能充分利用其胜利的小盟友得益,最终让一个更危险的敌人获取了最大的利益。 [34]
当然,人们觉得当时的信息易于获取:汉人的定居问题是众所周知的,且汉朝使者和其他人可以帮助判断南匈奴的能力,尽管距离遥远,但肯定有关于草原局势和鲜卑的情报。考虑到窦宪和窦太后的机会主义,了解边疆事务的人也需要谨慎行事。然而,恰恰相反,一些经验丰富的军官也有这种好斗情绪。尽管一些大臣认为保守派的观点很好,但他们的动机主要与朝中的道德和权力理论有关。正如张奂和一些改革派成员一样,他们对前线事务的兴趣是有限的。
在这里和其他场合,那些本该知道结果的人做出了错误的预估,造成177年的错误出征,再加上朝廷的政治压力(如外戚利益或宦官的影响)变得愈加严重,洛阳朝廷的边疆观往往与实地情况没有多大关系,最明显的是虞诩所指出的:他曾在西北地区服役,主张根据西汉的情况制定政策,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参照了《禹贡》的观念。他个人的理想主义无关紧要,但这种理想化的想法居然得到了受众们的欢迎,而且他的提议并没有受到更专业之人的反驳。
尽管朝臣一直讨论道德和公众利益问题,但几乎没有人理解或同情民众的未来。在这场军事角逐中,民众被迫留在边地或被逐出家园,然后又再次被迫返回。即使汉朝军队最终获得了成功,他们也没有过多关注他们应该保卫的民众。
朝廷对非汉族群的态度同样轻率,有时甚至是残酷的。无论作为敌人还是盟友,他们永远不是谈判的真正对象,而且很容易上当受骗或被背叛。
 我们也听说有官员真诚地对待非汉族群,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但这类人是例外,且段颎在2世纪60年代末进行的两次行动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然而,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几年后的184年,非汉族群和叛军的大规模崛起使凉州脱离了汉朝的控制。
我们也听说有官员真诚地对待非汉族群,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但这类人是例外,且段颎在2世纪60年代末进行的两次行动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然而,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几年后的184年,非汉族群和叛军的大规模崛起使凉州脱离了汉朝的控制。
从长远来看,无论成功与否,这场大战役都重创了东汉财政。进攻北匈奴的花销虽然没有被具体量化,但很明显,代价是巨大的;整个2世纪,朝廷都处于财政困境中。 [35] 后人面临的许多困难都可以通过预先准备而加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