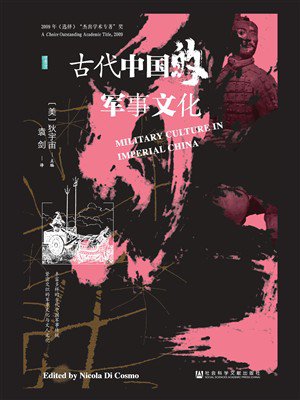导论
西方的军事史学家对于中国军事史专业研究的匮乏长期以来让人颇为感慨。一部近期出版的关于中国战争的作品的评论者将这一领域视为“远未开发”的,并热切地欢迎“实证研究”的出现,以平衡《孙子兵法》和中国军事经典得到的近乎全然的关注。 [1]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由于诸多作品的问世,尤其是在整体研究分类方面一些作品的出现,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深化。 [2] 两本论文集已经广泛收录了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军事史领域的一些最佳作品。 [3] 但平心而论,那些声称将军事史作为其主要专业领域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数量的增长,是一个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因为之前的几代汉学家并没有将军事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假如军事史学家一段时间以来认为,在军事史领域中国史无法与欧美历史相比较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有影响力的看法,即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天生对战斗和战争不感兴趣,所以很少或者根本不在意军事议题。
[4]
在雷海宗1939年出版的那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这种观念被解释为帝制晚期和20世纪的产物,并与“去军事化”(amilitary)甚或“非军事化”(demilitarized)的文化观念(无兵文化)相关联。
[5]
雷海宗的观点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儒家文化削弱了中国的战斗力,中国已经衰弱,对此观点已有相关分析,所以就没有必要再重申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帝制晚期与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信念。
[6]
在避免“无兵文化”这一术语引起歧义的前提下,
 我们仍然可以说,对这一术语的一般性理解,以及对其信仰的生成,在于中国的士大夫系统性地贬低了社会和历史中军事的地位,以致军事虽然身处政治关注的中心,但在文化领域被边缘化了。近代史学家可能会认为“反军事转向”(antimilitarist turn)的开始,导致了军民分离以及对唐朝(618~907年)中期至宋朝(960~1279年)初年甚至更早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军事职业的系统性低估。在未来的研究着眼于整个社会对军事的态度而非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对军事的态度之前,这种对军事在中国社会中所处地位的阶段性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另一个类似的观点是,中国的文化成就观念——其中最占优势的可能是孔孟哲学传统——对于毛笔的重视远胜于刀剑。在对外政策中,原则同样是和平优于战争、说服优于强迫,而武器和暴力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军事史学家正确地指出,在中国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文化中,至今仍然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中国对待战争的态度,自古以来就以“和平主义”和防御原则为主导。
[7]
我们仍然可以说,对这一术语的一般性理解,以及对其信仰的生成,在于中国的士大夫系统性地贬低了社会和历史中军事的地位,以致军事虽然身处政治关注的中心,但在文化领域被边缘化了。近代史学家可能会认为“反军事转向”(antimilitarist turn)的开始,导致了军民分离以及对唐朝(618~907年)中期至宋朝(960~1279年)初年甚至更早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军事职业的系统性低估。在未来的研究着眼于整个社会对军事的态度而非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对军事的态度之前,这种对军事在中国社会中所处地位的阶段性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另一个类似的观点是,中国的文化成就观念——其中最占优势的可能是孔孟哲学传统——对于毛笔的重视远胜于刀剑。在对外政策中,原则同样是和平优于战争、说服优于强迫,而武器和暴力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军事史学家正确地指出,在中国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文化中,至今仍然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中国对待战争的态度,自古以来就以“和平主义”和防御原则为主导。
[7]
自然,从这些假设中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种将使用武器的职业降级到人类活动外部边缘的文化,可能会使战争和士兵从历史的现实中完全消失。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中国历史,就很容易消除任何“非军事化”历史的概念,因为各种战争无处不在,从开疆拓土和对外征战,到内战、“统一”战争和防御战争。在宏观层面上,从历史的开端,就存在一个军事精英集团,虽然它已经有所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就像贵族、世袭阶级或专业集团),但它在镇压叛乱和建立王朝、保卫国家免受入侵,或者从事对外征战的事业中,继续发挥着核心作用。军事服务,不管是征兵、世袭还是义从,在任何既定的时间里都会囊括很大一部分人口。大众文学歌颂游侠、剑客、武术家和著名将领的尚武精神。遥远战争、森森白骨和血流成河的景象让人难以忘怀。文职官员经常讨论军事问题,涉及费用、战略、政策和武器。直到现代,人们还在继续阅读和评论古代的七大兵书。遗憾的是,许多军事著作已经散佚了,但军事著作仍然是一个专门领域,有时,例如在明代,依然有大量兵书著述。总而言之,中国历史当中各种军事事件、辩论和著述相当之多。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说中国文化作为一个集合性的主体产生了一种自我认知的话,那么,在根本上,这种认知与我们所认为的与民间或文学价值相对而言的“军事价值”(military values)并不一致,这影响了那些记录过去的人对军事事件的理解、记录、传播甚至是合理化的方式。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合理假设的是,中国历史上“战争”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战争的文化建设、军事活动,以及军人的角色、他们在社会和政治阶梯中的位置有莫大的关联。基于这一普遍的前提,为了集中讨论前现代时期军事事务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渗透程度,本书旨在通过关注军事文化(military culture)而不是试图探究中国军事史或战争史,来对中国军事历史研究做出贡献。什么是“军事文化”?这是一个需要加以定义的短语,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就像在欧洲或美国的历史语境中一样,这个短语存在多种用法和解释。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在不要求详尽的前提下,挑选出四个独立且截然不同的含义。
第一,军事文化是指一种离散的、有界限的行为和行为体系,由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惯例以及独特的信仰和符号组成,军队成员应该遵守这一体系。 [8] 第二,军事文化可以是一种战略文化,其中包括决策过程,它超越了军人的具体行为,包括那些在战略选择中所进行的知识积累与传播,并在民事和军事层面,基于这些论述验证其所处的位置,检查其既有的状况。 [9] 第三,军事文化可以被理解为一套价值观,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对战争和军事组织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例如,斯巴达可能被视为拥有比雅典更发达的军事文化。一些社会发展出一种对于军事(通常是进攻性的行为)的特殊偏好和意愿,这种偏好和意愿植根于许多民间机构,从教育到财政管理,不一而足。某些准军事组织(如童子军)和一些团体(在这里,我们可能会联想到护士或乘务员的培训和科层组织)的军事化社会生活也可以归因于灌输给整个社会的军事文化。 [10] 第四,军事文化指的是一种美学和文学传统,这种传统重视军事事件,并将那些完成军事壮举之人的地位提升到史诗和诗歌、绘画、公共庆典以及国家仪式中的英雄和半神的水平。
在中国历史中,研究军事文化意味着最重要的是努力在超越经验层级的基础上,去理解战争、社会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认识士大夫、平民和文学发展参与形塑军事机构的性质、军事理论以及战争文化的方式。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武”(军制、军事)的原则与“文”(文化、民事)的原则是对立的;虽然两者的意义还不完全清楚,但人们普遍认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作为两种对立但互补的人类行为方式,一种基于文化手段,另一种则基于武力。
[11]
此外,“武”经常与“蛮夷”和域外民族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在典型的相关思想中,以“文”“武”两种民族的二元循环关系来解释这些民族在面对外来军事力量时具有的暂时优势变得可能。这种相互交替的早期观念(预示着后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时期),在司马迁对其所撰《史记·匈奴列传》的评注中被确证,其基本原理是用以下的句子来解释的:“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军事上的担忧是最重要的,因为匈奴着实令人畏惧。
军事上的担忧是最重要的,因为匈奴着实令人畏惧。
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第十二章中所指出的,清朝统治者利用他们的“武力”来强化其作为统治者和统治族群地位的合法性。同样,在与北方袭掠的关系方面,“文”和“武”被用来描述有文化的、“非军事”的南方和陷于混战的北方。多元二分法揭示了“武”的原则在多元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定义和演进所产生的影响。
尤其是在西方,对于前现代中国军事及其多方面的社会和文化影响相对较低的学术兴趣,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即中国军事史领域的理论化程度较低,以及中国军事史学家为了专业的标准化,可能被迫与西方玩追赶游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假命题。任何成熟理论的进步,只能通过对中国文化与战争实践的特殊演进过程加以更大关注而获得,故不能寻求纯粹运用西方化的衍生理论,因为它们所基于的社会研究与中国的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在西方和欧洲语境下成熟的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提供可对比的材料和一些理论模型,以供批判性评价。例如,纵观中国的社会历史,认识到武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必要的,而在理论层面上,这不仅没有得到充分考虑,而且被有意识地边缘化了。历史学家很难找到一种与帝制中国社会历史相关的理论,来揭示军事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2] 即使是对朝代兴衰的陈腐解释,也通常更多地关注民间事件,而不是军事原因。“唐宋转型”这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仍然是一种对于中国历史中出现的“现代性”加以阐释的主要范式,它对军事结局几乎没有分析,尽管安史之乱(755~763年)作为一个高潮性事件,在中国和欧亚历史中都产生了深远和持久的影响。 [13] 与此同时,一旦我们将军事图景纳入考虑范围,那么,同样的唐宋转型论就较少被视为重大历史的分水岭,因为中国军事组织的变化,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既不是革命性的,也不是前所未有的,而是一些压倒断裂性的连续性要素。 [14]
西方则恰恰相反,从罗马帝国的军事化和战略文化,到中世纪的骑士社会,再到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革命,军事史对社会变革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近代早期欧洲受教育的圈子中,贵族阶级定义了某种类型的男性模式和状态,而作为优秀之人的最终追求,罗马理想中的勇气和知识相融合所引发的力量有时会被那些对武术教育的优势加以肯定的人质疑,例如蒙田(Montaigne),他对帖木儿和其他蛮族的评价很高,因为他们具有优良的战斗技能。 [15] 如果贵族被认为只把文字看作武器的次等附属品的话,那么,对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正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非常清楚地指出的那样:“一个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或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事业。” [16] 当然,有些人对此表示反对,并拥护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学习和教育的蛮力最终与野蛮无异,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军事活动本身是失礼的,或者不适合有自尊的绅士。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些深入的研究试图对军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与自我形象加以界定,但结果喜忧参半,并受中国历史编纂学对个人“褒贬”评判特质的影响。 [17]
这种对欧洲和中国之差异的简要描述,表明了机械性的比较方法的局限性。在讨论亚洲和西方的军事历史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等权威人士发现,“西方的战争方式”以四个独特要素为基础:先进的技术、优良的纪律、军事传统的延续以及挑战与回应的循环。 [18] 虽然“中国的战争方式”也可能包括传统的延续,例如,内嵌于军事经典之传播和讨论的传统,但我们很难就中国能与西方共享的其他特征达成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我们很难罗列出一个像帕克所给出的那样被西方历史学家广泛接受的清单。相反,中国军事史的具体特征是难以识别的,因为它们还没有通过军事历史和文化的系统研究而被呈现。在中国和西方,军事历史上的“变迁”概念不能被认为是相同的,也不能被明确地识别出来。例如,直到19世纪为止,西方语境中对于技术的强调,在中国语境下似乎是错误的,当西式武器开始进行工业化生产时,中国军事现代化这一更广的议题变成了某种变革的关键。 [19] 军事变革肯定会在中国的历史中发生,在战争时期,它可能与军事机构和组织形成了更密切的联系。 [20] 的确,从本书的若干章节中可以得出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军事领域的连续性特征似乎不同于民事领域的连续性特征。军事习俗、仪式、世袭军事精英的形成、军事法规、组织原则和文化习俗的传播,可能遵循各自的发展轨迹,可能彼此相关,但又依赖社会和知识层面的变迁。这些见解,如果得到证实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历史上人们看待变化的方式的理解,不管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标准。
对中国军事具有明确影响的一个因素是,从中国历史记载的源头开始,亚洲腹地与中原之间跨越文化边界的互动一直都被视作尚武族群的摇篮。统治中原或者与中原关系密切的王朝(如北魏),无疑对军队的组织结构及军队作为战斗和社会力量的功能的改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蒙古人建立军户世袭制的做法,在明朝社会中仍然是一股重要的潜流,尽管此时文官势力重新确立了对军队的主导地位。然而,在明代政治家和决策者的辩论中,军事行动、著作和制度仍然占据很高的地位。正如石康(Kenneth Swope)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明朝并不代表中国军事传统的最低点;它是由军队建立和维护的,在王朝接近灭亡时,军队依然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21]
只有通过对比亚洲和西方的军事史,而不是寻求相似之处,比较方法和共同情感才能最有成效地发展;但在建立比较基础之前,仍有必要在广阔的中国历史范围内,确定研究中国文化之军事方面的具体路径。本书各章所提出的一种共识是,军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从西方传统借用,以获得广泛兼容的模板。
中国军事史特殊和鲜明的特点,始于对军事事件之历史叙述的特质,书中的许多章节都对此有所强调。一般的庆典或讨伐、巨大的胜利或惨败、关于既定的战争及其准备的政治讨论,以及战争的结果——结束敌对状态,通过协议或重组边地防御,或者攻占土地并降服敌人——在各个层面都要高于对军事行动的任何实际描述。借用约翰·基根(John Keegan)那句有用的话来说,“战争的面貌”(face of battle)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中国的历史叙述当中。在某些情况下,各朝的历史都允许对战争进行全面的重塑,但中国军事史学家可以使用的史料来源与西方传统的资料来源完全不同。中国庞大宏富的文学和历史作品,以及悠久的军事写作传统,可能会合理地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关于军事的信息一定很丰富。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对资料来源进行充分的挖掘或探究,以获得完整的答案,但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一般人必然会像我们在西方看到的那样,对军事知识进行细致的注解、描述、分析和传播,这是不正确的。历史经典著作是不同的,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考虑到这些差异,指望中国的军事史沿着完全基于西方经验的军事史发展路径前行,则是不合逻辑的。
最后应该提到的一点是各章节的时间范围,也就是说,特别关注古代中国时期,为此,我们将其定义为大约从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800年。叶山(Robin D.S.Yates)和苏炀悟(Ralph D.Sawyer)的两章(分别为第一章和第二章)都跨越了前帝制时期和帝制时期的传统界限,即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在另一端,本书实际上结束于乾隆统治时期(1736~1795年)。应该补充指出的是,由于直到最近,中国军事研究的两大趋势,一方面与军事经典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西方的影响”有关,所以前帝制时期(前1500~前300年)和帝制晚期及现代时期(尤其是1800~2000年)比帝制时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对帝制时期加以特别关注,有助于在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军事史的影响,虽然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葛德威(David Graff)的《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300~900年)》( Medieval Chinese Warfare:300-900 ),但这些领域的研究依然落后。
本书所包含的章节不拘一格,但集中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集中于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通过作者的专业化和知识取向来加以呈现的。他们共同呈现的复杂多样的军事文化阐释模式,显示了军事视角与中国历史的关联性,并探索了融入社会、政治、文学和艺术的军事文化元素。
通过观察军事在社会中的地位,一些作者分析了民间和军事领域在历史上的联系。例如,在第一章中,叶山阐述了军事法和民法之间深刻而动态的联系。在第十三章中,戴英聪探讨了清军的财政状况及其与清朝财政管理的关系。第二个相关的主题是知识趋向和宗教信仰对军队的影响,这在苏炀悟和S.R.吉尔伯特(S.R.Gilbert)的章节(分别是第二章和第十章)中可被明显看出,而在韦栋(Don J.Wyatt)的研究(第八章)中也有所共鸣,他从个人和传记的角度探究了对军事的价值观、职业、知识和经验的认知。关于第三个主题,鲁惟一(Michael Loewe)(第三章)、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第四章)和戴德(Edward L.Dreyer)(第五章)对帝制早期军队的组织和作战以及对关于某一军事行动的辩论、批准、计划和实施等进行了论述;而在戴德所撰写的章节中,政治和军事行动的结合经由一项细致的历史重构工作得以呈现。第四个主题,涉及军事事件和军事“价值观”在非军人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如第九章赖恺玲(Kathleen Ryor)对于明代刀剑收藏的研究,以及第十一章方秀洁(Grace S.Fong)对明清鼎革间关于战争和暴力之文学的贡献。第五个主题是关于我们研究军事史的历史敏感性和具体资料有效性的问题,其中包括对文献资料中军事事件的建构;在戴德所撰写的第五章以及葛德威的第六章中,我们找到了传统文献如何呈现军事事件的例子。最后,有几章讨论了政府与对外关系领域的军事文化;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第七章)、卫周安(第十二章)以及濮德培(Peter C.Perdue)(第十四章)描述了“军事文化”在政策制定、边疆管理和政治精英的自我表现方面的显著特征。
在第一章中,叶山通过对前帝制时期和帝制早期军事法的历时性研究,有力地论证了军事法对中国早期刑法典的影响,揭示了军事文化如何渗透到民间领域,并影响了帝制早期军事制度的形成。在战国时期(约前475~前221年),军事法的原则在法家的思想中被作为模式加以运用,并被应用于平民,如连坐和通过奖惩来规范行为的一般观念等。此外,在很大程度上以军事法为基础的刑法,最终被文官用来管理社会的军事方面。军事法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关于军事编队、仪式和内部纪律的规定,深受当时的文化信条——如宇宙观、传统道德、占卜术以及相关思想——的影响。对这些资料来源的仔细分析表明,帝制早期的军事文化与早期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密切相关。
苏炀悟在第二章中阐述了从战国时期到东汉的军事预言,也就是从哲学思考和思想体系演变的角度来解释或预测各种与军事相关情况的方法。通过对军事经典和其他历史文献的挖掘,苏炀悟展现了丰富多样的“超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在作者的思维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习语,通过对它的解读,行家们可以做出预测。预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关于“气”的问题。“气”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品质,它对军事的成功至关重要。正确地预测自己和敌人的“气”,是衡量军队相对实力的核心。观察“气”——在物理上可以表现为识别蒸气和云的形式——并了解其运动的方式,启发人采取正确的行动:进攻或撤退、谨慎或激进。这些预言方法是在战国晚期和汉代的相关思想框架下发展出来的,类似于阴阳五行体系的物理变化理论。军事事件与某种世界观并不相关,这种世界观相信形而上学原则以及物理现象的内在统一和相互依存。苏炀悟认为,这些体系可能会减轻战争和破坏带来的焦虑,从而提供一种对自己军事命运的掌控方式。这或许可以解释这些观点的生命力,尽管人们怀疑它们是否在实际的战争行为中发挥过作用。然而,这些预言所适用的范畴和支撑这些预言的哲学原则,向我们揭示了古代中国军人的心理世界,他们可能不相信或不会实践这些预言,但也不可能完全忽略这些预言。因此,它们为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增添了重要的元素,体现出对哲学思辨思想的渗透。
如果说西汉的军事史比其他朝代的更广为人知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鲁惟一在这一领域的基础性贡献。 [22] 在本书的第三章,鲁惟一对汉朝军队的情况进行了概述,强调其战略和战术方面的表现。鲁惟一指出,战斗的细节描述、士兵人数、实地军队的调动、地形、部队的士气、经验和军备、他们所面对的敌人以及所有其他要素,往往难以获知,因此无法对军事事件进行全面的分析。然而,帝国军事结构的实质及其演变,可以通过朝廷的政策来加以描述。从对行政事务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从战国到汉朝,军事思想对边防,特别是将帅所产生的影响。针对汉朝军事文化的问题,鲁惟一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汉朝军队能否被定义为“专业”军队。这一问题为我们论述中国军队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尤其是因为它需要与西方历史学家关于军事组织的争论进行比较。例如,当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等著名军事史学家谈到“远在这一千年(也就是第二个千年)中叶之前的中国和古罗马,就存在由国家控制的专业军队”时,这一定义当然也包括汉朝军队。 [23] 但是,东汉时期普遍兵役的废除,意味着专业素质的重大转变,不管是从训练到等级制度,还是从纪律到招募,都是如此。 [24]
在第四章中,张磊夫更恰当地从“战略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东汉军事文化的问题,这些战略文化涉及北部边防,特别是对匈奴和羌人的战争。这章在开头概述了东汉时期的军事建设,接着阐述了从1世纪中期到2世纪末关于东汉边疆战争的争论和政策。
军事行动建立在对局势加以评估和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讨论基础之上,这些政策可能涉及军事、对外交往或政治行动。从张磊夫对东汉北方战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在涉及北部边疆的问题上,政治家的特定目标和可用信息的质量,与嵌入古典传统的既定原则和标准观念相比,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廷臣和军事指挥官所采取的“试错”性质的务实立场表明,在军事文化中,灵活性和现实政治与更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发生了冲突,在这种立场下,朝廷会诉诸相对“蛮夷”而言具有优越性的旧观念。中国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通常取决于对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以及各自希望达到的目标所做的评估。然而,对东汉与匈奴战争的分析表明,“鹰派”和“鸽派”在争论自己的观点时,必须考虑各种因素,从对不可靠盟友的承诺到财政压力,不一而足,但正如张磊夫指出的那样,朝廷的政治影响力是其军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涉及对非汉群体使用武力时。汉朝战略家对匈奴的所作所为,指向一种战略文化,它遵循一种基本的实用主义路线(这种态度接近濮德培在第十四章中提到的“实践逻辑”),但也被一种超越了直接关注和特别分析的逻辑所引导,有时会转向一种更加意识形态化的路线(濮德培称之为“理论逻辑”)。无论我们把这种辩证对立称为“实用主义VS意识形态”,还是“实践逻辑VS理论逻辑”,在制定战略决策时,这两种原则,一种更具动态性和适应性,另一种更具静态性和刚性,似乎很明显是相互对立的;但最终真正削弱东汉军事力量的,是经济资源的分散和朝廷军事权威的逐渐瓦解。 [25]
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出版了第五章,也就是戴德所写的那一章,作为他身后的贡献。他的突然早逝,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在军事史领域,他是真正的先驱之一。与此同时,让我们深表感激的是,他的学术遗产将包括收录在本书的这篇文章,它是一个结构紧密的章节,分析了西晋的“八王之乱”。这场混乱发生在4世纪初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别关键的转折点上,见证了统一帝国的加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近三个世纪的分裂和动荡时期。正如第三章和第六章所指出的那样,第五章对事件的处理几乎完全集中在战略讨论上,特别强调各方采取的战略和明智决策。通过对这一重要军事事件细致而下苦功的重构,戴德对王朝贵族的内部运作、统治精英的军事化、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渗透性,以及军事优先进入政治话语和修辞的方式等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五章还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清晰方式,举例并罗列出我们可以拼合起来理解军队数量、行动以及军队结构的信息类型。关于战争的叙述也检验了官方史学惯有的局限性:在这里,除了最基本的信息之外,对战争和战役的完整描述完全超脱于传统的历史写作。
在第六章中,葛德威直面了军事事件在正史中表现形式方面呈现的潜在问题。葛德威指出,正史记载常常包含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军事信息,因此他考察了这些记载的主要来源。许多此类文献的文学性质,类似于圣徒传记和选集,并不适用于传递事实;相反,这些文献是为了颂扬一位将军的美德,宣扬一项军事功业的价值或唤起军队的士气。其他的文献,如“行纪”、诔碑文和赏赐法令,同样没有包括具体战争的相关信息。通过分析这些材料,并将其与正史的叙述进行对比,葛德威认为,唐代和之后的文学世界,从根本上远离了战场。胜利是通过写作来庆祝的,但写作本身是一种非常文人化的文学传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宣战文书与军令(“檄移”)收录于刘勰(522年卒
 )所著的6世纪著名文学批评作品《文心雕龙》。在“檄移”一篇(第二十篇)中,刘勰大量引用了《司马法》《国语》《左传》《史记》《尚书》等经典著作,描述了这些著作的文学性质,同时规定了宣战文书和军令既要为文学(文),也要为军事(武)服务。许多文化都用华丽的修辞来歌颂士兵和将帅。例如,希腊的赞美诗是为庆祝胜利而创作的,但与战场经验或战斗几乎没有关系。中国的文学作品似乎被文学范式所主导。用葛德威的话说,在正史中经常发现的细节,暴露了儒家对军人的蔑视。他们强调所要求的技能中最为哲学的部分,如运用巧妙的计谋和制订出色作战计划的能力,而对实际实力、武器、经验和战斗技能的讨论则停留在一种道德的半模糊状态中,这并不一定会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这种文学上的偏见,似乎在中国文学中比在西方传统中更为根深蒂固。然而,从战场上脱离出来,并没有消除一切军事力量,而是出现了一种表现模式,与文化阶层的文化原则相一致。葛德威关于战争的现实与其表现之间关系本质的基本论点,可以被用来发展更复杂的理论模型,这也许是一种民族志类型,可能会使进一步探究在官方叙述的汇编中起作用的文化过滤机制成为可能。
)所著的6世纪著名文学批评作品《文心雕龙》。在“檄移”一篇(第二十篇)中,刘勰大量引用了《司马法》《国语》《左传》《史记》《尚书》等经典著作,描述了这些著作的文学性质,同时规定了宣战文书和军令既要为文学(文),也要为军事(武)服务。许多文化都用华丽的修辞来歌颂士兵和将帅。例如,希腊的赞美诗是为庆祝胜利而创作的,但与战场经验或战斗几乎没有关系。中国的文学作品似乎被文学范式所主导。用葛德威的话说,在正史中经常发现的细节,暴露了儒家对军人的蔑视。他们强调所要求的技能中最为哲学的部分,如运用巧妙的计谋和制订出色作战计划的能力,而对实际实力、武器、经验和战斗技能的讨论则停留在一种道德的半模糊状态中,这并不一定会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这种文学上的偏见,似乎在中国文学中比在西方传统中更为根深蒂固。然而,从战场上脱离出来,并没有消除一切军事力量,而是出现了一种表现模式,与文化阶层的文化原则相一致。葛德威关于战争的现实与其表现之间关系本质的基本论点,可以被用来发展更复杂的理论模型,这也许是一种民族志类型,可能会使进一步探究在官方叙述的汇编中起作用的文化过滤机制成为可能。
在第七章中,斯加夫谈到了中国军事文化的一个经常有所体现,却很少得到应有重视的方面,那就是中原王朝从域外文化,特别是从亚洲腹地文化借鉴的内容。与战争和军事远征有关的域外族群在最早的文字,即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最常提到的一些“蛮夷”,因其好战而著称。“戎”这个术语在古代经典中指的是域外族群,已经被理解为“武力”和“军事”的同义词。《史记》中对匈奴的描述是“以战攻为事”,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作为“军事族群”的说法贯穿了整个中国传统史学。斯加夫认为,唐朝的军事文化直接受到了亚洲腹地传统的影响。由于边疆防御对于王朝统治和领土完整的维护是如此重要,所以,考虑到中原王朝和草原汗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吸收与融合亚洲腹地军事文化这一渗透性的过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争论可以很容易地延伸到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时期,因为每一个主要的中原王朝(汉、唐、宋、明),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或多个草原势力。因此,斯加夫论点的含义超出了唐朝,他同时指出,存在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整体性的军事文化,它们在中国历史中不断发展并相互影响。游牧民族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前一直是中原地区民众面临的最大军事威胁,他们制定了特殊战略,而这些特殊战略促进了中原军队战术和行动的发展,特别是在7世纪,北方的军事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统治的基础。斯加夫以他对唐朝军事史的既有研究为基础,从唐朝边疆军队的组织和作战方面入手,转而研究唐朝早期军队的文化特征,认为它将中原和突厥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高效的共生关系。 [26]
在第八章中,“文”与“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韦栋对宋代三位军事人物之传记的评述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这三人分别是柳开、范仲淹和童贯。他们的生平,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和事迹,推翻了当时流行的观念,即在宋朝,军人和文人官僚之间存在严格的区隔。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活跃于宋朝早期的柳开以其学术成就而著称,曾多次被征召担任军事指挥官;最终,他被描绘成一个充满野性、看似无拘无束的人。在对柳开行为的描述中,有很多野蛮行为的暗示,这可能表明他的军旅生涯与失礼行为之间只有一纸之隔。但是,正如韦栋所指出的,这种对人物的描述可能反映了王朝初创的那个暴力时代,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那一代人的情景,那时,粗暴野蛮和学术成就(柳开是进士)并不被视为水火不容。在宋代文化中,随着字面上的记述被理想化地加以分离,文与武、文学成就和军事事迹日渐两分,范仲淹和童贯的形象也愈加深化。
范仲淹也是一位进士,应时代之变,他从文官阶层中迅速成长起来,应对各种挑战,在为对抗西夏的军队服役时,成为军事智慧的典范。在中国历史上,像范仲淹这样因长期担任军事职务而成就英名的高级政治人物的例子绝非罕见,这是文官事业和军事责任、知识和经验的共生关系的缩影,而这种共生关系,我们常常能在著名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传记中发现。
韦栋的第三个案例所关注的是,在北宋历史上最为痛苦的时刻,一位复仇心切的皇帝的突发奇想,导致了童贯的垮台。童贯的职业生涯揭示了政治权力和军事领导人之间不稳定关系的另一面。军事领导人既可以被视为忠诚的典范,也可以被贴上懦弱无能的标签,我们必须假设,只有少数人的形象能在其死后得到恢复,这要感谢史书的编纂者在理论上所宣称的据事直书理念。在韦栋对这三个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于北宋朝廷与其军事方面关系的比喻。即使是最“文”的朝代,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体现在北宋杰出军事人物行为中的军事精神以及对他们同时代人的评价和历史判断,这些评价和判断反映了一套关于军队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价值观和信念,这不仅是军事文化的一部分,更是文化本身的组成部分。
与韦栋的章节相关的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傅海波(Herbert Franke)对马扩的研究,傅海波的研究并非基于王朝历史,而是基于马扩的自传。 [27] 马扩是童贯的门生,是一名戍守边关的职业军人,既曾作为使节出使女真,也曾率军与女真交战。他的才能显然受到了女真人的赏识,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军人的局限性和文化模糊性,这使他更容易在野蛮好战的族群中而不是在他的同胞中得到赏识。他显然受过教育——写过自传,偶尔还作诗,这证实了军人形象的复杂性,或许还表明他拥有比文人更多的自我表现自由。马扩将自己的生活描述成一部军事传奇,其中充满了冒险举动,但他身上也不失忠诚和孝顺的核心品质,这些品质使他坚守自己的国家、传统和文化。这些个人的著述,与许多关于军事事件的正史叙述形成的鲜明对比,在某些情况下,让我们得以瞥见军事阶层的自我形象。
在元朝统治之下建立起来的军户世袭制,在明代保证了军户较高的社会地位。作为精英成员,他们的文化如何与文人精英的品味、社会和文学活动以及教育形成交集?在第九章中,赖恺玲阐述了“文”与“武”如何被理解为互补而非对立的原则,尽管必须保留两者之间的区别,但两者之间的对立——以及完全封闭的文化普遍性——被认为是精英文化自我表现的衰落而非繁荣的标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个阶层之间没有相互怀疑甚至仇恨;更确切地说,这意味着这两个阶层的成员并不生活在封闭的文化圈当中,他们选择获得自我修养和社会声望的方式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例如,军事精英襄助艺术,而且对他们来说,拥有名画是地位的来源和文化修养的佐证。事实上,军事阶层对艺术进行资助的例子,可以在中国历史的深处找到,这可以追溯到北朝时期,那时,军事阶层就已经确立了其统治地位。 [28] 赖恺玲指出,在把军人描绘成粗鲁恶棍的普遍形象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对艺术和文学的乐趣并不陌生的人,比如李如松。一旦揭示了刻板印象背后的偏见,我们不仅有理由质疑文人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带有军事文化的色彩,也有理由质疑军事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被故意曲解为文人文化。赖恺玲还讨论了军事象征的价值,如文武精英收藏刀剑的行为。在明代,无论是讨论刀剑、制造刀剑,还是收藏刀剑,显然都是普遍存在的、为社会所接受的活动。在中华文化中,曾有一句表达军人地位低下的俗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29] 赖恺玲巧妙地揭示了这句俗话内部的不协调之处: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廷臣和将领都很注重用好钢铸造刀剑——毕竟,战争不是用钉子打的。最后,文人收藏刀剑的嗜好定义并描述了文武之间的流动关系,同时揭示了这两种建构背后的文化交织现象。
在第十章中,S.R.吉尔伯特通过对清代武举考题的透视,探讨了军事文化之于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的意义。吉尔伯特指出,康熙皇帝将儒家经典中最不具军事色彩的《孟子》和《论语》纳入了针对胸怀大志的军事统帅的课程。通过对这些文献与军事教育关系的专业分析,吉尔伯特质疑康熙皇帝因对《孟子》的偏爱而牺牲了那些被奉为中国军事经典的书,如《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康熙皇帝从幽古恢复原始的军事和哲学知识统一性的尝试,基于自身广泛的第一手经验,他认为这对指挥而言非常有效。另外,康熙皇帝依然认为《孙子兵法》和其他军事文献中的知识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无用的、具有误导性的。在乾隆时期,作为武举考试的一部分,儒家经典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恢复文武分离的回应,即便两者相近,也依然有所区别。这个有趣的论点指出了康熙皇帝对军事教育的理解与他的孙子——乾隆皇帝的观点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如果我们将吉尔伯特的见解与卫周安关于文化“军事化”的论述(第十二章)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乾隆皇帝是“文”与“武”知识正式分离而非融合的坚定支持者。卫周安将这种划分归因为对“武”与清朝的北方和非汉渊源的联系,这在理论上被认为是为了加强满人作为统治者的文化独立性,而吉尔伯特将其解读为乾隆皇帝对中国长期以来“五经”和“七书”分离传统的认同。这两种观点汇合在一起,勾勒出清朝军事文化的发展轨迹,从而为有关清朝帝制文化、满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专门议题增加了一个重要维度。
战争、盗匪、社会动荡和压服,迫使受害者面对破坏他们物质世界的创伤性事件,这些事件往往会经由心理、道德和知识资源而深深影响他们的命运。明朝的崩溃和清朝的统一战争所带来的暴力冲击了原本安全的世界,无处不在的军事活动严重摧残了手无寸铁的居民。司徒琳(Lynn Struve)呈现了在明清鼎革时期出现的关于个人和社会创伤的个人化描述。 [30] 在第十一章中,方秀洁以类似的方式,但更多地从文学方面,探讨了人们如何使用各种各样的写作形式来为自己创造一个避难所,以应对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并为自己的道德选择进行辩护。这些资料来源就其文学和社会内容而言很重要,但它们也提供了关于士兵行为和平民状况的信息。方秀洁专注于两种体裁——日记和诗歌。她发现,男性更喜欢日记,而女性更喜欢诗歌。武德被推崇,而且选择抗击侵扰者和强盗,支持弱者和流民的人被描绘为英雄。这种“游侠”(也可以是女性,就像方秀洁所说的那样)的主题,在中国传说中有悠久的传统,在《史记》中留下了不朽的古代典范,作为大众对武术和剑术痴迷的例子,也作为一种道德准则的象征,虽然没有受到经由文学修养获得的智慧和知识的启发,但得到了真正美德的启发,因此值得赞颂。如果文官和文人认为毛笔比刀剑优越的话,那么,在危机和战争时期,刀剑就会比毛笔更有用。方秀洁指出,文学是暴力的避难所,是情感的宝库,这种情感经历了从恐惧到绝望,从自怜到认命的过程。
在第十二章中,卫周安扩展了她之前写过的一个主题,论述了清朝鼎盛时期几位皇帝特别是乾隆皇帝统治下文化的军事化。 [31] 军事化在这里意味着向清朝的政治和公共文化注入一股强大的军事方面的内容。将亚洲腹地传统(用柯娇燕的话来说) [32] 表现为“武”,将中原传统表现为“文”,这是完全说得通的,因为这两种原则的和谐平衡被认为比一种不完美的平衡更可取,这种不完美的平衡会让一方永远占据统治地位。满人的天赋,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贯彻中华文化中长期确立的一种观念,即北方民族被赋予了优越的军事才能,从而体现出一种对抗性的“武”式原则;不如说是扭转了试图把满人描绘成野蛮人和文明之敌的局面,对“武”的占有使他们获得了平等的地位,补充了文明而不是对抗文明,从而没有放弃文化的多样性。卫周安指出,公共文化和宫廷文化的军事化助力了清朝,并推动了清朝上半叶的积极进取。清朝在19世纪失去了内部权力和威望,与此同时,其军事力量也在对抗西方和日本的过程中日渐衰弱。
军事文化中更为传统的一面,可以用一句古语来概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何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维持军队的给养,这是与西方军队进行比较可能产生有趣结果的领域之一,但中国方面相关知识的匮乏,严重限制了这种比较的应用。 [33] 在第十三章中,我们要感谢戴英聪,她让我们了解了清朝鼎盛时期军事财政的结构,特别是军事人员的收入和后勤保障的成本。文官机构的一些部门和普通民众中的一些人参与了复杂网络的建设,这些网络本应为士兵提供所需的资金。戴英聪考察了清代军事财政制度的成就与不足,为理解清代军事危局与晚清国家危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戴英聪对军事管理的规则和法规与档案报告中所载的事实之间的不一致之处所做的探索,尤为深刻。这是对混淆官方法规与实际情况的任何诱惑的必要纠正。戴英聪还指出,军事史,特别是帝制晚期的军事史,必须尽可能依靠档案和非官方的报告,因为在编纂官方历史时,会存在特有的政治偏见和文学惯例。最后,戴英聪还强调了明、清军事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尽管在历朝历代,中国的官僚行政传统在地方和中央机构中都有实质上的连续性,但类似程度的连续性的假设,不应该扩展到军事领域。如果说明代的军户世袭制度,与蒙古人在中原建立的制度具有连续性的话,那么,从明到清的军事文化的大部分领域,如边疆防务、军事动员和戴英聪章节中所关注的财政管理和后勤保障,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濮德培认为,明朝的战略文化与清朝的大为不同。 [34] 在第十四章中,他列举了两个平行的矩阵,用来定义帝制晚期中国的“军事文化”和“商业文化”,并以此呈现为三种逐渐拓展的意义。他对边疆战略和管理做了论述,并进一步对比了西北和东南两处边疆,在这两处边疆地区,商业与军事的关系颠倒了过来:第一种情况是军事和商业相辅相成;在第二种情况中,它们相互对立。对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状况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与军事文化(在濮德培的第三种意义上,指的是“整个社会对于胁迫的态度”)相关的无形联系,而这种军事文化与军事之外的需求和逻辑紧密关联。“战争与贸易”之间的关系曾被学者们探讨过,他们认为这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一个关键方面,表现为资源冲突与由贸易和贡品优待所保证的和平之间的摇摆式交替。 [35] 濮德培也展示了军事和商业逻辑的连续性和交叉点,同时描绘了一幅从多层面阐述的引人入胜的理论图景,并以全面和比较的角度分析边疆关系。濮德培对军事和商业的并行分析表明,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北方和南方边疆,而应认识到军事干预和金钱的双轨行动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联系。
[1] Bernstein,Lewis.2001.Review of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书评,ed.Hans van de Ven 方德万.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军事史杂志 65.3:776-777.除了一些关于孙子和军事经典的作品之外,这本仍在被讨论的书(van de Ven,2000)在Kierman,Frank A.,Jr.,and John K.Fairbank 费正清,eds. 1974.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出版之前,对中国军事史研究的贡献最大。
[2] 涉及19世纪之前的相关出版物有Graff,David A.葛德威and Robin Higham.2002.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军事史.Boulder,CO:Westview Press;Graff,David A.葛德威.2002a. Medieval Chinese Warfare,300-900 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300~900年).London:Routledge;Lorge,Peter 龙沛2005a. War,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900-1795 早期近代中国的战争、政治与社会.New York:Routledge;Perdue,Peter C.濮德培.2005a.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1680-1760 中国西征:清朝在欧亚中央地带的征战.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Waley-Cohen,Joanna 卫周安.2006.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清代战争文化.London:I.B.Tauris。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增加几篇 War and Society (2000)特刊所收录的文章,以及 Modern Asian Studies 题为“War in Modern China”(1996)的专辑,其中包括几篇关于中国历史上战争与文化关系的文章。
[3] Lorge,Peter 龙沛.2005b. Warfare in China to 1600 公元1600年前的中国战争.Burlington,VT:Ashgate;Swope,Kenneth M.石康,ed.2005. Warfare in China since 1600 中国1600年以来的战争.Burlington,VT:Ashgate.与前现代时期更相关的是前者,其中包括发表于1939~2003年的25篇论文。
[4] van de Ven,Hans 方德万,ed.2000.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Leiden:Brill,p.6.
[5] Zhong guo wen hua ,1968.
[6] Kuhn,Philp 孔飞力.1970.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帝制中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0-13;Swope,Kenneth M.石康,ed.2005. Warfare in China since 1600 中国1600年以来的战争.Burlington,VT:Ashgate,p.xi.
[7] Scobell,Andrew 施道安.2002.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中国及其战略文化.Carlisle,PA: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U.S.Army War College,pp.3-10.
[8] 在Johnston,Alastair Iain 江忆恩.1995. 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22-27中,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对中国关于“军事文化”及其与“战略文化”关系的观点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另可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9] 参见Mott,William H.,IV,and Jae Chang Kim 金在昌.2006. 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Shih vs.Li 中国军事文化理念:势与利.New York:Palgrave;Johnston,Alastair Iain 江忆恩.1995. 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 Wilson,Stephen.1980. “For a Socio-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Culture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西方军事文化.” Armed Forces & Society 武装力量与社会 6.4:527-552.
[11] Falkenhausen,Lothan von 罗泰.1996. “The Concept of We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Ancestral Cult 中国古代祖先祭祀中的文观念.”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中国文学论文集 18:1-22,pp.5,8.
[12] 对于前帝制时期,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在他的 Sanctioned Violence (1990)中认为,战争和暴力组织是前帝制时期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战国时期大规模步兵之形成的研究可参见Kolb,Raimund Theodor.1991. Die Infanterie im alten China:Ein Beitrag zur Militaergeschichte der Vor-Zhan-Guo-Zeit 中国古代的步兵:对战国之前军事史的贡献.Mainz am Rhein:von Zabern。然而,关于帝制时期的情况,类似程度的理论阐述尚未出现。
[13]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唐朝对外关系和内部发展的过程中,军事事务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参见Twitchett,Denis 崔瑞德.2000. “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 唐朝大战略中的吐蕃.” In Hans van de Ven 方德万,ed.,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pp.106-179.Leiden:Brill。这篇精彩的文章表明,对广泛的历史解读而言,认真对待军事问题是会有所助益的。
[14] Graff,David A.葛德威.2002a. Medieval Chinese Warfare,300-900 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300~900年).London:Routledge,pp.246-247.
[15] Supple,James J.1984. Arms versus Letters:The Military and Literary Ideals in the “ Essais ” of Montaigne 武器与文字:蒙田《随笔》中的军事和文学理想.Oxford:Clarendon Press,p.71.
[16] Connell,William J.,ed.2005. “ The Prince ” by Niccolo Macbiavelli,with Related Documents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及其相关文献.Boston:Bedford/St.Martin’s Press,p.84.
[17] 关于“军事地位的文化证据”,请参阅一篇早期的充满见地的文章:Fried,Morton H.1952. “Military Status in Chinese Society 军事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美国社会学杂志 57.4:347-357,pp.352-354。另可参见Lo,Winston W.1997. “The Self-Imag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军队自我形象.”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亚洲史杂志31.1:1-24这篇优秀文章,以及Creel,Herlee Glessner 顾立雅.1935. “Soldier and Scholar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的军人和学者.” Pacific Affairs 太平洋事务 8.3:336-343.这一旧文。
[18] Parker,Geoffrey.1993. “Comment on Shin’ichi Kitaoka 北冈伸一,‘Army as Bureaucracy:Japanese Militarism Revisited 以军队为官僚:日本军国主义再认识,兼评北冈神道,’ and Arthur Waldron 林霨,‘War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战争与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军事史杂志 57.5:105-109,p.107.
[19] 技术很可能扮演了一个目前无法被衡量的角色。在中国工业的几个发展节点上曾大规模生产武器以及对技术的引进(如明末),可能都在中国历史上引发了重大的变革,但目前尚不足以评估其历史意义。火器的使用,特别是以西方模型为基础的加农炮,在晚明时期已经成为诸多研究的对象。作为一般参考书目,可参见Di Cosmo,Nicola狄宇宙.2005. “Did Guns Matter?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与枪炮何干?火器和清王朝的形成.” In Lynn A.Struve 司徒琳,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pp.121-166.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 作为中国军事史的基本年表,它暗示了在帝制时期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变化,参见Dreyer,Edward L.戴德 2002. “Continuity and Change 持续与变迁.” In David Graff and Robin Hingham,eds.,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军事史,pp.19-38.Boulder,CO:Westview Press。
[21] 15世纪的明朝有许多军事上的败局,比如在土木堡大败于蒙古军队。然而,在16世纪和整个万历皇帝统治时期,明朝的军队很少遭遇惨败,尽管我们必须再次注意努尔哈赤于1619年在萨尔浒击败了明朝的一支强大军队。关于对晚明军事的重新评价,参见Swope,Kenneth M.石康.2004. “A Few Good Men:The Li Family and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in the Late Ming 几个好人:李氏家族与晚明的北方边疆.” Ming Studies 明代研究 49 (Spring):34-81。
[22] 在一系列研究文章中,最有影响力之一的仍然是Loewe,Michael 鲁惟一.1974a. “The Campaigns of Han Wu-ti 汉武帝的征伐.” In Frank A.Kierman and John K.Fairbank 费正清,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pp.67-118。
[23] Black,Jeremy.1998.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Chang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从历史角度看军事组织和军事变革.”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军事史杂志 62.4:p.872.
[24] 关于这一议题,参见Mark Lewis 的杰出文章(Lewis,Mark Edward 陆威仪.2000. “The Han Abolition of Universal Military Service 汉朝废除普遍兵役制.” In Hans van de Ven方德万,ed.,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pp.33-75.Leiden:Brill.)。另可参见Yates,Robin D.S.叶山.1988. “New Light on the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exts:Notes on the 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ecialization in Warring States China 中国古代军事文献新解:战国时期军事专业化的演变与发展札记.” T’oung Pao 通报 74:211-248。
[25]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别也让人回想起孔孟学说与Johnston的作品 Cultural Realism (1995)中战争(parabellum)范式的对比。
[26] 参见Skaff,Jonathan Karam 斯加夫.2000. “Barbarians at the Gates?The Tang Frontier Military and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门口的野蛮人?唐代边防与安史之乱.” War & Society 战争与社会 18.2:23-35。
[27] Franke,Herbert 傅海波.2003. Krieg und Krieger im chinesischen Mittelalter(12.bis 14.Jahrhundert):Drei Studien 中古中国(12世纪至14世纪)的战争与勇士:三项研究.Stuttgart:Franz Steiner,pp.19-121.
[28] 游牧族群的军事精英对艺术赞助也并不陌生,参见Wong,Dorothy C 王静芬.2003. “Ethnicity and Identity:Northern Nomads as Buddhist Art Patrons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族性与身份:南北朝时期作为佛教艺术庇护者的北方游牧民族.” In Nicola Di Cosmo 狄宇宙and Don J.Wyatt 韦栋,eds., Political Frontiers,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民族边界和人文地理,pp.80-118.London:RoutledgeCurzon。
[29] Tong Yubin 佟玉斌.1997. Junshi chengyu cidian 军事成语词典.Beijing 北京:Changcheng chubanshe 长城出版社,p.122.
[30] Struve,Lynn 司徒琳.1993. 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China in Tiger’s Jaw 来自明清巨变的声音——虎口下的中国.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31] 参见Struve,Lynn 司徒琳.1996. “Commemorating War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纪念18世纪中国的战争.” Modern Asian Studies 现代亚洲研究 (October):869-899;以及Struve,Lynn 司徒琳.2003. “Military Ritual and Qing Empire 军事仪式和清王朝.” In Nicola Di Cosmo 狄宇宙,ed., 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 亚洲腹地历史上的战争,pp.405-444.Leiden:Brill。
[32] Crossley,Pamela K 柯娇燕.1992.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中国皇权的多元性.” Americam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 97.5 (December):1468-1483,p.1472.
[33] 戴英聪写过一篇关于清军经济方面的作品,参见Dai,Yingcong 戴英聪2001. “The Qing State,Merchants,and the Military Labor Force in the Jinchuan Campaigns 金川战役中的清政府、商人和军事劳动力.” Late Imperial China 晚期帝制中国 22.2 (December):35-90。濮德培对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清朝鼎盛时期的后勤状况进行了有益而精确的描述,清军在这方面的表现应该会给西方历史学家留下深刻印象,参见Perdue,Peter C.濮德培 1996.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Russia,and Mongolia 17~18世纪中国、俄国和蒙古的军事动员.” Modern Asian Studies 现代亚洲研究 30.4:757-793。
[34] 参见Perdue,Peter C.濮德培.2000. “Culture,History,and Imperial Chinese Strategy:Legacies of the Qing Conquests 文化、历史和帝制中国战略:清朝征战的遗产.” In Hans van de Ven方德万,ed.,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pp.252-287.Leiden:Brill。
[35] 例如,可参见Jagchid,Sechin札奇斯钦,and Van Jay Symons.1989. Peace,War,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两千年来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