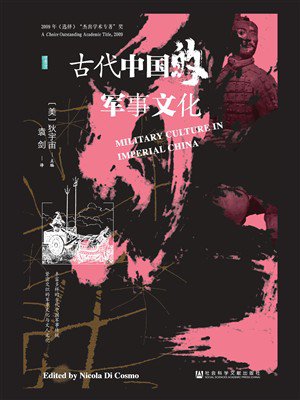中国早期的军事法
在青铜时代,中国的军事和战争是祭祀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早期文化和宗教实践的一个核心特征。在季德源看来,在夏、商、西周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771年,军事法有五种主要形式:誓言(誓)、宣言(诰)、命令(命)、仪式(礼)和酷刑(刑)。 [13] 誓言可能是五种形式当中最早的一种,在战役开始的前一天晚上,由将领对他的部队口头宣布。儒家经典之一《尚书》的传文中,有誓书五篇,但它们是否真正反映了历史上的实情,或许还有待商榷。其中的“甘誓”,是夏朝统治者启在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时所发表的誓言。“汤誓”是商代统治者汤的誓言,当时他打算消灭夏朝最后一位残暴统治者——桀。“泰誓”由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战前夕所宣,随后,他横渡黄河孟津,讨灭了商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纣王。另外,“费誓”则是鲁公伯禽在攻打淮夷、徐戎等“夷狄”之际所说的话。誓言是在仪式上被清楚地表达出来的;誓言陈述了讨伐对象的过错和罪行,进而说明采取行动的原因,并声称这是合理的;它制定了官兵作战的规则,并威胁若有违抗者,一律处死。这也是提高军队士气的一种手段,并以一种契约的形式约束全体官兵。如果不遵守契约的条款,他们将沦为人牲献祭于国家祭坛(社)上。
因此,这种由最高统帅发出并期望完全服从的誓言,与罗马军队士兵自己宣誓的誓言大不相同,后者是“对指挥官的个人效忠”,是代表士兵忠诚的神圣约束,对它的亵渎会受到人和神灵的惩罚。 [14] 誓言也不同于“盟”,“盟”据信始自东周,是在上天面前由平等或接近平等的人宣誓,用牺牲者的血加以封印,对违反约定的人施加超自然的惩罚,并有一份埋在地下的书面记录。 [15]
由于认识到三代(夏、商、周)历史先例的重要性,这种誓言在战国和帝制时代的战役前被继续加以宣示。《武经七书》中的《司马法》就建议:“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16]
唐代8世纪中叶由李筌所编纂的一部军事百科全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以及曾公亮及其同僚在北宋11世纪中叶所编的官方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
以及曾公亮及其同僚在北宋11世纪中叶所编的官方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
 都记载了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誓言。两者都提供了最高统帅对其麾下部队所宣誓言的样本或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誓言都表明将军声称有权执行天罚,因为他从皇帝那里得到了斧钺,象征着剥夺生命的权力。在宋朝,皇帝向将军颁发一柄礼剑,象征他有权对敌人和麾下违反军事法成文规定的士兵处以极刑,而不用将罪犯移交中央司法机关。
都记载了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誓言。两者都提供了最高统帅对其麾下部队所宣誓言的样本或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誓言都表明将军声称有权执行天罚,因为他从皇帝那里得到了斧钺,象征着剥夺生命的权力。在宋朝,皇帝向将军颁发一柄礼剑,象征他有权对敌人和麾下违反军事法成文规定的士兵处以极刑,而不用将罪犯移交中央司法机关。

季德源认为的第二种早期军事法,即“诰”,是一种由上级(通常是统治者)发布的法律指令,它也赋予下级权力以实施惩罚。《尚书》记载了许多例子,但没有一个特别涉及战争或军事事务,因此,季德源认为“诰”作为军事法一种形式的说法可能不足为信。
西周时期的许多青铜铭文都提到了“命”,语境是周朝统治者赋予下属指挥周军或接管其祖先行政职权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授予或权威的确认,通常出现在仪式上,该仪式往往在周天子的祖庙里举行,并辅以礼节性的贵重物品。仪式由接受荣誉、职责和礼物的个人通过铸造一件或多件青铜器来加以正式记录。这些铭文是献给特定祖先的,并准备在以后的祭祖仪式中进行复述。信息本身通过放置在容器中的熟食和饮品媒介传递给祖先。 [17] 然而,命或令并不仅限于军事活动,它们也是青铜时代精英内部商品流通和个人威望的一部分。这种流通发生在仪式盛宴上,柯鹤立(Constance Cook)指出,在西周晚期(前9~前8世纪),军事装备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取代了早期常见的珠玉串。 [18] 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写的:“战争和军事装备(无论是弓箭、旗帜、行仪、护甲、盾牌,还是战车装备)的流通、转让以及传播,都是西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商代早期的文化制度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19]
最后,对于季德源所认定的早期军事法的最后两种形式——仪式(礼)和酷刑(刑),正如一些学者所证明的那样,在春秋时期(前8世纪中期~前5世纪),礼支配了战争的行为规范。
[20]
但是,礼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制史和军事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受篇幅所限,本章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至于酷刑,考古发掘和碑铭材料都清楚地证明了它们确实发生过,但这些酷刑是否在一种特定的军事背景下实施,并与军队参与的献祭活动分开,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季德源用中国传统文献证明中国存在早期军事法,但他的结论可能会再次受到质疑。
[21]
尽管如此,郭锦(Laura Skosey)已经证明某些类型的军事行为,特别是被称为“征”的惩罚性行动,其目的是惩罚那些被认为忤逆天意的不法之徒,并将战争与新兴的法律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至于酷刑,考古发掘和碑铭材料都清楚地证明了它们确实发生过,但这些酷刑是否在一种特定的军事背景下实施,并与军队参与的献祭活动分开,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季德源用中国传统文献证明中国存在早期军事法,但他的结论可能会再次受到质疑。
[21]
尽管如此,郭锦(Laura Skosey)已经证明某些类型的军事行为,特别是被称为“征”的惩罚性行动,其目的是惩罚那些被认为忤逆天意的不法之徒,并将战争与新兴的法律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然而,军事法确实在随后的战国时期开始逐步扩展,时限大约是公元前5~前3世纪。
然而,军事法确实在随后的战国时期开始逐步扩展,时限大约是公元前5~前3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