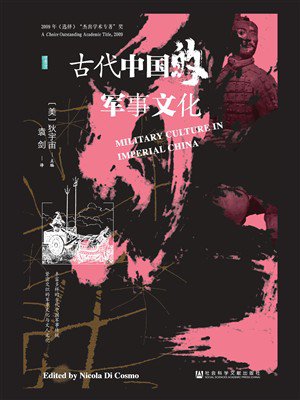战国时期的军事法
据铭文记载,西周时期开始形成法律程序, [22] 公元前7~前6世纪,各封国开始出现第一部成文法典。 [23] 然而,战国时期的情况与早期大不相同,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军事法才真正得以发展。
战国时期,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等方面出现了根本性变革,这是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广泛研究的课题。在军队的发展方面,有几个重大的变化。首先,军队规模扩大,步兵成为军队的核心,最终取代战车成为主要的进攻力量。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各诸侯国从北方草原民族那里接受了骑术和骑兵,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骑兵变得越来越重要。 [24] 当然,很明显,步兵在早期的战争中至关重要,但我们掌握的信息来源强调了青铜时代贵族驾驶战车在早期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之下,在战国时期,所有健全的男性对国家而言都负有服劳役和兵役的义务(妇女只服劳役,除非在围城战中,稍后会论及),所有诸侯国都发展出户籍登记制度,使政府当局能够征取税收、招募劳役以及增调军事资源。因此,在这一时期,军队的主体由下层精英,即士所指挥的应征者组成,正是士引起了孔子的兴趣,这些人后来转变为文人(士大夫),并通过他们在帝制时代对官僚制度的掌握主导政治权力。
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的了解比以前的要多得多,因为参战国家的实质存续,取决于其拥有的强大而有效的军事力量。在这一时期,首次有理论专家专门撰写军事方面的著作,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孙武(或称孙子)和他的《孙子兵法》。除此之外,几乎每一位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必须关注军务,并对如何参与军事冲突提出自己的见解。儒家哲人荀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作品集第十五篇就专门论述了他不认同与孙武所提理论路线相关的思想和实践。 [25] 这些军事家游历诸国,试图说服统治者采纳他们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是成功的。然而,与当时哲学家的著作一样,关于军事的大量著作很少能从这一时期留存下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宋时期(960~1127年)由七部兵书汇编而成的《武经七书》,它被列为后世武举考试的核心文本。许多战国时期的军事法都可以从这些文献中找到。
至少到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专门的军事管理著作才出现,《左传》引用了公元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和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的《军志》,而《孙子兵法》则引用了《军政》。《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
[26]
战国晚期的兵书《尉缭子》提到了两条军事法,即“离地遁逃之法”和“战诛之法”。
[27]
我们在这些文献中所看到的是军事法的发展,旨在加强战国时期日益庞大的军队的纪律,并协助训练来自自耕农的义务兵。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军事法,就不可能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兵力(一次可能多达10万人)。

最重要的是,传统上与所谓法家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家政治家,似乎采纳了军事组织或法律的某些基本原则,并将其应用于全体平民。这对中国的社会形态和之后整个帝制时期的法律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的商君卫鞅成功说服秦孝公对秦国的军事法进行了改革,这一改革为秦国在下个世纪最终击败所有对手,并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建立统一帝制奠定了基础。在这里,后一个故事可以说众所周知,而对商鞅的改革,则有必要加以简要概述。
第一,他对秦国管辖的所有人口进行划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然后再扩大到更大的单位,并采取连坐制,各层组织之人对其成员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28] 在秦军中,五人一伍,十人一什,都是从这些家庭单位中抽调出来的,这样一来,来自五家一伍的人就在军队的五人小组中服役。这就保证了在军中服役的人彼此之间非常了解,他们也很可能通过血缘关系和/或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愿意为救本组其他成员之命而战斗到底。作为一个整体,平民的等级制度反映了军队的等级制度。在这两个机制的每一级中,国家赋予军官或官员管理其单位的权力,并对其下属的表现承担法律责任。因此,通过这一秩序的建立,国家能够管控社会的所有成员,渗透到家庭的核心,打破了家庭内部的团结。每个社会成员的忠诚和团结都转到了秦国。
第二,在连坐制下的民事活动中,由伍长领导的五家成员对彼此的行为负责,并有义务检举其他成员的罪行;否则,他们将承担同等的罪责。在军队里,各伍成员对彼此的安全负责。如果一个人被杀,所有其他成员都将被指挥官处死,除非他们设法杀死一个敌人,并用其首级来补偿他们自己的损失。在民事和军事领域,连坐制的名称表明,那些位于左、右、前和后的人对个人的行为负有责任。这种空间识别显然比在平民领域更容易想象,因为地理和地形的性质,在平民领域,家庭之间理想的空间关系很难描绘。这就是我认为连坐制是从军事领域引入并适用于平民领域的原因之一。这种连坐制在帝制时代就已经实行了。汉代以后,它在北宋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年)所谓的家庭责任和相互保护的保甲制度中复兴,到了明代,德川幕府在17世纪将这一制度借用到日本。 [29] 显然,在当代中国依然有它的对应物。
这就引出了商鞅制度的第三个部分。商鞅的改革是建立在奖惩的正向和反向刺激基础上的,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人性本来就是邪恶的,只能对外界的影响做出反应。惩罚多而严厉,奖励则少而慷慨。事实上,商鞅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了重组,因此,只有(或至少主要是)战斗中的军事胜利(军功),才是衡量社会和法律地位、威望以及经济实力的唯一标准。他建立了十七等军功爵制,其中前八个等级对一般农民和平民开放。获取一个敌方首级可获得一级爵,获取两个敌方首级则被授予二级爵。军官们也会根据其下属获取首级的数量,获得类似的爵级晋升奖励。他们不被允许(违则受到惩罚)亲自砍下敌人的头。因此,秦军的职能就有了严格的规定。秦国的这种理想,实际上反映在发现于秦始皇陵东面的陶俑身上。在那里,普通士兵俑都有武器,但军官俑没有。军官们负责用《孙子兵法》中提到的旌、旗、锣、鼓,指挥前进后退、左右运动。等级制度在接下来整个汉代的四五百年间一直延续。砍下敌人的首级作为决定在战场上功勋的方法,至少持续到1500年后的宋朝,而奖惩制度仍然是后世军事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
同样,这些军功等级授予受赠者法律和社会地位。它们可以被用来修改对持有者的惩罚;或者说,持有者自己也可以用它们来抵消惩罚或通过交还等级来提升罪犯或奴隶的低下地位。 [30] 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末的统一战争前线,两个年轻的秦人在木牍上写了一封信(1975年发现于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墓葬),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军事法对这一奖赏体制的复杂操作。在这封信里,年轻人询问他们通过斩首获得的军功等级在他们的家乡是否有效。这些等级可以提高他们自己和父母的社会声望和法律地位,并减轻后者违法时地方官员可能施加的惩罚。 [31]
在1975年发掘的同一组墓葬中,公元前217年一位地方官员随葬的一批竹简里还出现了两份法律案件的记录;两个案件的记录都记载了公元前266年邢丘之战中两名男子争夺一名被杀者首级之事。在第二起案件中,总部的军事长官质疑被杀者的身份,并怀疑这两个人可能谋杀了自己的一个秦国士兵。由于被杀者头上是独具特色的秦国发型,所以长官下令:“有失伍及(迟)不来者,遣来识戏次。” [3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秦制对秦国臣民的好处。尽管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制裁,这些士兵却可以利用刑法来谋取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因此,商鞅变法之后的140多年时间里,秦国一直保有民众对它的忠诚,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们转向因睡虎地秦简的发现而为人所知的秦国军事法的其他方面和例子之前,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另外两个对军事法产生深远影响的进展。随后,我将简要回顾一下战国末期被围城市的军事法。
这些进展中的第一个是在《司马法》中被提到的。大致是说,军队中的行为和平民生活中的行为有了明显的区别。在这两个领域里,个人如何展现自己,如何走路、说话和穿衣,都是不同的。“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33] 儒家学者特别关注仪式行为和修身养性,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军事形式区分开来。从文化上讲,儒家礼仪是一种个人修行的形式,它的意义只有与军中实践相区别或对立才能得以呈现,在军队中,则个人的个性必须被消除,必须实行统一的集体行为。这种区别的一个主要影响是,一旦将军收到了象征他有权处决罪犯和那些违反军事法之人的斧钺,那么,任何人,甚至连统治者或后来的皇帝,都无权违抗或反对他的命令,直到他放弃他的权威为止。因此,军事法表明,由于皇帝是超自然的天子和超人类领域的调解人,所以皇帝既是法律的源头,又凌驾于法律之上。 [34]
第二个进展则是镂刻的青铜或木质的符的出现,它赋予军官权力,使其能够调动自己手下的军队。符被剖成两半,一半放在中央政府衙署,另一半给了军官。只有当中央的一位高级官员发出另一半符,而这名军官又将其与自己的一半相匹配时,他才能召集士兵进行作战。这一制度,再加上为出使者颁发“节”,为官员甚至皇帝及其母亲等关系密切的人员颁发印章,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未经授权的武力使用和未经许可的通过关隘和站点的货物流通和人员流动。伪造或滥用这样的符、节或印章被视为严重犯罪,并会受到严厉惩罚。这些符在后来的帝制时代继续被使用,关于其使用的法律已经在汉代遗址中发现, [35] 并在唐律中保存下来。 [36] 这种符信制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日常实践和意识中,从汉代开始,特别是在道教中,正如石秀娜(Anna Seidel)所展示的那样,符被用作控制和转移鬼魂邪恶力量的有效手段。 [37] 它们赋予持符者巨大的精神力量。中国人在建筑物的门柱上贴象征吉祥的、避邪用的文字,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今天,最初也源于早期军事上对符的使用。
现在谈谈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实施的军事法。这些规定保存在哲学著作《墨子》的最后两篇中。 [38] 在山东省银雀山的一座公元前130年的汉墓中,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段落,标题是“守法”和“守令”。很明显,当一个城市受到敌人日渐逼近的威胁时,它被称作“守”或“令”的指挥官掌管,指挥官会宣布城市所有居民应遵守的法律。这些法律范围广泛且数量很多,它们都被写在榜上,张贴在居民可以阅读的所有地方,如十字路口、通往墙头的楼梯等。假装不了解法律内容而违反法律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所以,这就假定有足够数量的识字居民能够阅读告示,并将其内容告知他们的亲友邻里。
其中许多法律的形式是“在所有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做”,或者“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罪行而受到惩罚或处决”。这表明,允许什么样的过错和对某一罪行加以惩罚等许多法律观念在战国晚期发展起来,这些观念在睡虎地的秦律中都可以找到,如“意”“欲”“谋”等,而这在军事法中被有意识地不予采纳或接受。
在墨家法律中,很明显,违反特殊法的罪犯的意图或心理倾向是什么并不重要:事实上,所有人都受到守城者的严厉惩罚。实际上这也是后来军事法的一个特点。斩首处决是军事罪犯通常受到的惩罚,但在叛国和通敌的情况下,也会处决叛徒的亲属,根据连坐法,还会处决叛徒周围的人。只有意外对一座建筑物纵火,才会被处以砍断四肢、削去耳鼻的惩罚,妇女似乎没有受到过这种惩罚。而故意纵火的话,罪犯会受到车裂的严峻惩罚。在公元前338年,商鞅的保护者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背叛了之前曾冒犯过的新君主,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惩罚。偷窃和强奸会被判处死刑,这些规定在后来的军事法中都存在。卖淫的娼妓,以及那些在军中唱歌或哭泣的人,都会被割耳朵,而那些隐藏像“棋”这样可以用来模拟战术活动的游戏的人,或者那些允许马或牛在军中四处奔跑并引起混乱的人,也都一样。
 割耳被认为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因为人们之后不能再戴耳环,而耳环是用来显示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被割耳的人还会被认为身体是残缺的,所以这些人不能祭祀他们的祖先。墨家也很细致地制定了用药物疗治士兵、捐赠肉类、妥善埋葬在战斗中牺牲的士兵的规则。官员们在冲突结束后举行妥当的葬礼,并亲自参加悼念死者的活动。后来,唐宋时期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在唐朝,医者和勤务人员在军队前进时,如果为了避免被敌人俘虏或折磨而遗弃病人或活埋病人,都会被处以死刑。宋朝制定了将遗体送还家属的详细规定,国家会根据军官的军衔和死去士兵所属的军种,捐赠棺材和坟墓。
割耳被认为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因为人们之后不能再戴耳环,而耳环是用来显示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被割耳的人还会被认为身体是残缺的,所以这些人不能祭祀他们的祖先。墨家也很细致地制定了用药物疗治士兵、捐赠肉类、妥善埋葬在战斗中牺牲的士兵的规则。官员们在冲突结束后举行妥当的葬礼,并亲自参加悼念死者的活动。后来,唐宋时期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在唐朝,医者和勤务人员在军队前进时,如果为了避免被敌人俘虏或折磨而遗弃病人或活埋病人,都会被处以死刑。宋朝制定了将遗体送还家属的详细规定,国家会根据军官的军衔和死去士兵所属的军种,捐赠棺材和坟墓。
另一条墨家法律也具有文化意义。萨满(巫)、祈祷者(祝)和占星家(筮)奉命向民众告知好兆头,但要向统治者报告实情。如果“望气者”说了些使人吃惊或害怕的不祥之辞,他们将被处死。占卜是三千年来军事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将军完全不考虑占卜,因为他知道自己麾下的士兵和军官完全相信占卜与决定成败和生死的关系。
 在唐宋时期,《武经总要》规定:“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以动众心者,斩。”
在唐宋时期,《武经总要》规定:“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以动众心者,斩。”
 将道教和佛教纳入军事法,显然反映了后来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变化。然而,与前帝制时代一样,战后的军队并没有忽视宗教仪式和习俗。相反,它们是由指挥官精心控制、操纵和实践的,以确保军队的凝聚力、安全性和最终的胜利。历代兵书中有许多关于各类神灵的祈祷,这些祈祷是将军和官员在战役开始时或进行过程中所做的,例如对马神、佛教北方天王毗沙门天(佛教四大护法之一)等。
将道教和佛教纳入军事法,显然反映了后来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变化。然而,与前帝制时代一样,战后的军队并没有忽视宗教仪式和习俗。相反,它们是由指挥官精心控制、操纵和实践的,以确保军队的凝聚力、安全性和最终的胜利。历代兵书中有许多关于各类神灵的祈祷,这些祈祷是将军和官员在战役开始时或进行过程中所做的,例如对马神、佛教北方天王毗沙门天(佛教四大护法之一)等。
 这些可以被认为是狄宇宙在本书导言中所讨论的军事文化的第四种含义的要素。
这些可以被认为是狄宇宙在本书导言中所讨论的军事文化的第四种含义的要素。
至于成功防御的奖赏,墨家给予所有参加防御的男性两级军衔,并给予特别负责的军官更高的军衔。参加防卫的妇女,因为她们本身没有资格获得军衔, [39] 所以每人获得5000钱;而没有参加防卫的男女,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每人获得1000钱,他们还将被免税三年。文献记载道:“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之三岁,无有所与,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 [40]
事实上,战国时期文献中的许多军事法,从不服从指挥官的命令和不在指定的时间到达集合点,到分配口粮和管理旌、旗、鼓、锣的规则,都与后来帝制时期的军事法大体一致。因此,从前帝制时期到帝制时期,军事实践有很强的延续性,但每个时期都各有特色。至于谁在战国时期负责管理军事法,这一点似乎也与后来的时代保持了连续性。在军事法规定的被围城的情况下,上面我们看到的守或县令,是县级的最高级别官员。在征战的军队中,则是督军(监军)和执法官(军正)这两个出现在帝制时代的官员主要负责军队的法律管理。这两种军官最早源于春秋末期的齐国,记录在《司马穰苴列传》中,
[41]
穰苴依靠从军时学到的军事法知识,处决了监军庄贾,因为庄贾在会合时迟到了;然后又处死了齐景公所派使节的仆从以及牵引马车的左马,因为它超速闯入了军营。
 这些战国时期的军事法是由一个在公元前221年战胜所有对手并建立秦朝的国家制定的,我们现在将转向中国军事法史的下一个阶段。
这些战国时期的军事法是由一个在公元前221年战胜所有对手并建立秦朝的国家制定的,我们现在将转向中国军事法史的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