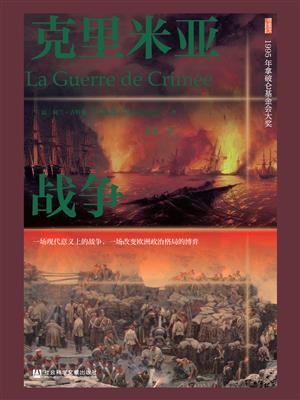圣地之争
一场俄国将主要参与其中,其政治利益与宗教信仰将受到挑战的冲突,我们有理由担心它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
我们担心一切可能的后果,当然首先要知晓拜占庭的宗教对抗牵涉的各方利益,然而,在法国,除了佩尔西尼(Persigny)大力揭露的那个“神职人员小集团”,还有谁真正充分了解那里的宗教纷争和利益纠缠呢?用佩尔西尼的话来说,这个小集团“像一条蛀虫那样……在外交部的隐秘角落里驻扎下来” [1] 。
皇帝本人深陷危机之中,他不得不向图弗内尔(Thouvenel)坦白——一次重大而令人不安的坦白——他“并不知道圣地事件的细节”
 。长久以来,在法国,提起巴勒斯坦僧侣的处境只会引起厌烦与嘲讽,1789年革命的继承者们不会再因宗教问题被动员起来。
。长久以来,在法国,提起巴勒斯坦僧侣的处境只会引起厌烦与嘲讽,1789年革命的继承者们不会再因宗教问题被动员起来。
但是,1850—1853年圣地之争的第一集刚刚上演,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德·拉·瓦莱特侯爵(le marquis de La Valette)就从这场冲突中吸取了教训!他写道:“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起僧侣事件,要么不要插手,要么就支持这场冲突。”

在俄国,政治原因与宗教原因在圣地问题中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遏制法国支持的天主教徒的影响,不仅是捍卫东正教的信仰,还意味着与革命精神做斗争,为神圣俄罗斯(Sainte Russie)的强盛而努力。
可以设想,沙皇一旦涉入一个如此敏感的地域,他的回旋余地是有限的:作为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作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他实质上注定要走向绝对。对于俄国人民来说,沙皇的任何让步都无异于卸任。沙皇选择的任何事业都是神圣的,任何反对沙皇的行动都是大逆不道的,俄罗斯之外的民族多少只能算是附庸民族。
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在《斯拉夫人》(
Les Slaves
)中写道:“[沙皇]并不是凭借他的皇帝名号进行统治;加冕、名号,甚至合法的皇位继承权,都与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毫无关系。人民几乎不知道皇帝的名号。”

实际上,对于有着6000万人口,追求“高度灵性生活”的俄罗斯民族而言,沙皇的统治手段是向他们的心灵和灵魂中注入一种本质上神性而非凡俗的道德激情。这种无与伦比的力量,任何其他君王都不具备!但是,硬币也有其反面:一旦启动,神圣俄罗斯只有在实现目标后才能停止,倒退是被禁止的,因此沙皇的任何判断失误都可能是致命的。
确切地说,在执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绝对权力之后,人们对于尼古拉一世的判断能力还能有何期待?就连亲俄的法国大使卡斯泰尔巴雅克(Castelbajac),在写给图弗内尔的一封信中也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沙皇和[涅谢尔罗迭](Nesselrode),尤其是沙皇,都是被宠坏的孩子,他们不喜欢反对意见,即使是最友善的反对意见。”

圣地之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八个世纪前,即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所证实的那场公开的危机。
但是,教会分立论者确实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吗?
无论罗马天主教徒们——或“拉丁人”——同意与否,东正教徒们都问心无愧: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希望教会分裂的是教皇,因为早在863年,他就革除了东正教主教佛提乌(Photius)的教籍:仅仅因为他的错误,所有试图让两个教会复合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基督教世界的这个巨大创痛,是罗马造成的。是罗马离开了君士坦丁堡,而非像西方认为的那样,是君士坦丁堡离开了罗马。因为顾名思义,除了东正教,还有谁会是一个诞生于东方的宗教的神圣传统的守护者呢?早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天主教已经完全信服于西方的精神,认为必须通过占有领土来行使教皇的世俗权力,从而巩固自身的权威,而正是几个法兰克人,这些教皇永远的同谋,矮子丕平和查理曼,为天主教建立了家业。打算把一个国家交给那个恰好说过“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这是何等荒唐!
从那时起,对于罗马教会来说,大局已定。它不再是一个跨越国界、精神相通的信徒的社会。它正变成众多机构中的一个。它不像在东方那样,仍然是浸润国家的一种精神力量,而是正变成与其他国家无异的国家,除了一点:它在其他国家中拥有一些殖民地!
“利用”世俗权力的罗马教会多么可耻地玷污了基督教的原则,而忠于传统的东正教会只是为了服务于基督教原则而存在。
确实,一切都已事先注定,基督教世界一长串的厄运可以开始了:难道不是教皇与西方皇帝之间无休止的对抗,将首先破坏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原则吗?
这场不幸的冲突难道没有直接导致第二次教会分裂,即宗教改革的那次分裂吗?这次分裂是忠实的信徒们对一个徒有虚名的基督教会感到愤怒后的合理反应。
两个世纪后,反基督教的原则,即所谓的启蒙运动的原则——它首先攻击宗教信仰这个制度的黏合剂——难道不正是从宗教分裂打开的缺口趁虚而入吗?
这种反基督教的原则在革命中不是盛行吗?从本质上讲,这个原则是对神权的否定,因为它宣称的主权——人民的主权,正试图在欧洲各地摧毁摇摇欲坠的制度,因为它弘扬的唯一价值是人类“自我”的价值。 [2]
在这场大灾难中,罗马教会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它所做的,是篡取一个它不再代表的神圣原则,它成为质疑者的帮凶,为大革命铺平道路。大革命的钟声如今已经在圣彼得教堂的门前敲响?这有什么可惊讶的?罗马教会一旦与世俗利益的土壤联结起来,就成了必死的。因此,教皇权力成为大革命的牺牲品,这是事物的因果报应,这是上帝不可阻挡的正义。

然而,在19世纪中叶,东正教徒的胸怀是何等宽宏啊!基督不是说过“凡一家自相分争,就必败落”吗?愿罗马重新回到普世教会的怀抱,它的一切都将被宽恕!愿教皇涕泪横流地投入沙皇的怀抱,天上的“一”将在尘世重新找到它失去的统一!罗马一直声称要先把君士坦丁堡,然后把莫斯科召回它身边?如今,是莫斯科请求罗马回到它身边:
最后一次,重新考虑一下吧,旧世界。
野蛮的七弦琴请你参加
和平的宴会、工作的宴会,以及最后一次,博爱的宴会! [3]
毕竟,时代变了,只要俄国东正教廷设在君士坦丁堡,它就不得不首先承受一部分拜占庭帝国的软弱,再承受一部分奥斯曼征服的耻辱。
但自从它迁移到莫斯科后,东正教教会掌握的便是俄国的一部分权力,以及它日益增长的威望。当东正教会主教公会(le Saint-Synode)在彼得大帝的旨意下成为沙皇的温顺工具时,它便全心全意地效忠于俄国统治者的野心。1846年,当俄国沙皇访问罗马时,糊涂的天主教徒也许以为他们看到了迷失羔羊的忏悔回归。但对于东正教徒来说,基督的代理人只是在离开几个世纪之后回到了家。他才是基督教的前领袖、君士坦丁大帝的合法继承人,而西方的皇帝们,这些教皇的造物,从来都只是些没有头衔的新贵。
天主教徒现在说服自己还来得及:查理曼已不在巴黎,也不在亚琛,他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他非但没有去向格列高利十六世(Grégoire XVI)乞求道义或精神上的认可,而且在来到罗马时,声称要将基督教起源时的力量和东方传统的神圣性归还教廷,或者让教皇归还他1054年被篡夺的神圣信托:基督教西方的命运主宰权。 [4]
还有一个国家一直声称要与教皇共同承担基督教西方的统治权,那就是法国。如今在波拿巴治下的法国,还是像过去那样说话底气十足;即使在政教分离之后,法国的各位统治者依然将自己视为历史上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国王的继任者。
早在5世纪末,克洛维(Clovis)的受洗便令尚未出生的法国成为“教会的长女”: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诞生的法兰克王国,第一个将自己的命运与教皇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多亏了这天才的灵光,西坎布里人(Sicambre)
 的剑才得以所向披靡。
的剑才得以所向披靡。
后来,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后,哈伦-拉希德(Haroun-al-Rachid)让查理曼保管著名的“圣墓钥匙”。它尽管是传说中的钥匙,却象征着阿拔斯哈里发(le calife abasside)所承认的西方皇帝所拥有的权利:保护圣地,保护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无论他们是当地人还是朝圣者。 [5]
十字军东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的事业,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从发起、宣讲、组成到指挥,几乎全部由法国人完成。这次东征于1099年攻占了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几个法兰克国家,在将近两个世纪中,这些国家的王位都被布洛涅(Boulogne)、布尔格(Bourg)、安茹(Anjou)、吕西尼昂(Lusignan)、尚帕涅(Champagne)、布里耶纳(Brienne)几大家族占据。从1099年到1291年,从其最广阔的领土到塞浦路斯,总之,黎凡特法国(France du Levant)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存在,并在这些地区及其民众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再次征服并没有剥夺当地基督徒举行敬拜的权利,萨拉丁(Saladin)随后还承认了圣路易对基督教在东方的圣地所拥有的道德权利:一种宗教上的占有。
在这些与基督的生平和受难有关的地方——无论如何,僧侣们就是这样说的——建起了高墙环绕、半是圣所半是堡垒的教堂与修道院,僧侣们就这样生活在半土匪的牧羊人、敌对的游牧民,或是贪婪的官员们长期制造的危险环境中。
圣地的情形就是这样,方济各会的修士受命对它进行看守和维护,在那里举行礼拜,接待来自基督教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最终,不得不说,在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存需要的驱动下,他们把圣地变成了一个收益丰厚的商业资产。
法国人对圣地依然怀有强烈的怀旧情绪,法兰克人在东方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必须开花结果:1517年,巴勒斯坦圣地连同整个叙利亚全部落入奥斯曼人之手,不久之后,弗朗索瓦一世与苏莱曼大帝结成了令人震惊的同盟,并在1535年成为首位与苏莱曼大帝签订著名的《基督徒或外侨的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s,下简称《领事裁判权条约》)
 的欧洲君王。在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法国同时在政治、商业与宗教上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圣地被宣布“像过去一样”属于拉丁僧侣,也就是说属于法国国王保护下的天主教徒。
的欧洲君王。在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法国同时在政治、商业与宗教上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圣地被宣布“像过去一样”属于拉丁僧侣,也就是说属于法国国王保护下的天主教徒。
这是对天主教徒在圣地拥有的某种历史权利的正式承认,尽管众所周知,历史权利从来既不完全是权利,也不完全是历史……
《领事裁判权条约》分别于1569年、1581年、1597年、1604年、1673年及1740年续签。它们几乎不再具有政治内容,而是主要处理商业问题,但1604年、1673年和1740年的条约明确重申了法国在圣地的权利,及其作为东方基督徒监护国的地位。1720年,奥斯曼帝国的一位重要人物到访法国,这一事件非同寻常,其目的是进一步确认法兰西王国的这些特权——如果需要的话。 [6]
后期的法国—奥斯曼帝国《领事裁判权条约》具有一种特殊性质。首先,它们是在与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相同的政治结盟背景下与路易十五签订的:在16世纪是为了对抗奥地利,在18世纪则主要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帝国。1740年的条约显示,君士坦丁堡承认法国在前一年《贝尔格莱德条约》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贝尔格莱德条约》让奥斯曼帝国摆脱了困境。因此,圣彼得堡一直认为1740年的条约无效,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何况,1740年条约的第二点特殊之处在于,它第一次以七项条款,在无可辩驳的法律基础上,确立了给予法国的保护权。第33条保证拉丁僧侣“仍然像过去那样拥有他们所有的朝圣场所”。
事实上,厘定这个问题是必须的,因为现状不断朝着损害天主教徒利益的方向发生改变。法国在东方的影响力受到俄国的猛烈冲击,尽管法国那时试图将俄国遏制在“东方大坝”之后,俄国却在向南方蔓延(见附录I)。
正是从16世纪开始,从伯罗奔尼撒到巴勒斯坦,整个奥斯曼帝国中那些献身于敬拜、教育、慈善或圣地保护的基督教牧师那本已岌岌可危的处境中的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
这种状况实际上并不是土耳其人造成的,而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只要基督徒能克制他们劝人改宗的冲动,土耳其人通常并不在意他们。各个基督教派对他们共同的、一直潜伏的危险无动于衷,尽管这种危险本应使他们团结起来,而实际上他们相互之间却难以和平共处。有5世纪就与罗马分离的亚美尼亚人,有与亚美尼亚人相似的埃及科普特人,有近似于天主教徒的黎巴嫩山的马龙教派,有某个叙利亚教派的信徒,也有某个埃塞俄比亚教派的信徒,特别是还有天主教徒,尽管人数很少,在16世纪只有几百人,却更加活跃,他们有着不知疲倦的传道热忱,不仅向基督教其他教派的“迷途者”,还向穆斯林传播福音,这就必然导致他们与奥斯曼帝国当局的各种纠纷。
圣地掌握在天主教徒手中,这自然会引起强烈的嫉妒与垂涎,尤其是在东正教徒之间。东正教徒通常被称为“希腊人”,在这块古老的拜占庭土地上占有数量优势,急于承担这一优势天生赋予他们的角色。在过去,当圣地属于阿拉伯人时,他们只是作为朝圣者来到这里。但自1517年,已经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再次统治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后,东正教的神父像圣方济各的“拉丁”僧侣一样,把耶路撒冷、伯利恒或拿撒勒当成了自己的家园。
因此,他们很快开始了暗中行动。通过各种手段,他们获得了奥斯曼帝国通过发布旨令而赋予他们的权利,这通常是在圣所中担任执事的权利。在此之前,只有天主教徒才拥有这项权利。对这些权利的侵占引发了天主教徒的抗议,也正因此,1535年最初的《领事裁判权条约》对这个问题做出郑重厘定。
不幸的是,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恰好是法国伟大的传教世纪:1609年,耶稣会教士来到奥斯曼帝国,嘉布遣会教士随后于1625年到来。希腊僧侣与拉丁僧侣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法兰西王国的大使们启程之前收到的所有指令都在强调“他们的首要职责”: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
1637年,希腊人同样得到穆拉德四世(Mourad IV)发布的三项旨令,扩大了他们在圣地已经拥有的权利,直到1666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德尼·德·拉·艾-万特莱(Denis de la Haye-Vantelay)才设法令这些权利得以取消。在过去二十年里,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确实经历了风雨动荡,法国大使的父亲让·德·拉·艾-万特莱(Jean de la Haye-Vantelay),也是其在君士坦丁堡的前任,甚至被苏丹关进监狱,奥斯曼帝国拉丁神父的地位也受到这些政治动荡的影响。

当希俄斯(Chio)的希腊人“凭借重金和诽谤,以能够想象的所有暴力、疯狂和渎圣行为,将天主教徒举行圣礼的24座教堂” [7] 据为己有……就连1673年的《领事裁判权条约》——尽管它再次确认了天主教徒之前拥有的所有特权——也无法收回这些教堂;1699年,凡尔赛宫还委派德·费里奥尔(de Ferriol)大使提出归还希俄斯教堂的要求,“至少归还一个,如果不能归还更多的话”……
因为导致这种局面的不仅仅是希腊人的阴谋手段,或法国—奥斯曼帝国“联盟”的不测风云,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从来都乏善可陈。正是在1669年
 ,这个帝国的衰落成为显而易见的现实。在君士坦丁堡做出的决策与在耶路撒冷实际执行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仅仅因为地处偏远,耶路撒冷的帕夏就享有某种事实上的自治,而且那里的官员和士兵因为薪俸拖欠,已经成了各种诱惑的绝佳对象。
,这个帝国的衰落成为显而易见的现实。在君士坦丁堡做出的决策与在耶路撒冷实际执行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仅仅因为地处偏远,耶路撒冷的帕夏就享有某种事实上的自治,而且那里的官员和士兵因为薪俸拖欠,已经成了各种诱惑的绝佳对象。
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土耳其人也是以此进行某种报复:如果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开始扮演帝国宗主的角色,那么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觉得自己是整个基督教命运的主宰……
俄国在18世纪摆脱了次要角色的地位,成为一个强国,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俄国对奥斯曼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强,直到1774年订立《库楚克—凯纳吉(Kutchuk-Kaïnardji)条约》。这项条约明确宣告了奥斯曼的衰弱,却似乎以非常含糊的措辞给予圣彼得堡一种对奥斯曼帝国东正教徒的保护权。为此需要做出一些努力来进行解读,但这有什么要紧?正是在这个时期,奥斯曼的东正教教士开始宣泄他们对拉丁神父的愤怒,这符合俄国的利益;俄国极力以东正教徒的保护者自居,而这些拉丁神父则得到圣彼得堡无可争议的敌人——法兰西王国的支持,尽管是如此遥远的支持。
也是在这个时期,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友谊波澜曲折,为俄国的行动提供了理由:1756年,法国在与奥地利结盟之后,又与俄国结盟,这怀着何等的利益盘算!这个联盟的大逆转对奥斯曼来说无异于背后插刀。穆斯塔法三世(Mustapha Ⅲ)很清楚该怎样表达他对凡尔赛宫的怨恨:对于自18世纪初一直受到严格限制的圣地的希腊人,他立即给予一些新的特权,特别是从1757年开始将圣墓教堂划归他们所有。

当然,当我们深入探究这些数不胜数、无休无止的纷争时,就会对宗教产生怀疑!几个世纪来,所有这些上帝的子民到底为了什么而争斗不休?
他们争斗不休,是为了这个或那个教派能有权利在这个或那个教堂里祷告,先于其他教派在其中举行祭礼,合法地拥有一个小礼拜堂或祭台,在教堂里展示自己的宗教仪式物品,悬挂象征其合法权利的一盏吊灯或一幅画,在土耳其人的事先许可下在教堂里建一道墙或修理一个拱顶,
 先通过小的边门,然后通过大门进入教堂,最终禁止其他教徒进入教堂!
先通过小的边门,然后通过大门进入教堂,最终禁止其他教徒进入教堂!
震惊的朝圣者们面对的只是吵闹、打斗,甚至骚乱,而作为仲裁者的土耳其人,对这一切抱着看笑话甚至轻蔑的态度,有时赶来在教堂内部用大棒将这些朝圣者驱散!
更重要的是,圣地,不仅是对前来提升灵魂使之接近上帝的朝圣者们开放的教堂、一种宗教信仰凌驾于另一种宗教信仰之上的象征,它还是僧侣们在险恶的环境中赖以生存的事业,一种连续供给饭食、住宿、蜡烛、圣像、圣牌、各种饰物的事业,一种贪婪收取赠予、供品与布施的事业。
这是一场利益争夺的混战,所有的交战手段都被允许,更何况各方的上级都不在圣地;作为地区所有者,因而也是秩序维持者的土耳其人待价而沽,耶路撒冷当局随时会因为一些人支付的500银币,而放弃执行另外一些人花2000银币令君士坦丁堡制定的措施;西班牙和奥地利为了自身利益,凭借各种手段和大把金钱试图获取法国国王对拉丁僧侣的部分影响力;普鲁士和英国则分别自立为犹太人和黎巴嫩的德鲁兹人的保护者;最终,俄国不是挑起东正教徒的骚乱,便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的骚乱,这个导致奥斯曼帝国混乱和解体的因素,对于圣彼得堡的政策却极其有利。
显然,法国,尤其是太阳王的法国,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甚至几乎未能履行其使命:它原本是所有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但太过希望成为纯粹的天主教国家,于是因忽略其他教派,而将这些教派拱手置于其他权势的影响力之下。
但有一点法国是无可指责的,即使这并不符合某些作者的理论:的确,不是所有人都给予宗教问题同等的重要性,结果并不总是与付出的努力相称,但法国的历届统治者和历届政府都会在必要时向奥斯曼帝国当局表示抗议,要求他们遵守各项条约,为被剥夺财产或受到欺辱的天主教徒伸张正义。
确实,我们遗憾地看到,连皮埃尔·德拉戈尔斯(Pierre de la Gorce)这样严肃的作者,在这方面都附和那些在克里米亚战争上强烈指责拿破仑三世的一贯的反波拿巴主义者,他宣称“法国长期以来对来自耶路撒冷的怨言充耳不闻”,“直到1850年,政府才下决心向奥斯曼帝国当局重申1740年的郑重约定”。 [8]
事实上,无论在1740年之前还是之后,对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和公使们的指示都始终强调宗教问题。比如,1747年至1754年在君士坦丁堡任职的阿勒尔伯爵(le comte des Alleurs),被建议在宗教事务上采取“强硬”态度。1755年至1768年,阿勒尔伯爵的后任韦尔热纳伯爵(le comte de Vergennes)上任伊始就被提醒,“陛下的虔诚及其作为教会长子的身份促使他对宗教做出的保护,必须是其驻君士坦丁堡公使们的首要目标”。1768年上任的圣普里斯特伯爵(le comte de Saint-Priest)则被要求“努力维护供我们行使神圣信仰之用的圣地的所有权。国王曾强烈建议韦尔热纳骑士在从君士坦丁堡卸任之前完成一场特别谈判,其议题是收回希腊人从法兰克修士手中夺走的圣地”。伯爵尤其对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主教会议持戒备态度,该会议“向大公提出动议,要求驱逐所有拉丁人”。1785年至1792年的法国大使舒瓦瑟尔-古菲耶伯爵(le comte de Choiseul-Gouffier)收到提醒,“收复从法兰克修士手中夺走的圣地”的谈判未能成功,因此请他“以最大的关注和坚韧” [9] 来处理这个问题。
公共安全委员会(公安委员会)本身,无论其反教权的立场如何,也明白这里有巨大的国家利益需要维护。德斯科什(Descorches),公安委员会驻奥斯曼帝国的首任大使,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明确指示:“关于法国大使在与宗教及基督教信仰保护者身份——我们的大使始终被赋予这一身份——相关的职能上所享有的特权,公民德斯科什虽然并不过分重视,但仍保留它们赋予他的所有权利,即使只是为了维护法国的大臣们迄今所享有的尊重。”这些人“在法国的宗教政策虽然不以宽容和克制著称” [10] ,在这个问题上却极具远见卓识!
督政府显示出同样的考量:督政府的大使奥贝尔·迪巴耶(Aubert du Bayet)将军于1796年初到达博斯普鲁斯时,即要求“恢复法国大使的权利,特别是恢复保护君士坦丁堡及黎凡特港口城市的天主教堂的权利”
 。
。
我们已经看到,革命政府谨慎地避免放弃一项延续数百年的特权,在其之后,第一执政在1802年6月24日的《法土和平条约》中加入了条款2,这项条款完全恢复了1740年的《领事裁判权条约》。1804年,他又出面干预,将希腊人侵占的客西马尼园归还天主教徒。
1811年,皇帝拿破仑通过法国大使德·拉·图尔-莫布尔(de la Tour-Maubour)先生向奥斯曼帝国政府传话:虽然他允许希腊人修复圣墓教堂三年前被大火烧毁的穹顶,但这并不能给予希腊人他们企求的新权力。
 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尽管是位还俗的主教,但不停地激发其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的热忱,以“恢复并充分行使……保护黎凡特天主教堂的权利”。
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尽管是位还俗的主教,但不停地激发其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的热忱,以“恢复并充分行使……保护黎凡特天主教堂的权利”。
作为狂热的宗教捍卫者,路易十八的政府,以及随后的查理十世的政府,则不放过任何出面干预的机会。
因此,路易十八政府强烈抗议1817年苏丹颁布的一项旨令,在当时如日中天的沙皇亚历山大煽动下颁布的这项旨令宣称,圣地既不属于天主教徒也不属于希腊人,而是属于土耳其人。巴黎无法接受将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相提并论,但与沙皇就此进行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至于查理十世,得益于其大使吉耶米诺将军(le general Guilleminot)的积极努力,他成功地为君士坦丁堡受到迫害的亚美尼亚天主教徒讨回了公道,还促进制定了各种行政措施,旨在改善信奉天主教或属于罗马教会的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生活状况。
最终在1835年,七月王朝让鲁森元帅(l’amiral Roussin)进行军事干预,他为天主教徒恢复了在阿森松教堂举行祭礼的权利。这座教堂在很久以前落入穆斯林手中,因此一直禁止基督徒入内。此前,在最终于1830年7月30日签订的关于希腊问题的《伦敦条约》的终场谈判中,路易-菲利普政权说服英国人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与俄国人德·利文(de Lieven),使之关注在希腊天主教徒问题上“法国的特殊处境”,并且同意向希腊天主教徒提供保障,这些“保障应能替代迄今为止(法国)采取的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由此,英国,特别是俄国,正式承认了法国一直以来对奥斯曼帝国的天主教徒行使的保护权。
1847年,七月王朝的大使布尔克内(Bourqueney)不得不再次进行干预:前一年的11月1日,天主教徒在圣墓教堂里已经拥有不止两个小礼拜堂,希腊人却在建于“伯利恒之星洞”遗址上的圣诞教堂里窃取了一枚法国“银星”徽章。自远古以来,这枚徽章就在圣诞教堂里,象征着拉丁僧侣对这块圣地的占有。
表面上看来,这也许是桩小事,但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决定性事件。
因为哪个政府会不明白这一点?在皮埃尔·德拉戈尔斯精巧地称为“争论的微粒”的背后,是大国势力之间的对抗,特别是法国和俄国势力的对抗,这些势力通过宗教问题牵动大国在东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当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小规模战争后,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诉求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令人难以进行分析。但法国仍然具有建立在国际条约基础上的一般权利,只有各方共同达成的协议才能对其进行质疑,而奥斯曼帝国颁布的有利于希腊人的旨令,从来都只是其内政管理法令,苏丹可以自行将其撤销。
有人会说,俄国也可以依靠双边外交行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但是,这个内容极其含糊的条约丝毫没有提及圣地,除此之外,它是在1740年《领事裁判权条约》之后订立的,而该条约从未被废除。(见附录Ⅱ)
因此,不可能像勒内·吉耶曼(René Guillemin)等人那样,坚持认为俄国享有与法国类似的权利。 [11]
此外,法俄两国在奥斯曼帝国发挥或准备发挥的影响力的性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法国的影响从来都只涉及几百名,后来是几千名天主教神父,而且他们通常是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绝不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因此,正如圣普里斯特伯爵所写的那样,对他们使用“保护权”一词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补充说,这个词“就是为了误导那些不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 [12] 。
另外,俄国通过武力或阴谋,试图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的,是对奥斯曼帝国1100万~1200万东正教臣民行使的真正保护权;很简单,由于这些东正教臣民的组织构成了行政和司法级别上的准自治社区,对于奥斯曼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来说,沙皇的主权取代了苏丹在自己国家的主权!
1850年,第二共和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奥皮克将军(le général Aupick)负责跟进一份档案,我们已经看到,这份档案从来就没有真正封存。有人可能会断言,拿破仑三世只是为了所谓的帝国政策的需要而故意创建了这个档案,比如莫里斯·加科特(Maurice Garçot)的那句“自从他登上了帝国的宝座” [13] 就暗示了这一点。但路易-拿破仑早在恢复帝制两年多前,就已干预拉丁人的利益,那时他刚刚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的“帝国”前景似乎已经确定。此外,同样在1850年,西班牙、皮埃蒙特与那不勒斯王国难道没有公开支持法国的行动?比利时难道没有借机要求君士坦丁堡修护布永的戈弗雷(Godefroy de Bouillon)的墓地,而奥地利难道没有要求遵守它自己与苏丹之间的协议?
因此,必须承认,波拿巴家族的一员进行的这种干预属于法国的历史传统,而不是像人们经常断言的那样,属于拿破仑的思想体系,后者只存在于某些人的头脑中,而且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和平笼罩着苏丹帝国,甚至敌对的各教会也和平共存,而此时,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冷静地、毫无动机地采用了已被遗忘的天主教信仰的事由,开始把它作为一个楔子加以利用,以打破世界和平……”
英国人亚历山大·威廉·金莱克(Alexander William Kinglake)在其享有盛名的著作《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与历史》( Origine et 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Crimée )中就是以这种充满恶意的措辞来谈论圣地事件的。不幸的是,尽管长期以来最严肃的历史学家对这些谎言进行了批驳,公众还是普遍接受了金莱克的论断。这些论断因发表时间早而享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特权,而且被所有敌视帝国的作家不厌其烦地重新提起。 [14]
因此,即使在今天,人们仍然特别倾向于认为(法国)“直到本世纪中叶……都采取放任的态度”,“正是由于法国的默许”,东正教徒才享受到他们逐渐获得的利益;人们认为奥皮克将军的指令是要求“严格执行”1740年的条约,而该条约在缔结时只不过是法国“从土耳其人手里夺来的一项特许权”;人们还认为拉丁朝圣者“通常只是带着旅行日志的一群法国游客”;认为法国保护东方天主教的“抱负”可以“追溯到虔诚基督徒国王(Roi Très-Chrétien)的情妇们是虔诚信徒的时期”;认为法国的大使“似乎在强硬指令的授意下……如果谣言可信的话,最先谈到诉诸武力”;他们最终认为,正是拉丁僧侣们对“拥有伯利恒教堂正门钥匙,而不是满足于侧门钥匙”的要求,长期以来令问题难以解决,并导致了军队的出征以及舰队的威慑举动。
所有这一切确实与拿破仑三世的黑色传说极其“贴合”,因此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迹。
但是!
1850年5月28日,当奥皮克将军在君士坦丁堡向奥斯曼帝国外交大臣阿里帕夏(Ali-pacha)递交了一份照会,为天主教徒们追讨布尔克内三年前未能获得的补偿时,天主教徒们持续不断的抱怨中又多了一个新的复杂问题,即伯利恒银星被偷事件,这一事件的象征意味过于重大,因而不可能不产生严重后果。
法国自然援引1740年条约,但正如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次年议会复会时所言,法国要求的,不过是“一项交易,它可以终结经常因圣地所有权而产生的可悲的纷争”。的确,1848年12月天主教徒以压倒性多数投票给他,如果路易-拿破仑放弃法国在东方的传统政策,他们是不会理解的。
但也不能为了赢得法卢(Falloux)与蒙塔朗贝尔(Montalembert)的多数派,而试图剥夺希腊人自16世纪以来积累的众多利益。因为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可以带来名分。因此,法国大使的语气虽然恰如其分地坚定,却谦恭有礼,毫无威胁意味。他所希望的是,为了相关各方的利益,最终“结束反复出现的难题,让这个难题永远延续下去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此外,对驻君士坦丁堡法国外交官语言强势的指责,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错误的:长期以来,君士坦丁堡陷于强国之间各种相互矛盾、错综复杂的要求之网中,只有在压力甚至是威胁下才会顺从,而威胁恐吓正是俄国人的专长。俄国外交官德·布特维耶夫(de Bouteviev)会说:“俄罗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角色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简单得多:那就是永远成为奥斯曼最大的朋友或最大的敌人。”其他强国怎么就不该或多或少地提高自己的声调,以免被完全排挤出局呢?
因此,在1850年的5月底,土耳其人倍感为难:怎样才能满足法国这个灾难发生时可能需要的朋友,而不惹恼俄国这个一向多疑、很可能招致灾难的潜在敌人?所以,从搪塞推诿到各种遁词,从外交旅行到宗教节日,君士坦丁堡尽其所能地回避问题,直至最终决定任命一个伊斯兰—基督教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从1851年7月1日开始工作,在秋天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推出了一项协议草案。
这项协议草案对于天主教事业来说只成功了一半,其所有诉求都远未得到满足,但这毕竟是双方希望的一项交易,也是双方达成的一项交易,将近18个月的东方式的讨论已经令巴黎的内阁疲惫不堪,何况还有很多其他议题需要关注,于是,内阁批准了这项草案,并委托奥皮克将军的继任者德·拉·瓦莱特先生尽快商定协议。
但这一切没有考虑到俄国,而俄国始终保持警惕,并且经常有特工提供情报。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大臣蒂托夫看到交易就要达成,急忙赶到阿里帕夏的府邸,直截了当、气急败坏地说:“任何违反现状的行为都将被我主认为是对其尊严的侮辱!”10月28日,加加林亲王(prince Gagarine)向苏丹转交了一封沙皇的亲笔信,这封语气专横、令人不安的信引起了奥斯曼政府大臣的恐慌,因为它唯一的要求就是立即停止与天主教徒的谈判。
正是尼古拉一世对巴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这场谈判的亲自干预,真正开启了圣地的危机。
事态令土耳其人感觉受到了侮辱,尤其是这些事件与他们并无直接关系,对他们来说,这次事件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法国和俄国,哪个最令人恐惧?
于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借口需要进一步的信息,选择召集第二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全部是穆斯林——以便进行一项极富东方特色的活动;自从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往日的强盛,政府就擅长这项活动:给一些人面子上的满足而又不触怒另一些人。
就是在那时,仅仅在那时,此前一直“甜言蜜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法国大使开始变得言辞“激烈”:刚刚结束冗长会谈的瓦莱特会不会看到他的“佩内洛普之毯被重新拆开了”
 ,就像他给图弗内尔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就像他给图弗内尔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对法国大使来说,幸运的是,来自法国的消息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支持:政变成功了,1851年的全民公决对总统来说是一场胜利,很明显,法国将再次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国。因此,1852年1月26日,轮到阿里帕夏“甜言蜜语地”向瓦莱特透露“一切都安排好了”。
接下来的2月8日,被认为可以调停各方的旨令切实地颁布了。
然而,这项旨令给予天主教徒的只是纯粹形式上的满足:承认他们在客西马尼的圣母教堂举行礼拜的权利,以及保留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两道边门钥匙的权利,并承诺将正门的钥匙也交予他们。此外,据称丢失的银星将被找回并重新安置于伯利恒。但作为交换,此前确保他们一年一度在阿森松教堂举行礼拜的专有权利被取消,穆斯林现在主持着阿森松教堂,他们允许天主教徒进入教堂:从今往后,希腊人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进入圣所的权利。天主教徒过去拥有的专有权利没有任何一项归还给他们,更重要的是,这项旨令丝毫没有提及法国的历史权利,而那是天主教徒的诉求的法律依据。
因此,与当时的状况相比,他们获得的仅有的两项利益就是:在圣母墓教堂举行礼拜的权利,以及拥有伯利恒教堂正门钥匙的权利。但是,除了1740年的条约已经承认他们拥有这些权利之外,伯利恒教堂钥匙的移交甚至没有给予他们在这座教堂举行礼拜的权利,英国临时代办罗斯上校在给英国政府的信中写道:“事实上,移交钥匙算不了什么;它没有给予天主教徒在教堂里举行礼拜的权利,它只是允许他们进入教堂下面基督诞生的山洞,天主教徒在那里有两个圣所:马槽与东方三博士的洞穴。”
至于法国临时代办萨巴捷(Sabatier),他在5月5日给图弗内尔的信中写道:“第一个特许是虚幻的,第二个特许是可笑的!圣母墓在城墙外5分钟路程的地方,我们的教徒想去那里时将会受到各种侮辱……在伯利恒,我们会得到教堂钥匙,但大门也会一直关闭。”
事实上,在耗费了大量精力之后,成果却是微不足道的,尽管瓦莱特在君士坦丁堡被完全孤立,其观点却与其大臣和拿破仑三世的观点一致:这场关于圣地的争论跌到了外交谈判的冰点,除了结束,不再值得采取任何行动,即使法国只是从中得到一种原则上的满足。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法国大使没有炫耀胜利,2月15日他在给图弗内尔的信中写道:“我无须告诉您,旨令颁布一周后,我做出了低调的姿态,没有在街上悬挂彩旗!但是,我们对手的喊叫声让人以为我们取得了比实际情况更全面的胜利。”
不幸的是,在巴黎,瓦莱特的朋友们要为他吹嘘胜利:天主教报界,特别是《争论报》( Débats )——社长阿尔芒·贝尔坦(Armand Bertin)是大使的一位密友——竭力夸大他取得的微薄利益。
这场非常不合时宜的宣传触怒了沙皇,激起了东正教徒的怒火,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佩尔西尼写道:“神职人员的小圈子像赢得了一场国家胜利那样为一个幼稚的成功而扬扬得意。” [15]
对那些头脑最清醒的人来说,形势实际上令人心酸,萨巴捷写道:“我们被打败了,却很开心。”他痛苦地看到权势显赫的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站在“那些取笑我们的人的最前列”。
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结束了:当奥地利代理大使对自己强大的天主教对手的不幸幸灾乐祸时,当英国大使像讥讽“僧侣们的争吵”一样讥讽法国不可救药的“荣誉本能”时,瓦莱特对2月8日的旨令表示了赞同,并于3月15日外出休假,准备像过去那样让教皇和修士、土耳其人、俄国人、希腊人与拉丁人统统都去见鬼。

然而,在敌对的阵营里,人们觉得掌握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法国大使刚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东正教徒与俄国人的联合行动迫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布了一项与2月8日的旨令相反的旨令!之前承认天主教徒享有的可怜权益被取消了,形势又回到了奥皮克将军时期的状态。东正教徒要求在耶路撒冷公开宣读对他们有利的旨令。这道程序并非惯例,其目的只能是羞辱巴黎,而天主教徒将奋力争取让这项旨令只被记录在案,而不被公开宣读。
妥协终将达成:旨令将在耶路撒冷的帕夏、主教、一些官员与外交官组成的有限的听众面前宣读。希腊人会就此罢休吗?谈判还得进行:天主教徒可以在圣母教堂举行礼拜,但“不能对场地现状进行任何改变”,这使得他们无法在一个分立派教堂的祭坛上举行礼拜。同样,他们也会得到伯利恒教堂的正门钥匙,但阿菲夫-贝伊帕夏(le pacha Afif-bey)明确告诉他们,那把钥匙他们一年只能用四次。
夏天,休假回来的瓦莱特明白过来他被耍了。8月25日,他写信给图弗内尔道:“今天,雷希德帕夏(Rechid-pacha)亲口给我提供了证据,阿里帕夏在发布2月8日照会的同时也拟定了为希腊人发布的旨令。他亲口承认,他把照会传达给俄国人,却向我们隐瞒了为希腊人发布的那道旨令。”
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外交大臣德鲁安·德·吕(Drouyn de Lhuys)向英国驻法大使宣称:如果奥斯曼帝国政府发表一份声明,保证在发布“希腊旨令”的同时无意背弃对法国所做的承诺, [16] 他就满足了。在关于这道旨令的宣读问题上,瓦莱特已经向福阿德-埃芬迪(Fouad-Effendi)保证“他会在这个问题闭上眼睛,不让它成为与君士坦丁堡发生争执的议题” [17] ,总之,瓦莱特最终放弃要求一项连科普特人和阿比西尼亚人都在圣母教堂内拥有的权利:在其中拥有烛台灯和圣像的权利。如果考虑到上述这些情况,我们只能承认:在整个事件中,“将和解精神发挥到极致是法国政府的荣誉” [18] 。
因为最终,法国没有像瓦莱特在8月所说的那样,要求得到“根据条约天主教徒有权得到的圣所的十分之一”。法国几乎没有得到它要求的任何东西,特别是1740年条约作为天主教徒的权利依据未能得到承认。
但天主教徒或多或少地能在圣母教堂举行礼拜,还能每年四次打开伯利恒教堂的大门,这些足以激起东正教徒的怒火,因此在1852年的这个夏天,巴黎决定着手替换瓦莱特,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圣彼得堡进一步的让步来平息局势。德鲁安·德·吕在给卡斯泰尔巴雅克将军的信中写道:“调离我们的大使就能减少一个令人恼怒的因素。恕我直言,我们同涅谢尔罗迭先生一样,对报纸上发表的吹捧瓦莱特侯爵的文章感到生气。我们可以非常真诚地告诉您:我们不想进行对抗。如果我们不是有所承诺,我们不会主动挑起这个事件。”因为法国驻俄国大使有理由对他的所见所闻感到担忧,他在3月31日给图弗内尔的信中写道:“整个事件在俄国公众舆论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骚动,尽管他们通常并不关心政治……”
在危机的这个阶段,仍有一个应对之策:俄国沙皇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之间直接达成和解,1852年12月2日,后者刚宣告为法国皇帝,称拿破仑三世。
情势难道不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吗?1853年1月16日,尼古拉一世在圣彼得堡接见卡斯泰尔巴雅克时告诉他,他很高兴看到“外交议定书事务终于完成”
 ,并且收到拿破仑三世一封亲笔信,信中就圣地问题向他做了“友好而值得信赖的解释”。
,并且收到拿破仑三世一封亲笔信,信中就圣地问题向他做了“友好而值得信赖的解释”。
然而,尽管沙皇宣称“赞成和解”,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俄国皇帝仍在追求实现二十年来他为之历尽风险的宏伟蓝图,他决定究诘前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究诘奥斯曼帝国外交大臣福阿德-埃芬迪拒绝下令公开宣读“希腊旨令”,究诘最终给予天主教徒的可怜的特许。谈到苏丹时,他说“陛下对他食言了”,这一冒犯需要补偿。1月14日,涅谢尔罗迭以极其平静的语气致信布吕诺男爵(le baron de Brünnow):“就这样,损害已经造成,现在是修复它的时候了。东正教徒的豁免权被侵犯,苏丹向皇帝郑重许下的诺言也被违犯,这一切都需要补偿。”
他又极尽刻薄地补充道:“火炮曾被称作国王们最后的手段。法国政府做出了表率。这就是他一开始据此宣称要在的黎波里和君士坦丁堡采取行动的手段。尽管我们有合理的申述对象,并且可能要等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补偿,我们还是会采取一种不那么仓促速决的态度。”

然而在1853年的1月间,西方国家的总理(首相)们收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称俄国军队将补充军备,并向多瑙河公国调集军队。

2月8日,基塞列夫(Kissélev)在巴黎向外交大臣德鲁安·德·吕宣称沙皇准备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一名临时大使,负责一劳永逸地“完成”圣地事务。但如何完成呢?这位俄国外交官无法做出具体说明。第二天,在回答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提出的同样问题时,涅谢尔罗迭回答说,这位谈判代表“将在现场予以告知,因为很难具体说明保证给予希腊人的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侵犯”。
沙皇的临时大使缅什科夫亲王于2月11日离开俄国首都。帝国总理府反复强调,他携带的指令“都是和平的”。那么,为什么俄国军队现在集结在摩尔达维亚边境呢?商贩和穿越摩尔达维亚的旅行者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该如何解释他们选择尊贵的芬兰海军上将——海军大臣兼总督殿下——这样一位权势显赫而且以举止粗暴著称的人物来解决一桩如此微不足道的事件呢?

无论如何,巴黎不希望君士坦丁堡成为法俄对峙的决斗场,拿破仑三世让拉库尔(Lacour)
 取代了瓦莱特。
取代了瓦莱特。
英国采取了同样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允许他们自己的大使安心地去度假,因此沙皇特使面前的土地仍是自由的,因为法国和英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代表只有他们的公使馆秘书贝内代蒂(Bénedetti)和罗斯上校。然而,两国政府的动机并不相同:法国想显示其和解的愿望,而此时的英国则觉得事不关己,主要是想避免激怒俄国。
因为前一年的12月16日,对巴黎怀有好感的德比勋爵(lord Derby)内阁遇到了一个平常的财政问题,十天后,一个毫不亲法的联合内阁取代了德比勋爵内阁:亲俄的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成为英国首相;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负责外交事务,2月21日他被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取代;法兰西帝国唯一的朋友,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则被排挤到内政部。
总的来说,英国人对几个星期前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宣告成立的第二帝国满怀戒备。
然而,英国内阁表面上的平静,英国外交官在人们谈及沙皇时所说的安抚之言,英国内阁坚定地拒绝分担拿破仑三世政府的不安,在巴黎,人们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 [19]
2月28日,缅什科夫亲王在君士坦丁堡下船,受到成千上万聚集在码头上的狂热希腊人的欢迎,亲王后面的随行人员主要由穿着五颜六色制服的军人组成,显示着君王的气派。不久之后,黑海舰队总参谋长、海军少将科尔尼洛夫(le vice-amiral Khornilov)与比萨拉比亚的军队参谋长尼卡波钦斯基将军(le général Nikapotchinski)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途中,缅什科夫在敖德萨对军队进行了巡视,检查了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港的舰队。
整个3月,围绕着这项奇特的外交使命,气氛日益变得沉重起来,更加奇怪的是,俄土会谈的主角们对会谈内容秘而不宣。面对罗斯或贝内代蒂的提问时,缅什科夫几乎只是以讽刺之言或俏皮话进行回答——在圣彼得堡,他以擅长说讽刺俏皮话著称,而奥斯曼帝国的大臣们则固守着一种近乎恐惧的沉默。这些都足以令西方使馆的代办们,开始向他们的政府发送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消息。
3月23日,法国地中海舰队离开土伦港驶往萨拉米斯湾(baie de Salamine)停泊,似乎是为了平衡俄国军队在摩尔达维亚边境的集结。但在英国,尽管金融界和商界对此表示担忧,内阁仍然表现出同样的略带轻蔑意味的平静。克拉伦登评论道:“德鲁安·德·吕是一个非常平庸无能的大臣。” [20] 3月23日的《泰晤士报》则写道:“所有这些担忧都毫无意义。我们确实无法理解罗斯上校的恐惧。”
一向警觉的英国难道失明了吗?
特别是4月初,拉库尔与斯特拉特福德上任伊始,就认清了局势并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英国人已经成了熟知东方现实的精明行家,对英国人来说,彻底解决引发这场危机的圣地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也许应该相信,双方的立场并不像圣彼得堡所说的那样相距遥远:经过几天的谈判,拉库尔与缅什科夫于4月22日达成协议,似乎终结了三年的激烈对抗。
因此,天主教徒将能使用他们的敬拜器具在圣母教堂里举行礼拜,但仅仅位列第三——在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之后,每个教派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而希腊人并未得到任何优先照顾,他们之所以排在第一,仅仅是因为在整个东方,人们都习惯在清晨祈祷。
因此,天主教徒保管伯利恒教堂的大门钥匙,但根据约定,这把钥匙只允许他们进入圣所,而他们不能在希腊人眼皮底下关闭圣所。
因此,为了显示公平与慷慨,教堂的看门人将是希腊人,但他无权阻止天主教徒进入教堂……
5月4日,苏丹批准了协议文本,各方都很满意,圣地之争似乎终于解决了。
但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有谁不知道基督徒们代代相传的那个古老预言呢?根据这个预言,在拜占庭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奥斯曼的王位将恰好在八个世纪之后坍塌。因此,正是在1853年,土耳其人将被赶出君士坦丁堡,“被丢弃到亚洲”
 ……
……
圣地之争结束了。
东方的战争可以开始了。
因为法国人的皇帝肯定不会再像十年前,当他还是囚禁在哈姆堡(fort de Ham)的路易-拿破仑亲王时那样,发出这句感叹:“俄国想要君士坦丁堡,那就把帝国的这块残骸给它!”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