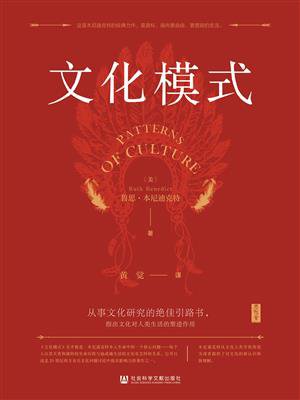序
20世纪,人们对社会人类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开辟了许多新路径。老办法是人们利用点滴证据建构人类文化的历史,这些证据取自全世界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失去了文化间的自然接触。如今这种老办法已经站不住脚。于是人们通过对人类文化具体特征的分布进行研究,辅以考古学证据,努力重构历史联系。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从这个视角观察的领域越来越宽广。研究者试图在不同文化特征之间建立起坚实的关联,并借此建立更广泛的历史关联。文化通史研究曾假设相似的文化特征有可能独自发展,这种可能性已经被否定,或者不再占据重要地位。进化论的方法和对独立地域文化进行分析的方法都曾试图揭示文化形式的发展顺序。研究者试图通过前一种方法建构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整体面貌;后一种方法的支持者,至少那些较为保守的支持者,则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单位,是单独的历史问题。
受深度文化分析的影响,对与文化形式不可分割的材料进行收集得到了极大的推动。这些搜集而来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这些信息让我们觉得可以把社会生活分成泾渭分明的类别,比如经济、技术、艺术、社会组织、宗教,而且它们之间鲜有关联。而人类学家的位置则令人想起歌德的讽刺:
想认识生物,记述生物的人
首先便要驱逐精神,
结果是得到些零碎的片体,
可惜没有精神的联系。

对活文化(living culture)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每种文化的整体性的强烈兴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特质一旦离开了它的整体环境就变得无法理解。然而试图将文化看作仅由一套条件控制的整体,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纯粹的人类学—地理学,或经济学,或其他形式主义的方法,都只能提供扭曲的画面。
试图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进行把握,这样的意愿迫使我们将标准化行为的描述仅视为通往其他问题的跳板。我们必须将个体置于其所处文化中加以理解,也必须将文化视作个体经历加以理解。这与历史方法并不抵触,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注反而揭示出文化演变的动态过程,促使我们通过对相关文化的细致比较来评价我们获得的证据。
由于材料的特点,文化生活问题常常表现为文化中不同方面相互关系的问题。这种研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文化中整体性(或缺乏整体性)的程度,凸显不同类型文化的各种整合形式,并且看到文化中不同方面繁多的关系模式,不宜笼统论之。然而,这种研究却无益于或者只是间接地促进我们对个体与文化的关系的理解。
这种理解要求对文化的精神特质具有深刻洞见,并且了解主导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各种心态。本尼迪克特博士将文化的这种精神特质称为文化形貌(cultural configuration)。她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以三种文化为例阐明了这一问题。她所列举的三种文化各有一种广泛存在的主导理念。这种方法有别于剖析社会现象的所谓功能方法,其关注点在于发现基本心态,而不是纠缠于每种文化项之间的功能关系。这不是历史方法,但论及全面形貌时例外。文化形貌只要还在延续,便会规限始终从属于它的变迁方向。相较于文化内容,文化形貌常具有突出的恒定性。
本尼迪克特指出,并非每种文化都有某种主导特性,然而我们也许对促成个体行为的文化驱动力了解越多,就越能发现某些控制情感的因素、某些理想行为占上风,它们导致那些从我们这个文明的角度来看属于异常的态度。于是,人们对社会与反社会以及正常与反常的相对性有了新解。
本尼迪克特选取的极端案例更突出了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弗朗兹·博厄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