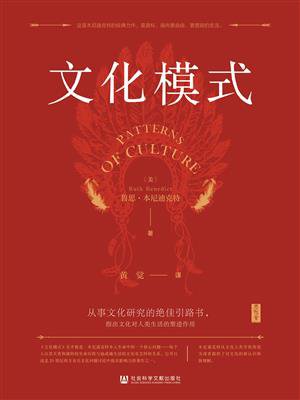第一章
习俗研究
人类学将人作为社会动物加以研究,其关注点落在人的身体特征和工艺技术,以及风俗习惯和价值观方面,这些因素将某共同体区别于属于其他传统的所有共同体。
在社会科学里,人类学独具一格,其研究对象包括本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就其目的而言,在人类学研究里,任何关于婚配和生育的社会规则都与我们自己社会里的规则同等重要,即便这些社会规则属于婆罗洲海地达雅克人(Sea Dyaks),与我们自己文明中的相应社会规则不可能有丝毫的历史关系。对人类学家来说,我们自己的习俗与新几内亚某部落的习俗或为两套不同的社会体系,却都是为了解决相同的问题而形成的。因此,人类学家一定不能厚此薄彼。人类学家所关注的是人类行为,并不局限于某一种传统——我们自己的传统——所塑造的人类行为,而是关注任意一种传统所塑造的人类行为。人类学家关注不同文化里的大量习俗,试图理解这些文化的变迁和分化方式、它们借以表达自己的不同形式,以及民族习俗如何影响构成该民族的个体的生活。
现在没人把习俗看作了不起的大事。我们觉得自己大脑内部的工作机制特别值得研究,却认为习俗是再普通不过的行为。可是事实恰好相反。纵观全世界,传统习俗无不由大量具体行为组成,它比任何人在个体行为中所能进化出的东西更令人惊叹,无论他的行为有多反常。而这还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习俗在经验和信仰中扮演了支配性角色,而且变化无穷,这才是头等重要的事实。
谁也不会用新生儿的眼光看世界。每个人眼里的世界都受一套特定习俗、制度和思维方式左右。即便在哲学思考中,人类也不能摆脱这些定式;关于真与假的观念仍会以某种特定的传统习俗为参照系。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着重指出,习俗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与个人行为对传统习俗可能产生的影响相比较,就如同一个人母语的全部词汇之于他牙牙学语时说出而后被家人经常使用的那几个词。一个人倘若认真研究那些自发形成的社会规则,他所能得到的顶多不过是一次精确而实事求是的观察。个人生活史首先是适应其共同体内部代代相传的模式和标准。一个人从出生伊始,其经验和行为就被自身所处的那些习俗所塑造。他学会说话时,便已然是其文化的小小产物;等到他长大并能在其文化中参与活动时,他所在文化的习惯便也是他的习惯,他所在文化的信仰便也是他的信仰;他所在文化的不及之处,便也是他的不及之处。在这个社群中出生的每个孩子都是如此。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孩子,无一能得到哪怕千分之一。在我们必须了解的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习俗的作用。如果我们不了解习俗的法则和变化,我们就断然无法了解使人类生活变得复杂的主要事实。
只有接受某些基本观点,并坚决反对另一些基本观点,关于习俗的研究才能造福于人。首先,对于选中的研究对象不能有厚此薄彼之心,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要求。在一些争议较小的研究领域,如对仙人掌、白蚁或星云性质的研究,将相关材料分组并考察一切可能的差异形式和条件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我们已知的天文学规律,或者,比如群居昆虫的习性,都是通过这种方法了解的。只有在研究人类自身时,社会科学主要学科才以对一个区域性变种的研究——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取代对其他变种的研究。
如果我们满脑子都是自己与原始人的差异、自己与野蛮人的差异、自己与异教徒的差异,那么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首先必须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信仰并不比邻人的迷信更高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制度其实是建立在相同的(超自然的)前提之下的,因此我们必须全盘考虑,我们的信仰不过是其中一种。
19世纪上半叶,西方文明里最开明的人也不懂人类学的这条基本原则。有史以来,人总是捍卫自己的独特性,并以之为荣。在哥白尼时代,唯我独尊的观点涵盖一切,甚至包括我们居住的地球。14世纪的人拒不接受地球属于太阳系的观点。在达尔文的时代,人在太阳系这事上向敌人投降了,却又竭尽所能来捍卫灵魂——上帝赐予人的一种说不清的属性——的独特性,拒不承认人类的远祖源于动物王国。不论其论点多么缺少连贯性,不论这个“灵魂”的性质多么可疑,甚至不论19世纪的人其实一点不在乎与任何异类成为兄弟,这一切事实都不敌进化论与人的灵魂的独特性相抵牾而引发的无与伦比的暴怒。
公平地说,这两场仗我们都打赢了,即使尚未尘埃落定,我们也离胜利不远了;但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愈演愈烈。如今我们忙不迭地承认,地球围绕太阳转,或人类的祖先是动物,这些与人类成就的独特性简直毫无关系。倘若我们只是碰巧居住在太阳系里众多行星的一颗上,那岂不是更值得骄傲?倘若进化使彼此敌对的人类种族与动物相联系,那么我们与它们之间可证的差异就愈加明显,我们的制度也就更显独特。“我们的”成就和“我们的”制度是独一无二的,与那些“劣等”种族的成就和制度不可同日而语,必须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因此直到今天,不论关乎帝国主义问题还是种族歧视问题,抑或基督教与异教比较的问题,我们所考虑的独特性依然不是全球范围内各种人类制度的独特性,也无人在意这些,而是自己的成就和制度、自己的文明的独特性。
因历史的机缘巧合,西方文明比已知任何其他地域性群体的文明传播得更远,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自立为标准,于是我们以为人类的行为具有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有时一些非常原始的民族对于文化的作用,甚至比我们有更强的意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与多种文化有过密切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宗教、经济制度、婚姻禁忌在白人文化的面前式微。他们舍弃一套制度,接受了另一套他们常常不能完全理解的制度,心里却非常明白人类生活的安排千变万化。有时他们会像人类学家一样,将白人文化的主要特征归结为商业竞争或战争制度。
白人的经历则不同于此。他可能从未见识过自己文化之外的人,见过的外人也都早已欧化。倘若他有过出游的经历,很可能周游了世界,却从未在国际酒店以外的地方居住过。他对其他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其周遭可见的是同样的习俗、观念,这让他相信整个世界就是如此,却向他隐藏了一个事实:这一切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他也不再费力深究,便认为人性等同于他自己的文化标准。
不过,白人文化的广泛传播并非孤立的历史现象。在相对较近的年代,波利尼西亚人也将自己的文化从翁通爪哇传播到复活节岛、从夏威夷传播到新西兰,说班图语的部落文化则从撒哈拉沙漠传播到南部非洲,但我们仅将此视为某些地域性人种的过度发展。西方文明则发明出了全套的交通手段并做了全面的商业安排,以支持它在全球传播。回顾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白人文化传播产生的心理后果远远超出物质后果。这种世界范围的文化传播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使我们不必认真对待其他民族的文明。我们的文化因此获得了非常强的普遍性,乃至我们早已不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此事,反倒认为事情必然如此,别无他途。我们因为自己的文明依赖经济竞争,就说它是人性可依赖的首要动机。我们把受自己的文明塑造并在儿科诊所里记录的幼儿行为称作儿童心理,亦即人类幼崽都会有的行为。谈到伦理问题,或者家庭组织,我们也是这种思路。我们将自己熟悉的每种动机都视为必然,总要把自己限于一地的行为等同于普天之下的“行为”,把自己经社会化形成的习惯等同于与生俱来的“人性”。
如今,现代人已让这种观念存在其思维和实际行为中,而这种观念的源头则可追溯到先民对于“我自己的”封闭群体与外人的区分。这种区分普遍存在于所有原始民族中。一切原始部落在其分类中都有一个种类叫“外人”。外人不仅外在于对部落内自己人有约束作用的道德准则,而且总体上说压根就算不上人类。大量通用的部落名称显示出原始人的自我认知,而这些词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里都表示“人类”,即他们自己,如祖尼
 (Zuñi)、提纳
(Zuñi)、提纳
 (Déné)、基奥瓦
(Déné)、基奥瓦
 (Kiowa)等。封闭的群体之外不存在人类,尽管事实上从客观的角度看,每个部落周边都有其他部族,他们共享技艺和物质发明,共有复杂的风俗,这是不同族群在行为上相互学习的结果。
(Kiowa)等。封闭的群体之外不存在人类,尽管事实上从客观的角度看,每个部落周边都有其他部族,他们共享技艺和物质发明,共有复杂的风俗,这是不同族群在行为上相互学习的结果。
原始人从来不会向外俯瞰全世界,不会将“人类”视为一个群体,也感受不到自身与同类的共性。他自始就偏于一隅,高筑藩篱。无论选妻还是取人头颅,最重要的就是分清她(他)是自己这群人还是地盘之外的人。自己这群人及其各种行为方式,都是举世无双的。
现代人则有“上帝的选民”和“危险的异族”之分,而其文明中的不同群体在基因上和文化上错综关联,一如澳大利亚的众多丛林部落。这种态度背后自有漫长的历史延续性为其撑腰,俾格米人就是如此。人类的这一特质根深蒂固,难以清除,但我们至少可以努力厘清其渊源,看清其复杂的表征。
在宗教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时代,西方文明的普遍态度便可作为上述问题的表征,而人们论及此事时,总认为它至关重要,是由宗教感情而不是上述普遍的偏狭所驱动。任何一个封闭群体与外人的区分,在这里都化为宗教的虔敬信徒与异教徒的区分。数千年来,这两类人之间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双方的思想、制度无一不相互抵牾。甚至两种宗教本来大同小异,而各自的制度却一律被视为水火不容:一边关乎神圣的真理和虔敬的信徒,是神启,是上帝;另一边则关乎人类的错误,是谎言,是诅咒和魔鬼。对立群体的态度绝无同等观之的可能,因而也就根本谈不上通过对资料的客观研究来理解宗教这一人类重要特征的性质。
对宗教的这种态度已然成为标准,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至少我们已将那种荒诞的独特性抛在身后,接受了对宗教的比较研究。然而,类似的旧心态在我们的文明中依然以其他方式普遍存在,例如宗族偏见。这令我们不由得怀疑我们对宗教的成熟认识究竟是因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孩童的无知,还是仅仅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宗教已不再是重要战场。一旦事关文明中最鲜活的问题,我们似乎就远离了在宗教领域已相当普遍的那份超然。
还有另一种情况令严肃的习俗研究出现较晚且研究者用心不专,而这种困难比上述问题更难以克服。研究社会理论的人不大容易关注习俗问题,因为他们自己的思考也脱不开习俗,如果失去习俗这副“眼镜”,他们什么也看不见。越是基础性的事务,就越不容易受到有意识的关注,这种盲点并不神秘。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获得有关国际信贷、学习过程或精神神经症中自恋因素的大量数据后,既利用这些数据开展工作,也受限于这些数据。他们不会考虑还存在其他社会情况,在其中所有因素的安排都可能大不一样。换言之,他们不会考虑文化的调节作用,而认为他们所研究的特质具有已知且必然的表征,这些表征是绝对的,因为这是他们必须处理的所有材料。他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某一地区的态度就是“人性”,对这些态度的描述则涉及“经济学”或“心理学”。
从实践的角度看,这种态度无伤大雅。儿童须接受传统教育,研究我们自己学校中的学习过程至关重要。同理,我们常对关于其他经济制度的讨论不屑一顾,这也情有可原。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只能活在由自己的文化规定的“我们-他们”架构中。
的确如此,而且,讨论不同文化时,最好别忘了它们存在于空间中。这一事实更衬托出我们的冷漠。然而,限于史料,我们只能从时间上首尾相连的不同文化获得例证。我们无论如何也逃不开时间的连续性。哪怕只回望一个世代,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修正,有些甚至就出现在我们最私密的行为中。这些变化相当隐秘,我们只有在事后才能察觉情况的改变。若不是我们未到万不得已,始终刻意回避私密领域的文化变迁,我们早已采取较现在更为明智且直接的态度了。造成这种抗拒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对文化规约(cultural conventions)会错了意,特别是夸大了那些碰巧属于我们的民族和时代的文化规约。只需对其他文化规约略有了解,知道这些规约可能千差万别,就大大有益于促成理性的社会秩序。
研究不同文化对于今天的思想和行为还有另一种重要意义。现代生活方式使多种文明近距离接触,而目前绝大多数人还是以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利态度面对这种情况。文明前所未有地召唤真正具有文化意识的人客观看待而不是惧怕、责难其他民族的社会所规定的行为。
在种族和民族互相接触的今天,对异族的蔑视并非唯一的道路,更非以科学为基础的道路。盎格鲁-撒克逊的偏狭传统与其他任何文化特征一样,仅属于一时一地。西班牙人拥有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几乎同样的血缘和文化,却没有后者的偏狭。在西班牙人统治的国度,种族偏见大异于受英、美统治的国度。美国人所不能容忍的显然不是生理上血缘相距遥远的种族相混合。波士顿曾强烈抵制爱尔兰天主教徒,新英格兰磨坊小镇曾抵制意大利人,这些抵制行为与加利福尼亚州抵制东方人并无二致,这依旧是内外有别的习惯在作祟。我们比原始部落更没理由在这方面抱残守缺。我们已经游历过并且夸耀自己的成熟,可是我们不知道文化习惯的相对性,将与标准不同的人群建立联系的益处和乐趣拒之门外,在与他们打交道时不守信誉。
当前西方文明迫切需要认识种族歧视的文化基础。我们沉醉于种族歧视,连与我们同一血脉、情同手足的爱尔兰人也不能容忍。挪威人曾与瑞典人不共戴天,就仿佛他们身上流淌着不同的血脉。法德两国开战时,划出一条所谓的种族分割线,将巴登人与阿尔萨斯人分开,全然不顾他们从体型上看同属于阿尔卑斯亚种。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口自由流动的时代、一个社会中最优血统混杂通婚的时代,竟然大言不惭地宣扬什么种族纯粹。
对此,人类学家从文化的本质和遗传的本质两个方面做出了回应。说到文化的本质,我们需要回到人类社会尚不存在的远古。大自然在一些社会中通过生物机制长期维持哪怕最细微的行为模式。不过,这些社会不是人类社会,而是昆虫社会。把蚁后放入一个空穴,它依然会复制性行为的每一个特征,以及蚁穴的每一个细节。这些社会性昆虫一丝不苟地执行大自然的安排,绝不造次,它们的本能行为体现整个社会结构模式。一只蚂蚁孤零零地离开蚁群,失去其蚂蚁社会的等级属性或养育模式,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小于它未能完好地复制自己的触角形状或腹部结构的概率。
无论是福还是祸,人却截然相反。人类部落的社会组织、语言、本地宗教,都不会由人的生殖细胞承载。过去在欧洲,人们偶然会发现被遗弃的儿童在森林中生存下来,与其他人类完全隔绝。这样的儿童彼此非常相似,林奈
 (Linmeus)将他们单独归为一个独特的种,称为“野人”(Homo ferus),并认为他们是人类中一种罕见的侏儒。这些智力迟钝的“畜生”对自己何去何从毫无兴趣,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有节奏地前后摇摆身体,根本学不会使用其语言器官和听觉器官。他们裹几片破布来御寒,探手从沸水中捞土豆而浑然不觉疼痛。当然,他们无疑是在婴儿期遭到遗弃的孩子,而他们所有人缺少的正是与同类相处的经历,人只有与同类相处才能培养并磨砺属于人的种种能力。
(Linmeus)将他们单独归为一个独特的种,称为“野人”(Homo ferus),并认为他们是人类中一种罕见的侏儒。这些智力迟钝的“畜生”对自己何去何从毫无兴趣,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有节奏地前后摇摆身体,根本学不会使用其语言器官和听觉器官。他们裹几片破布来御寒,探手从沸水中捞土豆而浑然不觉疼痛。当然,他们无疑是在婴儿期遭到遗弃的孩子,而他们所有人缺少的正是与同类相处的经历,人只有与同类相处才能培养并磨砺属于人的种种能力。
我们的文明更讲人道,因而我们在文明社会见不到“野人”。然而,倘若一个婴儿被另一个种族或文化的人收养,这个问题就会清楚地显现。一个东方孩子被西方家庭收养,就要学英语,要在其养父母面前表现出与其玩伴相同的态度,长大要从事与他们相同的职业。他要学会自己后天进入的那个社会里的一整套文化特质,而其亲生父母所属的那个群体则与他毫无关系。倘若全体人民经两三个世代摆脱其传统文化,并转而接受一套异族的习俗,就会在更大规模上经历同样的过程。美国北部城市的黑人
 文化与同城的白人文化非常接近,在细节上也几无二致。数年前对哈林区(Harlem)展开的一项文化调查显示,黑人特有的一种流行爱好是赌次日证券交易额的最后三位数。白人与之相对应的爱好是亲自到股市豪赌。相较而言,黑人的爱好成本低,但其不确定性和刺激性丝毫不亚于白人的爱好。这种爱好与白人的爱好有所不同,但差距不大。哈林区黑人群体的大多数其他特征则与同时期白人群体的特征更为接近。
文化与同城的白人文化非常接近,在细节上也几无二致。数年前对哈林区(Harlem)展开的一项文化调查显示,黑人特有的一种流行爱好是赌次日证券交易额的最后三位数。白人与之相对应的爱好是亲自到股市豪赌。相较而言,黑人的爱好成本低,但其不确定性和刺激性丝毫不亚于白人的爱好。这种爱好与白人的爱好有所不同,但差距不大。哈林区黑人群体的大多数其他特征则与同时期白人群体的特征更为接近。
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到一些民族已能接受其他血统民族的文化。人的生物学结构并未妨碍这种接受过程,它并不会在细节上将人限制于任何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人类在不同文化中就诸如婚配或贸易制定的五花八门的社会解决方案,在人类原始禀赋的基础上都是同样可能的。文化并非一种经由生物性传递的复杂系统。
较大的可塑性是一种优势,弥补了失去大自然安全保障而产生的不足。人这种动物不像熊那样经过一代代进化而长出满身皮毛,以适应北极的环境。人学会了为自己缝制衣衫、建造雪屋。我们从人类之前和人类社会的智慧史中看到,这种可塑性正是人类开始并保持进步的土壤。在猛犸象时代,不具可塑性的物种产生—兴盛—消亡,周而复始,它们为适应环境而进化出的生物特征也是导致它们灭绝的原因。食肉猛兽以及最终的高等动物类人猿则缓慢地不再依赖于生物适应。随着可塑性的不断提高,智力发展的基础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常有人说,或许人类终将毁于智力的发展。然而没人指出我们有任何途径能返回社会性昆虫的那种生物机制,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不论是福还是祸,人类文化遗产终不能通过生物性继承。
现代政治必然导向一个结论,即我们仰仗某些优秀的种质遗传取得精神和文化成就,这种结论毫无根据。我们西方文明的主导权在不同时期从闪米特语诸族传给含米特人,又传给地中海白人亚种,后来再传给北欧人。我们的文明不论由什么人承载,其文化延续性毋庸置疑。我们必须接受人类遗传的一切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生物性传递的行为只是一小部分,文化过程在传统的承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人类学对种族纯粹论者的第二个回应是关于遗传的性质。种族纯粹论者上了神话的当。何谓“种族遗传”?我们大略知道它是父亲向儿子的遗传。在家族血统中,遗传至关重要,但遗传也仅限于家族血统。超出这一范围,遗传就是神话。在静止的小社会里,如偏远的因纽特人
 村庄,“种族”遗传几乎等同于亲子遗传,这时,种族遗传是有意义的。但对于那些分布广泛的族群来说,如北欧人,种族遗传没有现实基础。首先,北欧所有民族中都有一些家族血统同样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区或地中海地区的社会中。只要分析欧洲人口的体格构成,我们就会发现交叠现象:黑眼、黑发的瑞典人代表了更集中于南方的家族血统,我们也的确会根据对这些南方家族的了解来看待这样的瑞典人。他们的体格所表现的遗传特性属于他们的家族血统,而他们的家族血统并不一定局限于瑞典。我们尚不清楚相距多远,体格类型之间便不存在混杂。我们知道近亲繁殖会产生一个地方特有的类型,但这种情况在分布极广的白人文明中基本不存在。我们有时用“种族遗传”这种说法——还真没少用——来集合一群人,这群人拥有差不多的经济地位,从差不多的学校毕业,读差不多的周刊,这样的分类只不过是自己人和外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是说这群人真的具有生物同质性。
村庄,“种族”遗传几乎等同于亲子遗传,这时,种族遗传是有意义的。但对于那些分布广泛的族群来说,如北欧人,种族遗传没有现实基础。首先,北欧所有民族中都有一些家族血统同样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区或地中海地区的社会中。只要分析欧洲人口的体格构成,我们就会发现交叠现象:黑眼、黑发的瑞典人代表了更集中于南方的家族血统,我们也的确会根据对这些南方家族的了解来看待这样的瑞典人。他们的体格所表现的遗传特性属于他们的家族血统,而他们的家族血统并不一定局限于瑞典。我们尚不清楚相距多远,体格类型之间便不存在混杂。我们知道近亲繁殖会产生一个地方特有的类型,但这种情况在分布极广的白人文明中基本不存在。我们有时用“种族遗传”这种说法——还真没少用——来集合一群人,这群人拥有差不多的经济地位,从差不多的学校毕业,读差不多的周刊,这样的分类只不过是自己人和外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是说这群人真的具有生物同质性。
真正使人“抱团”的是文化,即人们共同的思想和准则。如果一个民族不以共同的血统为象征、喊口号,而是关注凝聚其人民的文化,发扬文化的优势,且认识到不同文化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个民族就会用现实思考取代危险的象征主义思维方式。象征主义思维方式会将人引入歧途。
人们开展社会性思考必须先了解文化的不同形式,本书探讨的正是文化的这一方面。如前所述,体格或种族未必与文化相关,因此在我们的论述中它们可以被暂时搁置,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出于某些特殊原因,二者才有关联。探讨文化最紧要的要求是选取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以此为讨论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区分人类由文化决定的不同之处,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类不可避免的共性。仅靠观察自己或者任何单一社会,我们都无法知晓哪些行为是“出于本能”,亦即由生物器官决定的。仅仅证明某种行为是自发的并不足以将这种行为归为本能行为。条件反射的行为与生物器官决定的行为同样具有自发性,而在人类的自发行为中,由文化形成的条件反射占比比较大。
因此,在探讨文化形式和文化过程时,从历史上与我们关系最远,且相互之间关系最远的社会取材,最能说明问题。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分布在广袤的地域,历史上相互交往,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这时原始文化便成为我们可用的资源。它们如同一间实验室,我们可在其中研究人类的多样性。这些原始文化相对孤立,许多荒蛮之地在数百年里逐渐演化出独特的文化主题。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信息,使我们看到人类可能有多么千差万别。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是理解文化进程的关键,它们也是我们现在和将来所拥有的唯一的实验室。
这间实验室还有另一个优势,与庞大的西方文明相比,各种问题在这里都比较简单。由于现代文明发明了各种便利的交通工具、国际电缆、电话和无线电传输设备,以及永久保留和广泛传播信息的技术,创建了各种不同的职业、信仰和阶层,并在全球形成统一标准,因此它变得过于复杂,人们不可能对之做充分的分析,除非人为地把它分成小块。这些不完整的分析难以成立,因为很多外部因素无法控制。研究任何一个人群,都会牵涉作为对照的其他不同人群的个体,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标准、社会目标、家庭关系和道德。而这些人群的相互关系千头万绪,对其评价无法触及必要的细节。原始社会的文化传统则比较简单,可以用成年个体的知识来概括,人群内的规矩和道德只有一种界定得非常清晰的通用模式。在这样简单的环境中,我们有可能评估各种特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错综复杂的文明中则根本办不到。
上述两个重视原始文化材料的理由与传统上对这些材料的应用并无任何关系。传统上,人们用这些材料来重建起源,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将不同文化的所有特质按进化的顺序排列,从最初的形式到西方文明中的最终发展。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探讨澳大利亚的宗教比探讨本国的宗教更能揭示宗教的原始形态,或者通过探讨易洛魁人
 的社会组织,我们就能回溯人类远祖的婚配习惯。
的社会组织,我们就能回溯人类远祖的婚配习惯。
既然我们被迫相信人类属于同一个种,那么各地的人背后便有同样长的历史。原始部落或许比文明社会更接近行为的原初形式,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我们的猜测不一定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当代的某种原始习俗就是人类行为最早的类型。只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获得有关早期初始状态的粗略知识,即研究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或近乎普遍存在的那几种特质是如何分布的。有几种普遍存在的特质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泛灵论和婚姻中的外婚限制是毫无争议的普遍存在。关于人类灵魂和来世的概念千差万别,看法不大统一。还有一些信仰与这些特质几乎一样普遍,我们可视之为人类非常古老的创造,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是由生物性决定的,因为它们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发明,所谓“婴儿期的”特征,已成为整个人类思想的基础。但经过深入分析我们便知它们或许与地区性习俗一样,是由社会决定的,只不过早已成为人类的自发行为。它们古老而普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形式就是原始时代的最初形式,也不可能通过研究这些形式的变体而返古溯源。即便我们将某种信仰的普遍核心分离出来,并从中区分其因地而异的不同形式,这种特征也可能是出自某种显著的地方形式,而不是一切所见特征的原初最小公分母。
由此可见,通过原始习俗溯源纯属臆想。用这种方法能构建出任何我们想要的起源,这些起源既可以互斥也可以互补。我们以这种方式利用人类学材料,只会导致一种空想以最快的速度取代另一种空想,却提不出任何证据。
通过原始社会探讨社会形态也未必一定与返璞归真的浪漫发生关联,这样的探讨并不是为了把较简单的民族诗意化。如今,时代标准各不相同,机械轰鸣嘈杂,于是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对这个或那个民族产生强烈的好感。然而回归原始民族为我们保留的各种理想并不是治愈社会弊病的良方。向较简单的原始民族求助的浪漫乌托邦主义或许诱人,但是在民族学研究中它利弊参半。
我们今天之所以必须认真研究原始社会,是因为它们为我们研究文化形式和文化进程提供了个案材料,有助于我们区分哪些反应属于特定的地方文化类型、哪些为全人类所共有。此外,这些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和理解文化决定的行为所扮演的无比重要的角色。文化及其过程和功能需要我们倾尽全力加以研究,了解尚无文献记载的社会实况将使我们获得无与伦比的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