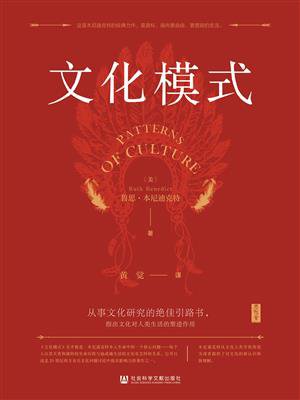第一节
掘根印第安人(Digger Indians)的一位头人(加利福尼亚人如此称呼他们),曾给我讲了很多他们的旧事。他[拉蒙(Ramom)]是基督徒,带领族人灌溉土地,种植桃杏。然而当他讲到亲眼看见萨满跳起熊舞,跳着跳着便化成了熊,他的手颤抖起来,激动得几乎发不出声。什么也比不上他的族人曾经拥有的力量。他最爱谈他们曾经吃过的沙漠食物,他喜爱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对其重要性了如指掌。他说那时他的族人吃的是“沙漠的力量”,从不吃罐头里装的和肉铺里卖的。后来出了这些新事物把他的族人给毁了。
有一天,拉蒙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起如何把牧豆磨成粉、将橡子烧成汤。“太初,”他说,“神给每个民族一只黏土杯,他们从杯中啜饮生命。”我一时没明白这比喻是出自他们部落中我从未见识过的某种传统仪式,还是他自己的想象。这种说法不太可能是他从在班宁
 (Banning)认识的白人那里听来的,他们不好议论不同民族的精神气质。不管这个比喻从哪里来,在这个谦卑的印第安人头脑里,它清晰而寓意丰富。“他们都用杯子舀水,”他接着说,“可杯子各不相同。我们的杯子碎了。它没了。”
(Banning)认识的白人那里听来的,他们不好议论不同民族的精神气质。不管这个比喻从哪里来,在这个谦卑的印第安人头脑里,它清晰而寓意丰富。“他们都用杯子舀水,”他接着说,“可杯子各不相同。我们的杯子碎了。它没了。”
“我们的杯子碎了”。那些使他的族人生活有意义的事物——餐桌上的家庭礼仪、经济体系的责任、村里接二连三的庆典、熊舞中的附体、他们的是非标准,这一切都离他们而去,随之离去的还有他们生活的形式和意义。老拉蒙依旧中气十足,在处理有关白人的事务上居于领袖地位。他并不是说他的族人濒临灭绝,他想表达的是他的族人失去了与生命同等珍贵的东西——完整的标准和信仰体系。其他的“生命之杯”还在,杯子里或许盛着同样的水,但他们的损失无法弥补,这不是东拼西凑便能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模具,它成为一个整体。他们曾经有自己的模具。
拉蒙所说的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跨越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天壤之别的两种文化。这是严酷的命运,是我们这些处于西方文明中的人不曾有的经历。我们成长于一种世界性文化之中,我们的社会科学、心理学和神学顽固地无视拉蒙的比喻所表达的事实。
姑且不论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单是生命的过程和环境的压力,就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头绪,这些头绪似乎全都可能支撑一个社会的生存。这里有各种所有制,其中包含可能与财产相联系的社会等级;这里有各种物品及其精巧的工艺;有各式各样的性生活、养育模式和后养育模式;有行会或教会,它们可能赋予社会某种模式;有经济交换;有神祇和超自然报应……我们还能罗列更多。每一样背后都有复杂的文化和仪式,这些文化和仪式占据了绝大部分文化能量,只留下一小部分用来建构其他特征。生活中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其他民族却不屑一顾,他们的文化取向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不贫乏。又或者,某种特征虽然是我们与他们共有的,但他们对之不厌其烦,我们看来便觉古怪。
文化生活如此,语言亦然。选择是第一需求。我们的声带、口腔和鼻腔实际上能够发出无穷多的声音。英语中的三四十种语音甚至和与之十分相近的德语、法语的语音也不完全相同。没人敢估量世界上各种语言总共使用多少种语音,但每种语言都必须选择并遵守一套发音规则,哪怕别人完全听不懂。一方面,一种语言即便使用数百个可能——以及实际记录——的音素,可能依然无法用以交流。另一方面,我们对与自己语言无关的其他语言会有很多误解,因为我们试图以自己的语音系统来解读他人的语音系统。我们只发一个k音,如果另一个民族在咽部和口腔的不同位置发出五个k音,我们便完全听不出这些词语和语句的区别,除非我们也学会了这些发音。我们有一个d音和一个n音,而其他民族可能有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发音,如果我们听不出来,一会儿把它写成d,一会儿把它写成n,便产生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差异。语言学研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懂得可能的千差万别的语音,每种语言从中选取自己的那一部分。
在文化中,我们也必须想象一个大弧拱,上面排列着各种潜在的兴趣点,可能由人的年龄周期决定,也可能由环境或人的各种活动决定。一种文化即便重视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可能依然像一种语言那样无法让人理解,哪怕这种语言使用了各种吸气音,各种喉塞音,各种唇音、齿音、齿擦音、喉音,从发声到不发声、从口腔到鼻腔。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是因为它从这个弧拱上选择了某些部分,每个人类社会都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了这样的选择。从另一个文化的视角看,每种文化都舍本逐末。一种文化几乎不承认钱的价值,而另一种文化却以钱为各种行为的基础。在一个社会中,技术即便在生死攸关的方面也无足轻重;而在另一个同样简单的社会中,技术成果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人们将其用得恰到好处,令人叫绝。有些民族在青春期文化上大费周章,有些则重视死亡,还有些重视来世。
对青春期的重视格外吸引我,一是因为青春期也是我们的文明的一个焦点,二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其他文化的丰富信息。在我们的文明中,有大量心理学研究文献强调青春期躁动不可避免。在我们的传统中,这个时期青年的心理特点必然是叛逆,处于青春期的少年闹得家庭鸡犬不宁,就如同人得了伤寒必然发烧。这样的事实毋庸置疑,在美国非常普遍,但我们可以对其必然性打个问号。
随便看看不同社会处理青春期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情况:即便在对青春期讨论最多的各种文化之间,受关注的年龄段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从一开始,如果我们总想着生理成熟期,那么所谓的“成年礼习俗”就是个不恰当的词语。这些文化里所谓的成熟期是社会性的,相关仪式是以某种方式确认儿童获得成年人的新身份。在不同文化中,行业与义务各不相同,入行仪式也千差万别。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成年男性唯一的高尚责任就是出征;而在另一个社会里,成年主要意味着获得戴面具以神祇的身份舞蹈的权利,而战士举行成年礼的年龄会相对较晚,仪式也不同。我们在理解不同的成年礼习俗时,最重要的是了解不同文化中成年期开始的标志,以及人们以何种方法获得成年人的身份,至于对成年礼性质的分析倒不那么重要。一种文化中的成年礼取决于这种文化对“成年”的认识,而不是生理上的成熟期。
在北美洲中部地区,成年意味着参战,获取战功是所有男性的最高目标。那里常见的成年礼主题以及不论年龄都须时刻备战的主题,都化为一场祈愿得胜的仪式。参与者不是互相伤害,而是自我伤害,他们从自己的手臂或腿上割肉、剁下手指、把重物钉在胸肌或腿肌上拖拽。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仪式可以获得强大的战斗力。
澳大利亚的情况与北美洲的不同。成年意味着即将成年的新成员可以参加仅限男性的宗教仪式,其基本特征就是排斥女性,女性不能获得关于这些仪式的任何知识,她们哪怕只是听见了仪式上牛吼器的声音,便要被处死。成年礼非常复杂,参与者象征性地与女性彻底断绝关系。成年男性在象征意义上自给自足,承担社会的全部责任。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剧烈的性仪式,并由此获得超自然的保障。
由此看来,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即便受到重视,首先也是从社会的角度加以解读。不过,一项关于成年礼习俗的调查揭示了另一个事实:男性与女性在生命周期内生理上的性成熟与它们在文化中的表现并不吻合。如果文化上强调性成熟是根据对此的生理学意义上的强调,则女孩的成年礼应比男孩的成年礼更重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成年礼强调了一个社会现实:在任何文化中,男性的成年权远较女性的成年权意义深远。因此,在上述社会里,人们通常更重视男孩的这一阶段。
也有在仪式上对同一部落内女孩和男孩成熟期一视同仁的社会例子。例如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内陆地区,青春期仪式是一次针对所有营生的魔法训练,女孩和男孩都要参加。男孩把石块从山上滚到山下,练成飞毛腿;或者投掷赌博中使用的小棍,以便将来在赌博中常胜不败。女孩从远处的泉眼打水;或者把藏在衣服里的石子扔到地上,将来生孩子便能如石子坠落般顺利。
在东非大湖区南迪人(Nandi)的部落里,女孩和男孩都要参加成年礼。不过,因为男性在文化中占统治地位,所以男孩成长期的训练比女孩的更受重视。在成年礼上,已经获得成年人资格的成员对他们必须接纳的新成员进行考验。他们在割礼上想出千奇百怪的法子折磨新成员,要求新成员表现出最彻底的吃苦耐劳的精神。男孩和女孩的成年礼分别举行,但方法大同小异。新成员不论男女都要穿着心上人的衣服参加仪式。在行割礼时,有人盯着他们的脸,他们不能有一丁点痛苦的表情。如果表现勇敢,他们会得到心上人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给予的奖赏,姑娘们也跑过去接受他们回赠的礼物。女孩和男孩经过这样的仪式,就获得了新的性生活资格:男孩成为战士,可以找爱人,女孩则可以嫁人。对男女两性来说,青春期的考验也是婚前考验,通过者从爱人那里得到棕榈叶作为奖品。
有的社会的成年礼也有可能仅涉及性成熟的女孩,而把男孩完全排除在外。中非地区为女孩设立的催肥屋最稚拙。当地人认为肥胖是女性之美的唯一标准,于是进入性成熟期的女孩便被隔离起来,有时持续数年,人们每天给她们喂食高糖、高脂食物,不让她们运动,还不停地往她们身上涂油。在此期间,女孩学习未来要承担的职责,隔离期结束后,她们要周游一圈,向别人展示其丰腴的身材,之后便嫁给骄傲的新郎。男性在婚前则不必进行这样的外貌改造。
女孩独有的性成熟期仪式通常以与月经相关的各种观念为核心,这些观念与男孩的性成熟期无关。经期女性不洁的观念非常流行,在部分地区,所有相关观念在女性经历月经初潮时都集中表现了出来。在这些情况下,成年礼的特点则与我们上面说的截然不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凯列尔印第安人
 (Carrier Indians)对女孩性成熟的恐惧达到了巅峰。女孩要过三四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一时期被称为“活埋期”。在这段时间里,女孩须在远离所有道路的地方用树枝搭一座棚子,独自住在野外。对于其他人来说,哪怕只是看一眼这个女孩也是有害的。她的脚印会污染道路与河流。她要披上用鞣制皮革做成的大头巾,以遮挡住面部和胸部,而大头巾在身后则拖到地面;肘部和膝部要缠上带子,以保护她不为体内充盈的邪气所伤。不仅她本人处于危险中,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也是威胁。
(Carrier Indians)对女孩性成熟的恐惧达到了巅峰。女孩要过三四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一时期被称为“活埋期”。在这段时间里,女孩须在远离所有道路的地方用树枝搭一座棚子,独自住在野外。对于其他人来说,哪怕只是看一眼这个女孩也是有害的。她的脚印会污染道路与河流。她要披上用鞣制皮革做成的大头巾,以遮挡住面部和胸部,而大头巾在身后则拖到地面;肘部和膝部要缠上带子,以保护她不为体内充盈的邪气所伤。不仅她本人处于危险中,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也是威胁。
与月经观念相关的女孩成年礼,很容易让相关个体感觉适得其反。神圣历来有两个方面:可能带来祸患,也可能带来福佑。在某些部落,女孩的月经初潮隐含着超自然的祝福。我亲眼见过阿帕切人(Apache)的祭司跪在一排神情严肃的小女孩面前,接受她们祝福的触摸。需要祛病的婴孩和老人也会赶来。青春期的女孩不是需要隔离的祸患之源,人们蜂拥而至,从她们身上获得超自然的祝福。在掘根人和阿帕切人中,女孩成年礼的观念与月经相关,这些仪式都没有男孩参加。男孩的成年礼包含一些简单的考验以及男性身份的证明,但是并不刻意强调。
由此看来,青春期行为并不由这一阶段的生理特征所决定(即便女孩也是如此),而由社会规定的婚姻或魔法要求决定。由于观念不同,一些部落认为青春期宁静祥和,具有宗教意味;而另一些部落则认为青春期危险而不洁,女孩在林中要大声喊叫,提醒别人避开她。我们也见到某些文化中并没有女性青春期的制度。但这些地方男孩的青春期依然十分受重视,例如在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青春期仪式可能是获得男性身份、参与部落事务的途径,而女性青春期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确认。
然而这些事实并未回答那个基本问题:所有的文化是否都必须应对这个天生躁动的时期,即便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博士在萨摩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萨摩亚女孩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有明确标记。婴儿期之后的最初几年,她会与邻家年龄相仿的女孩结成小群体,完全不与男孩来往。她的生活基本局限于村子里自己家所在的那个角落,而小男孩历来被拒之于外。她的唯一职责就是照料婴儿,但并不会因此足不出户,而是带着自己照料的婴儿四处走动,所以看孩子并不太妨碍玩耍。性成熟期开始前的两三年,她长大了,可以承担难一点的任务,学习较为复杂的技巧。这时她的玩伴小群体就解散了。她穿上成年女性的衣服,必须分担家务。这个时期相当无趣,波澜不惊,性成熟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女孩到一定岁数后,有几年快乐时光,她可以有随意而不负责任的恋爱关系。她总是想方设法让这段时光延长,推迟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女孩性成熟本身未经社会认可,人们对她的态度和期望依然如故。女孩在青春期之前的那种羞涩还会保持两三年。在萨摩亚群岛,女孩的生活节奏与生理上的性成熟并未同步,而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性成熟在一个不为人关注的平静阶段悄然发生,这期间不会出现什么青春期冲突。青春期在文化上被忽视,不仅没有任何仪式,而且在女孩的情感生活里以及村里人对女孩的态度上也显得无足轻重。
战争也是文化中可有可无的社会议题。即便都强调战争,不同的文化也可能有截然相反的目的、不同的涉及政权的组织,以及不同的制裁。例如,阿兹特克人可能将战争中获得的俘虏作为宗教祭品。而西班牙人作战的目的是杀死敌人,这在阿兹特克人看来就是违反了游戏规则,阿兹特克人对此不知所措,埃尔南·科尔特斯
 (Hernán Cortés)遂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阿兹特克人的首都。
(Hernán Cortés)遂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阿兹特克人的首都。
在世界各地,有些关于战争的观念在我们看来比这更离奇。例如,在有些地区,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从未发生过有组织的相互残杀。以我们对战争的了解,我们认为在两个部落的交往中,总是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交替出现,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也是世人非常普遍的想法。但是,一方面,一些民族根本无法理解和平状态,他们认为和平就等于承认敌对部落的人属于人类,而敌对部落的人,顾名思义,压根不属于人类,即便双方属于相同的种族、拥有相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民族可能同样无法理解战争状态。克纳德·拉斯麦逊
 (Knud Rasmussen)曾提到当他向因纽特人讲述西方社会的战争习俗时,对方一脸茫然。因纽特人完全理解杀人的行为。如果有人碍了你的事,你估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如果你做好了担责的准备,就把对方杀掉,社会不会因为你的强势而惩罚你。但是全村人出动与另一个村子的人打仗,或者一个部落与另一个部落打仗,甚至另一个村子成为一场偷袭的合法目标,这种事因纽特人闻所未闻。对他们来说,杀人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也没有我们这样的分类:这种杀人行为值得颂扬,那种杀人行为则是死罪。
(Knud Rasmussen)曾提到当他向因纽特人讲述西方社会的战争习俗时,对方一脸茫然。因纽特人完全理解杀人的行为。如果有人碍了你的事,你估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如果你做好了担责的准备,就把对方杀掉,社会不会因为你的强势而惩罚你。但是全村人出动与另一个村子的人打仗,或者一个部落与另一个部落打仗,甚至另一个村子成为一场偷袭的合法目标,这种事因纽特人闻所未闻。对他们来说,杀人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也没有我们这样的分类:这种杀人行为值得颂扬,那种杀人行为则是死罪。
我本人也曾试图与加利福尼亚的教团印第安人
 (Mission Indians)谈论战争,结果发现根本不可能。他们对战争的误解太离谱,他们的文化中没有支撑“战争”这一概念的基础,而他们努力理解这一概念,最终却把我们一身正气为之献身的大战理解为街头斗殴,他们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分的文化模式。
(Mission Indians)谈论战争,结果发现根本不可能。他们对战争的误解太离谱,他们的文化中没有支撑“战争”这一概念的基础,而他们努力理解这一概念,最终却把我们一身正气为之献身的大战理解为街头斗殴,他们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分的文化模式。
尽管战争在我们的文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有一种反社会的特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乱象丛生。战时言论——战争培养了勇气和利他精神,增强了精神的价值——令人生疑且不安。在我们的文明中,战争最好地说明了由文化选择出某种特质可能造成多大的毁灭性后果。我们认为战争有理,不外乎因为一切民族都认为自己拥有的特质全都有理,而不是因为战争具有经得起客观审视的优点。
战争并非孤例,我们从世界各地以及复杂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能看到对某种文化特质做出自以为是且常常最终导致反社会的强调。如果传统习俗与生物学原理背道而驰,这样的例子便格外醒目,例如饮食或婚配方面的种种规则。由于一切人类社会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一定关系内的人禁止通婚,社会组织在人类学中便有特别的意义。没有任何已知民族允许男性把所有女性视为潜在的婚配对象。其目的并非如人们常常假设的那样是要避免近亲繁殖,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男性生来就要娶自己的表妹(通常是舅舅的女儿)为妻。不同民族对于亲属通婚的禁忌完全不一样,但所有的民族都有这方面的禁忌。在人类所有的观念中,乱伦观念的文化解释最多、最复杂。被纳入乱伦范围的群体往往是部落中最重要的功能单位,每个个体对于其他个体的责任取决于他们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这些群体作为宗教仪式或经济交换中的功能单位,其重要性在社会历史中无论怎样说都不为过。
在一些地区,乱伦禁忌相对宽松,尽管存在限制,但男子可娶的女性相对较多。而在另一些地区,乱伦禁忌一直延伸到社会虚构的共同祖先,其结果则是可婚配的对象极其有限。这种社会虚构通过关系称谓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那些地区的人们不像我们这样区分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如父亲和叔伯、兄弟和堂/表兄弟,而是采用与我们不同的分类方法,用一个词表示“我父亲那边(包括关系、地域等)的同辈男性”。澳大利亚东部某些部落所用的亲属分类系统可谓极端,只要是同辈且有任何一点亲戚关系,他们就以兄弟姐妹相称,没有堂/表兄弟的说法,也没有与之相近的类别。
如此称呼亲属关系在世界上并不罕见。然而澳大利亚东部某些部落对男性与“姐妹”通婚的恐惧超乎寻常,因此制定了无比严苛的外婚制规则。例如库尔奈人(Kurnai)采用极端的亲属分类系统,因此对所有男性与“姐妹”发生性关系怀有澳大利亚部落特有的恐惧,也就是说,男性不能和与自己有任何关系的同辈女性发生性关系。不仅如此,库尔奈人对婚配还有严格的地域限制。有时,在部落所在的十五六个地方中,某两个地方的女性只能嫁到对方所在地区,这两个地方的人不能与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通婚。有时候,某两三个地方的人只能与另外两三个地方的人通婚。更有甚者,在澳大利亚境内所有部落,老年男性享有特权,其中包括娶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些规则自然导致了一种结果,即倘若当地某个群体里的年轻男性在娶妻时严守规则,那么这个群体里的女性就没有一位在禁忌之外。那里的女性或者因为与年轻男性母亲的关系而成为他的“姐妹”,或者已经被某个老年男性看中,或者因为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原因而不能嫁给年轻男性。
然而库尔奈人并没有因此而修改他们的外婚制规则,反而变本加厉地靠暴力执行。于是,想结婚的人只有奋力冲破规则——他们私奔。村里人一旦觉察,便会全力追捕私奔的人。如果一对私奔的男女被抓,只有死路一条。可那些追杀者也是这样通过私奔才结婚的。“道义”压倒一切,不过,有个小岛一直被视为安全庇护所。私奔的人一旦上岛,并在岛上住到第一个孩子诞生,他们便能以一通鞭笞为代价,重新为村里人接受。鞭笞不是闹着玩的,但他们可以自卫。挨打之后,他们就在部落里获得了已婚者的身份。
库尔奈人应对其文化困境的方法并无奇特之处,他们将行为中的某个方面扩大并复杂化,使之成为一种社会责任。之后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改变,或者自欺欺人。他们选择了自欺欺人。为了繁衍生息,他们对伦理做了某些心照不宣的修正。文明在进步,他们这种对待习俗的方式却依然如故。我们文明中的前辈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们一边坚持一夫一妻制,一边支持卖淫。红灯区最兴旺发达之日,也是对一夫一妻制的赞颂最陶醉之时。社会总会为最受欢迎的传统形式找借口。一旦这些形式失控,人们就不得不借助某种行为加以弥补,这时便会有人出来讴歌传统形式,就好像弥补性的行为压根不存在。
如此站在高处一览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便能清晰地看到几种常见的错误观念。首先,人类文化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环境或人的自然需求所发出的信号。我们很容易认为这种制度会一直紧扣初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现实中,这些信号只是一些粗略的草图、一串干瘪的事实。它们只是具体而微小的潜在可能,而围绕它们展开的复杂思考,有赖于许多外在因素。战争所表现的并非人好斗的本能。人的好斗实在微不足道,在部落间关系中根本得不到体现。人类文化一旦被制度化,决定其形式的思路并不是原始冲动。好斗仅仅是在“习俗之球”上的一记轻触,稍加控制,人也完全可能不出手。
假如我们对文化过程作如是观,则需要重述我们目前维系传统制度的许多论点。这些论点常常认为人类如果离开某些特定的传统形式就什么也干不了。提出这些论点的人甚至用某些特质证明这种论点的有效性,如从特定的财产所有制中产生的某种特定的经济动力。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动机,而且有证据表明,即使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这一动机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总之,我们无须把它当作生死攸关的问题,以免引起误会。自给自足是我们的文明高度强调的动机。即便因经济结构改变,这一动机不再像在西部拓荒和急速工业化时代那般迫切,我们依然能找到许多其他动机来适应新的经济组织,每种文化和每个时代都会从众多的潜在动机中选取几种。变革可能产生严重动荡,导致惨重损失,但这是由变革本身的困难造成的,而不能归咎于我们的时代或者我们的国家恰巧遇到了人类赖以维系的唯一动机。须知变革尽管千难万险,但必不可少。习俗发生一点小变化,我们就大惊失色,实在没有道理。文明变化的剧烈程度往往超出人类任何权力的意志或想象,然而完全可行。今天一点小变化就招致这么多批评,比如离婚率提高、世俗化在城市蔓延、贴面舞会流行,等等,而这些变化在略微不同的文化模式里就是“家常便饭”,它们一旦成为传统,便会与之前的旧模式具有同样丰富的内涵、同样的重要性和同等价值。
这件事的真相在于,不论是简单文化还是复杂文化,每个文化层面都存在人类制度和动机的无数可能性,而人的明智之处正在于对这些差异越来越宽容。人若非在某种文化中成长,并按照这种文化形式生活,便不可能完全参与这种文化,但他可以承认其他文化对于其参与者来说,具有等同于他从自己的文化中所认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