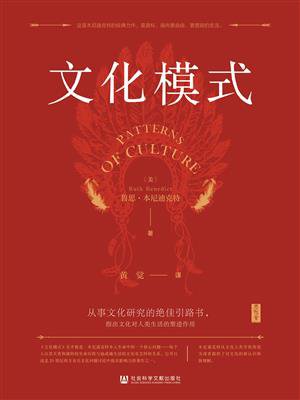第三章
文化的整合
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记录不可胜数。人类行为的某个领域可能在某些社会中被忽视,甚至人们可能连想都想不到它。它也可能宰制社会的全部有组织行为,无论什么外来情形都必须服从其管辖。历史上各自独立、相互之间没有内在关联的特质融为密不可分的一体,所产生的行为在未曾发生这些融合的地方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行为。其必然结果便是,行为的方方面面在不同文化中有各不相同的标准,从最正面的到最负面的。我们或许认为夺人性命这件事是所有民族一致谴责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倘若两个相邻的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或者依照习俗杀死自己的头生和二生孩子,或者丈夫对妻子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或者子女必须在父母变老之前将他们杀死,那么杀人就不算过错;或者,有人偷了一只鸡、拔掉了自己的上牙、出生于星期三,杀死他们也不算过错。一些民族对过失杀人者处以酷刑,而另一些民族则可能对这种行为不了了之。自杀可能无足轻重,有的人稍微遭人轻慢——部落里常见的事情——可能就一死了之,也可能是明智之人所能做出的最高级、最高贵的事。然而,自杀也能是一件可以当作奇闻逸事说说却难以想象真有人会做的事情。再或者,自杀是一种要受法律制裁的罪行,或冒犯神祇的罪孽。
不过,我们对世界上习俗的多样性也并非只能望洋兴叹。这里的自虐行为和那里的猎人头、这个部落的婚前贞洁观和那个部落的青春期性放纵,并非一串毫无关联的不知哪里会有、哪里会无的事实。同样,自杀或杀人的禁忌尽管没有绝对标准,但也不是纯然随机。即便我们认识到文化行为是地区性的、人为的、多变的,它也并未因此失去意义。文化行为还总是趋向整合,一种文化如同一个个体,其思想和行动多少遵循着一定的模式。每种文化都可能有其他类型的社会所未必具备的特定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各民族不断积累其经验,动机愈是急迫,不同的行为便愈将形成相同的形式。最杂乱无章的行动一旦被纳入高度整合的文化,往往会经历最不可思议的蜕变,表现出这种文化特有目标的特征。我们只有先理解一个社会的情感和思想根源,才有可能理解某些行为所采取的形式。
我们不能忽视文化模式的形成,不能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小事。现代科学在诸多领域发现了同一条规则,即整体不仅是所有部分的总和,而且是各部分以独特的方式组合并相互作用,最终产生的新实体。例如,火药并非仅是硫、碳、硝的总和,即便人们拥有关于这三种元素在自然世界中一切形态的大量知识,也依然不能说明火药的性质。三种元素的化合物具有各种元素都不具备的新潜力,其中任何一种元素的行为模式都完全不同于它在其他组合中的情况。
文化亦如是,它大于各种特质的总和。我们可能了解某部落的婚姻形式、仪式舞蹈和成年礼,然而对使用这些元素以实现其目标的整体文化却一无所知。人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周边地区的诸多特质中选取可用的、抛弃无用的;对另一些特质则加以改造,使其符合自己的要求。当然,整个过程可能始终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然而如果我们在研究人类行为模式的形成时忽略了这一过程,则无法明智地解读它。
文化整合一点也不神秘,它与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延续经历相同的过程。哥特式建筑最初不过体现人对高度和采光的追求,后来,在建筑技巧中发展出经典的品位,终于形成了13世纪独特而统一的艺术。它抛弃了不相容的元素,对另一些元素进行修正以为己用,又根据自己的品位创造了一些元素。当我们回顾这一过程时,难免使用一些泛灵论的说法,仿佛这种伟大的艺术形式是有选择、有目的地形成的。然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形式过于贫乏。实际上,这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并没有自觉的选择,也没有目的。最开始这种艺术形式不过是略微倾向于某些地区性的形式和技巧,后来这种倾向性变得越来越强,再通过越来越明确的标准进行整合,最终形成了哥特艺术。
作为整体的文化也经历了重要艺术风格所经历的这一过程。分别以谋生、婚配、战争和祭神为其目的的杂沓行为,按文化内部生长出来的无意识选择原则构成稳定的模式。一些文化没有发生这种整合,如同某些时代的艺术,还有许多文化我们不太了解,无法理解引发这些文化整合的动机。而发生了这种整合的文化,其复杂程度不一,有些甚至属于最简单的文化。这些文化在整合行为方面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而其整合方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人类学家几乎一边倒地分析文化特质,却鲜有将文化作为多元融合的整体加以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早期民族志描述性质的影响。古典人类学家并不依据对原始民族的一手材料撰写论著,他们是坐在“圈椅”里的学者,所用材料来自旅行者和传教士的逸闻,以及早期民族志学者肤浅而简略的记录。我们通过这些记录或可追踪某些风俗的分布,如拔牙或用内脏占卜,却不可能看到这些特质如何嵌入不同的部落而形成特有的形貌。形貌决定了不同行为的形式和意义。
以《金枝》( The Golden Bough )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和常见的比较民族学研究对各种特质进行分析,却无视文化整合的方方面面。从截然不同的文化中不加区别地零星选出一些行为,说明婚配或丧葬习俗,其结果是像弗兰肯斯坦那样机械地制造出一个怪物:右眼取自斐济,左眼取自欧洲,一条腿截自火地岛,另一条腿截自塔希提,所有的手指和脚趾都是从不同地区拿来拼凑的。这样的形象与过去或现在的现实根本对不上。最大的问题是,这就如同精神病学只罗列心理疾患的症状,却没有研究这些症状所造成的病态行为模式——精神分裂、歇斯底里、躁郁症等。精神病患者行为特质的作用、对整体人格的影响,以及它与经验中其他方面的关系,完全因人而异。我们若对精神过程感兴趣,只有将特定症状与某人的整体状态相联系,才能达到研究目的。
文化研究也存在同样严重的不切实际的情况。我们若对文化过程感兴趣,只有以那个文化中业已制度化的动机、情感和价值观为背景观察特定行为,才能理解其意义。因此,今天,最重要的是研究活文化,了解其思维习惯和制度的作用,这样的知识无法靠“肢解尸体”再重新拼装获取。
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反复强调文化功能研究的必要性。他批评常见的东拼西凑的研究,称其为“肢解尸体”,而我们本可以在“器官”有生命、能工作的状态下对之进行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对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特罗布里恩(Trobiand)群岛岛民长期广泛的研究,是关于原始民族全貌最好且最早的著作,开了现代民族学研究的先河。然而马林诺夫斯基仅强调特质在其文化中拥有活语境,它们具有功能性。然后他便对民族学研究进行了泛化,把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特质——义务对等的重要性、地方特色、特罗布里恩的聚居家庭——扩大到全部原始部落,而没有看到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形态只是已知许多类型中的一种,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经济、宗教、家庭领域安排。
(Malinowski)反复强调文化功能研究的必要性。他批评常见的东拼西凑的研究,称其为“肢解尸体”,而我们本可以在“器官”有生命、能工作的状态下对之进行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对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特罗布里恩(Trobiand)群岛岛民长期广泛的研究,是关于原始民族全貌最好且最早的著作,开了现代民族学研究的先河。然而马林诺夫斯基仅强调特质在其文化中拥有活语境,它们具有功能性。然后他便对民族学研究进行了泛化,把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特质——义务对等的重要性、地方特色、特罗布里恩的聚居家庭——扩大到全部原始部落,而没有看到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形态只是已知许多类型中的一种,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经济、宗教、家庭领域安排。
当然,今天的文化行为研究已不能简单地把特定地区的安排等同于全体原始民族,人类学家不再把原始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种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开始显示丰富的意义。
现代科学各领域的学者纷纷强调研究完整形态的重要性,指出不能仅耽溺于对部分的分析。威廉·斯特恩(Wilhelm Stern)在其哲学和心理学论著中指出,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他认为一切都必须以不曾分割的整体的人为出发点,批评内省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流行的原子化研究,主张采用人格形态调查法,整个构造派心理学在不同领域以这种方法展开研究。威廉·沃林格
 (Wilhelm Worringer)则指出这一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学研究。他对比了两个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古希腊时期和拜占庭时期,认为旧式的批评,即用绝对概念界定艺术并以古典标准评价艺术,根本无法理解拜占庭绘画和马赛克作品中所表现的艺术过程。我们不能用一种艺术标准评判另一种艺术成就,因为二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相同。古希腊人试图在其艺术中表达他们参与活动的愉悦,试图展现其生命力与客观世界的合一;而拜占庭艺术则以抽象概念为对象,表达与外部自然的深刻分离感。在理解这两种艺术时,除了比较艺术能力,我们更须考虑两种艺术差之千里的目的。两种艺术形式不一样,但都是整合的形态,一方会觉得另一方所采用的形式与标准匪夷所思。
(Wilhelm Worringer)则指出这一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学研究。他对比了两个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古希腊时期和拜占庭时期,认为旧式的批评,即用绝对概念界定艺术并以古典标准评价艺术,根本无法理解拜占庭绘画和马赛克作品中所表现的艺术过程。我们不能用一种艺术标准评判另一种艺术成就,因为二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相同。古希腊人试图在其艺术中表达他们参与活动的愉悦,试图展现其生命力与客观世界的合一;而拜占庭艺术则以抽象概念为对象,表达与外部自然的深刻分离感。在理解这两种艺术时,除了比较艺术能力,我们更须考虑两种艺术差之千里的目的。两种艺术形式不一样,但都是整合的形态,一方会觉得另一方所采用的形式与标准匪夷所思。
格式塔(形态)心理学
 最好地证明了以整体而非部分为出发点的重要性。格式塔心理学家指出,即便是最简单的感官知觉分析,也无法通过单独的感知解释整体经验。仅仅将感知切割成客观碎片是不够的。主观框架,即过往经验提供的形式,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自洛克以来心理学一直满足于研究简单关联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必须研究“整体属性”和“整体倾向”。整体决定部分,不仅决定其关系,还决定其性质。两个整体属于不同的种类,为理解它们,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各自不同的性质,将其置于二者相似的元素之上。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可从实验室获得证据的领域,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研究中的简单演示。
最好地证明了以整体而非部分为出发点的重要性。格式塔心理学家指出,即便是最简单的感官知觉分析,也无法通过单独的感知解释整体经验。仅仅将感知切割成客观碎片是不够的。主观框架,即过往经验提供的形式,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自洛克以来心理学一直满足于研究简单关联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必须研究“整体属性”和“整体倾向”。整体决定部分,不仅决定其关系,还决定其性质。两个整体属于不同的种类,为理解它们,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各自不同的性质,将其置于二者相似的元素之上。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可从实验室获得证据的领域,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研究中的简单演示。
19世纪的威廉·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强调整合与形态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伟大的哲学思想和对生活的阐释。他在《世界观的类型》(
Die Typen der Weltanschauung
)一书中特别分析了部分思想史,揭示出不同哲学体系的相对性。他认为,不同的哲学体系恰恰表现了不同的生活、情绪和感情,这些整体态度中的基本种类不可能互相转换。他强烈反对将这些整体态度中的任何一种态度视为决定性因素。狄尔泰并没有给自己探讨的不同态度贴上文化标签,但他的论述涉及最重要的哲学形态,以及腓特烈大帝时期和其他重要历史时期,他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导向对文化角色日益自觉的认识。
(Wilhelm Dilthey)强调整合与形态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伟大的哲学思想和对生活的阐释。他在《世界观的类型》(
Die Typen der Weltanschauung
)一书中特别分析了部分思想史,揭示出不同哲学体系的相对性。他认为,不同的哲学体系恰恰表现了不同的生活、情绪和感情,这些整体态度中的基本种类不可能互相转换。他强烈反对将这些整体态度中的任何一种态度视为决定性因素。狄尔泰并没有给自己探讨的不同态度贴上文化标签,但他的论述涉及最重要的哲学形态,以及腓特烈大帝时期和其他重要历史时期,他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导向对文化角色日益自觉的认识。
这一观点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其《西方的没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一书的书名并非出自作为全书主题的命运观,而是出自一个与该书论述无关的论题——文化形貌与生物体一样有无法逾越的“寿命”。他以西方文明中文化中心的迁移以及文化成就的周期性为基础,论述文明衰败这一命题。他在描述中以生物体的生死循环类比文明的盛衰,这样的类比当然也仅止于类比。他认为,每种文明都有灿烂的青春期、强盛的成年期以及土崩瓦解的老年期。
(Oswald Spengler)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其《西方的没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一书的书名并非出自作为全书主题的命运观,而是出自一个与该书论述无关的论题——文化形貌与生物体一样有无法逾越的“寿命”。他以西方文明中文化中心的迁移以及文化成就的周期性为基础,论述文明衰败这一命题。他在描述中以生物体的生死循环类比文明的盛衰,这样的类比当然也仅止于类比。他认为,每种文明都有灿烂的青春期、强盛的成年期以及土崩瓦解的老年期。
《西方的没落》主要因后一种历史解读而知名,但斯宾格勒在书中最有价值且最具原创性的工作是对西方文明不同形态的分析。他提出了两种重要的人生观:古典世界的阿波罗型的人生观和现代世界的浮士德型的人生观。阿波罗型的人认为自己的灵魂是“由最佳零件构成的宇宙”,在他的世界中没有意志的位置,冲突则是阿波罗型命运观严厉谴责的恶。他从不思索人格的内向发展,在他看来,生命总是处于外界严酷灾祸的阴影下。他最大的悲剧便是正常生存的乐园遭遇恶意毁灭。这样的灾祸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落在任何个体身上,导致同样的下场。
而浮士德型的人则自视为不断与各种阻碍抗争的力量。他心目中的个人人生历程是内心发展的过程,生命的灾祸源自他以往的选择和经验累积出的必然性。冲突是生存的本质,没有冲突的人生毫无意义,只有表面的生存价值。浮士德型的人渴望无限,他的艺术努力达到无限。浮士德型和阿波罗型是对生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方所推崇的价值观在另一方看来陌生且不值一提。
古典世界的文明建立在阿波罗型人生观的基础上,现代世界一切制度则体现了浮士德型人生观的意义。斯宾格勒还旁及埃及型文化,指出这种文化“认为人生是一条早已决定、不可更改的窄路,其终点是死亡的审判”。他也提及严守身心二元论的祆教(Magian)文化。但阿波罗型和浮士德型人生观是他论述的主体,他还认为数学、建筑学、音乐和绘画是这两种伟大而对立的哲学在西方文明不同时期的表现。
斯宾格勒的长篇论述不免令人眼花缭乱,这不完全是表述方式的问题,更是因为他论及的各种文明存在无法解开的复杂性。西方文明的历史头绪繁多,演化出不同层级的行业和阶层,包含无与伦比的丰富细节。我们对这一切所知不多,尚无法用两三个词语总结概括。浮士德型的人一旦走出极小的知识圈或艺术圈,便会觉得与我们的文明扞格不入。除了浮士德型的人,还有行动的强者和巴比特
 ,符合民族志研究原则的现代世界图景不能无视这些常见文化类型。我们可以用渴望无限的浮士德型来描述一种文化类型,也可以用纯然外向型来描述强者和巴比特,他们奔忙于无尽的世俗事务——发明、治理,借用爱德华·卡彭特
,符合民族志研究原则的现代世界图景不能无视这些常见文化类型。我们可以用渴望无限的浮士德型来描述一种文化类型,也可以用纯然外向型来描述强者和巴比特,他们奔忙于无尽的世俗事务——发明、治理,借用爱德华·卡彭特
 (Edward Carpenter)的说法,他们“永远在赶火车”。
(Edward Carpenter)的说法,他们“永远在赶火车”。
从人类学角度看,斯宾格勒描绘世界诸文明时,被一种观念束缚了手脚,以为多层的现代社会文化也像民俗文化那样具有基本的同质性。从我们现有的知识看,西欧文化的历史资料异常复杂,社会分化根深蒂固,我们很难对之做必要的分析。不论斯宾格勒提出的浮士德型的人对研究欧洲文学和哲学有多大的启发意义,也不论他强调价值观的相对性多么有理,他的研究终究不是定论,因为其他的图景也能成立。回望过去,对西方文明这样庞大而复杂的整体或许可以通过回顾进行概括,斯宾格勒假设的各不相同的命运观重要而真实,但是目前不论我们试图选取哪种单一特质来解读西方世界,其结果都会导致混乱。
较简单的文化有利于厘清一些在其他环境中含混不清或未能明示的社会事实,这是研究原始民族的哲学依据,在论及根本且各异的诸多文化形貌时则更是如此。文化形貌使生存形成模式,并塑造参与文化的个体的思维和情感。那么今天研究较简单的民族便是理解如今个体受传统习俗影响而形成习惯模式的最佳途径。这并不是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发现的事实和过程仅适用于各种原始文明。对于我们所了解的最高级、最复杂的社会,文化形貌同样必不可少,且意义重大,然而这样的社会所提供的材料过于复杂,且与我们距离太近,因而难以处理。
“绕道而行”反而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过程最经济的途径。达尔文发现人类与其动物王国直接祖先的历史关系过于缠结,因而无法用以确立生物进化过程,便转而利用甲壳动物的结构来研究生物进化。拥有复杂身体组织的人类所经历的进化过程难以厘清,而简单生物的进化过程却一目了然,研究文化机制亦如是。我们需要研究思维和行为在不那么复杂的人群中如何组织,以便获得启发。
我选择了三种原始文明,对其进行细致描述。理解少数几种文化中一以贯之的行为组织,比浮光掠影地观察多种文化更具启发意义。对世界的笼统观察无法使我们理解出生、死亡、青春期、婚姻等互不相干的文化行为如何与动机以及目的发生关联,我们只能先做比较容易的事情,即对少数几种文化进行多方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