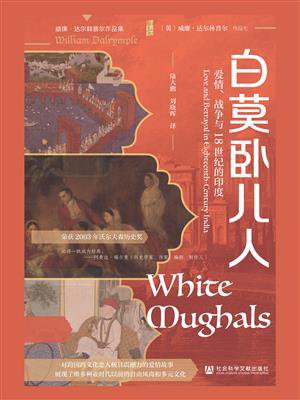序章
我第一次听说詹姆斯·阿基利斯·柯克帕特里克,是在1997年2月,当时我正在游览海德拉巴。
正值穆哈兰姆月
 里什叶派纪念先知的外孙侯赛因
[1]
殉难的节日。我刚刚完成了一本关于中东修道院的书,四年的工作让我精疲力竭。我来到海德拉巴,是为了逃离书桌和满满的书架,为了放松身心,为了随心所欲,为了再来一场漫无目的的旅行。
里什叶派纪念先知的外孙侯赛因
[1]
殉难的节日。我刚刚完成了一本关于中东修道院的书,四年的工作让我精疲力竭。我来到海德拉巴,是为了逃离书桌和满满的书架,为了放松身心,为了随心所欲,为了再来一场漫无目的的旅行。
恰逢春季。脚下的清真寺石板路暖洋洋的。我漫步在老城的各处圣所之间,随处可见身披黑袍的穆斯林哀悼者,他们吟唱着悠扬婉转的乌尔都语哀歌,纪念卡尔巴拉的悲剧,仿佛侯赛因是在一周前遇害的,而不是在公元7世纪末。这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印度城市。
并且,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少有人探索和描写的地方,至少在英语世界是这样;这里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与阿格拉或北方拉杰普特
 诸城邦的那种震撼人心、气势磅礴的辉煌不同,海德拉巴将它的魅力隐藏在外人的视线之外,用不起眼的城墙和迷宫般的街巷隐蔽它的光辉璀璨,不让好奇的目光接触。它只会慢慢地领你进入一个封闭的天地,那里的喷泉还在流淌,花儿在微风中弯腰,孔雀在果实累累的芒果树上啼鸣。在那里,隐藏在街道之外的,是一个永恒和静谧的世界,是逐渐逝去的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最后堡垒。正如一位艺术史学家所说,“海德拉巴的老绅士们仍然戴着菲斯帽
诸城邦的那种震撼人心、气势磅礴的辉煌不同,海德拉巴将它的魅力隐藏在外人的视线之外,用不起眼的城墙和迷宫般的街巷隐蔽它的光辉璀璨,不让好奇的目光接触。它只会慢慢地领你进入一个封闭的天地,那里的喷泉还在流淌,花儿在微风中弯腰,孔雀在果实累累的芒果树上啼鸣。在那里,隐藏在街道之外的,是一个永恒和静谧的世界,是逐渐逝去的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最后堡垒。正如一位艺术史学家所说,“海德拉巴的老绅士们仍然戴着菲斯帽
 ,仍然梦见玫瑰和夜莺,并为格拉纳达的陷落而哀悼”。
[2]
,仍然梦见玫瑰和夜莺,并为格拉纳达的陷落而哀悼”。
[2]
从海德拉巴老城出发,我开车去参观峭壁之上的戈尔康达要塞。六百年来,戈尔康达一直是该地区似乎源源不断地产出的钻石的集散地。在18世纪发现新大陆的钻石矿以前,这里是唯一为人所知的钻石产地。在城墙之内,游人会经过一连串的深宫、泳池、亭台楼阁和园林。法国珠宝商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于1642年造访戈尔康达时,发现这里的人们就像这些建筑显示的一样富庶而颓废。他写道,这座城市拥有超过两万名注册的名妓,她们每个星期五轮流为苏丹跳舞。
我很快发现,这种浓郁的浪漫的宫廷气氛,甚至感染了18世纪末抵达海德拉巴的那些头脑清醒的英国人。曾经的英国常驻代表府,如今的奥斯曼尼亚大学女子学院,是一座庞大的帕拉迪奥式
 别墅,它的平面布局与同时期的华盛顿白宫有点相似。这是东印度公司修建的最完美的建筑之一,位于一座巨大的设防园林之中,与海德拉巴老城只隔着一条穆西河。
别墅,它的平面布局与同时期的华盛顿白宫有点相似。这是东印度公司修建的最完美的建筑之一,位于一座巨大的设防园林之中,与海德拉巴老城只隔着一条穆西河。
我得知,这个建筑群是詹姆斯·阿基利斯·柯克帕特里克中校建造的。他于1797~1805年担任英国驻海德拉巴宫廷的常驻代表,相当于大使。柯克帕特里克显然接受和采纳了海德拉巴的服装和生活方式。据说,他来到这座城市不久之后,就爱上了海德拉巴首相的一名女性亲戚。柯克帕特里克在1800年遵照伊斯兰法律的要求,娶了海尔·妮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最优秀的女人”)。
在旧常驻代表府内,我发现以前的舞厅和会客厅的天花板上的灰泥成块地脱落,有些块状的灰泥有轿子那么大。楼上的旧卧室已经严重腐坏。它们现在空荡荡的,不见人迹,只有蝙蝠出没,偶尔有一对多情的鸽子在这里缠绵;楼下优雅的椭圆形沙龙被硬纤维板隔成许多小间,成了学院管理人员的办公室,显得很破旧了。因为房子的中央部分破损严重,对学生来说太危险了,所以现在学生们主要是在房子后面的旧象厩里上课。
即使是在这种半荒废的状态下,也很容易看出常驻代表府曾经是多么辉煌壮丽。它的南面有一个恢宏的半圆形河湾,可以通过一座巨大的凯旋门到达,凯旋门面对着穆西河上的桥。北面有一对英国石狮子,它们伸出爪子,趴在巨大的有山墙和柱廊的正立面之下。石狮子俯瞰着一大片桉树、香榄和木麻黄树,把东印度公司最宏伟、最庄重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在院落后部的灌木丛中还隐藏着惊喜。
在常驻代表府后部的花园里,我看到了柯克帕特里克对他妻子的爱的信物,虽然这个信物已经破损了。有一个传说(我估计是后人附会,但不乏魅力)是这样的:海尔·妮萨一辈子过着穆斯林大家闺秀那种与世隔绝的深闺生活,住在柯克帕特里克的花园尽头的一座单独的女眷深宫(bibi-ghar,字面意思是“女人的房子”),所以她没办法绕过丈夫的伟大作品(即这座府邸)去欣赏它美轮美奂的门廊。最后,常驻代表想出了一个办法,为他的新宫殿建造了一座等比例缩小的石膏模型,让她可以仔细观察她永远不会允许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不管故事的真相如何,这个模型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到20世纪80年代,后来有一棵树倒在上面,砸坏了模型的右翼。而模型左翼和中央区域的残骸躺在一块瓦楞铁之下,靠近莫卧儿风格的女眷深宫的废墟,深埋在一片藤蔓和爬山虎之下。这个区域今天仍然被称为“夫人花园”。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迷人。我离开花园时,已经陶醉在这个故事之中了,不禁想知道更多。这个故事与人们对“在印度的英国人”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也浪漫得多,于是我在海德拉巴的余下时间里都在四处追寻柯克帕特里克的踪迹,寻找能够给我讲述更多故事的人。
我不需要走很远就能如愿以偿。泽布·妮萨·海德尔博士是一位年长的波斯语学者,她在旧常驻代表府的一座不那么破败的厢房里教导她那些戴着面纱的女学生。泽布博士解释说,她是当时的海德拉巴首相鲁肯·道拉的后人。她说,她不仅熟悉这个故事的梗概,而且熟悉许多提到这个故事的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史料。
据泽布博士说,这些海德拉巴的史料明确表示,柯克帕特里克为了娶海尔·妮萨而皈依了伊斯兰教。史料还提到,尽管发生了这么一桩丑闻,柯克帕特里克在海德拉巴还是很受欢迎,自由自在地与人们相处,并采纳了这座城市的生活习惯。泽布博士尤其记得一本名为《胡尔希德·贾赫史》的史书中的一句话:“由于与该国的女士们相处过久,他非常熟悉海德拉巴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并接受了这些方式和习惯。”好几部波斯文史料还暗示,到最后,柯克帕特里克虽然是英国官员,却对海德拉巴的尼查姆(统治者)忠心耿耿。这些史料都没有被翻译成英文,因此对那些不熟悉19世纪德干乌尔都语或手抄本所用的高度印度化的波斯语的人来说,这些史料都处于未被研究的状态。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年长的海德拉巴伊斯兰学者熟悉这两门语言。
一天夜里,我参观了柯克帕特里克的主要对手米歇尔·若阿基姆·雷蒙将军的墓。雷蒙是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也是为尼查姆效力的雇佣军人。他和柯克帕特里克一样,也接受了海德拉巴的生活方式。柯克帕特里克的工作是把海德拉巴人拉到英国那边,而雷蒙试图说服尼查姆与法国人结盟。雷蒙去世后,被安葬在海德拉巴城外马拉克佩特的法国兵站上方的山顶。他的墓就在一座小型古典希腊风格神庙的下方,旁边有一座方尖碑。
雷蒙肯定放弃了基督教,他的坟墓上没有任何基督教的符号或图像,似乎能证明这一点。但他的海德拉巴崇拜者不确定他是否已经成了印度教徒或穆斯林。他的印度教徒士兵将雷蒙先生的名字改成梵文风格的穆萨·罗摩,而他的穆斯林士兵称他为穆萨·拉希姆。拉希姆是真主之慈悲的化身。尼查姆和其他人一样说不准雷蒙的宗教信仰,于是决定以一种宗教中立的方式纪念雷蒙的忌日(3月25日),把一盒方头雪茄和一瓶啤酒送到他的墓碑前。这个习俗显然一直延续到印度独立后最后一位尼查姆前往澳大利亚时;在雷蒙的忌日,我恰好在海德拉巴,所以我很想看看,是否有关于雷蒙的记忆留存至今。
雷蒙纪念碑原本建在海德拉巴城墙外几英里的一座荒凉的山顶上。但近些年的快速发展让海德拉巴成了印度第四大城市,这座山周围的所有地方都被开发了,如今只有山顶上的纪念碑周围还比较空旷,没有建起新的平房
 和住宅区。我在路的尽头下了出租车,登山前往神庙。在硫红色的城市夜空中,神庙的轮廓清晰可见。我走近的时候,看到柱子间影影绰绰,原来是善男信女在神庙背后的神龛点燃泥灯。也许这些人看到了我登山前来;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到达纪念碑时,他们已经踪影全无,只在墓前留下了祭品:几只椰子、几炷香、一些花环和几堆小金字塔形状的白色甜食。
和住宅区。我在路的尽头下了出租车,登山前往神庙。在硫红色的城市夜空中,神庙的轮廓清晰可见。我走近的时候,看到柱子间影影绰绰,原来是善男信女在神庙背后的神龛点燃泥灯。也许这些人看到了我登山前来;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到达纪念碑时,他们已经踪影全无,只在墓前留下了祭品:几只椰子、几炷香、一些花环和几堆小金字塔形状的白色甜食。
回到伦敦后,我四处搜寻关于柯克帕特里克的更多信息。有几本关于英属印度建筑的书提到了他的常驻代表府和他的印度夫人,但都很简略。有限的信息似乎都源自1893年《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詹姆斯·阿基利斯·柯克帕特里克的浪漫婚姻》,作者是柯克帕特里克的亲戚爱德华·斯特雷奇。 [3]
当我发现柯克帕特里克与兄长威廉的通信由威廉的后裔斯特雷奇家族保存,最近被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买下时,我才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突破。那里有堆积如山的写有“我的弟弟詹姆斯·阿基利斯·柯克帕特里克的来信”字样的信册(里面的纸张都因岁月的摧残而变得光亮而脆弱),还有许多卷镀金皮面装订的与英印总督韦尔斯利勋爵的官方信函、成捆的波斯文手抄本、若干盒收据,以及一份装在黄褐色大信封里的遗嘱。这正是传记家梦寐以求的那种随机而又详细的日常生活碎片。
买下时,我才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突破。那里有堆积如山的写有“我的弟弟詹姆斯·阿基利斯·柯克帕特里克的来信”字样的信册(里面的纸张都因岁月的摧残而变得光亮而脆弱),还有许多卷镀金皮面装订的与英印总督韦尔斯利勋爵的官方信函、成捆的波斯文手抄本、若干盒收据,以及一份装在黄褐色大信封里的遗嘱。这正是传记家梦寐以求的那种随机而又详细的日常生活碎片。
不过,乍一看去,许多书信显得平淡无奇、令人失望:关于宫廷政治的八卦;从加尔各答索取信息的请求;提供一箱马德拉酒或柯克帕特里克在海德拉巴的集市上买不到的蔬菜,如土豆和豌豆(居然买不到这些,真是出人意料)的偶尔恳求。这虽然足够有趣,但仍然不引人注目。我恼火地发现这些书信极少提及柯克帕特里克的宗教情感或私事。此外,许多更有趣的材料都是用密文写的。柯克帕特里克一谈到他的风花雪月,或者他参与建立的间谍网络,清晰而稳健的笔迹就会化为一长串难以理解的数字。
经过几个星期的阅读,我终于找到了载有海尔·妮萨书信的档案,发现其中一些书信没有加密。有一天,当我打开印度事务部的另一个硬纸板文件夹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下面一段文字上,它的笔迹小而稳健,字体倾斜:
首先,不妨指出,我确实安全地经受了一次严酷的考验,与这封信要谈的魅力十足的主角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幽会。就是在这次幽会期间,我全面而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妙人儿。我们聊了大半夜。这次幽会显然是由她的外祖母和母亲策划的,她们对她百般宠溺,允许她满足自己的渴望,因为这关系到她们的生存。这次幽会是在我家中进行的,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享用我显然受邀去享用的诱人盛宴。虽然上帝知道我没有能力克制自己,但我还是努力说服这位浪漫的年轻女性,请她摆脱激情的掌控。我承认,我自己也产生了这样的激情。她一次又一次地向我示爱,说她已经不可逆转地爱上我一段时间了,她的命运与我的命运紧密交织,只要能与我朝夕相伴,她愿意当最卑贱的婢女……
不久之后,我发现了几页被“翻译”过的密文,发现原来密文是简单的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的对应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整个故事很快就清晰起来了。
当我偶然看到东印度公司对此事的秘密调查卷宗时,又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调查卷宗里有从证人那里获取的宣誓证词,有详细而赤裸裸的问题,这些问题得到了惊人地坦率、无拘无束的回答。当我把调查卷宗拿在手里时,我心中残留的疑虑都烟消云散:这里有非常精彩的材料,足以写一本书。
随后四年里,我一直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艰辛劳作,偶尔回到德里和海德拉巴,查询那里的档案。在印度,不可避免地出了一些麻烦。在德里的印度国家档案馆地下室,有人在安装新的空调系统时,心不在焉地将全部六百卷《海德拉巴常驻代表档案》放在露天处,而当时正值雨季。等到我第二次再来看这些档案的时候,大部分档案已经无法挽救了,没有被水淹的档案也覆盖了厚厚的绿霉。几天后,档案馆认定这些霉很危险,于是六百卷档案都被送去“熏蒸”。我再也没有见到它们。
在同一个雨季,穆西河在海德拉巴泛滥,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海德拉巴老城的档案管理员将他们收藏的精美手抄本的残余部分挂在晾衣绳上晾干的画面。
尽管遭遇了这样的挫折,但我追踪的那个爱情故事开始逐渐成形。就像看着一张“拍立得”照片显影一样,轮廓慢慢清晰起来,色彩开始填补剩余的白色空间。
也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妙手偶得的时刻。经过三趟旅行、在多家档案馆待了几个月之后,在我最后一次去海德拉巴的最后一天,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逛查米纳塔门后面的老城集市,想买点礼物送给亲人。那天是星期天,集市大门半掩。我之前忘了给家人买礼物,眼看飞往德里的飞机只有5个小时就要起飞,于是我疯狂地从一家店跑到另一家店,寻找海德拉巴最重要的特产,就是有装饰的比德尔金属工艺品。最后,一个男孩自告奋勇带我去一家商店,说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个比德尔金属盒子。他带我深入广场清真寺背后迷宫般的街巷。在那里的一条小巷子里坐落着一家商店,他说我在那里一定能找到“booxies booxies”。
实际上这家店卖的不是盒子,而是书(就是我的导游一直想告诉我的“booksies”)
 ,严格地说也不是书,而是乌尔都语和波斯语手抄本以及非常罕见的印刷版编年史。这些书是老板在20世纪60~70年代从海德拉巴的一些私人图书馆收购的,当时海德拉巴那些属于贵族的宏伟的城市宫殿被拆毁,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现在,这些书堆放在一个只有较大的扫帚间那么大,而且尘土飞扬、光线昏暗的店铺里,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这位书商很厉害,对自己拥有什么书了如指掌。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什么之后,他从一摞书下面拿出一本巨大的、破烂不堪的波斯语书籍——《给世界的馈赠》,作者是阿卜杜勒·拉蒂夫·舒什塔里,我在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的书信里经常看到这个名字。这本六百页的大书原来是海尔·妮萨的这位亲戚妙趣横生的自传,是在她与詹姆斯结婚的丑闻发生不久之后在海德拉巴写的。店里还有其他一些手抄本,包括一本非常罕见的记述海德拉巴该时期历史的著作《阿萨夫史集》(
Gulzar i-Asafiya
)。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与店主讨价还价,离开他的店时,虽然少了400英镑,却多了一箱从未被翻译过的原始史料。它们的内容完全改变了我随后的工作。
[4]
,严格地说也不是书,而是乌尔都语和波斯语手抄本以及非常罕见的印刷版编年史。这些书是老板在20世纪60~70年代从海德拉巴的一些私人图书馆收购的,当时海德拉巴那些属于贵族的宏伟的城市宫殿被拆毁,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现在,这些书堆放在一个只有较大的扫帚间那么大,而且尘土飞扬、光线昏暗的店铺里,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这位书商很厉害,对自己拥有什么书了如指掌。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什么之后,他从一摞书下面拿出一本巨大的、破烂不堪的波斯语书籍——《给世界的馈赠》,作者是阿卜杜勒·拉蒂夫·舒什塔里,我在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的书信里经常看到这个名字。这本六百页的大书原来是海尔·妮萨的这位亲戚妙趣横生的自传,是在她与詹姆斯结婚的丑闻发生不久之后在海德拉巴写的。店里还有其他一些手抄本,包括一本非常罕见的记述海德拉巴该时期历史的著作《阿萨夫史集》(
Gulzar i-Asafiya
)。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与店主讨价还价,离开他的店时,虽然少了400英镑,却多了一箱从未被翻译过的原始史料。它们的内容完全改变了我随后的工作。
[4]
到了2001年,我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四年。我自认为对柯克帕特里克已经了如指掌,在一遍遍阅读他的书信时,在脑海中仿佛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不过,还有一些重要的空白留待填补。特别是对于柯克帕特里克去世后海尔·妮萨的遭遇,无论是印度事务部的文献,还是1893年《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的文章,都只字未提。又经过九个月的搜寻,我才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亨利·罗素档案中偶然发现了令人心碎的答案。这个故事从来没有被人讲过,似乎连柯克帕特里克的同时代人也不知道。它与《蝴蝶夫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日复一日,在汉弗莱公爵图书馆
 的纹章盾和深色橡木书柜之下,我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阅读褪色书页上罗素那经常让人难以辨认的圆形草体字,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才慢慢地在我面前完整地展开。
的纹章盾和深色橡木书柜之下,我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阅读褪色书页上罗素那经常让人难以辨认的圆形草体字,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才慢慢地在我面前完整地展开。
最后,就在我落笔的几个月前,在距离我在伦敦西区的家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属于柯克帕特里克和海尔·妮萨的后人的家族档案浮出水面。这就把故事延伸到了海尔·妮萨的女儿基蒂·柯克帕特里克的经历上,她的故事也同样精彩。她最初的名字是萨希布·贝古姆,出生后以海德拉巴的穆斯林贵族女孩的身份被抚养,四岁时被送往英国,抵达伦敦后受洗,从此与母系亲属完全断了联系。后来她被吸收到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圈子的上层,在那里,她迷住了她的堂姐的家庭教师,年轻的托马斯·卡莱尔,并成为卡莱尔的小说《拼凑的裁缝》的女主角布鲁敏的原型,被誉为“多姿多彩、容光焕发的曙光女神……最美好的东方光芒的使者”。
这最后一套家族档案讲述了一系列非凡的巧合,正是这些巧合让基蒂在成年后重新与她的海德拉巴外祖母取得联系,并让祖孙俩在时隔近四十年后通过感情洋溢的书信重新建立纽带。这些书信非常优美,萦绕着浓浓的悲伤,讲述了因偏见和误解、政治和命运而天人路隔的亲人的故事。其中一位在托基
 的海滨别墅用英语写信;另一位在海德拉巴的深闺用波斯语口授给抄写员,抄写员用撒了金粉的信纸书写,并将信装在莫卧儿风格的金丝锦囊中。外祖母的信向基蒂揭示了她的父母相识相爱的秘密,并让她自己发现了海尔·妮萨命运的悲惨真相。
的海滨别墅用英语写信;另一位在海德拉巴的深闺用波斯语口授给抄写员,抄写员用撒了金粉的信纸书写,并将信装在莫卧儿风格的金丝锦囊中。外祖母的信向基蒂揭示了她的父母相识相爱的秘密,并让她自己发现了海尔·妮萨命运的悲惨真相。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家三代人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在欧式服装和印度服装之间,在莫卧儿海德拉巴和摄政时期的伦敦之间漂泊的故事。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关于英国人的特质和帝国的性质,关于信仰,关于身份认同;实际上,也关于所有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重要的、固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或者,它们其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灵活的、可调整的和可协商的。在本书的故事里,通常情况下似乎是金科玉律的帝国二元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帝国主义者与底层民众、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被打破了。事实证明,许多代历史学家漫不经心地采用的宗教、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标签,至少是出人意料地不可靠的。不过,最让我着迷的一点是,虽然围绕柯克帕特里克故事的文献保存得很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去观察一个很少有人意识到曾经存在的世界,但故事中的情况本身绝非罕有的,而事件参与者自身也很清楚这一点。
研究越深入,我就越相信,我们对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的刻板印象(比如,他们是一个小规模的外来群体,与世隔绝地生活在他们管辖区
 的城镇、要塞与兵站中)需要修正。英国人在印度生活的这个早期阶段的基调,似乎是“混杂”和“不纯洁”的,是多种民族、文化和思想之间一系列出人意料却自然而然的交融。
的城镇、要塞与兵站中)需要修正。英国人在印度生活的这个早期阶段的基调,似乎是“混杂”和“不纯洁”的,是多种民族、文化和思想之间一系列出人意料却自然而然的交融。
无论是1947年之前在英国撰写的传统的帝国主义史书,还是独立后印度的民族主义史学,抑或是新一代学者(其中很多人倾向于遵循爱德华·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东方学》开辟的道路)的后殖民主义著作,都试图让我们相信,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与印度人是泾渭分明的,那个世界的种族、民族和宗教边界是清晰明确的。但柯克帕特里克家族生活的世界远比我们一贯想象的要混杂得多,种族、民族和宗教边界也都不是那么明确。 [5] 仿佛这种发生在早期的种族、思想、服饰风格与生活方式的水乳交融,并非任何人有意识努力的结果,也不符合任何人对历史的阐释。出于不同的原因,各方似乎都对这一时期的混杂与融合感到有些尴尬,所以宁愿假装这从未发生过。毕竟,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事物比较轻松。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我自己也是这一时期的跨种族婚恋的产物,我也有印度血统。所以我对上述问题越来越敏感。我们家族里似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不过它也并不让人惊讶:我们都听说过,我们那位出生于加尔各答的美丽、黑眼睛的高祖母索菲亚·帕特尔(伯恩-琼斯
 曾与她相爱)如何与她的姐妹说印度斯坦语,并且在沃茨
曾与她相爱)如何与她的姐妹说印度斯坦语,并且在沃茨
 为她画的肖像里,她的手腕上系着一条“拉基”(rakhi),即印度教的圣线或护身绳。但我挖掘档案之后才发现,她是一位来自金德讷格尔的孟加拉印度教徒女子的后裔,这名女子在18世纪80年代皈依了天主教,并嫁给了本地治里
为她画的肖像里,她的手腕上系着一条“拉基”(rakhi),即印度教的圣线或护身绳。但我挖掘档案之后才发现,她是一位来自金德讷格尔的孟加拉印度教徒女子的后裔,这名女子在18世纪80年代皈依了天主教,并嫁给了本地治里
 的一位法国军官。
的一位法国军官。
于是,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印度和英国之间曾经有一种共生关系。正如在印度的个别英国人可以学会欣赏并希望模仿印度文化的不同方面,选择采用印度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样,这一时期也有许多印度人开始前往英国,与当地人通婚并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
莫卧儿帝国的游记作家米尔扎·阿布·塔利布·汗在1810年用波斯文发表了一篇关于他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旅行的记述。他描述了在伦敦遇到的几名完全英国化的印度女子,她们随同丈夫和孩子来到英国,其中一位已经完美地完成了文化的“变身”,以至于“在她身边待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确信她是印度人”。
[6]
他还见到了非凡的丁·穆罕默德,他是一位来自巴特那
 的穆斯林地主,跟随他的英国恩公到了爱尔兰。
的穆斯林地主,跟随他的英国恩公到了爱尔兰。
在那里,丁·穆罕默德很快就和出身于盎格鲁-爱尔兰名门的简·戴利私奔,后来又与她结婚。1794年,他出版了《游记》,确立了他在科克
 社会的独特而出人意料的显赫地位。《游记》是有史以来第一本由印度人用英语写作的书,爱尔兰一半的士绅都买了这本书。1807年,丁·穆罕默德移居伦敦,在那里开设了英国第一家由印度人经营的咖喱餐厅,店名为“丁·穆罕默德的印度斯坦咖啡馆”。“在这里,士绅们可以享受用真正的印度烟草制作的水烟和最完美的印度菜肴,最伟大的美食家也承认这里的咖喱在英国无与伦比。”最后,他来到布莱顿,在那里开设了英国的第一家东方按摩院,并成为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国王的“按摩医师”。丁·穆罕默德的传记作者迈克尔·费希尔说得很对:“穆罕默德的婚姻和作为专业医生的成功程度告诉我们,不能把英国人后来的种族观念或立场往更早的历史时期投射。”
社会的独特而出人意料的显赫地位。《游记》是有史以来第一本由印度人用英语写作的书,爱尔兰一半的士绅都买了这本书。1807年,丁·穆罕默德移居伦敦,在那里开设了英国第一家由印度人经营的咖喱餐厅,店名为“丁·穆罕默德的印度斯坦咖啡馆”。“在这里,士绅们可以享受用真正的印度烟草制作的水烟和最完美的印度菜肴,最伟大的美食家也承认这里的咖喱在英国无与伦比。”最后,他来到布莱顿,在那里开设了英国的第一家东方按摩院,并成为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国王的“按摩医师”。丁·穆罕默德的传记作者迈克尔·费希尔说得很对:“穆罕默德的婚姻和作为专业医生的成功程度告诉我们,不能把英国人后来的种族观念或立场往更早的历史时期投射。”
 [7]
[7]
这恰恰就是许多关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印度的史书的问题所在:许多历史学家受到强烈的诱惑,想根据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行为与态度的刻板印象来诠释证据。不过,这些刻板印象显然与东印度公司官员和他们印度妻子真实的恐惧与希望、焦虑与愿景完全相悖。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储存的足以排列50英里长的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可以轻松地读到公司官员和他们印度妻子的大量书信。仿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不仅成功地将印度殖民化,而且更持久地将我们的想象力殖民化,排除了其他所有关涉到英印互动的图景。
自从大英帝国在20世纪后半期崩溃,大量印度人来到西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穿上了西方的衣服,接受了西方的礼仪。这种从东到西的文化交融,并不让我们感到惊讶。但是,相反的情况仍然让我们惊讶:如果一个欧洲人自愿接纳东方文化(伊丽莎白时代的说法是“变成土耳其人”,维多利亚时代的说法是“土著化”或“本土化”),这仍然是令我们惊愕的事情。
在詹姆斯·阿基利斯·柯克帕特里克去世仅七十五年之后,也是在他的女儿(英印混血、曾生活在托基和海德拉巴、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游走)的有生之年,吉卜林就写出了“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聚”的诗句。今天,人们倾向于嘲笑吉卜林;但当德高望重的学者也谈论“文明冲突”的时候,当东方和西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似乎正在进行另一场大规模对抗的时候,这群令人意想不到的跨文化人士能够及时地提醒我们,两个世界的调和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一直都是可能的。
[1] 侯赛因·伊本·阿里(625~680)是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阿里(什叶派的第一代伊玛目)的次子,也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阿里死后,其长子哈桑被迫放弃哈里发继承权,穆阿维叶一世建立倭马亚王朝,哈桑率阿里宗族退居麦地那。哈桑死后,弟弟侯赛因成为阿里家族的领袖。
680年,穆阿维叶一世驾崩,其子叶齐德一世继位为哈里发,侯赛因不承认他的地位,拒不向其效忠,并迁往麦加。不久,库法发生针对叶齐德一世的反叛,叛军邀请侯赛因前往主政。途中,侯赛因和两百余名拥护者被叶齐德一世的六千名士兵包围于卡尔巴拉。侯赛因及其跟随者拒绝投降,全体于10月10日的卡尔巴拉战役中阵亡。侯赛因之死标志着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彻底决裂,他也被什叶派穆斯林一致追认为第三代伊玛目。
[2] Mark Zebrowski, Gold,Silver and Bronze from Mughal India (London,1997).
[3] Edward Strachey,“The Romantic Marriage of James Achilles Kirkpatrick,Sometime British Resident at the Court of Hyderabad”,in Blackwood’s Magazine ,July 1893.
[4] 现代印度史学的一个奇怪之处是,对德干高原的研究仍然很少。对德干任何一个宫廷的严肃研究都很少,对德干文化史的研究尤其罕见。今天的史学界仍然经常把德干绘画错误地归类到莫卧儿或拉杰普特绘画中。在今天,历史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会得到一大群历史学博士的钻研,所以这样的巨大缺口就显得格外奇怪。海德拉巴和更广泛的德干高原的历史仍然是史学研究的一大空白。研究莫卧儿人的著作的数量是研究德干苏丹国的著作的一百倍。每当你找到一本关于海德拉巴的书,你就找到满满一架的关于勒克瑙的书。历史学家乔治·米歇尔前不久在《新编剑桥印度史》关于德干的那一卷的引言中写道:“很少有学者,无论是印度的还是外国的,大规模地研究过德干。至今很少有学者关注和研究德干,这有点让人惊讶。”见George Michell and Mark Zebrowski,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1.7:Architecture and Art of the Deccan Sultanates (Cambridge,1999)。——原书注
[5] 虽然如此,但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展现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在多大程度上像他们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样融入莫卧儿文化。不过这些著作还无法构成一个连贯的史学观点。将近三十年前,Percival Spear, The Nabobs (Cambridge,1963)描绘了这样的图景:18世纪一些爱抽水烟的英国人和他们的印度情人一起,在加尔各答过着舒适愉快的生活;而另一些英国人在穷乡僻壤的小镇和莫卧儿文化较偏僻的中心经历了更深刻的转变。他们穿上了莫卧儿服装,与莫卧儿贵族通婚,总的来讲在尝试跨越文化疆界,从而欣赏和参与晚期莫卧儿文化。后来的研究著作把这样的图景描绘得更细致。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聚焦于勒克瑙。在勒克瑙方面,Desmond Young、Rosie Llewellyn-Jones、Seema Alavi、Muzaffar Alam、Jean-Marie Lafont 和Maya Jasanoff详细描绘了混杂而包容的文化图景。在这样的环境里,克洛德·马丁、安托万·波利耶、伯努瓦·德·布瓦涅、约翰·伍姆韦尔和威廉·帕尔默将军这样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勒克瑙相当具有享乐主义气氛的晚期莫卧儿文明。见Desmond Young, Fountain of Elephants (London,1959);Rosie Llewellyn-Jones, A Fatal Friendship:The Nawabs,the British and the City of Lucknow (New Delhi,1982), A Very Ingenious Man:Claude Martin in Early Colonial India (New Delhi,1992)and Engaging Scoundrels:True Tales of Old Lucknow (New Delhi,2000);Muzaffar Alam and Seema Alavi, A European Experience of the Mughal Orient:The I’jaz i-Arslani(Persian Letters,1773-1779)of Antoine-Louis Henri Polier (New Delhi,2001);Jean-Marie Lafont,‘The French in Lucknow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Violette Graff(ed.), Lucknow:Memories of a City (New Delhi,1997)and Indika:Essays in Indo-French Relations 1630-1976 (New Delhi,2000);Maya Jasanoff关于勒克瑙的艺术品收藏与文化混合性的文章在2002年发表于 Past & Present 。Toby Falk、Mildred Archer和我找到了德里存在类似的“文化互化”过程的证据,尤其是在戴维·奥克特洛尼爵士、威廉·弗雷泽和詹姆斯·斯金纳的圈子里,这些人是英国驻德里常驻代表府的工作人员,时间从大约1805年到弗雷泽于1835年去世。见Mildred Archer and Toby Falk, India Revealed:The Art and Adventures of James and William Fraser 1801-35 (London,1989);William Dalrymple, City of Djinns (London,1993)。Seema Alavi还介绍了詹姆斯·斯金纳(有一半苏格兰血统,一半拉杰普特血统)如何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创建一种“莫卧儿与欧洲军事伦理的混合体”,并“采纳伊斯兰上流社会的风俗习惯,比如,抽水烟和吃莫卧儿饭菜”,见Seema Alavi, The Sepoys and the Company: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in Northern India 1770-1830 (New Delhi,1995),esp. Chapter 6。关于斯金纳的研究,另见Mildred Archer in Between Battles:The Album of Colonel James Skinner (London,1982)and Christopher Hawes in Poor Relations:The Making of a Eurasian Community in British India 1773-1833 (London,1996)。Chris Bayly展现了跨种族的性关系对于两种文化互相了解和学习是多么有帮助,而Durba Ghosh关于英国人的印度情人的重要著作展现了当时这种跨文化的性关系是多么司空见惯:C.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1996);Durba Ghosh,‘Colonial Companions:Bibis,Begums,and Concubines of the British in North India 1760-1830’(unpublished Ph.D.,Berkeley,2000)。Ghosh还展现了这种同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双向的进程,既影响了那些与欧洲人发生密切接触的印度女性,也影响了欧洲人自己。与此同时,Amin Jaffer的著作展现了公司雇员在英国国内的家庭生活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与莫卧儿两种文化的融合体,而Lizzie Collingham在另一部著作中强调了英国人的身体如何融入莫卧儿环境。Linda Colley展现了英国俘虏(尤其是被蒂普苏丹囚禁在塞林伽巴丹的英国俘虏)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各种原因而皈依伊斯兰教,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印度生活方式的不同方面:Amin Jaffer, Furniture from British India and Ceylon (London,2001);E.M. Collingham, Imperial Bodies:The Physical Experience of the Raj (Cambridge,2001);Linda Colley,‘Going Native,Telling Tales:Captivity,Collaborations and Empire’,in Past & Present ,No. 168,August 2000,p.172。Colley即将出版的著作 Captives 会继续详细阐述这个话题。
[6] Mirza Abu Taleb Khan(trans. C. Stewart), The Travels of Mirza Abu Taleb Khan in Asia,Africa,and Europe during the years 1799,1800,1801,1802,and 1803 (London,1810).
[7] Michael Fisher, The Travels of Dean Mahomet:An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ey Through India (Berkeley,1997),p.x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