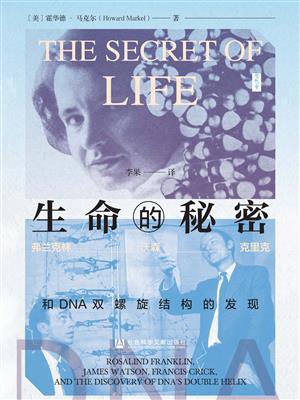第八章
问答小子
芝加哥
猛如猎犬,四处嗅探,像野人一般狡猾,与蛮荒为敌,
光着头,
挥着锹,
毁灭,
计划,
建设、破坏、重建……
笑年轻人的暴躁、魁伟、喧闹的笑、赤着上身,汗流浃背,他骄傲,为自己是杀猪匠、工具制造者、小麦堆放者、铁路工人和国家的货物装卸工而自豪。
——卡尔·桑德堡 [1]
就像索尔·贝娄的自传人物吉奥·马奇(Augie March)一样,詹姆斯·杜威·沃森也是“一个生于芝加哥的美国人”,他决心“用自己的方式创造纪录:先敲门,先录取;有时候会敲对门,有时候则相反”。 [2] 1928年4月6日,在芝加哥南区哥特式复兴风格的圣卢克医院,沃森迎来了值得纪念的幸运时刻。从来到世上的那一刻起,他就被称为吉姆。为了包装他对“DNA的痴迷”,沃森喜欢跟别人讲述他祖先的故事,他们是殖民地中富有开创精神的勇敢拓荒者,一路向美国大草原进发。他的一位亲戚威廉·韦尔登·沃森(William Weldon Watson)于1794年生于新泽西州,后来成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第一座浸礼会教堂(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牧师。他的儿子威廉·韦尔登·沃森二世(William Weldon Watson II)则北上来到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沃森二世在这里为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阴郁、魁梧的律师设计了一栋房子。沃森夫妇和林肯夫妇两家正好隔着一条马路相望。“诚实的亚伯”受命前往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后,威廉·沃森二世、他的妻子和儿子本(Ben)与林肯夫妇一起乘坐候任总统的就职列车前往华盛顿。本的儿子威廉·沃森三世(William Watson III)后来成了芝加哥地区一家旅店的老板。威廉三世的五个儿子中的托马斯·托尔森·沃森(Thomas Tolson Watson)就是吉姆的祖父,他“在新发现的梅萨比山脉(Mesabi Range)寻找财富,该山脉是位于苏必利尔湖西部明尼苏达州德卢斯附近的大铁矿区”。 [3]
吉姆的父亲老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Sr.)出身于伊利诺伊州富裕的拉格朗日公立学校,曾在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就读一年,后因猩红热中断学业。一战期间,他加入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第33师前往法国服役一年时间,其间身体也差不多恢复了。回到芝加哥后,老吉姆便放弃了成为一名教师的希望,最终在拉萨尔进修大学(LaSalle Extension University)找了一份收账员的工作,这是一所提供远程商业课程的函授学校。 [4] “老吉姆内心中从未想过赚大钱”,他热爱观鸟,而且成了一名出色的鸟类专家,1920年,他与人合作撰写了一本备受赞誉的芝加哥地区鸟类指南。 [5] 老吉姆的合著者是一位名叫小内森·利奥波德(Nathan Leopold)的少年,此人后来很快就跟好友理查德·勒布(Richard Loeb)一道臭名远扬了。1924年,两个年轻人对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产生了病态的迷恋,这种观念认为在智力上有天赋的人应该凌驾于统治下层大众的法律之上。 [6] 他们后来声称,这种反常的哲学促使他们绑架并残忍杀害了一个名叫鲍比·弗兰克斯(Bobby Franks)的14岁男孩。(克拉伦斯·达罗代表利奥波德和勒布参加了这场被媒体称为“世纪大审判”的庭审)。 [7] 值得庆幸的是,儿子仅仅继承了老吉姆对观鸟的热爱,而没有继承他选择观鸟伙伴的偏好,也没有继承他烟瘾成性的习惯,小吉姆尊称父亲为“求真、理性和正派”的人。 [8] 因此,小吉姆·沃森最初的职业目标是成为鸟类学家,立志于在野外发现新物种,并在某个州立大学任教。
他的母亲玛格丽特·珍·米切尔·沃森(Margaret Jean Mitchell Watson)曾在芝加哥大学就读两年,之后成了一名秘书,先是在拉萨尔大学,后又在芝加哥大学住房办公室工作。青少年时期的严重风湿让她患上了充血性心脏病,此后的余生里,玛格丽特动不动就会气喘吁吁,周末也常常卧床休息。她和老吉姆于1920年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小吉姆和伊丽莎白。
1933年,沃森的外祖母伊丽莎白·格里森·米切尔(“Nana”,“奶奶”)搬来与他们一家同住。米切尔夫人是来自蒂珀雷里郡(County Tipperary)的爱尔兰移民的后代,1907年新年夜,她的丈夫劳克林·米切尔(Lauchlin Mitchell,格拉斯哥出生的裁缝)在离开帕尔默宫酒店(Palmer House Hotel)时被一匹失控的马撞死,米切尔夫人因此成为寡妇。 [9] 父亲去世时,年仅14岁的玛格丽特·珍便负担起了照顾悲痛中的母亲的责任,全然不顾自己长期患病的事实。奶奶到来后,就照顾玛格丽特·珍的孩子来说,母女俩互换了角色。每天下午,温暖慈爱的奶奶都会在家门口迎接放学回家的吉姆和妹妹伊丽莎白(人称贝蒂),并在他们的父母下班前做晚饭。 [10]
跟许多邻居不同,沃森夫妇并不特别信教。玛格丽特·珍·沃森从小就是天主教徒,仅在圣诞节前夕和复活节时去做弥撒。老吉姆则从不去教堂。因此,沃森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天主教的逃亡者”。 [11] 就基督教信仰来说,沃森夫妇可能是不可知论者,但他们肯定对两个孩子灌输了狂热的知识信仰。1996年,沃森回忆道,“我家没什么钱,但有很多书”。 [12] 七年后的2003年,他还坚持说,“我最幸运的事情是父亲不信上帝,所以他对灵魂没有任何顾虑。我认为我们是进化的产物,而进化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谜”。 [13]
撇开书籍、鸟类和思想不谈,沃森一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按时付账单,尤其在大萧条多年来一直让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之后更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初,老吉姆的年薪减半至3000美元,为保住工作,他默默接受了减薪的待遇。于是,玛格丽特·珍在大学的兼职工作对维持家庭生计就变得格外重要。 [14] 沃森一家不仅是罗斯福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新政的受益者。
沃森一家住在卢埃拉大道(Luella Avenue)7922号,这是一栋“抵押率很高”的砖砌平房,面积为1604平方英尺,就在芝加哥南区第79街下面。沃森的父母曾因为拥有这个家而倍感自豪,房子二楼设有四间卧室,后有围栏。他们家过去(以及现在)距离芝加哥大学四英里多一点,距离杰克逊公园和密歇根湖南岸不到15个街区。吉姆和贝蒂就读的霍勒斯·曼文法学校(Horace Mann Grammar School)也近在咫尺。 [15] 后来,沃森“高兴地说,「他的房子」离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钢铁厂……比离芝加哥大学还近”——这样说并不准确,因为“加里工厂”远在南面约20英里处。尽管如此,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市值十亿美元的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波浪形的钢厂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他只需向窗外望去,就能看到工业废气形成的灰色长烟。

图8-1 詹姆斯·D.沃森,10岁,1938年
沃森是个瘦弱、腼腆、长相清奇、不爱运动的男孩,他双眼凸出,面部表情独特。白天,他喜欢观鸟而非打棒球。晚上,他会背诵从《世界年鉴》( World Almanac )的玛瑙字体(agate-font)页面上摘录的事实和数字,以此让自己安静入眠。 [16] 他在学校不受待见,经常鄙视那些“笨”男生,而那些男生也经常欺负他。
他的书生气至少给他带来一个社会优势。1940年,勤奋的芝加哥人路易斯·考恩(Louis Cowan)设计并制作了一档名为《问答小子》(The Quiz Kids)的广播节目,这档成功的广播节目在“阿卡塞尔兹(Alka-Seltzer)制造商”的赞助下先后在全国广播公司播放了13年之久。 [17] 每周,位于庞大商品市场大厦深处的演播室里,一群6~12岁的早熟、聪颖的孩子被提问各种问题,只为赢得100美元的储蓄债券。沃森回忆说,“我那个时候参加这个节目的唯一原因不过是,节目制作人就是我们的隔壁邻居。我很聪明,所以知道很多事实”。1941年,13岁的吉姆仅坚持了三周,就在一个跟《圣经》有关的问题上输给了7岁的露西·杜斯金(Ruthie Duskin),后者后来成了节目的常客。90岁的沃森仍然对自己短暂的广播节目生涯耿耿于怀,“嗯,是的,她是个犹太小姑娘。她很漂亮、外向,非常适合问答节目,当然,她对《旧约全书》也了如指掌”。 [18] 然而,沃森能够把童年的失落和不受欢迎转化为一种力量。20世纪80年代,沃森告诉一位同事,他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报复”那些欺负他的人。 [19]

图8-2 1942年,参加《问答小子》的沃森,左起第二个
上完文法学校后,沃森和姐姐进入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学习,这是一所著名的进步学校(走读式),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创办。沃森家族的孩子们都在15岁时就被大学录取,他们较早入学还要多亏沃森父亲在欧柏林时的大学好友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的积极支持。哈钦斯本人也是个天才少年,1929年,年仅30岁的哈钦斯便开始执掌芝加哥大学,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20] 两年后的1931年,他提出了一个全国闻名的四年制通识学位培养计划,该计划以当时还很新颖的“西方文明正典”(Great Book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课程为基础。1942年,哈钦斯宣布了一项更具创新性的计划,让吉姆和贝蒂这种有天赋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得以提前进入大学学习,从而“摆脱高中单调的死记硬背式学习”。 [21] 由于自己的年轻和不成熟,沃森的家庭支持对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芝加哥大学的仿哥特式校园位于芝加哥海德公园附近,是在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和老约翰·洛克菲勒的慷慨支持下建立的。这所相对年轻的学校始建于1890年,拥有20世纪最杰出的师资队伍以及求知若渴、乐于奉献的学生群体。1943~1947年,沃森在芝加哥大学学习鸟类学,追寻着父亲对鸟类的热爱。他的一位老师保罗·韦斯(Paul Weiss)是胚胎学和无脊椎动物学的资深教授,他回忆说,沃森在本科阶段“对课堂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或者至少看起来如此);他从不做任何笔记——但在课程末的考试成绩却总是位于班级前列”。 [23] 2000年,沃森对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的收获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他发现,他的期末考试很少是对授课材料的记诵,而是集中在延伸材料的正确性上:“在罗伯特·哈钦斯的大学里,取得好成绩靠的是思想,而不是事实。” [24]
虽然沃森的成绩单上全是“B”,但他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三大知识前提对他以后的求学生涯起到了重要作用:直接查阅原始材料,而不是鹦鹉学舌地照搬他人的解释;建立一套理论,说明一组特定事实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不要死记硬背,而要学会思考,把不重要的东西从头脑中清理出去。1993年,就在双螺旋结构发现40周年之际,沃森更加直截了当地谈到了自己的大学时光:“你从来不会被规则所束缚,废话终究是废话。”
 他并不觉得自己比同班同学“生来更加聪明”;相反,他只是更愿意挑战跟科学精神不符的传统智慧和理论。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追求知识,而不是家庭背景或财富。即便在少年时代,他就决心不为追求财富、“琐碎”学问或“闲暇学问”而浪费哪怕片刻生命。
[25]
他并不觉得自己比同班同学“生来更加聪明”;相反,他只是更愿意挑战跟科学精神不符的传统智慧和理论。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追求知识,而不是家庭背景或财富。即便在少年时代,他就决心不为追求财富、“琐碎”学问或“闲暇学问”而浪费哪怕片刻生命。
[25]
每天晚上临睡前,沃森都会阅读当时流行的长短篇小说。对他的想象力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25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阿罗史密斯》( Arrowsmith ),这是美国第一部描述医学家生活、职业和想法的小说。 [26] 吉姆同样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炮制的华丽幻想着迷,比如《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 )、《公民凯恩》( Citizen Kane )等电影杰作,以及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和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等的喜剧精品。
1945年,17岁的沃森发现(并很快读完)了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我在生物图书馆发现了这本薄薄的的书,读完之后,我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沃森后来回忆道。“基因是生命的本质,这显然是一个比鸟类如何迁徙更重要的话题,我此前尚未充分了解过这个科学题目”。
 对沃森来说,正如对威尔金斯和克里克一样,薛定谔的书更多是提出而非回答“每一套完整的染色体如何包含「遗传」密码”之类的问题。
[27]
对沃森来说,正如对威尔金斯和克里克一样,薛定谔的书更多是提出而非回答“每一套完整的染色体如何包含「遗传」密码”之类的问题。
[27]
大四秋季学期,沃森选修了一门生理遗传学课程,授课人是群体遗传学(研究种群内部和种群之间的遗传变异和差异)的创始人之一苏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沃森在赖特教授身上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打算成为的榜样,他经常向父母夸耀赖特的“聪明才智”。 [28] 赖特向他介绍了奥斯瓦尔德·艾弗里于1944年开展的DNA实验研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让沃森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回答的问题:“基因是什么?……基因是如何复制的?……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29] 开始上了几周赖特的课后,沃森就放弃了鸟类学,开始学习遗传学。虽然他在19岁时(1947年春)就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但他知道,要想揭开基因的神秘面纱,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沃森首先需要进入一所研究生院,掌握科学方法,并最终获得学术界的联合许可证——博士学位。
沃森的博士项目申请被加州理工学院拒绝。后来,哈佛大学录取了他,但哈佛未能真正吸引这位年轻人,部分原因在于哈佛大学生物系仍以19世纪分类学而非实验为基础。更实际的原因在于,哈佛大学没有为他提供可用于支付学费、食宿费用的奖学金,让他无法支付搬到麻州剑桥的生活成本。他从附近的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了更为优渥的录取条件,该校为他提供了包括食宿在内的全额奖学金,供他攻读生物学研究生课程。印第安纳大学可不是一所普通的州立大学,这里是基因研究的沃土。赫尔曼·穆勒(Hermann J. Muller)领导了相关研究,他把果蝇暴露在不同剂量的辐射之下,并评估了果蝇基因组的突变情况,这项研究为他赢得了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图8-3 吉姆·沃森,毕业照,芝加哥大学,1947年
事实证明,另外两位教师也是吸引沃森前往印第安纳报到的重要因素。第一位是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特雷西·索内伯恩(Tracy Sonneborn),他在选修第一门生物学课程之前曾一直立志成为一名拉比。索内伯恩研究的是单细胞生物草履虫的遗传学。第二位是一名犹太医生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此人为逃离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和反犹主义盛行的意大利,先是逃到了法国,接着又逃到了美国。 [30] 他后来成为沃森一辈子的良师益友。与刘易斯虚构的马丁·阿罗史密斯一样,卢里亚研究的是噬菌体——攻击细菌的病毒。从本质上讲,它们是“裸基因,是生物体的精简版”。 [31] 噬菌体的存在是为了感染其他活细胞并在其中复制。由于噬菌体的复制速度很快,卢里亚可在几个小时的实验中就能追踪其遗传过程,而不用几天、几周或者更长时间。 [32]
研究生时期的沃森经常身穿轻便的长袍,喜欢嘲笑印第安纳校园(Hoosier campus)里的“男大学生”和“返校节皇后”的滑稽行为。在男学生还穿着大衣打领带上课的年代,沃森就已经习惯了不系领带的衬衫、破旧的短裤和没有鞋带的网球鞋。他尽量不理会拥挤的人潮,对同龄人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他对生物系许多成员的评价同样不友善。在竞争奖学金被拒后,他笨拙地向父母掩饰自己的失望:“他们这笔钱可为系里培养一个有着一流求知欲的人。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本校少之又少。”
 1947年秋,同样进入印第安纳大学的意大利移民医生雷纳托·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就是为数不多的一流人才之一。
[33]
沃森总喜欢向年长之人寻求建议并与之建立友谊,他和杜尔贝科在大学网球场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在实验室间隙去网球场打上一两轮网球。
1947年秋,同样进入印第安纳大学的意大利移民医生雷纳托·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就是为数不多的一流人才之一。
[33]
沃森总喜欢向年长之人寻求建议并与之建立友谊,他和杜尔贝科在大学网球场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在实验室间隙去网球场打上一两轮网球。
由于资历尚浅,沃森被分配到动物学大楼顶层的一间小办公室,“原来的电梯还是靠拉绳升降的”。在沃森所在办公室的下面几层,一位孤独的教授当时刚好转变了研究方向,从瘿蜂(gall wasps)及其进化的研究转向了人类性欲这个仍然禁忌的话题。此人唤作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他的工作让年轻的沃森感到厌烦,因为金赛的研究结果“统计学色彩太浓,与其说是色情,不如说令人作呕”。 [34]
在离开家前往印第安纳的第一年里,沃森继续观察鸟类,并沿着约而当街独自漫步——那里是“最令人向往的女生联谊会所在地,我能在那里看到比科学楼里漂亮得多的女孩”。他还喜欢在周六下午参加大学的足球比赛,跟其他两万名球迷一起坐在旧的纪念体育场里呐喊助威。 [35]
跟罗莎琳德一样,沃森每周都会给父母写信,讲述自己的学业和参与的各种活动。这些信件都被精心保存在冷泉港实验室的档案中,为我们了解沃森这一时期的生活提供了一手材料。在第一封家书中,沃森写道,他遇到了卢里亚,并获准选修后者的病毒学课程,尽管沃森还没有选修过细菌学入门的先修课程:“在我告诉他我的学习经历,以及我想成为一名遗传学家后,他便让我加入课程了。他是个意大利犹太人,拉蒙特·科尔(LaMont Cole)告诉我,他对待学生像对待‘狗’一样。然而,他无疑是学校里最优秀的人之一。他很年轻,大约30~35岁年纪,在病毒属方面(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做了深入研究。我应该从他身上多学点东西。”
[36]
在另一封信中,他把赫尔曼描述为“现代生物学的伟人之一”。
 但一周后,他又抱怨穆勒的课程(以及必要的实验课)“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困惑”。他的讲座就“更难了,但也因此更有趣”,然而,穆勒未能说服沃森跟随他“从事果蝇研究。能研究微生物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但一周后,他又抱怨穆勒的课程(以及必要的实验课)“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困惑”。他的讲座就“更难了,但也因此更有趣”,然而,穆勒未能说服沃森跟随他“从事果蝇研究。能研究微生物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图8-4 萨尔瓦多·卢里亚和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在冷泉港,1952年夏
沃森被索内伯恩和卢里亚深深吸引。他曾写道,索内伯恩的微生物遗传学很受欢迎,“研究生们「关于他的」闲谈反映了大家对他毫无保留的赞美,甚至是崇拜……。与此相反,许多学生都害怕卢里亚,因为他非常瞧不上犯错的人”。沃森的评价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傲慢,他说,“我没有看到传言中卢里亚对蠢人不友好的举止”。在印第安纳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沃森选择了卢里亚的噬菌体遗传学,而非索内伯恩的草履虫研究。 [37] 起初,他经历了所有学生经常都会遭遇的不安全感:他担心自己不够聪明,无法被老师的“核心圈子”接纳。但这位年轻人却以某种方式平息了自己的情绪,最终迎难而上,“我对噬菌体了解得越多”,沃森在2007年回忆道,“我就越被它们如何繁殖的奥秘所迷惑,甚至在秋季学期还未过半时,我就不打算在穆勒那完成学业了”。 [38]
沃森认为,通过果蝇研究基因已经过时了,噬菌体才是未来,这充分体现了他超前的意识和事业洞察。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了预测科学发展道路和下一件重大科学事件的超凡能力。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沃森选择了遗传学,而不是鸟类学和经典的描述生物学。此时,他作为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年级研究生,专注于微生物遗传学实验而不是果蝇研究。然而,与诺奖得主穆勒相比,他选择与名不见经传的卢里亚合作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因为穆勒的名气本身就能够帮他在随后的几年里获得一个学术职位。这是他在职业发展方面遇到的风险之一,这些风险会给沃森带来回报,但当时的沃森还想不到这些。
在沃森开展的第一个研究项目中,卢里亚要求沃森“看看被X射线灭活的噬菌体是否仍能基因重组,并产生缺乏亲代噬菌体中受损基因决定因子的可繁殖的重组后代”。 [39] 卢里亚用紫外线灭活噬菌体,然后让其感染大肠杆菌宿主细胞的方式证明了这个想法。接下来的三年里,沃森会把噬菌体菌落暴露在各种放射性诱变剂中,让它们经受考验。
沃森很快就发现,卢里亚对待任何人都“像对待狗一样”。“卢”是一位慷慨、乐于助人、做事有条理的教师,与学术圈中的许多差劲的学者不同,他会帮助学生成长。接下来的几年里,卢里亚为沃森打开了众多机会之门。1948年,他促成了沃森与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克斯·德尔布吕克的首次会面,后者被证明是沃森的知音和终生挚友。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是“噬菌体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们组虽然人数不多,却彻底改变了遗传学,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得诺贝尔奖。
 德尔布吕克很有人格魅力,性格很温和,吸引了众多年轻科学家加入他的研究团队;其他的先驱分子生物学家则把他捧上了神话的殿堂,说他是甘地和苏格拉底的结合体。
[40]
尽管他们的年龄和位置不同(德尔布吕克是一位42岁的著名科学家,而沃森当时还是年仅20岁的一年级研究生),但从他们在卢里亚的公寓里握手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用对方的名称呼彼此。正如沃森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所说的,“几乎从德尔布吕克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会失望。他没有拐弯抹角,言谈的意图也很清楚”。
[41]
德尔布吕克很有人格魅力,性格很温和,吸引了众多年轻科学家加入他的研究团队;其他的先驱分子生物学家则把他捧上了神话的殿堂,说他是甘地和苏格拉底的结合体。
[40]
尽管他们的年龄和位置不同(德尔布吕克是一位42岁的著名科学家,而沃森当时还是年仅20岁的一年级研究生),但从他们在卢里亚的公寓里握手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用对方的名称呼彼此。正如沃森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所说的,“几乎从德尔布吕克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会失望。他没有拐弯抹角,言谈的意图也很清楚”。
[41]

图8-5 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和噬菌体研究小组成员,1949年;从左到右依次为:让·魏格尔、奥勒·马洛、埃利·沃尔曼、冈特·施坦特、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和G.索利
1948年,卢里亚安排沃森在冷泉港实验室继续从事噬菌体研究,沃森喜欢在长岛湾游泳,还能使用附近的纽约市纪念医院(现在的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强力X光机。在给父母的信中,沃森讲述了他在国庆节周末前往纽约的经历,比如到布鲁克林弗拉特布什区的埃贝茨球场棒球公园的情形:
昨晚我们几个人去看了道奇队的夜场比赛……那场比赛可真精彩,球队的表现也达到了我的预期。从我短暂的停留来看,布鲁克林似乎是个非常拥挤和贫穷的城市,多数居民不是犹太人就是意大利人。粗浅地说,这里很不宜居。

到1949年,沃森已经穷尽了用X射线让噬菌体变异的所有可能,他开始撰写论文。德尔布吕克和卢里亚认为,沃森需要学习一些生物化学知识,以拓宽自己的科研范围。1949年秋,在芝加哥举行的噬菌体小组会议休息期间,二人与哥本哈根大学的赫尔曼·卡尔卡尔(Herman·Kalckar)坐下来商量了让沃森到卡尔卡尔的实验室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的事宜。
 在卢里亚的指导下,沃森撰写了自己第一份基金申请书,旨在获得在哥本哈根的工资和生活费用。与多数在申请项目过程中煎熬的学生一样,沃森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充满了对大概率被拒的可能性的焦虑。
在卢里亚的指导下,沃森撰写了自己第一份基金申请书,旨在获得在哥本哈根的工资和生活费用。与多数在申请项目过程中煎熬的学生一样,沃森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充满了对大概率被拒的可能性的焦虑。

1950年3月12日,他应邀参加了由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管理的为期两年的默克奖学金(Merck Fellowship)面试。在纽约市充满艺术气息的纽约客酒店(Hotel New Yorker)的主宴会厅里,几位白发苍苍、自视甚高的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坐在一张长桌旁。候选人都是争强好胜、渴望成功的男性,他们紧张地坐在大厅里;每隔一小时,就有一位委员打开宴会厅的大门,邀请下一位候选人进入,就其研究项目的优劣势接受答辩。两周后,委员会给沃森寄来了一封挂号信,通知他已经获得了默克奖学金。
 在写给为他感到自豪的父母的信中,他腼腆地承认:“由此看来,我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有了经济资助和眼下新的起点,他得以把精力放在更多琐碎的事情上,比如申请护照、购买合适的衣服和安排旅行等。
在写给为他感到自豪的父母的信中,他腼腆地承认:“由此看来,我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有了经济资助和眼下新的起点,他得以把精力放在更多琐碎的事情上,比如申请护照、购买合适的衣服和安排旅行等。

1950年9月11日清晨,沃森乘坐“斯德哥尔摩号”(MS Stockholm,瑞典-美国航线上最小的船只,也因此在航程中多有磨难)抵达丹麦,一路上他因为航程颠簸而晕船(六年后的1956年,斯德哥尔摩号与命途多舛的意大利邮轮安德里亚·多利亚号相撞)。整个航程中,沃森一直在服用德拉马明(Dramamine)来抵御船体不断颠簸造成的呕吐和不适。
 在抵达丹麦的第一天,他就给父母写信说哥本哈根“太棒了”(Wonderful),比弗兰克·卢瑟“同名”的热门歌曲《美丽的哥本哈根》(Wonderful Copenhagen)还早了一年。他在信的结尾谈到了自己的观感:“出乎意料的是,丹麦姑娘是我见过最有魅力的了。一般来说,她们的脸蛋都不难看——这跟美国的多数女孩形成了鲜明对比。”
[42]
在抵达丹麦的第一天,他就给父母写信说哥本哈根“太棒了”(Wonderful),比弗兰克·卢瑟“同名”的热门歌曲《美丽的哥本哈根》(Wonderful Copenhagen)还早了一年。他在信的结尾谈到了自己的观感:“出乎意料的是,丹麦姑娘是我见过最有魅力的了。一般来说,她们的脸蛋都不难看——这跟美国的多数女孩形成了鲜明对比。”
[42]
两天后的9月13日,从舟车劳顿中缓过劲来的沃森前往卡尔卡尔负责的细胞生理学研究所报到上班。卡尔卡尔是在纳粹入侵丹麦之前离开欧洲的犹太人,战时多数时间他曾辗转供职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和纽约公共卫生研究所。战后,卡尔卡尔回到丹麦,重新加入科研重镇哥本哈根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的王是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他因为“原子结构和原子辐射的研究”获得了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卡尔卡尔与玻尔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卡尔卡尔的弟弟弗里茨(Fritz,1938年猝死,年仅27岁)曾在玻尔门下学习。
[43]
卡尔卡尔与玻尔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卡尔卡尔的弟弟弗里茨(Fritz,1938年猝死,年仅27岁)曾在玻尔门下学习。
[43]
卡尔卡尔研究所的前研究员、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伯格(Paul Berg)形容他是“一个梦想家,经常为自相矛盾的观察结果寻求新颖的解释”。在科学上,他“是最早提出高能键概念的人之一,高能键是氧化代谢过程中捕获和储存自由能的形式”。对那些不是很了解这些关键生物化学原理的人来说,回想一下以ATP(三磷酸腺苷)的分子形式传递的细胞动力源可能会有所帮助。 [44] 卡尔卡尔才华横溢,“充满活力,爱开玩笑”。他常用阿卡韦特酒或樱桃海灵利口酒来庆祝自己或组上的研究人员做出的每一个大小发现。他的英语和母语丹麦语语法都有点蹩脚,总是从“似懂非懂”的语句开始,几乎总会走向难以理解的地步。 [45] 卡尔卡尔的许多同事都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终究没有获奖,因为他的“个性和对广泛的研究兴趣让他无法专注于一两个问题”。 [46]
1938年,德尔布吕克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期间给卡尔卡尔介绍了噬菌体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47] 12年后,卡尔卡尔萌生了成立自己的噬菌体研究小组的计划,并招募沃森和德尔布吕克的另一位门生(protégé)冈瑟·斯滕特(Gunther Stent)到其研究所工作。然而,就在这两位年轻科学家抵达哥本哈根时,卡尔卡尔却改变了主意,转而要求沃森专注于“核苷酸的新陈代谢”研究。 [48] 沃森既不具备也不想掌握如此精细的生物化学研究的精细操作技巧,随即认为这个项目不过死路一条。正如克里克后来在为一本名为《松动的螺丝》( The Loose Screw )的书酝酿开场白时所写的那样,他希望这本书能纠正沃森在《双螺旋》中的夸张形容,沃森在其中说道:“吉姆的手总是很笨拙。只需看看他剥橘子的样子就知道了。” [49]
9月19日,就在他们获得研究资金一周后,卡尔卡尔派遣斯滕特和沃森前往国立血清研究所,他们在这里开始与此前在加州理工学院德尔布吕克噬菌体实验室学习的另一位学生奥勒·马洛(Ole Maaløe)合作。
 沃森和马洛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他们在噬菌体的DNA中加入放射性示踪剂,以世代连续跟踪病毒,从而测量前代传递给后代的放射性DNA数值。
[50]
沃森和马洛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他们在噬菌体的DNA中加入放射性示踪剂,以世代连续跟踪病毒,从而测量前代传递给后代的放射性DNA数值。
[50]
沃森一开始并不喜欢哥本哈根大学,曾给家里写信诉说自己在那里的无聊和不快。在其中一封信中,他描述了自己花350克朗(约50美元)购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骑着它在两个研究所之间骑行1.5英里的独特乐趣。
 然而,这不过是他为数不多的入乡随俗之一。他唯一的社交活动便是与那些英语说得不错的人交往。2018年,他在回忆当初在哥本哈根的岁月时说,“我从未想过要学习丹麦语。我对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不感兴趣。当时我只对DNA感兴趣”。
然而,这不过是他为数不多的入乡随俗之一。他唯一的社交活动便是与那些英语说得不错的人交往。2018年,他在回忆当初在哥本哈根的岁月时说,“我从未想过要学习丹麦语。我对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不感兴趣。当时我只对DNA感兴趣”。

1951年1月14日,沃森在给父母的信中谈到了“阴雨连绵”的“悲惨”气候。他渴望天气好转,这样就可以恢复每天骑自行车和散步的习惯了,“除了工作和阅读,几乎无事可做。最近几天,我一直在阅读「约翰」斯坦贝克的一些短篇小说——《小红马》(
The Red Pony
)和《长谷地》(
The Long Valley
)等,非常享受”。
 其间,他还在电影中找到了一些额外的安慰。一天晚上,他和马洛一起观看了1950年的经典黑色电影《日落大道》。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饰演的怪异默片明星诺玛·德斯蒙德(Norma Desmond)和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干脆利落的导演手法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在观影时,“我很容易就能代入进去,就感觉自己回到了加利福尼亚”。
[51]
其间,他还在电影中找到了一些额外的安慰。一天晚上,他和马洛一起观看了1950年的经典黑色电影《日落大道》。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饰演的怪异默片明星诺玛·德斯蒙德(Norma Desmond)和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干脆利落的导演手法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在观影时,“我很容易就能代入进去,就感觉自己回到了加利福尼亚”。
[51]

图8-6 吉姆·沃森和贝蒂·沃森在哥本哈根,1951年
幸运的是,沃森与马洛的合作产出了“足够的数据,足以让他们在著名期刊发表文章了,而且按照一般的标准,「他」知道自己可以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不用工作,也不会被判定为没有成果”。 [52] 他深信生物化学不适合自己,于是耗费了很多时间向其他研究员抱怨卡尔卡尔的研究计划有些隔靴搔痒,并对实验室的其他人说:“在「了解」DNA的结构之前,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基因是如何复制的。” [53]
不过,沃森在家书中谈到了卡尔卡尔对他不遗余力的指导。1950年11月初,卡尔卡尔带着沃森参加了丹麦皇家学会(丹麦版的国家科学院)举行的一次著名科学聚会。皇家学会坐落在属于嘉士伯啤酒基金会的一栋“雄伟”大楼里,会员由“一群非常高贵的人组成,他们多数都在55岁以上……「一」进入大楼,就给人一种每周聚会的男士俱乐部印象”。学会主席是玻尔,“参加会议的特邀访客非常少——仅有当晚的演讲者可以且仅能带一位客人。卡尔卡尔当晚要发表演讲,并带我一起前往。我一辈子都没有感觉如此年轻过。尽管有这种年纪代差,我还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在聚会上,沃森了解到丹麦科学界主要由富有的嘉士伯啤酒基金会资助。他以年轻人的口吻兴奋地说道:“该基金会的负责人由皇家学会选举产生,因此事实上哥本哈根最大的产业受科学家的掌控。”
 皇家学会并不是嘉士伯啤酒基金会慷慨资助的唯一受益者。玻尔及其家人就住在嘉士伯豪宅里,一座意大利高级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位于啤酒厂厂区,沃森形容它是一座“微型宫殿”和博物馆的结合体,里面摆满了各种精美的艺术品、家具和植物。这座宫殿由酿酒厂的主人雅各布森(J. C. Jacobsen)建造,1887年雅各布森去世后,他把这座宫殿留给了父母,正如沃森所描述的,“丹麦最杰出的人都住在这里,玻尔将一直住在这里直到去世。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20年”。
皇家学会并不是嘉士伯啤酒基金会慷慨资助的唯一受益者。玻尔及其家人就住在嘉士伯豪宅里,一座意大利高级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位于啤酒厂厂区,沃森形容它是一座“微型宫殿”和博物馆的结合体,里面摆满了各种精美的艺术品、家具和植物。这座宫殿由酿酒厂的主人雅各布森(J. C. Jacobsen)建造,1887年雅各布森去世后,他把这座宫殿留给了父母,正如沃森所描述的,“丹麦最杰出的人都住在这里,玻尔将一直住在这里直到去世。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20年”。

皇家学会会议结束后不久,沃森“被告知玻尔要来”参加他下周在哥本哈根大学举办的一次讲座。可以想象,沃森和父母在得知这个消息时会是多么自豪。沃森父母当时并不知情,但那天下午的确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提出原子结构的科学家来聆听提出DNA结构理论的科学家的讲座。讲座结束后,沃森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谦虚道,“我非常认真地准备要讲的内容。我想我讲的还不错,玻尔似乎很感兴趣,还参与了热烈的讨论”。在信中,他用同样多的篇幅大谈特谈他在那个星期看的一部电影:《鬼魂西行》(
The Ghost Goes West
),一部1935年的英国喜剧片,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执导,罗伯特·多纳特(Robert Donat)主演。他认为这是一部“极出色的电影,「它」创造了一种令人愉悦的精神”。


图8-7 “自行车之城”哥本哈根
12月的头两周里,沃森又开始向父母发牢骚了。这次,他抱怨的是哥本哈根的圣诞节过于商业化,各种商店的巨大橱窗里摆放的都是装饰着彩条的圣诞树。
 12月21日,沃森的情绪突然180度大转弯,他压抑着自己的兴奋劲给家里写信说,“卡尔卡尔要去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动物学站,时间是4月、5月和6月。我可能会跟他一同前往。应该还蛮有趣的。我们会买一辆车开到那里”。
12月21日,沃森的情绪突然180度大转弯,他压抑着自己的兴奋劲给家里写信说,“卡尔卡尔要去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动物学站,时间是4月、5月和6月。我可能会跟他一同前往。应该还蛮有趣的。我们会买一辆车开到那里”。

这封简短的信不仅洋溢着兴奋之情,而且还预示了沃森一生中最重要的知识之旅。
[1] Carl Sandburg,“Chicago Poems,” Poetry 3,no. 4 (March 1914):191-192.
[2] 本章第一句的完整版是:“我是美国人,出生于芝加哥,按照我自学的自由方式做事,并将以我自己的方式创造纪录:第一个敲门,第一个被录取。”Saul Bellow,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New York:Viking,1953),1.
[3] James D. 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Lessons from a Life in Science (New York:Knopf,2007),4;author interview with James D. Watson (no. 1),July 23,2018.
[4] 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5.
[5] 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5. 每年都有二十多种莺迁徙到芝加哥杰克逊公园沃森家附近,其中最著名的是柯克兰莺。James D. Watson (Sr.),George Porter Lewis,Nathan F. Leopold,Jr., Spring Migration Notes of the Chicago Area ,privately printed pamphlet,1920,JDWP.
[6]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 ,translated by Thomas Common (New York:Modern Library/Boni and Liveright,1917). The novel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y in four parts from 1883 to 1885. 该书标题现更多被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Thus Spoke Zarathustra )。
[7] James D. Watson,ed., Father to Son:Truth,Reason and Decency (Cold Spring Harbor,NY: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2014),53-87;Simon Baatz, For the Thrill of It:Leopold,Loeb,and the Murder That Shocked Jazz Age Chicago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9).
[8] Watson,ed., Father to Son ,title page.
[9] 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6.
[10] Victor K. McElheny, Watson and DNA:Making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Perseus,2003),7.
[11] James D. Watson, Genes,Girls and Gamow:After the Double Helix (New York:Knopf,2002),118.
[12] Carolyn Hong,“Focus:Newsmakers:How Beautiful It Was,This Thing Called DNA,” New Straits Times (Malaysia),December 1,1995,15.
[13] David Ewing Duncan,“Discover Magazine Interview:Geneticist,James Watson,” Discover ,July 1,2003,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03/jul/featdialogue.
[14] 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7.
[15] McElheny, Watson and DNA ,6-7.
[16] Lee Edson,“Says Nobelist James (Double Helix) Watson:‘To Hell With Being Discovered When You’re Dea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18,1968,26,27,31,34.
[17] 考恩后来创建了《6.4万美元有奖竞猜》电视节目,并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的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国之音的总监。1964年至1965年,他的妻子宝琳是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的主要民权活动家。1976年,他们双双死于纽约市东六十九街15号韦斯特伯里酒店公寓的一场大火,起火原因是“吸烟不慎”;“Louis Cowan,Killed with Wife in a Fire;Created Quiz Show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1976,1.最初的赞助商是迈尔斯实验室生产的“阿卡塞尔兹”;后来,该节目由阿卡塞尔兹和迈尔斯实验室的另一种产品“每日”维生素片共同赞助。节目的问答主持人是乔·凯利(Joe Kelly)。See also Ruth Duskin Feldman,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Quiz Kids:Perils and Profits of Growing Up Gifted (Chicago:Chicago Review Press,1982),10.
[18] Author interview with James D. Watson (no. 4),July 26,2018. See also Larry Thompson,“The Man Behind the Double Helix:Gene-Buster James Watson Moves on to Biology’s Biggest Challenge,Mapping Heredity,”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2,1989,Z12;Feldman,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Quiz Kids.
[19] McElheny, Watson and DNA ,8.
[20] “Heads University at 30,Dean Hutchins of Yale Named U. of C. Chief,Youngest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 Chicago Daily Tribune ,April 26,1929,1.
[21] Nathaniel Comfort,“‘The Spirit of the New Biology’:Jim Watson and the Nobel Prize,” in Christie’s auction catalogue, Dr. James Watson’s Nobel Medal and Related Papers:Thursday 4 December 2014 (New York:Christie’s,2014),11-19;quote is on 13.
[22] McElheny, Watson and DNA ,7.
[23] Robert Olby, The Path to the Double Helix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4),297. Olby interviewed Weiss for his book on April 25,1973.
[24] Interview with James D. Watson on Talk of the Nation/Science Friday ,NPR,June 2,2000,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74946. See also James D. Watson,“Values from a Chicago Upbringing,”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758 (1995):194-197,reprinted in James D. Watson, A Passion for DNA:Genes,Genomes and Society (Cold Spring Harbor,NY: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2001),3-5;相关内容改编自1993年10月14日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纽约科学院和牛津大学格林学院主办的“双螺旋:40年的前瞻与展望”会议上发表的餐后演讲。See also McElheny, Watson and DNA ,14-16.
[25] 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49.
[26] Sinclair Lewis, Arrowsmith (New York:Harcourt,Brace,1925);Howard Markel,“Prescribing Arrowsmith,”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September 24,2000,D8.
[27] Erwin Schrödinger, What Is Life?: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with Mind and Matter and Autobiographical Sketch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21.
[28] Letter from James Watson to his parents,November 21,1947,WFAT,“Letters to Family,Bloomington Sept. 1947-May 1948.” See also William Provine, Sewall Wright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29] James D. Watson,“Winding Your Way Through DNA,” video of symposiu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September 25,1992 (Cold Spring Harbor,NY: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1992);quote appears in McElheny, Watson and DNA ,16.
[30] Salvador Luria, A Slot Machine,a Broken Test Tube: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3),41-43.
[31] Thomas Hager, Force of Nature:The Life of Linus Pauling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5),409.
[32] McElheny, Watson and DNA ,17-29;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38-54;William C. Summers,“How Bacteriophage Came to Be Used by the Phage Group,”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6,no. 2 (1993):255-267.
[33] Howard Markel,“Happy Birthday,Renato Dulbecco,Cancer Researcher Extraordinaire,” PBS NewsHour ,February 22,2014,https://www.pbs.org/newshour/health/happy-birthday-renato-dulbecco-cancer-researcher-extraordinaire.
[34] 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40-41;James H. Jones, Alfred Kinsey:A Public/Private Life (New York:Norton,1997);Jonathan Gathorne-Hardy, Sex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A Life of Alfred C. Kinse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
[35] 印第安纳州队在1947赛季的表现非常糟糕;该队在九大联盟中与爱荷华队并列第六名,九大联盟在1946年因芝加哥大学退出而丧失了其标志性的“十大”名号。芝加哥大学于1939年终止了橄榄球项目。尽管印第安纳篮球队在1947-1948赛季只获得了第八名的成绩,但吉姆更喜欢印第安纳篮球队的比赛。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45;几年后,沃森在哥本哈根进行博士后研究时,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我怀念布卢明顿的篮球比赛”;letter from James D. Watson to his parents,December 13,1950,WFAT,“Letters to Family,Copenhagen,Fall-Dec. 1950”。
[36] Letter from James D. Watson to his parents,undated,fall 1947,WFAT,“Letters to Family,Bloomington Sept. 1947-May 1948.”拉蒙特·科尔是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他是沃森1947-1948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之一。See Gregory E. Blomquist,“Population Regulation and the Life History Studies of LaMont Col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29,no. 4 (2007):495-516.
[37] James D. Watson,“Growing Up in the Phage Group,” in John Cairns,Gunther S. Stent,and James D. Watson,eds., Phage and the Origins of Molecular Biology (1966;Cold Spring Harbor,NY: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2007),pp. 239-245,quote is on 239.(此文也见:Watson, A Passion for DNA ,7-15.) See also James D. Watson,“Lectures on Microbial Genetics-Sonneborn (Fall Term,1948),” JDWP,JDW/2/6/1/5.
[38] 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42,45.
[39] Watson, Avoid Boring People ,46.
[40] John Kendrew,“How Molecular Biology Started,” and Gunther Stent,“That Was the Molecular Biology That Was,” in Cairns,Stent,and Watson,eds., Phage and the Origins of Molecular Biology ,343-347,348-362.
[41] John Kendrew,“How Molecular Biology Started,” and Gunther Stent,“That Was the Molecular Biology That Was,” in Cairns,Stent,and Watson,eds., Phage and the Origins of Molecular Biology ,343-347,348-362.
[42] Letter from James D. Watson to his parents,September 13,1950,WFAT,“Letters to Family,Copenhagen,September 15,1950-October 1,1951.” The music and lyrics of “Wonderful Copenhagen” were written by Frank Loesser in 195. (New York:Frank Music Corp,September 24,1951);the song first appeared in the 1952 film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starring Danny Kaye;https://frankloesser.com/library/wonderful-copenhagen/.
[43] Fritz Kalckar obituary, Nature 141,no. 3564 (February 19,1938):319;Herman M. Kalckar,“40 Years of Biological Research:From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to energy requiring transport regulation,” 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 60 (1991):1-37. 弗里茨·卡尔卡尔去世时正在研究核反应理论。《自然》杂志的讣告称他死于心力衰竭,但赫尔曼在本文引用的回忆录中指出,他的弟弟患有癫痫,在那个没有有效药物治疗癫痫发作的时代,他是在一次顽固性癫痫发作或癫痫状态中去世的。为了纪念弗里茨,赫尔曼·卡尔卡尔将他关于肾脏皮层氧化磷酸化的博士论文献给了弗里茨。
[44] Paul Berg,“Moments of Discovery:My Favorite Experiments,”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278,no. 42 (October 17,2003):40417-40424,doi:10.1074/jbc.X300004200;quotes are on 40419 and 40420. 伯格在核酸化学和DNA重组方面的研究成果广为人知。他还是1975年阿西洛马会议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会议讨论了新兴生物技术领域的潜在危害和伦理问题。
[45] Berg,“Moments of Discovery,” 40420-40421;John H. Exton, Crucible of Science:The Story of the Cori Labora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21-28. See also Kalckar,“40 Years of Biological Research”;“Herman Kalckar,83,Metabolism Authority,” New York Times May 22,1991,D25;James D. Watson, The Double Helix: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edited by Gunther Stent (New York:Norton,1980),17-21.
[46] Exton, Crucible of Science ,28.
[47] Watson, The Double Helix ,19.
[48] Watson, The Double Helix ,18.
[49] Francis Crick,“The Double Helix:A Personal View,” Nature 248,no. 5451 (April 26,1974):766-769.
[50] Letter from James D. Watson to his parents,September 16,1950,WFAT,“Letters to Family,Copenhagen,September 15,1950-October 1,1951.” See also Eugene Goldwasser, A Bloody Long Journey:Erythropoietin (Epo) and the Person Who Isolated It (Bloomington,IN:Xlibris,2011),55-60. Goldwasser later became well-known for identifying erythropoietin,the hormone manufactured by the kidney that,upon sensing cellular hypoxia or lack of oxygen,stimulates the production of red blood cells.
[51] Letter from James D. Watson to Elizabeth Watson,February 4,1951,WFAT,“Letters to Family,Copenhagen,September 15,1950-October 1,1951.” Sunset Boulevard (1950) was directed by Billy Wilder,screenplay by Billy Wilder and Charles Brackett,and starred Gloria Swanson,William Holden,and Erich von Stroheim.
[52] Watson, The Double Helix ,21.
[53] Goldwasser, A Bloody Long Journey ,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