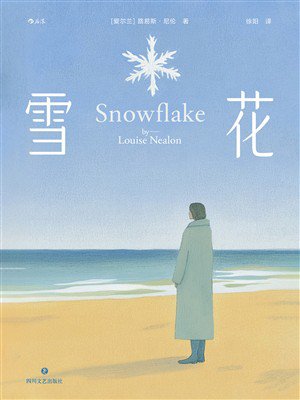水做梦的地方
妈妈死缠烂打,詹姆斯只好同意带我们去海滩。刮着风,下着雨,湿漉漉的一天。大晴天,妈妈绝不会起兴去海滩。天气越糟,她下海游泳的冲动就越强烈。这个想法是宙斯用闪电劈进她脑袋里的,他的雷声怂恿着她。今天的天气既疯狂到让妈妈想去,也安全到詹姆斯同意带她去。
“左转。往左!”妈妈说着替詹姆斯打开转向指示灯。
“你说我另一个左边吗?也就是我的右边?”
“不,左边!”
“梅芙,你想开吗?”
妈妈把詹姆斯的手从她膝盖上挪走。眼下他们的情绪都很坏。妈妈和詹姆斯只会因为“紫罗兰”发生争执。“紫罗兰”是辆九八款紫色丰田小福星。有一天,比利去找一个人谈买狗
 的事情,带回来的却是“紫罗兰”。每年爱尔兰全国车检,妈妈都要为她祷告。她每次都能勉强通过,詹姆斯手持证书归来,像个自豪的父亲那样拍拍她的引擎盖,眉开眼笑。妈妈喜欢“紫罗兰”,只是不喜欢开着她跑而已。
的事情,带回来的却是“紫罗兰”。每年爱尔兰全国车检,妈妈都要为她祷告。她每次都能勉强通过,詹姆斯手持证书归来,像个自豪的父亲那样拍拍她的引擎盖,眉开眼笑。妈妈喜欢“紫罗兰”,只是不喜欢开着她跑而已。
詹姆斯的狗雅各布开车都比妈妈强。詹姆斯开车时,雅各布坐在他腿上,开心地伸着舌头哼哧,脑袋探出车窗。他傻到家了。按理说,他可是牧羊犬。他还是个小狗崽的时候,詹姆斯就成天唠叨他长大后会成为怎样的好帮手,但长大之后,他只是变得更胖,更懒。如果雅各布是人,他可以当男模——你懂的,那种靠脸吃饭的。糟糕的伙食和健身计划并没有毁掉他的魅力,他的基因非常好。他有点哈士奇血统,毛发浓密发亮——黑白相间,略带棕色,他还有一双大大的金色眼睛。
可我的天啊,他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有一次,他大半夜的把奶牛从地里赶出去了,牛吓得半死,撞破两处电围栏,最后在墓地里踩来踩去,在墓碑和鲜花上到处拉屎。比利半夜把我叫醒,说奶牛闯进墓地了,我可以想象出小母牛如何努力地把屁股塞进侧门,像卡在十字转门的胖夫人一样尴尬地瞪眼。尽管如此,你还是不能当着詹姆斯的面抱怨雅各布。他会像护着妈妈那样护着雅各布的。
在我的印象里,詹姆斯一直在教妈妈开车。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说,妈妈知道怎么开车。她很懂车,这同一些人痴迷“世界大战”不无相似之处——可以抽象地探讨,却不见得乐意身在其中。打开引擎盖,她能说出每个零部件和它们的功用。可让她点火,她就会瞬间凝固。她会开启自我防御模式。詹姆斯称之为“非理性恐惧”。她却坚称自己是理性的。他们时不时就会为此争论。
“梅芙,要是你看不惯我开车,为什么不自己来开?”
“你不明白。”
“为什么我能开你就不能?”
“你能看清东西之间的界线,我不行。朝挡风玻璃外面望,我看不见把两样东西分隔开的线条。东西在我脑袋里糊成一团。”
❅❅❅
妈妈自己只开过一次,是去弥撒。两百米而已,但对她来说却是光辉时刻。她把车停在教堂外,给了詹姆斯一个大大的拥抱。詹姆斯吻了吻她的头顶。
弥撒过后,她朝我们家大门开时转弯打过头了,车撞到墙上,正好撞在那个十九岁男孩死去的地方。我们把“紫罗兰”送到修理处,她蹦蹦跳跳地回来了,但妈妈却没有恢复。从那以后,詹姆斯不再教她开车。
❅❅❅
一到停车场我就胸口一沉。我讨厌海滩活动。一想到沙子夹在脚趾间我就发怵。妈妈却要在沙子里打滚。还把它撒到自己头上。从海滩回来几天过后,她还会把手伸进裤子里,因为发现屁股缝儿里藏着沙子而微笑。
唯有妈妈对大海的热情才能压过她在屁股缝儿里发现沙子的热情。她总会没完没了地说,人体是多么神奇,居然可以适应海洋的水温。水一拍到她的脚趾,她的肺就会苏醒。潜入水中时,她念起大海不同分层的名字。“日光层,暮光层,午夜层,深渊……”她等到自己做好准备,就把脑袋泡进水中低语:“冬之冥后普西芬尼
 的超深渊。”
的超深渊。”
❅❅❅
妈妈说她喜欢在大海里游泳,但实际上她根本不游。她不会。她只是站在海里。詹姆斯犯了个错——去年圣诞节送她游泳课当礼物。她只去了一次就生着闷气回来了,詹姆斯努力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她说教练不喜欢她。
“我们还要在头上戴安全套——那种把头发从我头皮上扯开的橡胶玩意儿。水是死的。每个人都盯着我看。”
“那下次就别去了。”我说。
“你觉得詹姆斯能理解吗?”
“当然。”我说,尽管我希望他无法理解。
我希望他们为这事吵起来。但詹姆斯当然可以理解。他甚至因为她讨厌其他人看自己穿泳装而觉得她愈发可爱。那又是另一件事了。为了上游泳课,妈妈要买泳装。她去海里游泳,是赤身裸体地进去,就像出生时那样。
❅❅❅
詹姆斯不停地劝我跟他们一起下水,但和妈妈一起裸泳想来还是太可怕了。我努力不看她脱衣,却依然忍不住去看她那平坦的小腹、脊椎底部的腰窝、后背的曲线还有异常活泼的胸部。她阴毛不多——和她胳膊上的汗毛一样纤细金黄。
詹姆斯不会光着身子下水。总之下水前不会。至于进去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不知道她会不会把他的泳裤扒了。他们接吻。妈妈用自己包裹他。他很喜欢那样。
❅❅❅
我是来海滩捡贝壳的。我们家窗台上到处是各种海滩上的战利品——鸟蛤、竹蛏、扇贝、蛤蜊、蛾螺、玉黍螺……浴室里有一碗宝贝贝壳。妈妈把最好的贝壳留给“圣体龛”窗台——条纹帘蛤、长鼻螺,像小小瓷蝴蝶一样张开翅膀的樱蛤。我从“圣体龛”的窗台上偷过一只鹈足螺放在自己枕头底下。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发现它不见了。枕头下空留细细的沙痕。我想象着是牙仙
 把它从我合拢的拳头里撬走还回“圣体龛”的。
把它从我合拢的拳头里撬走还回“圣体龛”的。
我们曾捡到过一只女王凤凰螺。妈妈说,如果我把它贴在耳边,就能听到海浪的声音。然后她告诉我,其实我真正听到的是自己的脉搏——我身体里的那片海。
❅❅❅
潮已退去。妈妈和詹姆斯所站之处海水只没到膝盖,但浪花依然很有冲击力——那是一堵堵崩塌的墙,企图将他们撞倒。我降低视线,开始在一片零碎中翻拣。有些贝壳和蛋壳一样单薄,有些和牙齿一样厚实。我跳过竹蛏、贻贝和鸟蛤——它们只是大海的小卒子而已。换作小时候,我这会儿肯定已经大丰收了——每只鸟蛤都是宝——不过我现在更有鉴赏家的做派,只弯腰查看最稀奇的。有些根本就不是贝壳。啤酒瓶的玻璃碎片被大海收留,那些平平常常的棱角被洗得干净而奇异。某次我觉得捡到了一块骨头。我不敢拿给比利看,生怕他跟我说那是某种更平常的东西。
❅❅❅
我在想那个弥撒时站在后面的男孩。他总是一直站着。他那么酷,才不会坐下呢。他更喜欢站着晃悠,以此表明自己的不可知论。弥撒时我和他调情。准确地说,试着调情。我偷偷瞥他。每当四目相接,我就会发慌,然后移开视线。这样真是又蠢又吓人。说实话,很尴尬。
中学的时候我们是同校同班的,但我从不跟他说话。我现在依然会下意识地回避他。每次被迫和他互动,我都担心会打破我们之间的某种东西,可以说我害怕我会擅自闯入现实。就连迷恋他都缺乏原创性——人人都迷恋他。所以我生他的气,因为他将我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哪怕我们并没有像样地聊过天。
从前,我们每天早晨都会在储物柜旁把书包靠在一起。一想到它们整天都躺在彼此身边我就高兴。这令人感到慰藉。毕业了,我很是想念。比利说把升学考试叫作“离开
 ”太伤感了。从学校毕业是一件奇怪的伤心事。
”太伤感了。从学校毕业是一件奇怪的伤心事。
我最怀念的是那个没和我说过话的男孩。我对他的幻想仅停留于校园之内,那里像一座日渐被侵蚀的记忆陵墓。能让我重温这个白日梦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弥撒上见到他,把他的形象转移到海滩这类地方来。我望着妈妈和詹姆斯,努力想象他和我。在现实生活中跟他说话会让我觉得难以承受,此刻我却可以在想象中为他全裸。我在大海里吻他。
我俯身从沙子里拔出一根白色的羽毛。它很小,毛茸茸的。我把它包在一张纸巾里,放进口袋,就像私藏了一个秘密。
❅❅❅
我在矮石墙上垫一块毛巾坐下,膝盖抱在胸前。风把夹克衫的连衣帽吸到脑袋一侧,感觉像被兜在帐篷里。妈妈和詹姆斯出水,瑟瑟发抖地去拿毛巾。詹姆斯冲向汽车拿东西。
“感觉怎么样?”我问。
“太棒了。”妈妈答道。
“真他妈的冷。”詹姆斯喊道。
他去后备厢取出大购物袋。里面有包在锡纸里的三角火腿三明治,还有奶酪洋葱味的泰托薯片
 、一只茶壶、一包巧克力消化饼干、两瓶热水。他在茶壶里倒满水,把妈妈的羊毛帽盖在顶上,像个保温茶壶套。
、一只茶壶、一包巧克力消化饼干、两瓶热水。他在茶壶里倒满水,把妈妈的羊毛帽盖在顶上,像个保温茶壶套。
我将视线从正在穿衣的妈妈身上移开,把夹在我三明治里的薯片压碎。她拉起毛茸茸的夹克。最后戴上这顶被茶壶烘暖的羊毛帽。
“黛布丝,这儿有好贝壳吗?”詹姆斯问。
“还行。”
“我发现了一些不错的疣荔枝螺。”妈妈说。
“可它们都一副备受摧残的样子。”
“还记得我因为你那篇海滩故事被叫到学校去的那次吗?”妈妈问。
“嗯。”我很惊讶,她居然还记得。我很想知道她会怎样添油加醋地讲给詹姆斯听。
❅❅❅
大概是我八岁那年,妈妈发现我在海滩上抓了一把贝壳。我问她能不能把它们留下,她说如果我能记住它们的名字就可以。
“名字是有魔力的,”她说,“给东西取名字很重要——否则它们就不存在。你能想象我叫你菲奥娜或路易丝吗?”我摇摇头,八岁的我一想到存在其他的“我”就觉得恐怖。
我们从海滩回来后的那一周,妈妈被叫到学校里去了,老师要跟她谈谈我写的一个故事,故事的题目叫“我的暑假”。在我暖心的旅程中,我成天在海滩上收集和鉴别贝壳,直到妈妈喊我回家。每次妈妈都会用不同的名字呼唤我,比如“菲奥娜”“路易丝”什么的,喊到别的名字时我就分身两半,被叫错的那一半走进大海。故事的结尾,死亡率奇高。老师指着页面上的一个词让我念。“自杀。”我说,因为自己知道如此艰深的词而自豪。
妈妈和老师见完面,回家时面带微笑。她为我俩各泡了一杯茶,像跟成年人说话那样和我探讨故事。
“那些女孩们——她们应该走进海洋,”她说,“而不是大海。”
我点点头。
“海洋,”她又说一遍,“别叫它大海——太俗了。用恰当的名字。叫它海洋。”
“海洋。”我试着说。
“好多了不是吗?你可以在嘴里尝到它的声音。”
❅❅❅
那天夜里,她在我枕头下留了一封信,用兴奋的潦草字迹书就。文字我早已熟读成诵,尽管不太确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海洋。大声说出来。你可以在嘴里尝到它的声音。海洋(ocean)这个词来自希腊海神俄刻阿诺斯(Oceanus),他巨大的水体包裹着地球。无论水身在何方,最终都能找到回家的路,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在海浪平稳的呼吸中被摇睡着。海洋是水做梦的地方。
睡着的时候,我们会前往一个词语消解并失去意义的地方,如同雨水落进海洋。雨一旦滴落海面,就不再是雨。做梦的人一旦进入梦境,就不再是做梦的人。唯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