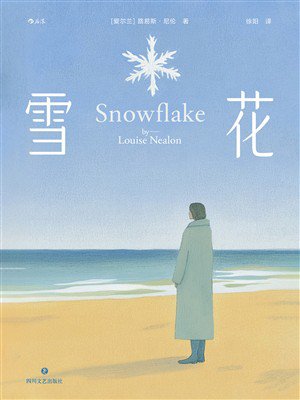赐福
我们从海滩回到家,詹姆斯去挤奶,我们花上一个半小时为墓园礼拜天做准备。每个人都会突然造访墓园,参加一年一度的户外晚间弥撒。这是一项既新奇又艰辛的活动——沉默的朝圣和全世界最无聊的户外音乐会在此结合。我们在逝去的亲人之上站一个小时,好事地窥探别人家的墓碑维护得怎样。
错落的墓碑整齐地排成行。小山顶上有一座大大的木十字架——四米高,两米宽——规格明显是参照了髑髅地
 背负的十字架。从前,这座十字架上有一尊真人大小的基督像,但有某个蠢货把他抢走了,空留一只孤独的左手钉在十字上。
背负的十字架。从前,这座十字架上有一尊真人大小的基督像,但有某个蠢货把他抢走了,空留一只孤独的左手钉在十字上。
这位神父是第一次主持墓园礼拜天,一看就知道。他的双脚在福特全顺
 尾部拖车搭起的简易圣坛上颤颤巍巍。不过他是个很有风度的人。约翰神父身材瘦小,菲律宾人。他和蔼可亲,不炫耀智商,就像担任圣职的路易斯·泰鲁
尾部拖车搭起的简易圣坛上颤颤巍巍。不过他是个很有风度的人。约翰神父身材瘦小,菲律宾人。他和蔼可亲,不炫耀智商,就像担任圣职的路易斯·泰鲁
 ,这个社区很快就喜欢上了他。足球队成功把他收编。事实证明,他是个干净利落的边锋。他似乎也很享受周六晚上跟小伙子们一起出去喝酒,顺着他们说那个“明早弥撒见”的老掉牙玩笑。
,这个社区很快就喜欢上了他。足球队成功把他收编。事实证明,他是个干净利落的边锋。他似乎也很享受周六晚上跟小伙子们一起出去喝酒,顺着他们说那个“明早弥撒见”的老掉牙玩笑。
墓园祝福一直都是糟糕的表演,但今年的表现差到了极点。合唱团想用莱昂纳德·科恩
 的歌曲替代赞美诗糊弄过去。《哈利路亚》
的歌曲替代赞美诗糊弄过去。《哈利路亚》
 是透过发挥状态不稳定的话筒尖叫出来的。他们唱到把他“绑上厨房椅”那一句。詹姆斯用胳膊肘碰碰妈妈,小声说些什么,他们两人都轻轻地笑起来,肩膀颤动。
是透过发挥状态不稳定的话筒尖叫出来的。他们唱到把他“绑上厨房椅”那一句。詹姆斯用胳膊肘碰碰妈妈,小声说些什么,他们两人都轻轻地笑起来,肩膀颤动。
人们当然会注意到詹姆斯站在我们家墓地这边,没站到自己家墓地跟前。他挤奶耽误了时间,我们家的墓地离门更近,所以他正好溜进来站在妈妈身边。他母亲雪莉一张臭脸,但她从来不说他。
我嫉妒妈妈能站在詹姆斯边上。他本人似乎就是地心引力,高高大大,宽阔的肩膀,有力的大手。我们的小吉姆,手跟铲子似的,比利说。只有比利不喊詹姆斯的大名。吉姆,吉米,小吉姆。如果他喊“詹姆斯”,那就是在讽刺——往往是为了逗弄妈妈。这是在展示权力,我觉得。光听他们说话,谁都会以为詹姆斯才是农场的主人。他是发号施令的人。来后门叫人的从来都不找比利,总是叫詹姆斯。詹姆斯来之前,他们找我外公。比利喜欢那样。院子里要是出了什么状况,责任都不在他。
我们站在我外祖父母坟前。我是以我外婆的名字“黛博拉”命名的。看到自己的名字刻在墓碑上感觉有点怪。家里人告诉我,外婆是在睡梦中去世的。后来我才知道是用药过量。没人跟我直说,这是从比利醉酒后多愁善感的言论推断出来的。
再后来,我听说了那件事,得知某天晚上小酒馆快关门时教堂圣器保管员贝蒂对比利说了什么。贝蒂是个紧张兮兮的小个子女人,喝酒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比利逗她开心,她却突然喊起来,说黛比·怀特是魔鬼的婊子,不该被埋在神圣的教堂墓地里。比利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要是她敢再说一个关于他母亲的字,就请自选一扇窗户——被丢出去。在酒馆里,他们依然尊称比利“选一扇窗户”。
约翰神父开始巡回,踏着拖车的台阶走下来,朝墓上洒圣水。九十高龄的科赫兰夫人在轮椅里,是被人推到墓碑边上来的,一整条厚被子拉到她的下颌处。她看起来好像快要在她丈夫身边躺下了。
比利不信教。这是他为了给父母扫墓每年唯一参加的弥撒。他会把墓地打扫干净,给花浇水。圣诞节,他会为他们献上圣诞花。眼下装点墓碑的是一盆黄色报春花。报春花是我外婆最喜欢的花。
❅❅❅
我不是来看外祖父母的。我想看一眼弥撒时站在后面的那个男孩。我看到他和家人一起走进来了。他穿着沃特福德的运动衫和牛仔裤。他的皮肤晒成了棕褐色,绝不可能是在爱尔兰消夏晒的。他肯定去了别的地方。我望着他祖父的墓。他躲在墓碑后面,但我恰好能看见他的胳膊肘。如果说我见过圣胳膊肘,那么非它莫属。
他好像感觉到我在望他,因为他挪进了我的视线。我往别处看。结果我和从前的钢琴老师奥德丽·基恩四目相对。她微微一笑,又低头看自己的脚。没有报以微笑,我有点儿内疚。奥德丽·基恩拥有我心目中最棒的卫生间。我以前会把大半节钢琴课都用来上厕所。她肯定觉得我膀胱有问题。我记得自己曾把食指掘进水箱顶部香薰蜡烛的蜡块里,把上蜡的指头伸到水龙头下面,惊叹于隔着蜡层居然无法感知水流。
有人跟比利说奥德丽·基恩在接受康复治疗,从那以后比利就不带我去学琴了。在我们教区,只要你没接受治疗,当个酒鬼也能被人接受。在这里,嗜酒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奥德丽一直默默地在家喝,人们还是会送孩子去学琴的。奥德丽的麻烦在于她承认自己有麻烦,麻烦在于人人都爱的酒。
我想象不出我钢琴老师醉酒的模样,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从前我夜里躺在床上时会努力将那位柔声细语、手指修长、穿戴整洁、耐心给我示范C大调音阶的女士,同酒馆里我知道的那些醉眼蒙胧的啤酒肚男人联系起来。完成康复治疗后,她用于打扮的精力要少得多。她任由头发变灰。我觉得这很适合她。我很好奇她戒酒多长时间了,到底有没有真正戒掉。
月亮早早地露脸。新月滑入天空,如同一枚硬币从投币口滚落。我感到一滴雨落在面颊上,骂起没有撑到弥撒结束的好天气。我等着更多的雨点落下,却没有等来。这感觉意味深长——那是一片微云从天空落下,如同赐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