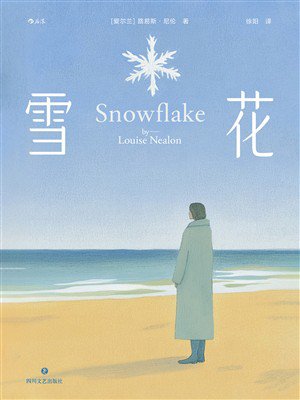穿落难裤的少女
每天我至少都会把学生卡、钱包或手机弄丢一次。每次都一样。我拍拍口袋。摸索摸索外套。我倒出包里所有东西。各种念头都在赛跑,我的大脑超负荷,我无法正常呼吸。我感到脸越来越烫。我的喉咙里好像有个肿块,我的手瑟瑟发抖,我似乎与周围的一切都脱节了。我飞奔或疾走,不知所往。我没去上课是因为在找学生卡。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直到最终在康诺利站的失物招领处寻回手机。我拥抱了某家星巴克在卫生间里捡到我钱包的咖啡师。每次团聚都激动人心,漫长的分别后更是如此。我看着它们,保证说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说我会好好爱惜它们。我像个不靠谱的父亲那样,发誓绝不会再次离开它们。
❅❅❅
值班室的那个人应该已经认识我了,但我还是得指着窗内展示的那一排待认领学生卡中的自己。
“那个是我。”我说。照片里的我看起来像个小孩子。
他把学生卡从窗口下面滑出来。
“非常感谢。”我说,“我保证不会再把它弄丢了。”
他抿一口咖啡,继续和身边的人聊天。
我的手一摸到那张塑料卡,呼吸就恢复正常了。
我朝推拉门边上的楼厅走去,但一节课刚好结束,我只得停下来让人群鱼贯通过。他们都在大笑——所有的人都在——享受着美好时光,而我,自己一个人跌跌撞撞,失魂落魄。
我甚至都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惊慌。没什么好慌的。我的时间都耗在丢东西和找东西上。我开始怀疑,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我是不是故意的。我卡在一个恶性循环里。这是最枯燥的自我破坏形式。
我去厕所喘口气。我排进队伍,瞥见镜中的自己。眼睛下方有青色的阴影。不断的自我折磨让我筋疲力尽。上大学之后我睡得更多,但那是让人越睡越累的睡眠。我在睡觉这方面的成绩快赶上妈妈了。昨晚我睡了十四个小时,可一到家就继续犯困。
我把手盖在脸上,让面颊冷却。一位女士从隔间出来。我迅速走向那片自由空间,将全世界屏蔽在外。我坐到马桶上,等自己恢复常态。
❅❅❅
文科大楼外面的长凳是为小团体、吸烟者还有老练觅食的鸽子们准备的。就连鸽子都能吓到我。
“黛比!”
肯定是赞茜。我唯一的朋友。朋友?熟人?知道我名字的人?我转过身,却没有看见她。
“黛比!”
“噢,嗨!”
她和一个男孩坐在某条长凳上。男孩的胳膊搂着她。
“黛比,这是格里芬
 。”
。”
“很高兴认识你,黛比。”格里芬伸出手,我握了一下。我尴尬地站在那里,直到他指指凳子另一侧。“坐呀。”
我溜到板凳上。感觉像在面试。
“大一的?”他指着我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说。
“是啊。”
他点点头。“你知道这玩意在二手书店差不多十块就能到手吧?”
“啊?我刚在霍奇斯·费吉思
 花了一大笔钱买的!”
花了一大笔钱买的!”
他们笑起来。
“也可能是其他什么该死的名字。”我脸红了,知道肯定是把名字说错了。
“你可以退啊。”
“那也不容易。说实话,他们态度真的挺好的。我还在我的会员卡上盖了几枚印花。”
“太真实了。每次去我都想把整个店买下来。新书闻起来是无与伦比的。”赞茜说。
格里芬嗅嗅我的包。“闻起来很贵。”他说着把烟灰从他的烟上弹走。
“你也是英文专业吗?”我问。
“哦天啊不是,我读完大学还想找工作呢。无意冒犯。我学物理的,最后一年了。”
“听起来很有意思。”
“的确。”
“格里夫
 是个天才,”赞茜说,“他还拿奖学金呢。”
是个天才,”赞茜说,“他还拿奖学金呢。”
“奖学金?”
“我大二参加的奖学金考试。谁都可以考。如果考得好,学费不用自己交,食宿免费。还发点钱。真是件好事。”
“噢。”我默默记下要申请奖学金,一定要不惜代价地拿到它。
格里芬看起来像是甲壳虫乐队某个成员的青春期儿子。他有一头毛蓬蓬的卷发。一条硬币项链在他胸毛上荡悠。
“格里芬你是哪里人?”
“阿迪,劳斯郡
 的。”
的。”
“你听起来不像阿迪人呢。”
“哇,谢谢。”
“我们那边有个打马掌的是阿迪人。”
“谁?”
“打马掌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他的口音特别逗。”
“你很少做自我介绍吧?你跳过了所有关于农业背景的介绍,直接说打马掌的。”他似乎竭尽所能让我尴尬。
“所以你已经想好毕业后做什么了?”我问。
“我想来想去还是打算专注于海洋学。”
“哇哦,研究气候变化什么的吗?”
“我读博打算专攻冰河世纪——冰盖是怎样形成的,还有它们最后为什么会消退。”
“厉害。”
“他还是助教呢。”他的官方发言人赞茜说。
“偶尔。工资不多,但可以让我不愁吃穿。”
“我们真该去喝几杯,”赞茜说,“黛比,跟我们一起喝。”
“我就不了。我得回家。詹姆斯过生日。”
“噢,真好!没事,下次一起。”她转向格里芬。“你来陪我喝。”
“我得回家换身衣服。”格里芬说。
“瞎说,你看起来棒极了。”
“你这条牛仔裤真不错。”我说。
“谢谢。”他摸摸黑色破洞牛仔布中间裸露的膝盖。“这条是新的。汤米·希尔费格
 。标签上说这条裤子落难了
。标签上说这条裤子落难了
 。”
。”
“它的存在感可真强啊。”
“你就是我那穿落难裤的少女。”赞茜说着揉乱他的头发。“多少钱?”
“不记得了。两百块?”
“你知道这玩意在二手慈善店差不多十块就能到手吧?”我说。
“哦——!”赞茜戳戳他的肚子。
他露出微笑,却想不出该拿什么来回敬我。
我道别离开,感觉自己扳回了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