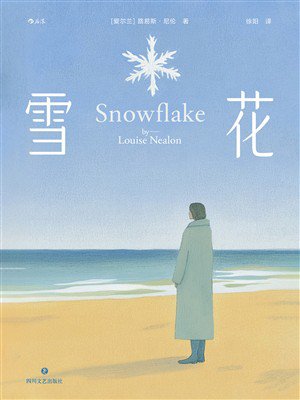二十五
我脑袋喝得昏昏沉沉,所以我任由它耷拉下去。我瘫在马桶座上,直到肚子贴着大腿内侧。我颠倒着看见自己几小时前第一次剃毛的某部位。此前我只是修剪——用手指理顺硬毛,像母亲给宝宝剪卷毛那样修理。我在想,是不是每个人这部分修完之后都像拔了毛的鸡似的——解冻后是粉色的,带着红点。唇部依然残留着象鼻末梢般的剃毛器刮不到的毛。一条舌头歪斜出来。以前我都没注意过它。很难相信它竟然一直都存在,在那一丛大胡子里探头探脑。
我希望厕所里还有其他女孩和我在一起,就像所有人都挤在一个小隔间里喝下各自手包里的小瓶酒然后轮流小解时那样。褪了毛却无人欣赏似乎是一种浪费——甚至没有醉酒的姑娘——来鬼鬼祟祟地偷看我把自己收拾得多整洁。我通常会等到最后一秒突然拉下内裤,夹紧大腿隐藏鸟窝,或干脆在外面等着,假装和坐在椅子上递出方块厕纸、保卫手头除臭剂和薄荷糖藏品的厕所保洁员展开友好的交谈。
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女性朋友。学校里有些女孩会像容忍流浪猫那样容忍我。我最多只混进过一个在活动板房后面游荡的小团体,但这个小团体里男女都有。这仅持续了几个月。我去那里只是为了和那群人中的一个男孩厮混,他有了女朋友以后我们仍旧是普通朋友。他依然会试图往我嘴里丢彩虹糖,直到他女朋友勒令他不再这么做。然后他们开始去商店吃午饭,我也不敢跟着他们了,就自己一个人待在活动板房那边读书。
我细细查看从自己身体里喷出来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冲走。湿漉漉的金色上嘶嘶冒着泡,好像啤酒沫。我在马桶座上蠕动,开始甩头发,第一次是为了让它蓬起来,再来几下是为了找刺激——直到我一头撞在小隔间的墙上。
卡西迪酒馆的厕所有着冬日牛棚的魅力。一只鸟儿在天花板的角落里筑了巢,鸟粪在墙壁的瓷砖上飞溅。不过,我发现,为了给詹姆斯庆生,雪莉还是奢侈地拿出了一整块新肥皂。水龙头的顶盖掉在水池里,要拧一只生锈的钉子才能开出冷水。这很讲究技巧,所以每个人都宁愿挨热水烫。水池边摆着一面全身镜。我站在它跟前,被自己孕妇般的形象惊呆。我总会忘记收腹。我穿的是一条黑色无肩带绷带裙,还有一双已经让我脚磨出水泡的高跟鞋。
厕所的灯光不留情面。我的头发扁塌塌、油腻腻的。我眼圈发黑,我面色苍白,我是橘色的,脖子以下是一道道仿冒的日光浴棕褐。我膝盖上有个小疙瘩。我正准备把它挤破,又发现腿上还有没刮干净的汗毛。最让我沮丧的是,为了今晚我已经倾尽全力。我的确下功夫了。决定穿什么真是让我绞尽脑汁。我已经在精神和身体层面准备了好几天——甚至可以说好几周。
我抿了一口伏特加白葡萄酒,再次朝镜子里望去。奏效。那喀索斯
 显然是在喝醉的状态下爱上自己的。
显然是在喝醉的状态下爱上自己的。
我考虑走出去找妈妈,却又不想卷入她与雪莉的新仇。妈妈想把自己给詹姆斯做的蛋糕摆在某张桌子上,但雪莉坚持认为它应该让道,因为她已经准备了一个像模像样的蛋糕。妈妈的蛋糕让人称奇。“2”用的全是煮熟的土豆,“5”则是八块黑面包,都是詹姆斯的最爱。公平地说,土豆是今天煮的,所以很新鲜,妈妈也主动请缨为客人分蛋糕、剥土豆、切面包,满足不同的需求。雪莉则说那会引发一场食物大战,扰乱派对,破坏她的小酒馆。
雪莉和妈妈永远无法和睦共处。这不仅仅是因为妈妈把詹姆斯引上歧途,还因为她们两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竞争。或者是嫉妒。我不知道。她们都渴求男性的关注,雪莉在吧台后得到了不少关注。她内心深处那只咯咯叫的母鸡无法容忍妈妈悄悄靠近她的客人们,让他们整夜心烦意乱。这里有个经久不衰的笑话:若是妈妈进门,酒馆打烊得会更早。
我扫视人群,寻找比利。我细细观察女士们的脸,如同看相一般全神贯注,好像单从她们的表情就能读出她们爱给私处剃比基尼式,还是更偏向于机场跑道或巴西式。我望着阿兰娜·伯克,想象她那高腰牛仔裤里垫满硅胶。她以前从第四节课就开始用蜡给胳膊褪毛了。
❅❅❅
哦天啊,他在那儿。
那个弥撒时站在后面的男孩。
❅❅❅
我朝吧台老客区走。但愿他正在看我。或许,要是我假装他不存在,他就会注意到我。
“嗨——黛比。”一个喝醉的孩子说着踉踉跄跄地朝我走来,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好让自己站稳。我记得他是康德伦家的。他肯定才十三岁左右。
“嗨。”我对他搭在我肩膀上的手说。
他尴尬得脸红到耳根,但酒精还是让他口不择言。“有机会跟你睡吗?”他问。
我把他的手从我肩膀上挪开,说:“等你到了青春期再来找我吧。”
他那帮朋友们开始大笑,我感觉到自己脸红了,于是便走开。我的心跳加速,跟一个十三岁男孩交锋按理说不至于跳成这样。显然,年轻一辈中肯定已经传开:我愿意跟任何一个有脉搏的东西睡。他们只要开口,或让朋友帮忙开口就行。
我会出于好奇亲吻男孩。我能看出那是不是他们的初吻——通常还真的是,虽说我们现在都十八了。你会大吃一惊的。他们中有些人拿我当碰撞测试假人。还有的以为他们可以随意摸我的胸或把手伸进我的内裤,直到我纠正他们的那些念头。我坚持维护电影分级。曾经有人请求我还原那个倒立的蜘蛛侠之吻。还有个男孩下雨天给我发短信,请求课间在活动板房碰面,我们在雨中接吻。他嘴里弥漫着可怕的口香糖气息,吻后他不停地谢我。我担心他以后再次请求,而我不好意思拒绝。事情就是这样。你一旦开始说“好”,就很难说“不”。我吻过许许多多不喜欢的男孩,仅仅是因为我可怜他们。我为他们从幻想跌入现实的那一刻助力。然而这很悲哀,因为现实湿漉漉的,叫人扫兴。我不是他们的梦中女孩。而我自己也只有一个梦中男孩,他弥撒时站在后面。
一些男孩真的很贴心。汤姆·墨菲吻我前会先摘下眼镜——把它叠起来放在窗台上,那个特别的角度让人觉得它在凝视我们。他牵住我的手,用手抚过我的面颊,然后再把舌头伸进我嘴里。那年我们十四。那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吻。我从来没有吻过自己喜欢的男孩。我不知道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
音乐停下,DJ喊詹姆斯上台接受二十五个吻。詹姆斯二十一岁生日那年去美国度假了,妈妈总是哀叹他的二十一岁生日没有好好过。以二十一岁的主题过二十五岁的生日,他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一群女孩排成队,我本打算加入,但亲吻詹姆斯会很奇怪——哪怕只吻面颊。板棍球队的几个小伙子骑在他身上。我们数到二十三,二十四。詹姆斯站起身来,把妈妈叫上来给了他第二十五个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