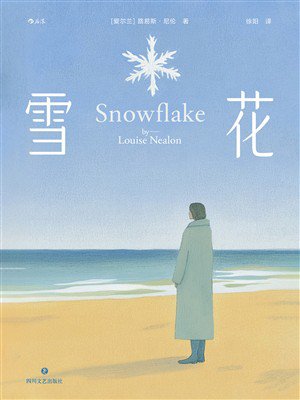旅行拖车
我舅舅比利住在我家屋后那片草地的一辆旅行拖车里。我第一次在路上看到另一辆旅行拖车时,还以为有人——某个孩子——冲着我来,把他绑架了。直到那时我才明白,旅行拖车按理说应该是旅行用的。比利的旅行拖车哪儿也不去。它落在一片混凝土块底座上,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我近旁。
从前,夜里我不敢入睡时总会去拜访比利。比利说只有窗口能看见月亮我才可以走出房子,而且我还要从花园给他带“愿望”。八岁生日那天晚上,我一看见圆圆胖胖的月亮就立刻下楼了,从后门出去,赤脚踏上湿漉漉的草地,树篱带刺的灌木抓住我,扯着我睡衣的袖子把我往回拽。
我知道“愿望们”在哪儿出没。树篱另一边,有一簇长在旅行拖车附近,像女巫们开大会。我把它们一朵朵摘下,草茎“啪”地轻声分离,断裂口分泌出黏黏的汁液,毛茸茸的白色脑袋相互碰撞,让我心满意足。我用手罩住它们,像在保护风中的蜡烛,小心翼翼,不想让任何一缕愿望被碰坏、遗失在夜色中。
采摘它们的时候,我的脑袋里回旋着几个音节——蒲公英,蒲公英,蒲公英。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已经用比利床底下的那本大词典查过这个词了。他解释说,英文“dandelion”源自法语“dents de lion”——狮子的牙齿。蒲公英最初是个漂亮的小家伙,一圈尖尖的黄色花瓣像极了芭蕾舞裙。
“这是它白天的裙子,但花儿终归是要睡觉的。它凋谢的时候看起来疲惫而憔悴,就当你以为它快不行了的时候”——比利举起他的拳头——“它变成了一个绒毛脑袋。”他舒展开自己的手指,从背后变出一朵白色棉花糖蒲公英。“一轮泡泡裙月亮。一次愿望的圣餐。”他让我像吹生日蜡烛那样把愿望吹开。“由梦组成的星座。”
比利打开旅行拖车的门,被我献上的愿望花束惊呆了。为了让他高兴,我采了许多。
“我知道,”他说,“我就知道月亮会出来为你庆祝生日。”
我们在一只空果酱罐里装满水,把蒲公英棉花似的脑袋吹进去,它们的羽毛漂浮在弯月面上,像小小的仰泳者。我把罐头盖上,摇一摇,赞美它们,看它们舞蹈。我们把罐头放在一沓阴冷潮湿的报纸上,让它凝视旅行拖车的塑料窗外。
比利在燃气灶的炉架上热了一锅牛奶。他的厨房看起来就像我梦寐以求的圣诞玩具。每次见它当真可以用,我都会大吃一惊。他让我搅牛奶,一直搅到冒泡、结成一层层可以用勺背挑开的薄衣。他倒巧克力粉,我用勺子迅速搅拌,一圈又一圈,直到胳膊酸疼。我们把冒着热气的棕色溪流倾入一只瓶子,把它带上屋顶去看星星。
蒲公英的种子要过很多天才会完全浸入罐中。它们紧抓水面,悬在水幕天花板上,直到看似放弃或厌倦。正当世人都以为它们必死无疑时,小小的绿尖出现了,像水中长着尾巴的植物美人鱼。比利把我叫过去,为这些倔强的小东西而惊叹——这是拒绝死去的心愿。
❅❅❅
今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敲比利的门时我有点紧张。我现在晚上不怎么去找他了。旅行拖车的表面碰在我的指关节上,凉凉的。它四周封着一圈橡胶条,像冰箱的门。我用指甲挖进松软的橡胶条,抠下来一点点。光滑的一条就此落下,如同火腿上剔下的一丝肥肉。一阵唰啦啦的翻纸声,地板上急促的脚步声,比利打开门,尽量掩饰看到我时的惊讶。
“噢。”他说着走回自己的扶手椅。
“睡美人呀。”我问候道。他今天早上没起来挤奶,是我替他的。
“嗯,对不住。”
“还是我生日呢。”我说。
“哦真他妈的要命。”他扮个鬼脸,“圣詹姆斯怎么没任你赖床
 呢。”
呢。”
“他不知道。妈妈忘了跟他讲。”
“我们太没诚意了。这次是什么?甜美十六岁?”
“自负十八岁。”
让他拧出一副被逗乐的笑脸是我小小的胜利。我等他转身灌水壶。
“大学录取通知书今天下来了。”我说。
他关上水龙头回头看我。“是今天?”
“嗯。我被圣三一
 录了。下个礼拜开学。”
录了。下个礼拜开学。”
他看起来很难过。然后他用手抓住我两边肩膀,发出一声叹息。“我真他妈的为你高兴。”
“谢了。”
“去他妈的茶,”他说着挥手把这个念头打发走,“去他妈的茶,我来拿威士忌。”
他在橱柜里胡乱翻找。盘子哗啦啦响,碗堆倒塌。比利试图用膝盖抵挡陶瓷餐具大雪崩。我本来等着帮忙清理,好给自己找点事做,可他已经起身,得意地握着一瓶尊美醇
 从柜子里冒出来。
从柜子里冒出来。
“生日快乐,黛布丝。”比利说。
“多谢。”我从他手中接过那瓶威士忌,好像在领取彩票大奖。
我们都尴尬地站着。我真心希望不必由我来提议。可按理说我现在是成年人了。我不能再坐等事情发生。
“今夜天空晴朗。”他终于开口。
“也真他妈的冷。”我说。
“柜子里有热水袋,如果你需要的话。”比利伸手去够天花板上的门,把通往屋顶的折叠梯拉下来。他穿着靴子噔噔地拾级而上,睡袋拖在身后,像个准备去睡觉的孩子。
我把水烧上。旅行拖车里的奇怪什物注视着我。一架老式木头飞机模型悬在他床铺上方。一个小人像荡秋千似的坐在上面,手里拿着一副望远镜。我们用有法语味儿的“皮埃尔”给他命名,因为他长着一撮小胡子。
热水袋的橡胶温暖着我的手。我两级并作一级爬上梯子,晚风扑面。感觉像是在船上。我们钻进睡袋的茧,躺在庇护着比利家的镀锌金属板上。我手底下的屋顶冰冷而光滑,感觉像躺在一块冰上。我们望着天空,好像没有我们它就撑不住似的。
我慢慢长大,旅行拖车顶上的视野是唯一没有变小的东西。我们能听见奶牛的蹄子沙沙掠过草地。它们闲逛着,嗅来嗅去,看看有什么动静。我呼吸着睡袋上的汗味,湿冷,夹杂着霉味。比利浑身散发着香烟和柴油的味道。套头衫的袖子耷拉在他的无指羊毛手套上。一丛胡子茬扎在他嘴边,向他的颧骨延伸,与他耳后的头发相接。
“给我讲个故事。”比利说。
“我不想讲。”
“你想的,”他说,“我来挑一颗星星。”
我假装毫无兴致,玩起睡袋的拉链。我把头发拢到耳后,等他登陆某个星球。
“能看见北极星吗?”
“不能,它只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罢了。”
“其实不是。天狼星才是最亮的。”
“你跟我说是北极星的。”
“噢,那我说错了。”
“开什么玩笑。”
“那你看到了?我以前指给你看过?”
“也就几百次吧,比利,但你跟我说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是第二亮的。”
“那我得自己找出第二亮的吗?”
“旁边有W的那个。”
“没错,我懂,是那颗看起来最亮……实际上却不是。”
“我得搞清楚我们是不是在说同一颗。妈的真要命。所以你看到它附近组成微弱‘W’的那五颗星星啦?”
我眯起眼睛在天空中搜索,试图把那些点连接起来。从前我喜欢假装自己也能看见比利看到的东西。我讨厌那种努力却得不出结果的尝试。根据我的经验,这和读盲文很像,只是换成了亿万英里之外的闪烁光点。太多了——它们成群结队地瞪着我,叫人无所适从。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找得愈发努力。比利把星星拆解成图画和故事,这样辨认起来容易一些。W就是比较好认的图像之一。
“嗯,我知道,”我说,“那个看起来像把摇椅的。”
“没错。”他说。他食指朝上,划出流畅的直线,把星星逐一连在一起,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卡西俄佩亚的椅子
 。”
。”
“我记得她。”
“很好——给我讲讲她的故事。”
“你知道那个故事的,比利。”我说。
“我没听你讲过。”
我叹口气来争取时间。人物开始在我脑海里聚集。
“来吧。”比利催促道。
“卡西俄佩亚是古代的一位王后——她是刻甫斯的妻子,”我解释说,“他也在上面呢。卡西俄佩亚是个有趣的人物。她挺漂亮的,但人们觉得她很怪。她披头散发,光着脚到处走,人们觉得很震惊——她可是皇室成员啊。她生了一个女儿,叫安德洛墨达,她教导女儿要自尊自爱——在当时算是激进的思想了。她的自由精神被人当作傲慢。人们渐渐都知道了,有个光着脚到处跑的嬉皮士王后,她爱自己,也教女儿这样做。波塞冬可忍不了。他决定要给人类提个醒,掌控权不在他们手里。于是他派了一只海怪去破坏她丈夫的王国。卡西俄佩亚得知拯救王国的唯一途径是用女儿献祭,于是就照做了。她用链子把安德洛墨达拴在悬崖边缘的一块岩石上,让她自生自灭。”
“真是个婊子。”比利说。
“唉,她别无选择。要么照办,要么眼睁睁地看着海怪害死所有人。”
“希腊人真他妈的是疯子。我能猜猜安德洛墨达最后怎么样了吗?”
“猜吧。”
“让白马王子给救走了?”
“那当然啦。”我说。
比利把那瓶威士忌递给我。它灼烧着我的喉咙。
“珀尔修斯杀完美杜莎,回来的路上顺便杀了海怪,出于礼节,安德洛墨达得嫁给他。”我说。
“经典。那卡西俄佩亚后来怎样了呢?”
我用手指着她。“她在那里呢,坐在摇椅上。波塞冬把她绑上去了,让她绕着北极转的时候头朝下,脚朝上。她被困在椅子里,一直转到时间的尽头。”
“天啊。”比利说,“一半时间都被倒挂着。这也许能让你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
“我只会觉得头晕。”
“也许刚开始的确会,但没准习惯就好了。”
“我觉得有重力挺好的,谢谢。”
“好到我可以把你从屋顶上推下去?”
他使劲推我的睡袋,我边滚边叫。“你个讨厌鬼,比利!这可不好玩。”
“不喜欢生日惊喜啊?”
“少来。”我说,但我的内心快乐而温暖。我想着自己的故事,又对着瓶子闷上一口。第一小口威士忌已经让我飘飘欲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