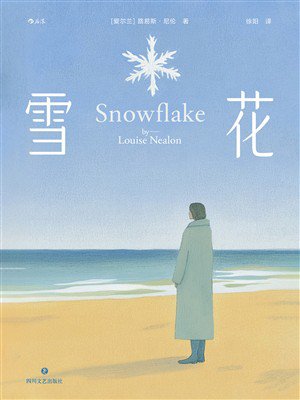走读生
这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却误了火车。比利坚持说我肯定来得及。他挤奶晚了,忙活完才送我去车站。所以这下我要迟到了。我也不确定迟到会错过什么。或许我应该努力交朋友——我担心好朋友一上午就会被抢完。这是迎新周,我看过那种讲述大学生活的电影。如果我能邂逅未来的闺密或恋人,肯定是在第一天。
我只见过十二月的都柏林。比利每年都带我去看圣诞彩灯。我对都柏林最初的记忆,是五六岁的时候跟比利一起在奥康奈尔大桥等车回家。巴士终于来了,单是上车避开瓢泼大雨和能把伞吹到翻面的狂风就已经叫人舒心。比利拍拍司机的窗户,把一张十欧的钞票拿给他看。他把钞票折起来,试着像变魔术一样把它塞进投币口。
司机看着他。“这你叫我怎么办啊?”
比利取出那张钞票,让我们后面的乘客们先投币。“老板,你零钱肯定够的。”他冲叮当作响的硬币点头说道。
“我长得像自动售货机吗?”司机瞪着我们,一直瞪到比利后退。
我们下车回到雨中。后来,我们都是坐火车。
看比利跟陌生人打交道感觉怪怪的。他似乎心里没底。每次他让我牵住他的手,我不知道这是为我好还是为他好。
但我们还是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城市漫游方式。一年又一年的记忆叠印,融为一体:路过邮政总局
 ,向库丘林还有其他小伙子们致意,然后过桥走上大坝街,有时会走到托马斯街去某家面包房,从一位皮肤像油酥糕点的可怕女士那里买五十分钱的香肠卷。有一次,比利给运河边的一位流浪汉递了一支烟,我们和他一起在椅子上坐下聊天,就像一些人弥撒过后聚在教堂门口闲聊那样。
,向库丘林还有其他小伙子们致意,然后过桥走上大坝街,有时会走到托马斯街去某家面包房,从一位皮肤像油酥糕点的可怕女士那里买五十分钱的香肠卷。有一次,比利给运河边的一位流浪汉递了一支烟,我们和他一起在椅子上坐下聊天,就像一些人弥撒过后聚在教堂门口闲聊那样。
在格拉夫顿大街上,我们望着布朗·托马斯
 橱窗里的一个木偶用锤子和钉子拨动一只鞋,玩具火车沿着它们既定的轨道咔嚓咔嚓地前行。比利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指着一位装扮成青铜雕塑的街头艺人说,我不介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的任务是让人快乐。要不就去当神父。他笑着说:“祝你好运。”
橱窗里的一个木偶用锤子和钉子拨动一只鞋,玩具火车沿着它们既定的轨道咔嚓咔嚓地前行。比利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指着一位装扮成青铜雕塑的街头艺人说,我不介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的任务是让人快乐。要不就去当神父。他笑着说:“祝你好运。”
比利一直希望我申请圣三一。“这是唯一值得去读的大学。不过他们封得严严实实的。”他指向纳索街侧门高高的石墙和尖头围栏,我们从来没进去过。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校园是开放的。我总觉得圣三一的情形和《肖申克的救赎》正好相反——你需要用好烟贿赂摩根·弗里曼,然后自己挖个地道钻进去
 。
。
去年学校带我们去某场升学就业指导会时,圣三一的摊位没派摩根·弗里曼。一位灰着脸、身穿海军蓝套装的女士给了我一本手册,她瞥了一眼我脏乱的校服,告诉我说,想进圣三一很需要脑力。她错了。真的不需要多少脑力。想进圣三一,不见得要多聪明,够倔就行。
❅❅❅
我在进城的列车上弄丢了车票。到康诺利站
 的检票口时才反应过来。我走到标着“问询”的小亭子跟前,向玻璃窗后的那名男子诉说我的遭遇。
的检票口时才反应过来。我走到标着“问询”的小亭子跟前,向玻璃窗后的那名男子诉说我的遭遇。
“你在哪里上车的?”他问。
“梅努斯。”
“票多少钱买的?”
“我记不得了。”
“证件能给我看下吗?”
“我一个也没带。”
“你叫什么名字,甜心?”
“黛比。呃,黛博拉·怀特。”
“你满十八岁了吗?”
“嗯。”
“哎呀,黛博拉,你要被罚一百欧了。”他指着玻璃窗下角的一块写有“定额罚款”的小牌子说,还从窗口滑过来一张纸。我仔细看了看:“二十一天内执行——若不缴纳——或将收到法院传票——判决后或将面临高达一千欧元的罚款。”
“我的票丢了。”我说。
“亲爱的,如果你买过票应该会记得一张多少钱。”
“可我真不记得。”
“这我就说不准了。把罚单拿给门口那个人看,让他放你出去。”
❅❅❅
我第一次独自进入都柏林,是以有罪之人的身份。
❅❅❅
我不知不觉地跟着一位上班途中的女士。她穿着运动鞋,铅笔裙,紧身裤袜,一手拿着外带咖啡,一手拿着公文包。她走起路来好像是在拼命追赶当天剩下的时间。我保持几步之遥跟在她身后。我们穿过一座宽阔的桥,它在我们所有人脚步的重量之下震颤,蹦蹦跳跳,像是给我们鼓劲。
我一直走到奥康奈尔大街才鼓起勇气请一位保安给我指圣三一的方向。他嘲笑了我,我脸红了,打心眼里讨厌自己。我朝着他指的方向走去,换上一副全新的坚定神情,看起来好像十分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我在大门的围栏旁边等了一会儿才进去。我看着人们从通往大学的小耗子洞里进进出出,心想为什么要把入口修得那么小。这让我想起六岁时曾偷听到的一集令人心神不宁的《奥普拉脱口秀》。我外公还在世的时候,日间电视节目就是他的软肋。中午吃完饭,他就坐下来看《奥普拉脱口秀》《法官朱迪》
[1]
或《智者为王》
[2]
里的安妮·罗宾逊
 。在《奥普拉脱口秀》的某一集中,有位头发乱蓬蓬的心理学家说,穿门而过可能会引发短暂失忆。女性观众们倒吸一口凉气,点头赞同,回想起自己离开房间后要去做某事却毫无头绪地挠头的时刻。
。在《奥普拉脱口秀》的某一集中,有位头发乱蓬蓬的心理学家说,穿门而过可能会引发短暂失忆。女性观众们倒吸一口凉气,点头赞同,回想起自己离开房间后要去做某事却毫无头绪地挠头的时刻。
看完节目之后,我不肯离开起居室,坚信自己很清楚那扇门要搞什么鬼——它想把我的记忆抹去。我死死抓住扶手椅,一头埋进垫子的褶皱里,妈妈想拉我起身,我踢来踢去,咬她的手。到晚上我才放弃抵抗,她把我拖进厨房吃晚饭。我一边跨那门槛,一边担心多久之后我会彻底忘记自己是谁。
这里的门好像也有类似的力量。我是谁,无关紧要。一旦穿过那扇门,我就会被改变。我还没准备好。感觉我好像该为自己举办一场葬礼。
我假装在等人,以防有人在观察我。我看看手机,看看手表,扫视路过的稀奇古怪的往来人群。中性的格郎基
 ,私立学校风格的校服,七分裤,阿伯克龙比&费奇
,私立学校风格的校服,七分裤,阿伯克龙比&费奇
 套头衫,拉尔夫·劳伦
套头衫,拉尔夫·劳伦
 T恤,点缀着不知名政治运动徽章的托特包。
T恤,点缀着不知名政治运动徽章的托特包。
一个穿黄雨衣的女孩从她的自行车上下来。她骑的是那种前面带柳条筐的复古自行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扯下那件雨衣的。黑头发、刘海、小雀斑、鼻环。她看起来很开心——兴奋,却很自然。
我穿着自己最好的牛仔裤还有比利的一件格子衫,袖口卷起,看起来就像要下地去挖土豆。我望着那个女孩消失在耗子洞里,走向通往前广场的入口。深吸一口气,我在她后面跟了上去。
❅❅❅
站在印着“迎新周”几个字的横幅底下,我非常清楚自己是新来的。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期待看到什么——或许是一个专门用于交友的小角落吧。我习惯于在冒险开口说话之前就知道对方的名字、他们的狗、他们老爹喝醉了是什么样。那儿的摊位和帐篷里挤满了人,似乎彼此都是熟人。不同的英语口音撞击着鹅卵石。我四处游荡,像一个自我意识极强的幽灵,等着被人注意到。
“你好啊!”
“我的老天。”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吓你的。”一颗大胡子牛油果在跟我说话,“我是严格素食主义协会的,为了澄清关于严格素食主义的谬论,我们来玩一个词语联想游戏。像这样,如果我说‘严格素食主义者’,你脑子里首先会想到什么?”
“希特勒。”
“啊?”
“希特勒是严格素食主义者,至少我听人这样说过。也可能只是宣传吧。或者乱讲的。”
“嗯,有意思。可你还是把这词和那个传言联系在一起了,尽管有证据表明它是假的。”
“关于希特勒的一些事儿就是刻进脑子里了。”
“你会考虑成为严格素食主义者吗?”
“说不好。我们家是开奶牛场的。”
“乳业把牛宝宝从妈妈跟前抢走。”他说。我听不出来他到底是开玩笑还是当真。“为了人类的饮食,几个世纪以来奶牛的基因一直在被修改。它们都成了弗兰肯斯坦
 的怪物,每一头都是。”
的怪物,每一头都是。”
“但弗兰肯斯坦只造了一个怪物。”我说。
他停下思考片刻,直到结论最终在脑海里形成。“没错。”他用手点着我说,好像自己冲破了终点线,赢了整场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我试着问。
“里基。”
“里基,”我重复道,“我会尽量记住的。”
“你不会的。”里基似乎想说点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做个严格素食主义者。”他挥着拳头说了这句。
❅❅❅
我排到一行队伍的末端,好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闲散。
“注册是在这排队吧?”那个穿黄雨衣的女孩在跟我说话。
“我觉得是吧。”我说。
“太好啦,我今天就是来注册的。你是哪个专业的?”她问。
“英文。”我说。
“哦太好啦,我也是。你住学生公寓吗?”
“啊?”
“学生公寓。大学宿舍?”她问。
“不呢,我住家里。路上大概一个小时。”
“噢,你是走读生!感觉如何?”她说起来好像真的很关心我的幸福感。
“呃,今天是头一回。”
“噢对,是啊,这个问题蠢得很。”她顿了一下。“对了,我叫‘桑蒂’。”
“很高兴认识你,桑蒂。你这个名字很酷。”
“非常感谢。我父母特别迷希腊神话。”
“噢。”我还没听过哪个希腊人叫“桑蒂”呢。
“你叫什么?”桑蒂有一双我只在音乐短片里见过的那种绿眼睛。
“黛比。”
她笑起来。“对不起,只是——你刚才指着自己。”
“我指了吗?对不起,我不太习惯做自我介绍。”
桑蒂是都柏林人,但她说话并不像都柏林盖尔语区的那些耍酷的孩子,那些人听起来跟外国人有一拼。她听起来很正常,很靠谱,很自然。她肯定多少有点不对劲。
“桑蒂!”一个戴贝雷帽的女孩朝我们走来。她矮矮胖胖的,戴着高档眼镜,背着一个棕色的皮革小包。
“嗨!黛比,这是我舍友,奥尔拉。她是克莱尔郡
 的。”
的。”
“很高兴认识你。”我说着同那个女孩用力地握了一下手。任何一个乡下人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这里只容得下一个来自无名之地的蠢蛋。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奥尔拉说起话来像是个皇室成员。
“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她问桑蒂。
“我要注册。”桑蒂说。
“太棒了,我也是。”奥尔拉从小包里抽出一个文件夹。“我东西应该都带齐了。”
“我们还要带东西来?”我问。
“你没带表格?”奥尔拉问。
“什么表格?”
“你得先在网上注册。他们发邮件了。”
“我还没看到。”我说,“我们家网太烂了。”
“哦天啊,”奥尔拉看起来都替我尴尬,“没带表格就真没必要排队了。”
桑蒂把头歪到一边望着我,好像我是她从后花园捡来的流浪狗。“没事的,这个礼拜随便哪天都能注册。”她说,“他们也就是给我们发发避孕套和防狼哨。”
“男生也有防狼哨吗?”奥尔拉好奇道。
“我觉得有吧,”桑蒂说,“如果不是人人都有,那就是性别歧视。”
“你知道哪儿有电脑吗?”我问。
“你去图书馆看了吗?”奥尔拉显然觉得我是个白痴。
“噢对啊,不好意思。”我说,然后一路道歉钻出队伍。
“在那边。”奥尔拉指着相反的方向说。
“谢了。”
我假装朝图书馆的方向走。我打开钱包,数出购买返程火车票的硬币。
[1] Judge Judy ,美国法庭真人秀节目,由曾任法官的朱迪·辛德林(Judy Sheindlin)解决现实生活纠纷。
[2] The Weakest Link ,源自英国的电视竞赛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