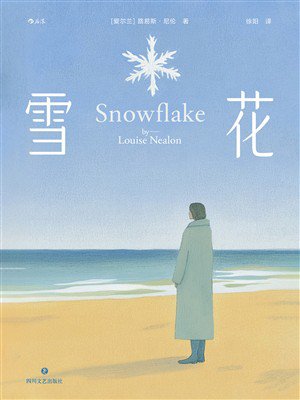西尔莎
我家的房子卡在山脚下的一道弯里。我们管这座小山叫“时钟山”,因为住在山顶小屋里的人叫“时钟”。我不知道他的真名,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喊他“时钟”。“时钟”每天去商店买报纸都会经过我家门口。他从来不打招呼。他闻起来就像古老的泥炭,而且他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抽烟斗的。有时我们转移牲口,詹姆斯会招他来帮忙,让他站在围栏口,那种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和他说话,因为他又老又孤单。他不怎么爱说话,但偶尔会猜猜我多大了。他总是把我想得比实际年龄小得多,要是我纠正他,他还会满脸狐疑地看着我。
一条路从“时钟”家的房子舒展开来铺向村庄,我们的牛群散布在公路两旁的地里。教堂尖顶露出树梢。路旁两棵橡树相向而立,枝条框出一幅风景画,树篱的修剪与之相称。一块写着“Fáilte(欢迎)”的牌子栖在小山弯道内侧,正对我家房子,欢迎那些穿过我们村通往别处的人们。
我们曾在大门口的墙上挂过一块木牌。我七岁生日时比利做的。我真的很想要一匹小马驹,但妈妈不同意。我只好给房子取名,虽然那完全是两码事。比利把它做成了木牌,因为这不花一分钱。我给了它原本属于小马驹的名字:西尔莎
 ——我想象着从小山“嗖嗖”地奔驰而下冲进我们家院子的自由。
——我想象着从小山“嗖嗖”地奔驰而下冲进我们家院子的自由。
这个名字用了几个月,直到某天夜里一辆车在我们的花园里出了车祸。那是一辆气流偏导器在尾部扬起的蓝车,它在碰撞的作用下左摇右摆,一头栽进我家的树篱。它下山的时候跑得太快了,滑到弯道路面一片难以看清的薄冰上,瞬间失控,径直撞上那块写着“西尔莎”的牌子。一名十九岁的男孩死了。某些纪念日,他的家人会在入口那儿的围墙留下一束白百合。我们看着那些花儿在脏兮兮的塑料包装里枯萎。
那辆车撞上我家围墙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中,我是个男孩,在开车。我不太记得梦里的经过,但我记得结局。直到最后一秒,我才看见山脚下的急转弯。我猛踩刹车,随后察觉到了轮胎下的冰面,说实话,那感觉很优雅。紧接着一个美丽的念头随之钻进我的脑海。周围的世界绕着我旋转,就像是一位女子出乎意料地领你在舞池里旋转一样,你感觉有点傻,似乎自己的男子气概被削弱了,但没关系,这只是找点小乐子,而且你觉得她很可能迷上你了呢……
妈妈说我尖叫着醒来,随后我们就听见那辆车撞到了围墙上。我悲痛欲绝。那个男孩的死是我的错。他冲进了我的脑袋,我挡住了他通往天堂的路。他碎成许多片,就像我们不时能在花园里发现的汽车残骸一样。我总是突然放声大哭,在睡梦中哀号。妈妈竭尽全力安慰我。
我晚上开始去旅行拖车那儿。有一次,比利对我失去了耐心。我告诉他,我睡不着是因为那个男孩还在我身体里面。他狠狠扇了我一巴掌,直到现在我都觉得难以置信。“那场车祸跟你没关系。”他大喊道,然后他捂着脸跟我说,他不是生我的气,他是生我妈妈的气。
我们再也没有换上新的“西尔莎”木牌。比利忘了,我也不敢提醒他。有些夜晚,我依然会坐在床上不敢入睡,等着下一辆车、下一个幽灵撞进我们的花园,踏上通往遗忘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