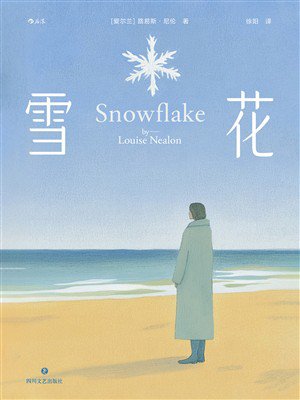被放荡刺伤
我向厨房的窗外望去,看到我母亲在我们的后园里,赤裸着在一丛荨麻里跳舞。它们的茎爬到她的胸口,就像一大群人在挥舞着示爱的棕榈帽。她扭转脊柱,肩头交替亲吻她颌下的空间。她的手在周身划着半月弧线,好像涉水而过。乍看她似乎一点都没被刺伤,可等她从荨麻丛里出来就能明显地看出,她已经将自己点燃。
等小伙子们回来吃午饭时,她已经把刺伤挠到出血。比利假装没看见。有一次他喝醉了,说那是“被放荡刺伤”。
妈妈给詹姆斯递午餐时,他伸手抚摸散落在她肌肤上的红疹子和白色肿块。
“你怎么了?”他问。
“我被一些荨麻刺伤了。”
“一些?你浑身都被扎了。你栽进去了吗?”
“不,我跳进去的。”
“啊?”
妈妈向他保证,她是成心挨刺的。
“你怎么会想出干这种事儿的?”
“里面有血清素。所以它们才会扎人——它们是为你注射快乐化学物质的天然小针。对你有好处的。”
“真是这样?”
“嗯。”
詹姆斯思索片刻,然后点点头。“有点道理。”
“小吉姆
 很乐意陪你一头扑进荨麻床呢,梅芙。”比利说着头也不抬地剥土豆。
很乐意陪你一头扑进荨麻床呢,梅芙。”比利说着头也不抬地剥土豆。
“啊,现在我可不一定了。”
“我能想到更好的麻醉法。”比利说。
“比利,两‘感’:快感和痛感。它们被配成一对是有原因的。”詹姆斯说。
“不过对他来说要换成两‘醉’:烂醉和宿醉。”妈妈补充道。
这并没有多好笑,但詹姆斯却大笑起来,连桌子都跟着一起发颤。
“我们都知道,酒鬼的类型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我很高兴我是那种喜欢和人打交道的。某些人血清素够多,可以躲在屋里,躺在床上一瓶一瓶地灌下去——”
“天啊,比利,淡定。开玩笑而已。”詹姆斯说。
“呀,有时候笑话反而是你可以说的最严肃的话。”
午餐时间就是这样。妈妈和詹姆斯对战比利和我。组队始终不变,坐下来吃饭前就分好了。
❅❅❅
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我母亲把我生下这件事。我似乎更有可能是像某种地狱维纳斯那样从泥塘里冒出来的,或者是从奶牛屁股里挤出来的。如果詹姆斯是我爸也完全说得通,因为他很爱妈妈,可我出生时他才六岁。詹姆斯从娘胎出来时就被缝进了他穿的那身约翰·迪尔
 工作服,生在一个没有土地的家庭。外公去世的时候他十六岁,在他母亲的小酒馆里给人打啤酒。比利叫詹姆斯来给我们干活。他简直是无所不能:挤奶,修篱笆,夜里任何时候都能出去给牛犊接生。经历了丧父之痛的妈妈一蹶不振,詹姆斯的出现让她精神百倍。
工作服,生在一个没有土地的家庭。外公去世的时候他十六岁,在他母亲的小酒馆里给人打啤酒。比利叫詹姆斯来给我们干活。他简直是无所不能:挤奶,修篱笆,夜里任何时候都能出去给牛犊接生。经历了丧父之痛的妈妈一蹶不振,詹姆斯的出现让她精神百倍。
詹姆斯只大我六岁。我夜晚趴在枕头上幻想亲吻的第一张脸就是他的。从前他早上来吃饭时,我总会笨拙地跟他玩捉迷藏。厨房里能藏的地方不多。我把自己裹进窗帘,腿就会露出来,更有不知道多少次,我躲在桌子底下尽量避开他的腿和脚,结果被一条伸到桌底下的毛乎乎的胳膊抓住,我放声尖叫。我试过躲进后门厅的衣帽架,但那里和厨房隔得太远,他忘了去找我。
我把詹姆斯当作迪士尼王子来爱。我习惯把对他的幻想和现实中的他区分开来。詹姆斯不在乎我母亲的声誉。酒馆打烊时,詹姆斯跟她一起回家,上她的床,丝毫不在意酒馆里人们的窃窃私语。
他们的年龄差并不明显,因为妈妈看起来年轻,詹姆斯显得老成。比利说詹姆斯一个下午就把青春期过完了。这是真的。上一秒他还是个小男孩,下一秒就变身成年男子了。他身高六英尺七英寸,是我们这儿的板棍球
 队长。他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去,看球从天而降,落进他伸出的手掌,仿佛那是来自上帝的礼物。
队长。他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去,看球从天而降,落进他伸出的手掌,仿佛那是来自上帝的礼物。
❅❅❅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但我觉得我知道自己是在哪里被孕育出来的。我们这儿的一片地里有座石器时代的巨石墓——国家历史文物,上面有一块来自政府的告示牌,破坏该区域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是青少年们经常跑去喝啤酒的地方。通往那片地的路上有块牌子写着:“钥匙可从威廉·怀特先生处获取。十字路口左转,左手第一辆旅行拖车。”比利就是那个给偶尔造访这座土墩的考古狂热者做向导的地方史学家。他受托保管钥匙,却常常让门敞开。
路边有两级标识入口的石阶,一条小径通往被栅栏围起的墓穴。简洁的青冢从地面隆起。一扇厚重的金属门引向巨石墓穴内部,踩扁的啤酒罐还有偶尔出现的避孕套包装点缀着这古老的墓葬。神圣的石头上刻着名字,歪歪扭扭的“舔我”在巨石的之字和圆圈铭文旁清晰可见。
这处文物叫福尔诺克斯(Fourknocks),名字源于两个爱尔兰单词:表示寒冷的“fuair”和表示小山的“cnoic”。我母亲被收入了福尔诺克斯的民间传说。1990年夏天,男孩们在巨石墓结束童子之身。妈妈只有一条规矩:不和同一个男孩交欢两次。没人当着我的面说这些故事,但他们知道我知道。地方史学家比利跟我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