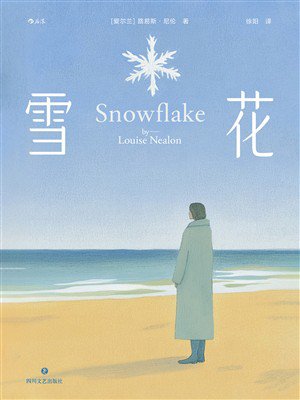圣体龛
我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上午与她并无交集。她的闹铃中午才会响起。佩屈拉·克拉克的《闹市区》
 循环播放。两点钟她会及时醒来给小伙子们做午饭。饭后她又回到床上。今天是星期天,是妈妈一周中唯一需要早起的日子,她要去参加十点的弥撒。
循环播放。两点钟她会及时醒来给小伙子们做午饭。饭后她又回到床上。今天是星期天,是妈妈一周中唯一需要早起的日子,她要去参加十点的弥撒。
我把黄油刀的刀片插进锁眼扭转,直到听见咔哒声。门嘎吱一声打开。佩屈拉·克拉克的声音从屋里向外扩散。我把闹铃关掉,望着妈妈在呻吟中回归现实。
“早。”我说。
“早。”
“我给你端咖啡来?”
“请吧。”
给妈妈煮咖啡是防止她再次昏睡过去的绝招。等我端着一杯麦斯威尔回来时,她已经裹着写作专用毯坐在桌前。
❅❅❅
妈妈在她的桌前坐下,在一本旧练习簿上记录昨夜的梦。她用蓝笔写,要是找不到蓝色的笔就会很失落。我出生前,妈妈就在写一本关于梦的书了。她跟别人说她是作家,但她写的东西从来没有发表过。她对杂志投稿和比赛都没多大兴趣,这兴许是件好事。
我们把妈妈的卧室称作“圣体龛”,因为门被漆成金色,而且她锁门用的钥匙和神父弥撒上用的那种差不多。只要有一片私人空间,周遭世界全部崩塌她也不介意。“圣体龛”可以充当艺术装置或地下剧院化妆间。有时我会趁她熟睡撬开门,只是为了到里面看看。
走进那间屋子就像步入一本立体书中。她从书里撕下一些页面,把它们贴在自己卧室的墙上。一页页纸构成一幅诗歌、小说和哲学书的拼贴画——全是关于梦的。她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像在设法寻找关联线索。
这些纸张用遮蔽胶带
 粘在一起。把一页页纸撕开能带来一种满足感。它们发出嘴唇张开前那种“啵”的一声,不情不愿。揭起一页飞舞的纸,下面躺着另一层梦。拉开约翰·菲尔德
粘在一起。把一页页纸撕开能带来一种满足感。它们发出嘴唇张开前那种“啵”的一声,不情不愿。揭起一页飞舞的纸,下面躺着另一层梦。拉开约翰·菲尔德
 某一首夜曲的封面,整本曲谱就从墙上翻滚出来。
某一首夜曲的封面,整本曲谱就从墙上翻滚出来。
一串刻着螺纹的锡贝壳穿在一股麻花辫上,从天花板垂下来。这些贝壳闪耀着异于尘世的光泽。我本以为触摸时它们会叮当响,可那却是令人失望的“嘎啦嘎啦”声,好像美丽的女子开口却是一副破锣嗓。
妈妈在床底放了一只装满明信片和艺术杂志图画剪报的褪色饼干桶,还有一筐小瓶装白葡萄酒,那是詹姆斯定期从他母亲的小酒馆里给她顺来的。一个小小的天青石蓝色头骨摆在她的窗台。一盏海军蓝的台灯立在她床尾的梳妆台上,活像一位戴着宽檐帽的胖夫人。它的光线将妈妈的影子投在墙上——她颀长的剪影延伸,去拥抱那够不着的沉睡躯体。
妈妈很少冒险走出门,除非是参加弥撒、去超市或社会福利办公室。比利会提醒她每周领取失业救济金。比利说那是她的艺术基金。他掌管着妈妈的银行账户。让妈妈自己管钱简直就是灾难,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比利每周开车载她去采购一次食物,她购物,比利在车里等。有时她只拿了一瓶奶昔和一只甜甜圈就回到车里,别的什么都没买,遇到那种情况,比利就打发她再进去一次。
妈妈只有在参加弥撒时才会努力做个正常人。外公笃信宗教。他在世的时候,我们每晚都要一齐跪在起居室里念诵《玫瑰经》。外公自尊心也很强。他希望全家参加弥撒时都保持良好的形象,所以妈妈把宗教同良好的个人造型联系起来了。今天出席弥撒的着装她已经选好。她要淋浴,花上至少一个半小时做准备。
淋浴前,妈妈先光着脚走到屋外。她小心翼翼地踏上草地,如同踏上一方舞台。然后她闭上眼睛,双手垂在两侧,掌心朝外,慢慢将空气深深吸入肺部——吸入一丝丝新鲜的现实,呼出她自己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