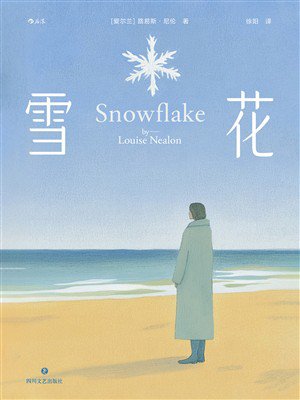封面女郎
我在城里可以一整天不和任何人说话。我常常在火车上消失,在文科大楼里消失,在都柏林的街上消失。上课时我自己一个人坐。为了避免与人互动,我甚至会从自动售货机买咖啡。经历了头几天屡战屡败的交友尝试之后,现在主动决定不和任何人说话反而让我宽心。
我尿意频繁,所以大半天都可以耗在进出厕所和蹲坐休息上。厕所是我充电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哭泣,打起精神,至少可以恢复成人形,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实。背包勒得我肩膀生疼。我一边在黏糊糊、汗津津的腋窝和双乳之间喷除臭剂,一边读墙上的涂鸦。它们大多是匿名的求助。我感受到小隔间向我推来的责任。卷纸筒上某句潦草字迹的主人有自杀倾向,还有其他一些算不上危急的沉思:“我并不享受性爱,是不是很奇怪?”下面有一句回复:“收缩宫颈,放松,姑娘!”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原理。
从厕所出去时,我撞上一个刚进来的女孩,跌跌撞撞地从我身边经过之前,她活泼地抛出一句“对不起”,冲撞的力量让我受惊。我感觉轻飘飘的,甚至可以想象我就这样被从自己体内撞出,飘进了她的身体。
“等等,黛比!”
是赞茜。她没穿黄雨衣,我没认出来。
“嗨!”
“有空一起喝咖啡吗?”
“现在吗?”
“如果有空的话?”
“嗯,好啊。”
“太棒了,我先方便一下。”
❅❅❅
赞茜从厕所里冒出来,看起来就像香水广告女郎。她穿着阔腿裤,一件蓝色针织套头衫,那顶低圆帽要是出现在比利的旅行拖车里也不奇怪,可戴在她头上却调和了一身搭配。
“走读感觉怎么样?”我们汇入快速流动的下楼的人群中时她问道。
“挺好的。”
“你来都柏林路上要多久?”
“火车大概四十分钟。但我们住的地方离火车站开车差不多要二十分钟,加起来一个小时左右吧。”
“所以你住在地地道道的乡村呀?”
“嗯,我住在农场上。”
“那很棒啊。你们养哪些动物呢?”
“我们只有奶牛。是个奶牛场。我舅舅的。”
“你在里面干过活吗?”
“今天早上是我挤的奶。”
“我天!要多久?”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你一个人挤奶吗?”
“嗯,但詹姆斯打扫牛棚的时候会顺便关照我。”
“詹姆斯是你舅舅?”
“不,詹姆斯只是在农场干活。我舅舅早上起不来。他昨晚出去了。”
“哈哈,礼拜二晚上就出去?”
“对比利来说,每天晚上都可以出去。”
我跟着她从一扇我之前从没留意过的侧门走出去。一辆救护车飞驰而过。我准备过马路,她却依然站在路缘,望着我。
“怎么了?”
“你刚才是在胸前画十字吗?”
我脸红了。“哦是啊。习惯了。”
“太可爱了。”
我想叫她立刻滚蛋。
“抱歉,这话有点居高临下。”她说。
“挺好的。”
“我是想说,那是好事儿。”
“我不太信教。”我说。
“我明白。我是说,我也讲不好。我不说啦。”
❅❅❅
我们穿过马路,走进一家咖啡馆。里面挤满了学生和游客,窗户上都凝结满了水珠。咖啡机声音大作,听起来好像是在施工现场。
“我去找张桌子。”赞茜喊道。
我不确定队伍从哪里开始排。
“你在排队吗?”一位女士问我。
“抱歉,不是。”我说着挪到一边。
赞茜凑到我耳边。“我给咱俩在那边找到位子了。”
“太好了,谢谢。你想好喝什么了吗?你要先点吗?”
点餐就是一种折磨。我饿坏了。我想吃午饭,但价格不菲。赞茜点的是花草茶,所以我点茶和巧克力蛋糕。没有会员卡,我向收银女孩连连道歉。
❅❅❅
我把我的那块蛋糕往赞茜那边推。“一起吃吧?”
“不用啦,谢谢。”
“我说真的,帮我一起吃。”
“我吃不了。我坚果过敏。”
“噢。”
“是啊,我以前根本就想不到自己会过敏。我以为过敏的都很弱。结果发现我自己就很弱。”
“你喜欢薄荷茶?”我指着她的茶问。
“不,也没有吧。”
“那你还点?”
“我在努力适应花草茶,因为它们有益健康。”
“花草茶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做的雏菊香水。把花碾碎放进水里。就连小时候我都没傻到去喝它。”
“听你这么说我感觉好多了,花了五块买这玩意儿。”
“你逗我呢?”
她指指收银台上方的黑板。
“简直就是抢钱。”我说。
❅❅❅
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如实向赞茜诉说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你妈妈和一个二十四岁的人约会?”
“没错。”
“她多大了?”
“三十六。她十八岁那年怀上我的。”
“哇哦。那你爸爸也很年轻?”
“她从没跟我说过我爸是谁。”
“连你都没说?”
我摇摇头。“说实话,我觉得可能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听起来很棒啊。以后你结婚的时候等着瞧吧。乡村版《妈妈咪呀》。”
赞茜总是滥用“很棒”这个词。她不喜欢谈论自己。关于她,我只知道她坚果过敏。
“你的手指是怎么一回事?”她问,好像已经察觉到我想在提问游戏中赶超她。
我伸出我的左手。“童年事故,”我说,“被门夹了。”
❅❅❅
每年春天,妈妈都会到我们家附近的地里去采灯芯草,为整个教区的人编圣布里吉德十字
 。二月伊始,她会带上一个装满十字的柳条筐去参加弥撒,神父会在圣坛上向她致谢。
。二月伊始,她会带上一个装满十字的柳条筐去参加弥撒,神父会在圣坛上向她致谢。
七岁那年,我想给她帮忙。长着灯芯草的那片地叫作沼泽——靴子踩上去吧唧响的童年中间地带,我一直都没弄清楚围着我的那片草到底生长在地上还是湖里。过去,我常常想象有河马泡在灯芯草草丛后面。
妈妈用剪刀利索地剪下灯芯草,把它们绑成一捆一捆的,装进一个粗麻布袋。我跟在她后面,试着自己拔灯芯草,但它们就是纹丝不动。通常,我越是努力讨好妈妈,她对我就越没耐心,但这次她忍了我,因为外公在附近挪围栏。我问能不能帮忙,她让我跟在后面拖那只装灯芯草的袋子。
我们带着灯芯草回到家。我尽量不出声,但就连我的沉默都能把她惹恼。
“出去玩,黛比。”
“但我想帮忙。”
“我不需要帮忙。”
“求你啦妈咪。我会很乖的。”
“我没空教你怎么编。”
“我知道怎么编,我们在学校里用烟斗通条编过。”我得意地冲她笑笑。
她从桌上抄起灯芯草就朝自己屋里走,那捆草像婴儿一样被她抱在怀里。
“我想帮忙,求你了,妈咪。”我开始哭,她开始跑。我追着她在走廊一路跑,伸手不让她关门,但她把门摔上了。我的手突然痛得眼前一黑。
❅❅❅
那天,我失去了两根手指的末端——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比利带我去了医院。等我们回到家,妈妈没提我的伤情,却给我泡了杯茶。那天夜里,她趁我熟睡把一封信塞到我枕头底下。这封信佯装道歉,实际上,她解释了为什么出现那种状况是我的错。
礼拜天,妈妈带着圣布里吉德十字去参加弥撒,神父在圣坛上向她致谢。人们出教堂回家时各拿走一个。这种十字是放在门廊上保护全家人免遭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