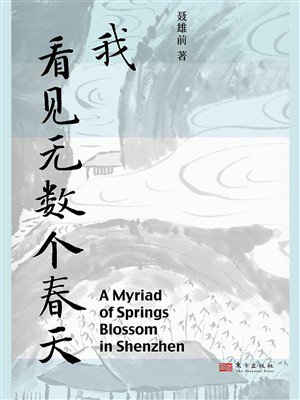阿温逃港记
一
1975年7月,温展云同学初中毕业了。他一直在东莞塘厦中学读书,一直当班长,一直是体育运动和文娱宣传的骨干。在他同年级的三个班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位列前十。初中毕业考试的成绩公布后,温展云同学满怀信心地去看榜,左看右看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他就去问他的班主任,班主任支支吾吾;他再去问塘厦中学的校长,校长说:“你家阶级成分高,书读得越多就越危险,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阿温回到家后大哭了一场。知子莫若父,他的父母知道阿温性格倔强,就安排兄弟姐妹盯一盯,确保家里不起幺蛾子。阿温有五个兄弟姐妹,姐姐最大,妹妹最小,中间是三个兄弟,阿温排行第二。阿温在家里不吃不喝,睡了四五天,经不起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抚慰,终于爬起来了,但眼神依旧空洞,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直到他的一个亲戚来他家,说惠阳地区文工团正在招生,要不要去试一试。阿温一听,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洗刷、穿衣、照镜子,叫姐姐帮他剪头理发,活生生的一个“曾志伟”。吃完午饭,他跟着亲戚坐了四个小时左右的公共汽车来到惠阳,在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守在惠阳地区文工团门口。七点钟文工团的大门没有开,八点钟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人,是汕头地区一个小青年,到八点三十分时,稀稀拉拉地来了二十来个俊男靓女。八点三十分之后,竟然又来了三十多个人。九点一到,工作人员就开始发报名表。宣传部领导、文工团团长、编剧和两位优秀演员坐在排练厅前排打分,五六十个文艺青年依次上台展示才艺。
阿温尽管是最早来的,但他绝不出头,等到二十多个人表演之后他才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能歌善舞,一直有“小曾志伟”之称。他走上台,脸不变色心不跳,安安静静,像一棵松一样站着。十秒钟,三十秒钟,四十五秒钟,当台下观众开始要发笑的时候,阿温稳准狠地唱出“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跨雪原的三个啊,气冲霄汉的六个啊……完全对标童祥苓的动作、声音和气势。台下的掌声雷动,至少持续了三分钟,五位老师更是第一次站起来为他鼓掌。作为“文革”末期的地区文工团,宣传“打偷渡、保经济”的任务非常重要。在阿温之前的二十多个文艺青年中,只有一两个获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在阿温之后的三四十个文艺青年中,也没有一个人的掌声超过他。一上午下来,五位老师都给阿温投了票。然而,当宣传部部长问及他的“家庭出身”时,阿温就活生生地被刷下来了。
阿温没有哭。
二
阿温的父亲找了许多关系,把阿温搞进了塘厦农机厂当学徒,工钱每月15元。但是他还是执着地热爱文娱宣传工作,先是当了塘厦人民公社文娱宣传队副队长,边工作边排练,后来把文娱宣传队直接搬到塘厦农机厂边上的一个仓库。1978年年初,阿温的哥哥咬着牙锻炼身体,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跑步十公里、游泳一公里,风雨无阻。他拉了弟弟阿温,也拉了几个没有读高中的同学,没想到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跑步和游泳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有三十多个小伙子参与进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外流人员就有四五百人。“游泳”这个词,在界河这边完完全全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提起游泳就有偷渡的嫌疑。幸亏,1978年9月全国游泳比赛在东莞县举行,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阿温的哥哥就钻了这个空子,在中秋节之前的十几天逃港了。阿温肯定和他哥哥商量过,但为避嫌疑,阿温提前和同事到东莞县城看了三天游泳比赛。
阿温他哥偷渡成没成功?一点儿消息也没有。阿温的娘天天在祈祷,阿温的爹天天苦着脸,嫁出去的大姐火速从外县赶回,阿温的弟弟和妹妹老老实实在家反省。批判他哥的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关键是被人民公社罚了500元,阿温家死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将多年积攒买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和蝴蝶牌缝纫机抵押给公社,公社领导说钱还不够,阿温的爹求爷爷告奶奶地花了大半个月时间才筹集到剩下的钱。还好,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逃港的哥哥有消息了,界河对面的塘厦老乡在个把月之后辗转报了平安。之前阿温的哥哥逃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报平安的塘厦老乡辗转告诉阿温一家,阿温的哥哥第一夜跑到了梅林山潜伏下来,第二夜花了三个小时急行军到沙河口,花了四五个小时在深圳湾顺风顺水地游到了新界。个把月的阴霾终于散去,大儿子如此幸运地逃港,真是菩萨保佑呵!阿温的爹很开心,唱着歌吹着口哨请亲戚和邻居吃了一顿饭。阿温的爹一直是做月饼、点心的大师傅,方圆几里地的喜事丧事都有他的影子。阿温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从来没有看到他爹如此开心过。
在阿温哥哥生死不知的日子里,阿温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打探各种各样的消息。有一天,他哥的一个朋友约阿温到一间冰室里喝冰水,想让他的弟弟逃港。阿温就说一个人搞不定,至少要两个人才能相互照应。他哥的朋友就说:“只要你牵头,十个八个都有。”阿温的豪气就上来了,说:“四个人最好,我牵头,你弟弟耐力好,其他两个一定要选身体强壮、游泳出众的伙伴!”
三
那年的中秋节是9月17日。阿温第一天在塘厦供销社买了一双运动鞋,第二天到东莞县城百货商店买了一个橡皮枕头,第三天向一个亲戚软磨硬泡借了一个指南针,第四天阿温再次检视自己的前途与命运,清醒确认自己不是培养对象。第五天中午下班,阿温召集三个伙计看南斯拉夫电影《桥》,四个人起码看过十遍这部电影了,完全是为了平复悸动的心。
大概是下午四点,他们登上塘厦火车站的列车,花了一个小时到了观澜牛湖,晚上急行军三个小时藏到坂田光头岭石鼓大队的甘蔗地里。那晚下大雨,他们一直哼着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一定把我来埋葬,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雨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阿温不断地为三个伙伴打气。天亮后,他们一直匍匐在草丛里,到下午三四点,他们悄无声息地溜到了梅林山。到晚上八九点钟,他们看到对岸的万家灯火,阿温说:“那边是天堂,死都要死到那里!”
塘厦到福田大概百里路,阿温一伙儿从来没来过,塘厦是国防二线,福田是国防一线,一线和二线的人民群众口音基本相同。当阿温他们打听到梅林山已是一线时,他们内心欢呼雀跃。第七天下午四点左右,两个基干民兵做例行的巡逻,不承想在梅林山深处和阿温一伙儿撞上,民兵一人拿着一根长棍,一眼就看出阿温一伙儿是偷渡者。阿温变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声嘶力竭地大喊:“两个两个一边,把棍子抢下来。”阿温一伙儿人里有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一把就抢了一个民兵的长棍,另一个民兵立即把长棍丢到了地上。阿温开始谈判,把他准备的药品、三公斤牛肉干都给了那两个民兵。民兵告诉他:“今晚放电影,是个好机会,你们中途从梅林水库游过去,沿着公路边埋伏。”阿温把民兵的话记在心里,看了半个多小时的电影,就开始撤退,在去梅林水库泅渡的路上,隐隐约约有人在跟踪,阿温急了,让三个人赶紧走。他自己闪到一棵大树边上,发现果然有两个人在跟踪。阿温出其不意地跳出来,一问是两个增城人,想偷渡。阿温问他们能游多久,增城人说已经练了两年多的游泳功夫。
阿温就答应了。
从梅林水库西边到深圳湾也就十几里路,白天在山上摘野果充饥,下午五点钟在国防公路路边的草丛中埋伏,认真摸清边防军巡逻的规律:第一组是三个士兵加一条狼狗,第二组只有三个士兵,第三组也只有三个士兵,然后循环往复。后来才知道,这国防公路就在现在的华侨城洲际大酒店旁边。等到七点多,天就黑了,阿温一伙儿从北边的草丛中飞跑出来,不到三分钟,就被狼狗发现了,幸亏四个人都身经残酷的训练。阿温撞到一个小草堆,翻了过去就是深圳湾,三个人拼命跟上去。两个增城人愣了一会儿,就被狼狗扑倒了。
阿温一伙儿四人在浅滩上飞奔,运动鞋很快就成了累赘。他们接近深水区的时候,齐刷刷用三口大气吹足了三个橡皮枕头,然后用一根结实的麻绳把橡皮枕头斜捆到背上。阿温真的是越逢大事越镇静,他竟然还拿出指南针辨别方向,发现偏了两度。阿温一伙儿游了两个多小时到达深圳湾的第一个航标,然后爬上铁架上的灯塔养精蓄锐。阿温一伙儿中的大个子抽筋了,阿温尽全力帮他做拉伸。大概过了二十分钟,阿温一伙儿又游了两个多小时,到达香港那边的第二个航标。他们又爬上铁架上的灯塔想歇一口气,不想香港的巡逻艇飞也似的飙来,围着铁塔转了三个圈,香港水警大声喊话:“我们看到你们了,赶紧下来,你们三个人赶紧投降!”阿温想:我们明明是四个人,香港水警难道瞎了?原来阿温还在给大个子做拉伸,阿温个子小小的,只露出灯塔下的一个头,大个子牛高马大坐在灯塔铁架第二级,完全把阿温遮住了。阿温人小鬼大,心说:切!你们三人投降吧,我躲到这里再游过去。他们三人就一个接一个从铁架上跳下水,巡逻艇停在那里放下舷梯让他们上艇。幽默的是,阿温还是被发现了,香港水警说:“你们再晚十分钟,我们就收工了。”阿温一伙儿气得吐血。
阿温一上岸,就闻到了香味,他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香味。他就想,香港真好啊,泥巴都是香的。香港水警把阿温一伙儿送到打鼓岭一个差馆(警局),先让他们洗澡,然后给每个人发了两套衣服。阿温一伙儿已经饿得不行,就低眉顺眼地问能不能吃几口饭,阿Sir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们早准备好了,阿温一看餐厅里有几十个偷渡者都在吃咖喱鸡饭和天府花生,他们四人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个大个子竟然吃了两份。然后阿Sir就让几十个偷渡者在两间大房子里打盹儿。早晨八九点钟,他们又吃了一顿咖喱鸡饭和天府花生。接着,一位女警官细声细气地和几十个偷渡者谈话,讲香港反偷渡的政策,要求他们遵守香港的法律,并一条一条地给他们解释。到下午一点多,他们又吃了一顿咖喱鸡饭和天府花生。
然后几辆警车就来了,阿温特别机灵,一跳上警车就守在后门的窗口,睁大眼睛盯着外面的世界。香港广告牌遍地都是英文,阿温一个字都不认识。车子开了三个多小时,他只认识四个字——“中国皮鞋”。大概五点钟,在文锦渡口岸,内地和港方的偷渡者进行交接仪式,在内地抓到的偷渡者叫“泥蛇”,在香港抓到的偷渡者叫“水蛇”,毫无疑问,在内地抓到的偷渡者远远多于香港。香港的几辆警车掉个头把车屁股放在港方的地盘上,中国的货车掉个头把车屁股放在内地的地盘上,一条红线,内地的车是空空的,港方的车是满满的。港方的“水蛇”爬上解放牌汽车后,直接就被拖到莞城收容所。东莞一个姓李的武装部部长守在收容所,直接以担心串供为由,把阿温一伙儿打散,一个一个地写材料,多次套路他们四人。幸亏阿温四人的材料基本一致,无非就是太穷了。三天后,东莞的几十条“水蛇”够满了一车,就开始一个礼拜的游街,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大多数是看客,少数人唉声叹气。
四
特别爱面子的阿温,当过文娱宣传队队长的阿温,得过无数次百米跑第一名的阿温,真的蔫巴巴了。半年多时间,阿温老老实实在人民公社种庄稼,领微薄的工分。谁都想不到,阿温一直在认真琢磨地图,脑海里把宝安县的地图路线搞得清清楚楚。
阿温开始单打独斗,他千方百计打听到东线莲塘的铁丝网有狼狗放哨,他从小就怕狗,更何况是狼狗,阿温就放弃了东线;在西线深圳湾已经碰了一次铁板,那五六个小时的海水浸泡让阿温脱了一层皮,游泳没伴儿太危险。那就只有中线罗湖火车站有隙可乘,阿温左思右想,确定在笋岗火车站扒火车。1979年4月,阿温熟门熟路地从塘厦火车站坐到观澜牛湖火车站,下车后带着干粮昼伏夜出,两天两夜后,在笋岗火车站等到了一列装着水牛的货车,货车车厢上严实地盖着帆布。凌晨五点多钟,阿温不声不响地用刀割断一根绳子,迅速蹲到车厢一个角落藏起来。大概过了二十分钟,火车直奔罗湖火车站,接受半个多小时的检查——谁会想到水牛肚下还有一个偷渡者阿温——就放行了。火车吭哧吭哧、慢慢悠悠开向香港大埔墟站,做好各种准备的阿温提前从火车上跳了下去。
阿温之前看了很多香港影碟,清清楚楚知道,从陆地上偷渡绝对不能穿破衣烂裤,他早就准备了西装革履。在跳下火车的那一瞬间,他毫发无损,立马就往铁轨边上的树林里钻,三下五除二脱下带着牛屎味的衣服,还没等到裤子拉上,一队五人的尼泊尔雇佣兵就把他团团围住。
阿温开始还试图沟通,半分钟后就知道这是鸡同鸭讲。阿温乖乖地举起手来,被五个雇佣兵带到附近的警局。这次阿温没吃咖喱鸡饭,也没吃天府花生,警官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就让他吃了一碗面条,然后用警车把他送到文锦渡口。
阿温愤愤不平,在香港都没有睡一晚,也没有和哥哥见一面。内地的警察连夜把他送到樟木头收容所,关了一个星期,然后十里八乡游街,再罚钱。
阿温呢,死猪不怕开水烫。
五
不到一个月,阿温横下一条心又纠集了两位街坊邻里。这两个小伙子一直在跑团,孜孜不倦地练游泳练耐力,时刻都在准备偷渡。阿温说,这一次还不成功,我就一头撞死。其中一个小伙子告诉阿温,他爸天天在家烧香敬菩萨,应该会成功的。阿温还是有些心虚,把干粮、橡皮枕头、指南针、药品等备齐之后,第一次主动跪在堂屋的神龛下,足足静默了三分钟,还叩了三个响头。
阿温清楚记得,第三次逃港的时间是1979年5月18日。三个人在塘厦火车站上车,到观澜牛湖火车站下车,然后急行军六七个小时到达梅林山,差不多天就快亮了。阿温发现梅林山的山顶上有一大片麦田,他们三人就钻进麦田的深处躲藏下来。经过一白天毛毛细雨的洗礼之后,牛蛙的叫声此起彼伏,夜黑得深沉。阿温又想从梅林水库游过去,一摸口袋空空如也,里面的指南针竟然不见了,阿温吓出一身冷汗。梅林水库这么宽阔,黑乎乎的一大片,阿温就说,我们转个圈往西边走,最多也就两三个小时到深圳湾。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沿着塘朗山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拐个弯就走到了塘朗山的北边,越走越远,一直走到了宝安的羊台山。
天亮了。阿温哭了。
跟着他的两个小伙子也苦着脸。阿温说:“这一次真的是碰上鬼打墙、迷魂阵,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赶快把橡皮枕头和药品埋到土里,每个人只留一点点干粮,赶快把换洗衣服拿出来穿上,不能留下一点点破绽。”然后三个人买了第一班从宝安到惠阳的公共汽车票。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阿温说,往南边走就是界河那边,检查得很严格;往北边走就是内陆,检查应该很随便。最重要的是,阿温需要扯一个谎才能圆了前两天失联的场,他就带着两个小伙子到惠州的姐姐家住了一天,然后,就说三人走亲戚去了,并且兴高采烈地拿出回家的车票亮一亮。
六
不到黄河心不死,正是阿温的画像。
1979年8月,他和一个姓冯的小伙子结伴从蛇口偷渡。那一晚下水时风平浪静,一个多小时之后风雨大作,他们花了六七个小时才上岸,泥一脚水一脚爬到打鼓岭,好不容易藏到茂盛的草丛里。阿冯在上午八九点钟就顶不住了,偷偷地从草丛中爬出来想找点儿吃的,不承想被巡逻队发现,还暴露了阿温的藏身处。还是那个打鼓岭的差馆(警局),还是吃咖喱鸡饭和天府花生,还是发两套衣服,还是在文锦渡口交接……
下午四点钟,阿温、阿冯被送回东莞大朗园看守所。大朗园看守所的偷渡者有一千多人,那一天恰恰是看守所的“剃头日”,有十几个剃头匠在操场上把所有的偷渡者剃成光头,然后这些偷渡者鱼贯而入进了牢仓。阿温鬼聪明,拿了一件衣服包了头混到光头队伍里面。牢仓有两层,熟人必须分开睡觉,以免串供。半夜时分,楼上的仓霸找阿冯要香烟,阿冯说:“我只有两包烟,也不知道要关多久。”然后就给仓霸递上两根烟,仓霸冷笑一声,挥手就打了阿冯三个耳光。阿冯哭着大喊阿温,阿温一个滚子就爬起来,顺手就摸到了一个啤酒瓶,飞也似的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举起啤酒瓶就往仓霸的头上砸。仓霸的马仔纷纷从床铺上起来,阿温和阿冯背靠着背,拼命地打,把一个马仔直接打倒在尿桶旁边,一直拿着半截啤酒瓶的阿温,竟然在拼命时将自己的大腿上刺了一个洞。眼看敌众我寡,岌岌可危,阿温大喊:“我是塘厦人,如果塘厦人愿意帮塘厦人,就赶快起来打呀!”
东莞大朗园看守所是两层楼,一楼、二楼都有十几间房,每间房有二三十个上下铺。阿温冲天一喊,就看到一个人拿起一块床板开打,这一人开打,一大半的塘厦人就开打。阿温走近几步,我的天啊,竟然是他的班主任黄老师!黄老师见到他的班长,就振臂一呼:“阿温,守住楼梯口,谁敢下楼就打谁!”这么大的声响,当然惊动了隔壁房间的偷渡者,阿温的那个房间被堵得水泄不通;很快,这么大的声响,也惊动了一楼的看守所警察,要不是阿温死死地守住二楼的楼梯口,二楼的偷渡者一定会连滚带爬去一楼,甚至越狱,那就是爆雷的事故。
阿温在东莞大朗园看守所被关了七天,最后一天的下午四点,广播里一直在喊名字,“温展云交赎金”“冯某某交赎金”,但阿温和阿冯已无分文,到下午七点左右才有亲人来送赎金,赎金一人130元。阿温就想,我哥一年前偷渡出去被罚了500元,我偷渡只被罚了130元,真的划得来。
阿温包着头回到家里,一路上都在唱歌。
七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解放。从1951年起,深港双方封锁了边界。之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及周边地区,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外逃19000人;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0000人;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0000人。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总共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到香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乡贤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阿温四次逃港的经历,基本暗合刘宝树先生的判断。三次偷渡到香港被遣返,一次在宝安羊台山陷入鬼打墙,阿温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但物极必反,1979年被认定为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也是对深圳来说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时段。希望从废墟中破土,改革在躁动中萌生。如今回望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无论对1979年怎样看重都毫不为过。这一年,诗人北岛写下了《岗位》:“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到三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看到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沉默了许久,然后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邓小平同志在时代的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实事求是的省委书记吴南生,也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揭开谜底。他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奇怪的是,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收入为0.70元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日收入为60港币到70港币,两者相差近100倍。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了邓小平那句话的含义。
老百姓是用脚来投票的!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叶剑英、习仲勋、谷牧、吴南生、袁庚等老同志达成共识: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深圳,并迅速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啊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阿温嗅觉敏锐,打死都不会再当偷渡者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招入深圳特区报报社当后勤,几年后跟着报社一位领导筹建海天出版社,一直在社里兢兢业业做后勤工作,2018年光荣退休。我有幸和他共事四年,学到了他的乐观和认真。
社里很多人都对他念念不忘,为什么?是他的传奇人生。我第一次听到他那九死一生的经历,他的人和事让我心生无限感慨。
最后,阿温说他有三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他哥六十七岁了,还要在香港打两份工,这是不是风水轮流转了?第二个想不到:他唯一的儿子快四十岁了还不找女朋友,他真的很急。第三个想不到:他崇拜五十年的偶像曾志伟怎么变成了坏蛋呢?
我告诉他,曾志伟好像不是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