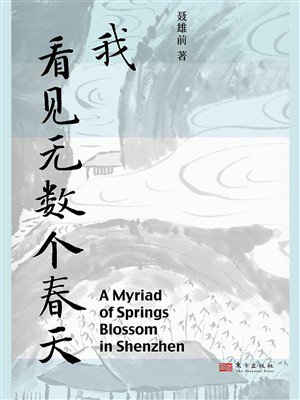怒火中烧的正月
一
1975年大年初一大清早,鹅公坪沉寂的土地上突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哭骂声。我爹和我娘急忙披衣起床,我爹准备打开堂屋大门,我娘一把将他扯住,说:“新年大吉,你要信点儿忌讳,外面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急急忙忙干啥?”接着,我娘就叫我起床,要我出去看看情况。我高高兴兴就答应了,脸也没洗就跑了出去。
哭骂声是从西边传来的,我循着哭骂声而去,很快就走到了邓家畬生产队那户王姓人家,只见他家已是一片狼藉。孙家嫂子带着三个女儿疯狂打砸:嫂子拿着一根棍子见人就打;大女儿孙玉梅,拿着一把铁钳到处敲打;二女儿拿着一把扫帚到处袭击;三女儿大概只有五岁,站在墙角里瑟瑟发抖。王家嫂子个头儿很小,又有残疾,却毫不畏惧,吆喝大女儿、二儿子和三女儿奋起抵抗,她气呼呼地大骂孙家嫂子:“你咯哒骚麻屁,你咯哒偷人婆,你还有脸来我家打砸抢呵,我拼死咯条命也要把你做的丑事揭发出来,告诉大队所有人,告诉公社所有人,告诉区里所有人,看你有脸活下去不,看你还骚不骚?……”在我来之前,已有两三个人在看架拉架,这一轮下来,邓家畬生产队几乎所有男男女女都来看热闹了,连相邻的鹅公坪生产队也来了一大半人。
两家的男主人都没有出现,想必都躲在自家屋里,一个懊悔,一个愤怒。
邓家畬生产队队长邓初冬也赶来了。初冬队长气得浑身发抖:“新年大吉,你们一大早就骂天骂地,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你们两家都有吃国家粮的,什么觉悟呵?什么境界呵?奸夫淫妇,丑死人了!要骂就到马路上去骂,要打就到马路上去打,反正你们也不要脸了,走,到马路上去!”泼辣的秋娥姐姐上前拖着孙家嫂子就走,初冬队长则顺手抱起孙家三女儿,催促着孙家大女儿、二女儿赶快回家。
这场架把王家嫂子的饭锅、菜锅、水缸都敲碎了,竹椅子和木凳子也损坏了几把。看架拉架的人都心中有数,看到要损坏柜子啊,桌子啊,床铺啥的,就有人紧紧拉住。把饭锅、菜锅、水缸敲碎是理所当然的——你奸了别人家的女人,一定要付出代价,不然这把火怎么发泄得出来呢?打一阵,骂一阵;再打一阵,再骂一阵,扎扎实实打骂了两个多小时,鹅公坪和邓家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知道了这件事。秋娥姐姐拖着孙家嫂子出门,出了一身大汗,然后搀扶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孙家嫂子慢慢往家走。刚刚走到她家的地坪上,嫂子突然转身直奔邓家大塘而去。秋娥姐姐愣了一两分钟,随即凄厉地大喊:“救命呵!救命呵!”
男男女女三三两两地聚在晒谷坪上嚼舌根,听到凄厉的“救命”声,两三分钟就赶到邓家大塘边。此时,嫂子已离开塘基十米远了,只看到一丛头发还漂在水上。邓初冬和邓家畬的一位后生朱云飞边跑边脱下棉衣、棉裤、布鞋,只留下一条短裤,跳入塘中。一个揪着她的头发,另一个拉着她的手臂,三下五除二就把她拖上塘基。见她神志还算清醒,邓初冬就立即安排四个人把她抬回家,叮嘱不要仰面向天抬,要胸脯向下抬,前面两个一手抓肩膀一手抓手臂,后面两个一手抱肚子一手抱膝盖,这样水就倒出来了。初冬和云飞冻得牙齿打战,急急忙忙回家烧一大把柴火,把寒气逼出来。云飞就提要求:“队长哥呵,我们奋不顾身抢救出一条生命,你总要打发我们一个包封吧。”
“打发个屁,谁给老子打包封?”初冬队长说。
二
这是一根人参引发的血案。
大概两年前,王家大哥拿回一根人参交给堂客,说:“去年你立了功,给我又添了一个崽,我现在双儿双女,每天睡着都会笑醒。这根人参奖励你,花了二十元从药店买的,好珍贵好珍贵哩!”众所周知,长白山野生人参大补,能够救命,鹅公坪最宽裕的人家也只能喝几口参须汤,王家大哥真是下了血本了。王家嫂子很感动,就认认真真把这根人参包得严严实实,藏到柜子深处。
不承想,去年的九月初,孙家嫂子又生了一个女儿。按乡里风俗,邻里邻居谁家生了宝宝或死了人,都是要去探望的。王家嫂子当然也去探望,问寒问暖呵,讲几句吉利话呵。孙家嫂子还在坐月子,王家嫂子坐在床沿上和她亲热地聊天,赞美毛毛(婴儿)长得精致。宾主尽兴之际,王家嫂子就看到一根人参摆在床头柜上,她指着这根人参说:“你真的有福气咧,你家老孙真的爱惜你哩,这么珍贵的宝物要多少钱才买得到啊?”孙家嫂子说:“老孙讲,只花了二十元咧。”王家嫂子笑眯眯地回家了。
回到家,她直奔收藏着珍贵人参的柜子,左翻一遍,右翻一遍,人参当然是不见了。她偷偷地大哭一场,她不是哭人参没了,而是哭男人很快就没了。为什么男人会没了?王家大哥尽管是孤儿出身,但书读得好,字写得好,浓眉大眼,身材修长,头脑灵泛,很年轻就当了乡村干部。而她个头儿矮小,有残疾,三十多岁就成了黄脸婆,养家糊口全靠王家大哥。她冰雪聪明,知道自己一闹必定家破人亡,乱搞男女关系在当时可是流氓罪,谁来养这些孩子呢。她就忍,她就咬牙,她就想招数。
想呵想,她就想清楚了,孙家大哥在外省的机械厂当工人,每年只有两次假,一次是“双抢”时的十五天假,另一次是春节的七天假。俗话说十月怀胎,孙家大哥最早也得是去年二月上旬才休春节探亲假,九月初就生娃,时间完全不对啊。电光石火间,她就抓住了孙家嫂子的死穴。
此后,她一两个月就去探望孙家嫂子一次,有时带点儿补品,有时带点儿糍粑,有时带点儿糖果,每一次都称赞这个小毛毛长得精致,长大后一定比三个姐姐都漂亮。
然后,她就被鹅公坪的乡亲们当成了蠢妇人。
有人暗示她:“嫂子呵,你要看紧大哥一点儿,现在好多妹叽都喜欢他哩。”
她就顶一句:“都老夫老妻的了,谁喜欢谁拿去就是了。”
有人说:“嫂子,有人讲生产队有个毛毛长得和你大女儿小时候一模一样,你晓得不?”
她就气呼呼地发飙道:“谁说的,我现在就去撕烂他(她)的嘴。”
有人就肝胆相照:“蠢嫂子呵,你想一想,×××七个月就生女,你有这个本领不?”
她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数,数了两遍。然后,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哭得痛不欲生,哭得山河变色。
她瘫坐在地上,伤心欲绝。七八个妇女有的拍后背,有的递手帕,有的端茶水,众口一词谴责孙家嫂子:有的说这女人家确实太骚了,天天涂脂抹粉的;有的说这堂客每天穿得花枝招展,肯定天天想着偷人;还有人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说,只怕奸情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好像有人在深夜碰到过你男人的单车停在她家屋后呢。
她听完爬起来,直愣愣地往塘边走去。当然,她心里有数,死不了。
她养了一天精神。丈夫骑着车回来过周末了,她做了一桌相对丰盛的饭菜,吃完后轻声细语给大哥讲,今晚我要办个事,你就不参加了,好好在家带一次崽。然后,她就带着两女一崽一人背一条凳子出门了,大哥还以为他们是去看电影呢。
她直奔晒谷坪而去,叫大女儿去初冬队长家借了一把柴刀和一个脚盆,叫儿子到云飞叔叽家借了一面铜锣。她把脚盆扣过来,从裤袋里取出一双破鞋丢到脚盆里,然后就叫儿子敲铜锣,重重地敲,狠狠地敲,敲了三四分钟,家家户户都有人出来了。于是,她就摆开阵势骂冲天娘。
首先,她痛诉家史。她问乡亲们:“我×××嫁到邓家畬有多少年了,有十六年了呵,你们看到我不尊重长辈不?不亲近邻居不?和哪个邻居吵过架不?出过恶言不?”
乡亲们众口一词:“没有,没有。”
她再问乡亲们:“我×××有自知之明,我三泡牛屎高,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要文化没文化,我就只有埋头做工,埋头相夫教子,尽量不给老王添麻烦。你们说,我在鹅公坪十六年是不是这样做的?”
乡亲们都说:“是这样做的,是这样做的。”
她就号啕大哭,说:“×得了呵,我的家要散了呢,我的四个崽女要吃苦了呢。我不要紧,上个吊投个塘喝瓶农药就一了百了,但老王怎么办呵?我那苦命的四个崽女怎么办呵?我要拜托给你们咧!”
晒谷坪上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站在邓家畬晒谷坪上的这大几十号人,大半此前就听过传言。此刻听当事人亲口挑明,众人心里都明白问题严重了,三三两两凑到一起,嗡嗡的议论声响成一片。
接着,她拿起两只破鞋,每讲一句,就重重地拍一下脚盆底,指名道姓列举着孙家嫂子的十条罪状。
“第一条,×××不守妇道,每一年春节都带着她老公到我家喝酒拜年,到现在我才知道,她是专门来勾引我家老王的,专门来给她老公戴绿帽子的,大家说她可恶不可恶?”
她就咬牙切齿地连拍两下:“可恶,真的可恶。”
“第二条,×××自作聪明,她老公二月回家过年,九月她就又生了个女儿,要不是好心人提醒我,我做梦都想不到她胆子这么大。她这是放卫星啦,她这是蒙蔽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她这是把她男人当成了一头猪啦。大家说她可恶不可恶?”
她就咬牙切齿地连拍三下:“可恶,真可恶,真的可恶。”“第三条,×××货阳奉阴违,我对她这样好,每个月都去关心她爱护她,每次都带着我们舍不得吃的东西,真心真意地把她当亲妹妹。千万没想到她有这么恶毒,嘴上喊哥哥,裤裆摸秤砣。我蠢呵,我眼瞎呵,我自作自受哩。”
这个时候,王家大哥抱着两岁多的小儿子冲进来,黑着脸说:“回去!”她说:“我还没讲完,那××的罪状有十条,我才只讲了三条。我明天还要到大队去讲,到公社去讲,到区里去讲,到县里去讲。我不但要讲这××,还要讲你这陈世美!”王家大哥就扬起手,她哭着喊着:“你打呵,你打呵,打死我,你就去找那个××,打死我,就清静了。”
云飞哥站了出来,把王家大哥扬起的手压下去,说:“不能打,打了就会死人的。”
秋娥姐带着一帮妇女站出来说:“不能打,嫂子讲得全对!”
初冬队长最后总结说:“家丑不可外扬,老王你一个国家干部,连裤裆都管不住,说出去对不起全国人民。你老老实实反省一下,过几天外省的干部回来过年了,够你喝一壶的。我还要想对策,看怎么给你擦屁股。云飞同志讲得对,搞不好就会死人的。”
就散了。
三
节前两天,孙家大哥如期回到鹅公坪探亲,之后便未曾出门。
大年初一大清早发生的那出闹剧,孙家大哥始终没有露面,受到了许多乡亲的质疑和诟病:有人说大哥太没有血性了,绿帽子都戴上了,哪里还要脸咧;有人说大哥可能是舍不得几个孩子,毕竟前面三朵金花人见人爱。和大哥共一个屋场的人就偷偷讲,他们曾透过窗户瞥见嫂子在地上跪了一夜,一直在哭咧。
孙家大哥在那个春节,一直没有出过门,也没有让任何人登门,家里死一般地静寂。也不知他哪天走的,鹅公坪每天只有一班公交,没有乡亲看到他上车。我估计,他一定是天亮之前就到走马街去等车了。
他这一走,留下了两个深远的后果:一是那个孩子在大半年后被送走,没有人敢问毛毛的去向;二是两家人成为四十多年的冤家,两家的大女儿和我同班,一直到高中毕业,她们都没讲过话,两家大人更是老死不相往来。
1975年春天,鸿文大哥、杏秋大哥带我一起踩田时,聊起了男女之事。杏秋大哥讲他到城步县烧木炭的经历,城步深山老林里的人太穷了,两毛钱就能和女人困一夜,有时三四个人轮流困,每一个人交两毛钱就可以,而女子的男人就在隔壁,一声都不吭。鸿文大哥就讲:“确实如此,哪像我们鹅公坪,二十元偷个情还闹出这么大的风波,王家大哥真是不值得。”杏秋大哥连连点头,说是不值得,你看看生产队哪一块麦地的中间没睡过狗男狗女,哪一条界基坑里没睡过露水夫妻?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傻笑。一点也不忌讳我这个十岁出头的细伢叽。
最好笑的是1978年秋天的一个周日,我跟着生产队的人到大芒垴山边的渠道去清淤,一个比我大五六岁的伢叽就讲,昨夜里×××回家,发现家门紧闭,晚上八九点钟就黑灯瞎火。他就使劲拍门,他堂客花了十几分钟才开门,顿时他就起了疑心。他大喊一声“杀鸡”,他堂客就晕倒了。他一想,不对呵,他堂客胆子蛮大的,肯定是偷人了。于是,他就拿起一把菜刀东敲敲西敲敲,不到五分钟就敲出来一个野男人。那个野男人从床底下爬出来的那个狗熊相,让他笑得岔了气,眼巴巴看着野男人跑了。
那个大哥哥最后气呼呼地说:“都是半边户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