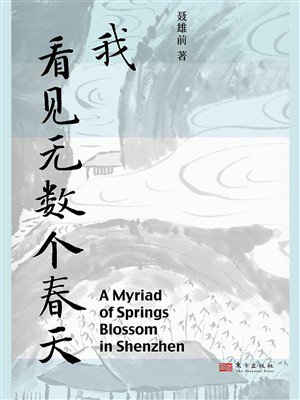鹅公坪的风,深圳湾的水
三把刀
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家乡双峰出了一回大名,“哑巴卖刀”的故事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位哑巴坐在京城街头摆地摊卖刀,地摊边竖着“哑巴卖刀,货真价实,一把二十,先试后买”的牌子。党报记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萌生了采访这位哑巴的念头。如何采访哑巴呢?答案是用笔。
记者写道:“你是哪里人?”
哑巴回复:“湖南省双峰县龙田乡金蚌村。”
记者又问:“这菜刀、剪刀、镰刀质量如何?”
哑巴自信地写道:“世界第一!”
这哑巴的字写得极好,记者一个劲儿地夸他的字有大家风范。记者当然不知道双峰县是中国的书画之乡。哑巴拿着菜刀砍石头,两把刀互砍,那削铁如泥的场景,深深震撼了记者。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就有了“营销不如真练,广告不如哑巴”的评论。那年寒假我回到家乡,远亲近邻都在讲,金蚌人真聪明,想出扮哑巴的妙招,赚大钱了。金蚌村是我堂嫂谭和莲的娘家,离鹅公坪十里地。每次侄女侄儿从金蚌村的外婆家回来,我都要逗他们:“又去打铁去了?当哑巴好玩不?”他们总是笑嘻嘻地点头。
金蚌三刀的历史可追溯至一百多年前,我甚至怀疑金蚌村曾是清末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打造刀枪的兵工厂之一。我请教金蚌村的好友贺文明律师,他证实1949年以前确有一批以打铁为生的铁匠,且多为大户人家。1956年公私合营改造成金蚌五金厂,成为当地唯一的铁工厂。又过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沉睡的金蚌,金蚌地界八个村的私人铁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超过百家。用文明律师的话说:“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叮叮当当银子来了。”
早期的三刀叫白水刀,只有铁没有钢,靠反复锻打提高强度,但仍不耐用,容易卷刃,刃口磨损迅速。金蚌人鬼聪明,很快提高了工艺水平,在刃口嵌入钢丝或钢条,使得刀具既能砍又能切,异常耐用。随后,镰刀和剪刀采用了嵌钢技术,菜刀则直接使用碳钢板。20世纪最后二十年,金蚌涌现出三位最著名的三刀代表:做菜刀的赵学林、做剪刀的龚时兵、做镰刀的胡明扬。他们技术精湛、头脑灵活,在政府引导和企业支持的良好营商环境下,竟然雄心勃勃地成立了三刀协会,并在金蚌地界将业务开展得红红火火。金蚌过半的劳动力,加上周边村镇的劳动力,组成了一支销售人员过万的队伍,他们叮叮当当奔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始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攻城拔寨、闯关夺隘的征程。在这二十年间,从白水刀到嵌钢条,从学自广东的铁把刀技术到碳钢板的使用,金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中包括专门生产钢板、刀背、刀把的各个环节,而刀厂则负责整体组装,包括焊接、打磨、淬火、抛光以及压花成型等工艺流程。金蚌菜刀、剪刀、镰刀的销量至少占据了全国市场的一半。
这门延续百余年的传统手工业技艺,历经风雨沧桑,三起三伏。金蚌三刀的销售过程,堪称惊心动魄。刀具管控具有特殊性,政府放开私人买卖时,金蚌人公开叫卖,称为“讲巴”;政府禁止私人买卖的时候,就只能装哑巴卖刀,刀具上统一打上“金蚌聋哑刀剪厂”的钢印。一装哑巴,就需要伪造残疾证、介绍信,这样做既能免于被当盲流遣返,又能免交各种杂税。20世纪80年代初,那位在北京摆地摊卖刀的“哑巴”,因政府再次放开私人买卖,终于可以公开地大声吆喝叫卖了。听我堂嫂谭和莲说,当时金蚌好多人愿意扮哑巴,那削铁如泥的表演、那残疾证带来的悲悯和免税优惠,甚至比正常人叫卖的效果还要好。
21世纪到来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金蚌三刀技术未能及时升级更新,市场被广东、浙江等地挤压,这个行业逐渐走向没落。除三刀行业扛把子赵学林的子孙进行机械化生产之外,有些人改行做农机、百货等,其他人则又回归到手工生产。如今,金蚌的铁工厂仅剩十家左右。
文明律师的父亲打了三十多年的铁,直到去世,一直打剪刀,质量一流,可以用三代。金蚌有人嫁女,按规矩要送一把剪刀作为嫁妆,而这些剪刀大多出自文明父亲之手。他说,哪里有父亲这样执执古古的手艺人。
1992年6月,我来到深圳工作,埋头苦干力求站稳脚跟。半年之后,在罗湖区桂园路红围街碰到双峰十四中一个邻班的同学。我问他来干啥,他指着市工商局的大门对我说:“想来工商局注册一个公司,少带了一份材料。”我说:“那好办,注册科副科长潘新水是汨罗老乡,我叫他出来。”三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不想第二天,他给我和新水一人送了一把菜刀。我说你是金蚌人呵,他说是呵。
此后,每当我经过罗湖区穿孔桥的时候,总会听到熟悉的乡音:“卖刀,卖刀,卖几好的刀”,我无数次停下单车,一只脚踩在台阶上问:“是金蚌人呵?”十有八九会得到回应。大概两年的时间,我的办公室就堆放了十几二十把菜刀,都是金蚌人送的。堂嫂谭和莲的哥哥是个奇人,在国内所有的大城市摆象棋残局谋生,百战百胜。他曾通过《女报》的办公电话找到我,我要请他吃饭,他说吃饭没什么意思,只有下象棋才有意思,留下一把刀就走了。我送了许多菜刀给同事和朋友,每一个都称赞我送的刀好。直到去年家里翻新后,我太太说:“要买刀了。”
想一想,金蚌的菜刀用了三十年了。
一张证
全国人民都知道,20世纪90年代,我的家乡湖南省双峰县龙田区是东南亚证件集团的总部,著名的“中国假证之乡”。党中央和国务院曾下发督办材料,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也多次追踪报道,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深圳应该是被东南亚证件集团攻破的第一个城市。为什么呢?第一,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不是熟人社会,在内地城乡,谁家的儿女上大学、当兵或成为工人,整个乡村或街道都心中有数。第二,鹅公坪离深圳近,深圳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东方风来满眼春,到处都是钱!能够直达深圳的空调列车只有从长沙出发的这一趟,其他地方的列车都要在广州中转。我的乡亲们眼光毒辣,面对着全国浪奔浪流闯深圳的各色人等,他们撒开大网做买卖。
一张证,决定一条命。
一张证,决定一个前途。
那个时候,深圳满眼都是年轻人;那个时候,深圳每一年都增加几十万人。我的乡亲们能够制作从一个人出生到死亡所需的各种证件:出生证、身份证、学生证、毕业证、获奖证书、退伍军人证、转业军人证、退休证、工商执照、驾驶证、行驶证、火化证等,甚至连国外的证件也能做得一丝不差。我接触第一个做假证的乡亲是院子塘生产队的,他家和我家是世交。他的父亲两天至少打了十个电话,说他崽被龙岗平湖派出所抓了。我一筹莫展,初来乍到还不认识一个警察,加之龙岗平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就只好说尽全力帮忙。第三天,救星出现了,《深圳法制报》的师兄刘刚强来到女报杂志社。那时正是夕阳西下,他来接太太回家过中秋。我看到刚强的警用摩托,眼睛立刻亮了起来。我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他夫人蒋睦民打了声招呼后,就坐着摩托赶到龙岗平湖派出所去“捞人”。那是1993年的中秋夜,我见识到了刚强出色的法律水平和沟通能力。
然后,我就不情不愿地开始了我的“捞人”生涯。我有一个巨大的软肋,家乡的老父老母还健在,侄女侄儿尚未成人。如果得罪了乡亲们,我的老父老母可能连上山都上不了。我清楚记得王辛勤老人办丧事那一幕,贵初、贵福兄弟没有第一时间去拜托各家各户帮忙,差一点儿就因“不懂礼数、摆臭架子”而门庭冷落。湘中人把出生讲成“落地”,把人生过程讲成“受罪”,把死亡讲成“上山”,出生是红喜事,死亡是白喜事,都看得非常重要,而人生的过程就是煎熬和受罪。我哥哥去世之后的十七年里,我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如果深夜电话铃声响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父母出事了。有几年时间,周末我带儿子到罗湖区德兴花园学画画时,开车来去的路上一看到0738区号的来电,我就会把车停到路边并打开双闪接电话,生怕噩耗从天而降。
还好,父母亲一年有几次电话,都是在大白天打来,我没怎么受惊。但家乡的乡亲们却惊到我了,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单“捞人”的活儿交给我父母,方圆十里地几乎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人来找我父母了难。他们带一只鸡或鸭,带一袋苹果或梨子;他们讲一段古,曾经给我家帮了个什么忙;他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哀求,只差没有下跪了。我父亲就发命令:“雄前宝,都是邻里邻居的,都是乡里乡亲的,你不搞定就不要回鹅公坪了哈。”
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搞,就咬牙切齿地搞。
在罗湖区桂园路红围街3号的院子里,我工作了整整八年。在这两三年间,桂园派出所民警至少抓了几十个从家乡来深圳制作假证的人。我求爷爷告奶奶地放了四五个,请刚强兄放了十几个,还请隔壁的《经济日报》驻深记者站邹大虎站长帮忙放了几个。那个时候,做假证的危害算是小事,搞好经济才是大事。到1996年年底,假证制作已经由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每个周末总有三五个人等在益田村77栋楼下的草地上,盼望着我去“捞人”。直到那时,我才坚决地说“不”。我在某杂志上发过誓,大意是:如果我不捞人或捞不出人,乡亲们把气发泄到我父母亲身上,父母去世,我就一个人挖坑把他们埋了。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在一本每个月销量达几十万册的杂志社当头目,名字、办公地址和通信电话都放在版权页上。我不找他们,他们找我一找一个准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李兵,他是李家朱妙玉的大儿子。妙玉姐太苦了,李兵从小也吃了许多苦,我如果不救他,良心就过不了关。第二个是同新叔叽的小儿子海燕,他在东莞做假证,被抓到闻名中国的樟木头收容所。我一个人去了一趟,又和刚强兄去了两趟,想尽办法也没搞定。同新叔叽和我父亲是干兄弟,大半辈子守望相助,我怎么能袖手旁观?第三个是梅山坪一个姓彭的人家,儿子被抓,在滨河派出所。他父亲就天天守在鹅公坪要我父亲“捞人”,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地磨。最后那王八蛋竟然威胁我父亲,说我家老坟山就在他家后面,他每年都去扫一扫看一看。我家老坟山在他家后面是真,他每年去扫一扫看一看完全是假话,纯粹是讹诈。我父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崽呵,老坟山动不得呀,你的祖先在里面,你哥哥在里面,我们怎么活呵……”
湘乡自古出刁民。1997年除夕夜,我坐在刚强兄的警用摩托上,他熟门熟路地在滨河派出所转了一圈,把那王八羔子捞了出来。我满腔怒火,在大年初一的凌晨出发,开车十一个小时,回到鹅公坪已是下午四点,我给父母拜了年之后,就准备叫上长斌、凤海、伏龙到梅山坪收拾这姓彭的,但被我父母死死劝住了。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带着三位伙计找上门去,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彻底服软才罢休。
后来我问了许多乡亲,做假证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乡亲们众说纷纭,大致可以确定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大家一致认为是福建莆田人带的头。乡亲们说,走马街有个灵泛的伢叽,在双峰十四中考大学没考上,一生气就跑到福建一家印刷厂打工。一开始是铅字印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激光照排系统很快取代了铅字印刷。走马街的这个伢叽跟着他师父学了两年多,看到他师父经常帮各路朋友做证件,而且做得惟妙惟肖,于是他就牢牢记住了各道工序。他师父或许没有牟利之心,徒弟却计上心来,很快就在走马街风生水起地做起了假证生意。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有时候真的害人。扫描、排版、复印、做钢印、刻私章,一台电脑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你要什么证就有什么证,要什么文凭就有什么文凭。走马街的那个灵泛的伢叽,就在走马街、鹅公坪、太平寺等热闹地方放出风声,并在走马街供销社、双峰十四中、秧冲供销社、秧冲中学、太平寺双涟火车站的大门上、墙壁上、电线杆上,贴上办证的广告。正是春潮滚滚、市场喧嚣的大好时光,无数的乡亲要进城,无数的青年要出湘闯世界,而这些证件、这些文凭就成了他们的“护身符”。
1993年下半年,刚强的太太蒋睦民从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调到《女报》当发行部经理,上任伊始便着手招聘司机。在人才市场,她看中了一个湖南小伙子,证照齐全。蒋大姐带着他到印刷厂运杂志,这小伙子虽全神贯注,但一看就不熟练。他小心翼翼进到桂园路红围街的小巷子,离仓库还有十几米就把车停下来,打开车厢就卸货,一路都是小跑。蒋大姐笑问:“你是不是还没出师啊?”小伙子顿时满脸通红。蒋大姐心善,决定留下他。过了几年,他承认自己办的是假证。
在《女报》工作的前十年里,每次招聘她都会碰到持假文凭的。我的母校湘潭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文凭造假的最多,这既因为湖南离深圳近,也因为北大、清华、中大的文凭太硬。鬼聪明的同事罗尔,高中未毕业就来深圳打工,先在原野公司当保安,后来进入《女报》做发行做编辑,写得一手好文章,做了七八年调不了户口,于是也偷偷买了个湘潭大学的假文凭,有我在他就不敢拿出来。看到他的成长,看到他的努力,我从市劳动局辛本兰大姐那里争取到一个“深圳十佳外来劳务工”的指标,才帮他拿到了深圳户口。他几年后才告诉我,我就说:“你命好。”
马克思曾引用过一句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无知者无畏,如果走马街那个伢叽知道这句名言,再贫困也不敢如此以身犯险。那个时代,最高级的证书也就二三十元,而他的批发价竟然高达三四百元,完全是死了又死的罪行。更何况,他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参与其中,胆大包天,一心一意地打造假证“托拉斯”。他的前辈,那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绘制五块、十块人民币的“画家”——已经醒悟。如今,他们的子孙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纷纷发起挑战,才使得走马街那伢叽不能一家独大,假证的价格也逐年下滑。
有十来年的时间,在深圳的人才市场、大企业招工市场、东门市场、华强北市场以及桥洞等地,都能碰到老乡,听到乡音。有时候我行走在大街上,会传来一丝轻轻的“办证,办证”声,我就停下来问:“你咯哒伢叽,书不读,工不打,是哪里的?”这伢叽就满脸通红,老老实实报出大队生产队的名字。好几次有人直接喊我雄前叔叽,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他们住在哪里,做假证的和销售假证的怎么分成?我一概不知。但每年回家探亲,我都能看到新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家乡的年轻人再次破了天荒,背着假证在祖国的大地上到处贩卖,背出去的是纸,带回来的是钱。咸同年间的湘军打得艰苦卓绝,而一百多年以后的假证生意却做得轻轻松松,家乡的年轻人坐飞机、坐火车,把全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市都走遍。那些年间,我基本上每年春节都回家陪老父老母过年。随便问一个年轻人在哪里做生意,不是上海就是乌鲁木齐,不是哈尔滨就是昆明。最离奇的是,有一年来新哥哥的儿子朱强是从拉萨赶回来过年的。我问他:“藏语你都懂?”他连连摇头。
一幅图
新千年以后,假证生意开始奄奄一息,原因在于计算机技术使得各学校毕业生的信息变得清晰可查,查文凭查证书手到擒来。家乡的年轻人实在聪明,做了最后一次挣扎,以PS技术制造淫秽照片,进行敲诈犯罪。
Adobe Photoshop,简称“PS”,是由Adobe Systems开发和发行的图像处理软件,主要用于处理像素构成的数字图像。借助其丰富的编修与绘图工具,用户可以高效地进行图片编辑。“万恶”的乡亲们到一个地方,就钻进图书馆收集各种当地名人的照片、经历、电话、工作单位,然后打印出一封千篇一律的敲诈信:“×××先生,你人面兽心、道德败坏,十天以内不打钱到这个银行卡上,我就举报到监察局和纪委。”信内附上一张PS图片,图片上是一张大床,床头拼接了名人的头像与一张从港澳偷渡来的黄色杂志中的裸女照片。据说,发出一百封这样的信,至少有五人会选择破财消灾,金额在五千元至一万元不等。
然后,“万恶”的乡亲们开始变本加厉,通过短信和微信发送带有网址的敲诈信息,其中的照片和动图不堪入目。那些不检点的官员、教授、企业家成为乡亲们的刀下鬼,有的老老实实交钱,有的直接被吓死。2005年前后,PS敲诈犯罪活动达到了高潮,甚至惊动了中央。中央随即组织严打行动,潭邵高速公路的广告牌和双峰境内的国道省道县道的广告牌上,都贴满了严打PS敲诈犯罪的宣传标语。全省、全市、全县投入大量人力进行地毯式排查,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才终于遏制住了PS敲诈犯罪的势头。那几年,县里的领导见到我就唉声叹气,也透露一些内部消息,说有百把个官员、教授和企业家或自杀或自首,都与双峰的PS敲诈犯罪活动有关。当时,我还快口快嘴地说:“这不是好事吗?他们都是成功人士,竟还如此下作,活该倒霉!”县领导说:“我们也这么想过,但走马街的老百姓确实扰乱了市场秩序,实施敲诈犯罪活动在先,败坏了人心和风俗。”另一位领导则打趣道:“一毛钱就能寄一封信,一百封信才十元,撒出去一张网,至少能收回几万元。微信、短信就更便宜了,简直是坐地收钱。这都是双峰人鬼聪明惹的祸。”
我在深圳也不断受到骚扰,至少有七个湖南老乡拿着敲诈信要我分析照片的真假。还有一个常德的朋友要我帮他了难,我心里暗自嘀咕:“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然后,笑嘻嘻地说:“应该是假的吧?你要小心哟。”有个傻×心惊胆战地守了我两三个下午,一定要我找人去了难。我说:“家乡有几万个做这门生意的,我离开家乡多久了,我怎么知道是哪个人发给你的?”他竟然气呼呼地说我不够朋友。更多的外地朋友问我怎么回事,我一概回答:“身正不怕影子斜。”
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间,家乡蒙羞。如果曾国藩大人泉下有知,定会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吐血三升。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开始,曾国藩就一直讲教化讲血性讲爱民,有人生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有天道三忌,“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有为人四知,“知命,知礼,知言,知仁”;有修身四课,“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曾国藩大力提倡教化,兴办私塾,为湘乡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很快将老湘乡塑造成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人文高地。众所周知的“无湘不成军”“无湘不成校”的说法,来源于此;“中华女杰之乡”“中国书画之乡”“中国院士之乡”也来源于此。
双峰人有背井离乡闯世界的传统,也有叶落归根的传统。曾国藩一生信奉父亲曾麟书的家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史上可考的曾国藩第一封家书,就希望家人今后给他回信时“以烦琐为贵”,这充分体现了一个远方游子对家人和故乡的深深思念。同治五年(1866),已坐上两江总督高位的他,竟然接连四次上书朝廷请求辞官回籍,延续了儒家知识分子老来“乞骸骨”还乡的文化传统。纵观历史,哪一个高官、哪一个巨贾不以故乡为根?不以告老还乡、落叶归根为最终归宿?然而悲哀的是,这种文化传统在我们这几代人中却逐渐丢失了。
永远不要责怪老百姓。多年以来,教育农民一直是重大课题。但事实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顺境中,农民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推动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逆境中,农民是最大的苦难承受者。毫无疑问,乡亲们在改革开放后的犯罪行为,是穷疯了饿怕了的一种表现。如果他们有田园、有子孙,能够晴耕雨读,那么双峰老家定会成为模范乡村。
在全中国推销金蚌三刀的那些日子,上万的销售人员都变成哑巴,他们心里是不是很痛?
在全中国制假贩假的那些日子,几万乡亲基本上不与客户用语言交流,他们总是以短信、微信约客户,一手收钱一手递证,惜言如金,非常高冷。
在全中国利用PS手段敲诈犯罪的那些日子,几万乡亲一个县一个县地扫,一个市一个市地扫,一个省一个省地扫,做好自己的功夫后,就坐等鱼儿上钩,坐地收钱。
在这三次让双峰人引起全国侧目的事件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双峰人在行事过程中语言的缺失。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改进技术,与时俱进地融入高科技和互联网元素,但就是不说话。除了我,有谁真正了解他们的痛,有谁真正了解他们的病在哪里?只有我清楚,乡音是他们的死穴。
我曾说过,乡音是我内心深处千万次的羞愧,是我生命河流中多次遭遇的暗礁险滩。作为一个“把故乡天天挂在嘴上”的双峰人,作为一个普通话讲得最差的异乡人,我深深体会到湘乡方言的伟大和神奇。然而,我却始终无法将其转化为普通话,想尽无数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龙槐生的文章写道:“他讲一口湖南话,那是他的乡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就有的权利。然而,当他不由自主地被时代抛到另一个地方后,他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了一个错置的身份标签、一个‘错误’。从此以后,他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感动他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说服敌人。原本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照’,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疾病’的象征、一个标签——意味着话讲得不好、话讲得不通。”鹅公坪离衡山龙槐生的家不过二十里地,这段话讲到了我的心窝窝里。
同在一个时代,邻县的邵东是“假药之乡”和“盗版之乡”,另一个邻县是“假银圆之乡”。在几轮严打之后,这些现象基本没有了。只有吾乡吾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根本的原因在于,邵东人和新化人的普通话要好一些,他们在作案时总会留下语言的蛛丝马迹,而语言又为他们改邪归正留下了活路和空间。然而双峰人呢?语言既是他们的生所,也是他们的死穴。
时间是一剂良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通话的深度普及,大规模的造假一定不会再有了。1992年我去深圳时,年过七旬的父亲给了我十一块袁大头。除了土地和房子,这是他唯一的财富了。他说其中有一块是假的,他一块一块地吹,吹出了那块假的。他想把那一块丢掉,我没有同意。现在我肯定分不清了。
我母亲和父亲去世的时候,附近村子的人都来了,很热闹。我就负责磕头跪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