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藏书楼到图书馆:奇妙的“变形记”
现如今,无论是城市中巍然矗立的大型图书馆,还是校园里温馨雅致的读书角,都能给我们提供阅读的便利。这种便利,既得益于印刷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离不开图书馆事业的持续进步。要知道,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阅读环境,在古人眼中或许是一种奢望!
中国的藏书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类似图书馆功能的藏书楼,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官府、书院、寺院和私人四大藏书体系。在印刷术发明前的漫长岁月里,书籍主要靠人手工抄写,生产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使得书籍成为稀世珍宝。因此,藏书楼中的典籍往往仅供皇家贵族、学者或私人藏书家使用,普通百姓很难接触到。由此可见,今天我们能够如此便捷地阅读书籍、获取知识,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伟大发明。
不过,虽然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与现代的图书馆都有着保存和传播知识的使命,但其功能和体验却大相径庭。那么,古代藏书楼是如何转变为现代图书馆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还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继承关系,也就是说现代图书馆是由古代藏书楼演变而来的,在演变的过程中,藏书楼的服务范围、服务方式和服务对象慢慢发生了变化,最终变成了现在的图书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古代藏书楼随着清朝统治的结束,也随之消亡了。我们国家现在的图书馆是在学习西方图书馆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与古代藏书楼有着本质区别。还有一种“继始”观点,认为现代图书馆是国人基于传统藏书楼文化,借鉴国外图书馆的建设理念而创建的。
上述三种观点其实各有道理,在此笔者不去讨论孰是孰非,先来回顾一下图书馆在中国的成长历程。
首先,让我们回到明朝万历年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他不仅将欧洲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此后两个世纪,陆续有欧洲传教士来华,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学术思想,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
随着中西交往的深入,晚清时期的一些驻外使节和留学生开始在其著述中介绍西方图书馆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当时中国一些开明士绅注意到,西方图书馆开放、共享的办馆理念,与中国传统藏书楼的封闭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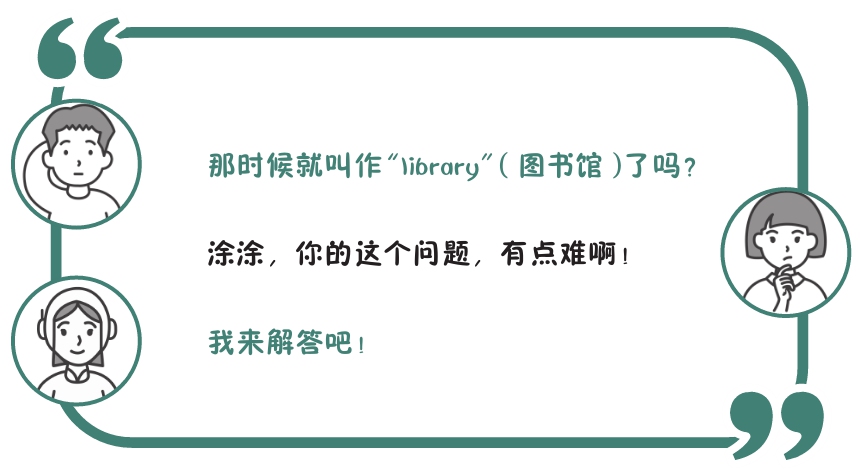
你知道吗?我们平时经常提到的“图书馆”这个词,其实有着一段有趣的“跨国旅行”故事呢!
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语中,“papyrus”表示纸莎草,它是西方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书写材料。后来,古希腊人就用和“papyrus”读音相近的单词“biblos”表示书籍,而“bibliothek”则表示存放书的地方。在拉丁语中,这个词则被写作“bibliotheca”。如今,在英语中,“bibliotheca”这个词仍然可以用来表示图书馆。
而我们更熟悉的表示图书馆的英文单词“library”则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古罗马人用“liber”(意思是书皮)这个词,慢慢发展出了“librarius”(关于书的)、“librarium”(书柜)这些词。到了中世纪,英格兰人把这个词发展为“librarie”,再后来就演变为我们现在英语中使用的“library”一词啦!
有趣的是,19世纪中期,“library”一词传入日本,日本人一开始将它翻译为“公共书库”或“大书馆”。直到1877年,东京一家图书馆印刷的图书目录上首次使用“圖書館”这三个字来对应英文的“library”和法文的“bibliothèque”。
在我国,“图书馆”这个新名词的首次亮相则是在1894年。当时,《教育世界》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里面第一次使用了“图书馆”这个新词。不过,当时“图书馆”一词的使用并不普遍,尽管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学习西方图书馆模式的新式藏书机构,但它们仍然沿用传统的称谓——藏书楼。
直到1903年,事情才有了变化。清政府发布了一份重要的官方文件——《奏定大学堂章程》,里面正式使用了“图书馆”这个词。这份官方文件就像给这个新词发了一张“身份证”,让它成为官方认可的名称。从此以后,“图书馆”这个充满现代感的名字就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流行开来,逐渐取代了传统“藏书楼”的叫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