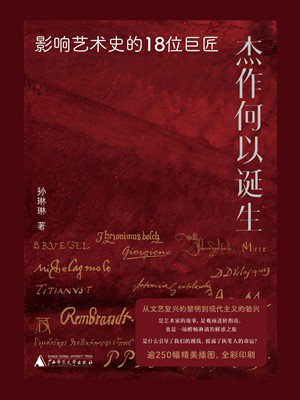第五章
博斯 世界是一个干草堆
荷兰人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约1450—1516),是达·芬奇的同代人。如果说达·芬奇的一生都在探求万物的真相,那博斯早早地就知道了。只不过,他用幻象取代了真相。
博斯生活在布拉班特公国(Duchy of Brabant)的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这个地名意为“伯爵的森林”,也是博斯名号Bosch的来源。Hieronymus,拉丁文读作“杰罗姆”。可想而知,他的画作《祈祷中的圣杰罗姆》( St. Jerome at Prayer ,图5.1)坦白了博斯的私人趣味——一个在林地间长大的孩子,时常钻到树洞里玩耍。被岁月掏空的洞令他着迷,长成强大的意象。这意象在他日后的画作中不断重现。

图5.1 《祈祷中的圣杰罗姆》,约1482年
博斯出自绘画之家,祖父、父亲、三个叔叔,以及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都是画家。他在家庭作坊学艺入行,30岁左右成家自立。1486年,约36岁的博斯加入斯海尔托亨博斯圣母兄弟会。这个保守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与欧洲其他地方的七千名精英保持着联系。通过圣母兄弟会,博斯结识了不少赞助人,尤其是勃艮第与西班牙贵族,其中包括勃艮第荷兰的统治者卡斯蒂利亚的菲利普一世(Philip I of Castile)。
现存被认为出自博斯的画作不到四十件,其中三联画约有十六件。这些画作虽然有祭坛画的形式,却不是为公众而作的祭坛画,而是满足贵族和精英需求的“高级定制娱乐系统”。这些画作没有其他佛兰德绘画里精致的笔触和层次,博斯尽可能平直地描画一切,只是为了呈现他的幻象。
早期的博斯作品多为定式题材,但已显露出些许奇幻的趣味,这种趣味刻骨铭心地伴随了他一生的创作。《死亡与守财奴》( Death and the Miser ,图5.2)是一幅残缺三联画的右侧面板,场景出自15世纪下半叶流行的临终指南《死亡的艺术》( Ars Moriendi )。画面表现在守财奴生命的尽头,善与恶进行最后的较量。画中多时空场景并置,正在打开箱子的人,代表床榻上濒死之人生前的敛财行为。符号化的神怪形象,在博斯日后的作品中频繁出现。

图5.2 《死亡与守财奴》,约1485—1490年
三联画《贤士的崇拜》( Adoration of the Magi ,图5.3)乍看是规规矩矩的《圣经》故事,该有的元素都有,情节明晰。但博斯在传统定式里塞进很多私货,心思都用在细节填充上。他把自己的乐趣和世界观带入画中,形成独有的风格。怪诞的形象出现在破败小屋内外,成为神圣时刻的目击者。左侧面板呈跪姿的赞助人和圣约翰身后,有一个回头张望的短小身影,那是圣约瑟,正在火边为圣婴烤干尿布。右侧面板的女赞助人和圣阿格尼丝身后,熊和狼正在攻击路人。远处的风景完全按照博斯的执念创造,有大规模的战斗场景和风格来源不明的高大建筑群。三块面板的风景不是完全连续的,天空正中艳阳高照。这些罗列的幻象,被博斯整合进经典叙事,世界的样貌如是,才能让他满意。

图5.3 《贤士的崇拜》,约1494年
合上面板,是《圣格里高利的弥撒》( Mass of Saint Gregory ,图5.4),这是当时流行的图像,经常出现在手抄本中。博斯依然画得精致,他在边框内又绘制了一重边框,这一重边框中描画的内容为画面增加了一层空间。整个画面的细节刻画简练而克制,有一种肃穆悲怆的气氛。可以想象,当画板打开,外部和内部形成的反差对观者的冲击。两个彩色的人物是后世添加的,他们是这件作品的捐赠者。

图5.4 《圣格里高利的弥撒》,约1494年
《耶稣背负十字架》( Christ Carrying the Cross ,图5.5)是三联画残存的左翼。画面构图饱满,层层叠叠的士兵与门徒拥向被十字架压弯了腰的耶稣,人物造型和表情是漫画式的。博斯没有顾及透视法,他的注意力在细节上。画面右侧盾牌上胀着肚子的蛤蟆象征异端,是博斯常用的符号。

图5.5 《耶稣背负十字架》,约1500年
面板背面绘有《有风车和学步椅的孩子》( Child with Pinwheel and Toddler's Chair ,图5.6)。孩子手里拿着风车,扶着古代的学步椅,寓意是耶稣从蹒跚学步走向殉难。

图5.6 《有风车和学步椅的孩子》,约1500年
随着经验的积累,博斯的个人风格渐渐成熟。《圣安东尼的诱惑》( Triptych of the Temptation of St. Anthony ,图5.7)是当时的热门题材,讲述埃及的圣安东尼独自隐修、抵御诱惑的故事。以故事为依托,博斯经营着自己日趋娴熟的三段式画面。在一主二副的框架下,以自有的逻辑填充繁复的细节。他用高反差的色调和高强度的冷暖对比,令第一眼看到三联画的观者,被不明就里的紧张感所吸引。

图5.7 《圣安东尼的诱惑》,约1501年
博斯制造了一个灾难现场。大地开裂,地火升腾、浓烟笼罩,精灵和鱼鸟在空中飞行,黑夜与白天并置,圣人与异端共处。洞穴的概念始终被强化,形成叠加交错的空间。当这些空间各自被加入不同的叙事,产生了今天我们熟悉的电影语言“蒙太奇”的效果。
绘画对于博斯,是纯粹的宣讲工具,也是当时最先进的视觉手段。在这件作品中,博斯展现了他强大的控制力和令人抓狂的劳动量。他知道以不断重复的符号化形象强化意念,也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这些形象隐与现的关系。他不厌其烦的、谜语一般的细节描绘,成功地勾起了观者的好奇心。观者会以解谜的责任感,耐下心来进入博斯的世界。这样看,一定有一个坚实的精神支柱,支撑起博斯和他的委托人们共有的意识形态。这赋予博斯笃定的使命感,他庞杂并且自信的工作就是证明。
在三联画中,主人公圣安东尼按照叙事逻辑出现了四次。左侧的面板,虚弱的圣安东尼在众人搀扶下走过木桥,他身边的红衣人据信是博斯的自画像。
面板外部昼夜二分,上演《耶稣被捕与耶稣背负十字架》( Arrest of Christ and Christ Carrying the Cross ,图5.8),仍是传统的灰色画,只有些微深红色的点缀,象征火焰。相对于里面的画芯,博斯的表达收敛多了。似乎这样的“外冷内热”成了他的一种定式。

图5.8 《耶稣被捕与耶稣背负十字架》,约1501年
《最后的审判》( The Last Judgment ,图5.9)的画面构成,继续了《圣安东尼的诱惑》的方式,但是三段式叙事的时空切换是完全不同的。左侧面板是关于亚当和夏娃的荒唐故事。中间面板的顶部描绘了造物主的光明境界,下部则花样百出地表现人类所遭受的惩罚。右侧面板干脆就是地狱图景。

图5.9 《最后的审判》,约1504—1508年
博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本领,他的每一个符号化的形象描绘都是清晰的,似乎有具体的所指。他用一种行为逻辑,把这些形象区分或者联结。当这些局部合理的碎片被整合在一起,在视觉上是神奇又丰盛的,同时促成了解读的荒诞感。这一套方法不是美学的,更像是视觉经验的编程法,在观者的心理层面产生影响。博斯使用的是一个小圈子的语言系统,这也许正是他所加入的斯海尔托亨博斯圣母兄弟会的共识。其具体的解释已经失传,但博斯的绘画足以让今人略知一二。
外部面板依然是静穆的纯灰色画——《圣詹姆士与圣巴沃》( St. James and St. Bavo ,图5.10)。左侧面板中,圣詹姆士在罪恶的土地上朝圣。右侧是圣巴沃救助穷苦人的场景,其中的老妇形象还出现在博斯其他画作中。

图5.10 《圣詹姆士与圣巴沃》,约1504—1508年
《耶稣加冕荆冠》(
Christ Crowned with Thorns
,图5.11)可能是博斯细节刻画最精到的作品。情景出自《圣经》故事,表现耶稣被行刑前的时刻。饱和的画面中,围绕耶稣的四个人物形象迥异,服饰带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博斯生活的年代,战争与瘟疫在欧洲肆虐。这幅画可以被看作一个讽喻,影射当时的政治环境。右上角头戴橡树叶的人,象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当时他以武力重建教廷权威。左上角帽子插着十字箭的人,代表与教皇结盟的王权
 。他戴着护甲的手,正在为耶稣套上荆冠。左下角佩新月头巾的蓄须者是土耳其人,他诡异地盯着耶稣的胸口,同时抚摸耶稣伸出衣袍的手。右下角伸手为耶稣解衣的仰视者,象征犹太人,他侧脸的轮廓被深色的斗篷清晰地勾显。这四个鲜明的形象,或许暗示着教皇借力异教徒攫取权力。被他们围困的耶稣,则超然于自身的危难,眼神滑向画外虚空之处。这种出离于博斯式嘲讽语境的悲悯,令人印象深刻。相比博斯擅长的忙碌喧闹的造景,这幅画安静从容的气质是他作品里不多见的。
。他戴着护甲的手,正在为耶稣套上荆冠。左下角佩新月头巾的蓄须者是土耳其人,他诡异地盯着耶稣的胸口,同时抚摸耶稣伸出衣袍的手。右下角伸手为耶稣解衣的仰视者,象征犹太人,他侧脸的轮廓被深色的斗篷清晰地勾显。这四个鲜明的形象,或许暗示着教皇借力异教徒攫取权力。被他们围困的耶稣,则超然于自身的危难,眼神滑向画外虚空之处。这种出离于博斯式嘲讽语境的悲悯,令人印象深刻。相比博斯擅长的忙碌喧闹的造景,这幅画安静从容的气质是他作品里不多见的。

图5.11 《耶稣加冕荆冠》,约1510年
16世纪末,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迷上博斯。1591年,他买下博斯三联画中最明亮最离奇的代表作:《尘世乐园》( 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图5.12)。这时博斯已离世七十五年。

图5.12 《尘世乐园》,1490—1510年
这件作品接近四米长,高密度的内容,让它显得比实际尺寸更庞大。三块面板从左至右依次表现伊甸园、尘世和地狱。博斯营造了一个孔洞遍布,水系环绕的广袤园景。在这个空间里,以对称的方式安放了大量生物体般的建筑空间,小到帐篷,大到城堡。左侧面板明朗清奇,气氛高古。伊甸园里物种丰富,简直就是一部进化史,而且画家依着自己的想象添加了大量谐趣的注脚,从中可以看出刚刚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的视野。这一系列造景,是在讲述伊甸园的主人公亚当夏娃堕落之前的时光。
中间面板表现尘世,博斯设置了多重的比例关系。遍布画面的人物和兽畜,透视比例和风景契合,建立了视觉可信的基础。而花果枝叶、禽鱼虫贝,这些人们熟悉的事物被肆意地放大。在这一层比例无法自洽的基础上,博斯得以放置由微至巨的自造活体空间。这多层叠套的设置,产生了亦幻亦真的效果。博斯从不惰于细节的描绘,赋予画面中繁多的人物以人类所有的行为。如同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所有的人物都是赤裸的。这些怪诞的身体语言经过量化,形成道德层面上的挑战。在这里,人的形象是符号化的,博斯忽略了具体的人,专注于成就一套不可思议的视觉呈现。他利用隐藏在人们心理层面的先验,制造出令观者惊叹又微微尴尬的奇境。在当时,能够看到如此惊艳的视觉描述,应该是稀有的体验。
右侧面板色调深重,暗示了地狱。酷刑的场面贴近日常生活的认知,足以引发魔鬼就在身边的惊悚感。巨大的乐器代表肉欲,折腾着纵乐的人类。头戴铁锅的鸟怪是地狱王子,以堕落的灵魂为食,出自描绘地狱场景的12世纪爱尔兰手抄本《特努格达利的愿景》( Visio Tnugdali )。最醒目的形象,是一个被树枝般的腿脚支撑的中空躯干,附和了一张回望的面容,以恶作剧式的微笑看向画外,给了三段叙事一个了结的目光。据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推测,这是博斯的自画像。在黑暗的远景中撕扯出的光亮,形成了绝望的悲剧感。难以想象,博斯竟预言式地实现了几百年后工业时代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达成的光效。
博斯的画,详尽地呈现人类行为的可能性,以及他揣测中的终极报应。这在当时,可能属于一个类似加密语言的系统。画作的受众应该是一个特殊群体,基于共识,能够破解画中符号的具体含义。在今人眼中,博斯制造了一幕视觉盛宴,同时也进行了一场既直白又晦涩的道德宣讲。
外部面板的《创造天地》( Creation ,图5.13)代表着博斯和他的委托人的世界观。上帝位于画面左上,远望着自己初创的天圆地平的世界。那里没有喧闹嘈杂,也没有人的痕迹。

图5.13 《创造天地》,1490—1510年
《蒙福者的上升》( Ascent of the Blessed ,图5.14) [1] 给了上天堂一个具体的图示。博斯画了一个确凿的隧洞,而且这是他所有画中最光明的洞。他用画笔强调了倾泻的光感,产生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光学镜头达到的效果。光照亮了悬浮的天使和他们拥护的蒙福者。这幅画的神奇之处在于,画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了通天的视角,使这一历史性的宗教概念清晰地成像。

图5.14 《蒙福者的上升》,约1505—1515年
《干草车三联画》( The Haywain Triptych ,图5.15)也是菲利普二世的收藏,是对一句佛兰德谚语的视觉演绎:“世界是一个干草堆,每个人都能从中撷取他所能撷取的东西。”(The world is a haystack, and each man plucks from it what he can.)画面中央巨大的干草车周围,亚当夏娃的后代们自顾自地“上演”着德行。除了跪在干草车顶仰头祈祷的天使,没人注意到上帝正在注视着一切。他们任由鬼怪将干草车拖向右侧面板的地狱中。

图5.15 《干草车三联画》,约1512—1515年
在三联画的外部面板上,博斯画了《小贩》( The Pedlar ,图5.16)。画中人衣衫褴褛,疲惫地行走在佛兰德苍凉的风景中。他的身后,描绘了几组各行其是的人,与画面前景的骸骨、乌鸦与狗呼应,似乎在暗示人生旅程的孤独与最终的死亡归宿。贩夫走卒是画家晚年偏爱的寓言形象。这幅画淡然伤感的氛围,与画芯里的喧哗形成了强大的反差。

图5.16 《小贩》,约1512—1515年
博斯没留下任何私人信件或日记,只有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市政记录和圣母兄弟会的账簿提到他的名字。博斯将信仰和理念完全寄托于绘画。他的画由大量看似直白的细节构成,但其中暗藏机关,需要从宗教和伦理的层面解读。据说菲利普二世将他的画挂在卧室,经常一看就是几小时。在当今的博物馆,观者往往会在博斯的画前停留很久,与其说在辨识,不如说是解谜。
博斯的时代有人采取与他类似的风格作画,他身后也有像老勃鲁盖尔这样的追随者,但博斯的脑洞是开得最大的。他为什么这样画?近几十年,研究者逐渐达成共识:博斯并非异端,他的视觉语言系统,没有超出那个时代正统宗教体系的框架。他对天堂与地狱、罪恶与堕落的描述,与中世纪晚期的说教文学和布道是一致的。当然他从未忘记在其中加进私货,这些成就了他极端个人化的标志,也契合了特定委托人的观念和趣味。
此外,斯海尔托亨博斯人文思想活跃,伊拉斯谟
 就是在那里受教育,并成为教会的尖锐批评者的。博斯的骇俗画面中,隐含着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20世纪的人们觉得超现实主义新颖,可能是因为淡忘了博斯。在爆发的想象力方面,博斯并未被超越。
就是在那里受教育,并成为教会的尖锐批评者的。博斯的骇俗画面中,隐含着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20世纪的人们觉得超现实主义新颖,可能是因为淡忘了博斯。在爆发的想象力方面,博斯并未被超越。
1516年的斯海尔托亨博斯,胸膜炎肆虐,博斯没能幸免于难,但他的作品幸存了下来。解读他作品神奇的钥匙也没丢,且人人都有,那就是人类卓越的视觉系统。
[1] 这幅画是博斯表现来世景象的四联画的一部分,其他三部分分别为《人间天堂》( Terrestrial Paradise )、《堕入地狱》( Fall of the Damned into Hell )、《地狱》( H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