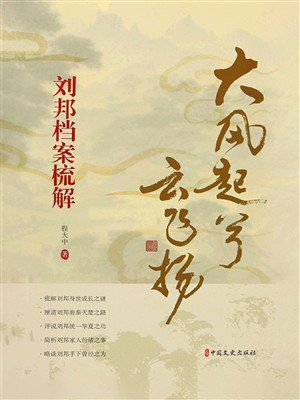从司马迁写《史记》说起
(序)
生活于西汉中期的司马迁所编撰的《史记》,是最早介绍西汉初期历史并完整传世至今的史料。《史记》为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约 3000 年的历史,其中对秦末汉初历史的介绍,尤其详尽生动地展现了无数精彩的人物故事。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该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所指主要是发生在秦汉时期的事情记载,因为之前的史述应该是司马迁取材于《竹书纪年》《世本》等先秦书籍,内容应该不会使班固作出如此直接明了的点评。班固说“其文直、其事核”,是说《史记》文字表达比较直白,且事实清楚;而“不虚美、不隐恶”,则是说《史记》中记载的人和事,没有虚夸溢美,也没有弃恶隐瞒:所以说是“实录”。作为后辈且亦是汉朝史官的班固,对《史记》作出如此评价,应该是基于对已知汉初历史的真切认识,因此他的评价也最具有权威性。
《史记》之所以能获得班固“实录”的评价,应该是源于司马迁扎实的文史功底、亲履的耳闻目睹、对陆贾实时记载文本的参考,以及尊重客观事实的严谨写史态度。
一、司马迁家学渊源,读万卷书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初五大夫,建元、元封年间任太史令,负责天文历法及朝廷的文书档案整理工作。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益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对天文星象、阴阳吉凶、黄老之术均有广泛的涉猎研究。因此,司马迁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并养成了读书学习的好习惯。《太史公自序》陈述为:“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除跟随父亲学习外,还曾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等。在他担任太史令后,又有条件以工作职责之便,翻阅学习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中提供的线索看,司马迁对上至古老的三代典籍,下至西汉司马相如等人的文章辞赋均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档案,更是他重视学习的必修内容。
司马迁扎实的学习积累和出身于史学世家的教养,使他具有一种源于血脉而致力于求实的文史大家之风骨。其父司马谈不仅知识广博,更是一位史学造诣很深的大家,他曾就先秦思想发展史写出《论六家要旨》一书,较高的学术价值一直为后世史学界所肯定。在他任太史令时,又立志撰写一部通史,并草拟了《太史公书》,可惜他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因病去世。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将该书写作纲要及积累的资料交给儿子司马迁,并告诉他说:“我们的祖先在虞舜夏禹时代主管过天文,在周朝做过太史。你以后若能做太史令,不要忘记我还没有写完的这部书。当今汉朝建立、国家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事迹很多,我们身为史官,如果不能把这些记录下来而造成历史文献的短缺,那就可悲了。”
 在当时已开始独尊儒学且百善孝为先的社会语境中,本已学识渊博的司马迁必然以父嘱为其人生奋斗之目标,且会认真负责地完成父亲遗愿。况且,三年后汉武帝刘彻真的安排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之职,这也使他更有工作之便完成父亲的遗志。由此,他耗时十四年之久,最终完成了《太史公书》(东汉末期始简称为《史记》)——这本自己致力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
在当时已开始独尊儒学且百善孝为先的社会语境中,本已学识渊博的司马迁必然以父嘱为其人生奋斗之目标,且会认真负责地完成父亲遗愿。况且,三年后汉武帝刘彻真的安排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之职,这也使他更有工作之便完成父亲的遗志。由此,他耗时十四年之久,最终完成了《太史公书》(东汉末期始简称为《史记》)——这本自己致力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
二、司马迁亲履考察,行万里路
司马迁自述生平,曾回顾自己在弱冠之年开始的考察之旅:“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 20 岁时开始的这次长途游历,起始于秦地,大致向东南方向,然后向北绕回“梁、楚以归”。他到过浙江的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去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楚国诗人屈原;还到达曲阜,考察了孔子讲学的遗址;还到过“鄱、薛、彭城”等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最后还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也就是说,司马迁在传说“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当地“长老”还进行了以口述史学为形式的访古调查。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入仕郎中后还曾跟随汉武帝巡行了各地,并奉命去巴、蜀和西南昆明一带视察。即“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司马迁 20 岁时开始的这次长途游历,起始于秦地,大致向东南方向,然后向北绕回“梁、楚以归”。他到过浙江的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去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楚国诗人屈原;还到达曲阜,考察了孔子讲学的遗址;还到过“鄱、薛、彭城”等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最后还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也就是说,司马迁在传说“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当地“长老”还进行了以口述史学为形式的访古调查。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入仕郎中后还曾跟随汉武帝巡行了各地,并奉命去巴、蜀和西南昆明一带视察。即“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司马迁这种几乎遍及全国的实地游览和考察,使他获得了大量感性的历史地理知识,为以后写作史书积累了重要而丰厚的知识储备。
。司马迁这种几乎遍及全国的实地游览和考察,使他获得了大量感性的历史地理知识,为以后写作史书积累了重要而丰厚的知识储备。
司马迁作为时任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遵父嘱游历天下,对开国皇帝刘邦及其早期同伴战友们的活动生平尤为关注。他曾专程赴丰沛做过调研,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的最后一段,他这样介绍其丰沛之旅和感想:“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司马迁不仅游历丰沛,还去了韩信的家乡淮阴。他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文末写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宋代文学家马存在其《赠盖邦式序》一文中,这样评价司马迁的行履出游:“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他还认为,司马迁的出行并不是单纯地为游览而出行,而是在已有书本知识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文化目标:“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的行迹均有助于他的“文章”:“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观之,岂不信矣哉!予谓欲学子长之文,先学其游可也。”

三、司马迁曾以陆贾所著《新语》《楚汉春秋》为重要参考
陆贾是在反秦时就跟随刘邦的幕僚,他不仅以能言善辩常被刘邦委以外使之责,还在刘邦取得天下后,以“马上可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之警言使刘邦猛醒。因此,刘邦指示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即要求陆贾写一部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之道的书,以参考学习。而陆贾也不负所托,陆续写出了共含有十二篇文章的著作。据《史记》记载,这部书得到了刘邦及众大臣的高度认可。因为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新语》论述秦汉及古代国家兴败的内容被刘邦称善,说明其中的描述不仅具有历史真实性,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该书至 700 年后的南朝梁代时仅存两篇,已不能完整反映该书的内容,但仅百年后的司马迁所看到的《新语》还是完整无缺的,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最后曾写道:“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此语固然是为赞扬陆贾的辩才,但也说明司马迁看到了完整的《新语》,并借此了解了先秦帝王先贤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总结。
陆贾在成书《新语》后,又将楚汉间发生的斗争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述。《后汉书·班彪传》载:“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我们理解,《新语》虽然被刘邦称善,但主要讲述的还是治国的道理,以及秦朝何以亡国而汉朝何以立国,而对楚汉之争的历史过程描述则相对简单。但楚汉之争又恰恰是刘邦人生胜王败寇的关键时段,所以陆贾在后来文帝时期又写了主要反映楚汉相争的《楚汉春秋》九篇。虽然该书逸于南宋而未能完整传至后世,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仅是清代逸文或其他史书中的只言片语,但我们依然可以判定,仅百年后的司马迁写《史记》,肯定会以当时仍然完整的《楚汉春秋》作为重要参考史料。
四、司马迁曾经受到的“腐刑”经历,增加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可信性
《史记》具有“实录”可信性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从司马迁曾经的不幸遭遇分析得出。司马迁在父亲去世不久后的元封三年(前 108 年)担任太史令,并按照父亲的遗嘱开始写《太史公书》。但到天汉二年(前 99 年)的时候,发生了关于如何处理骑都尉李陵投降匈奴的廷议,司马迁因自己的直言险些被杀。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妥妥的是忠臣良将之后,但他在被匈奴俘虏后,受到了汉武帝及朝廷的误判。在惊闻李陵投降匈奴后,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投降匈奴。汉武帝就此询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力排众议说:“李陵主动请命,仅带五千步兵深入敌人腹地,和三万多敌人骑兵作战多日,杀了很多敌人。李陵被捕没有自杀成仁,一定是想将来以功赎罪报答陛下。”
司马迁有违众意的回答让汉武帝很生气,他认为司马迁不将杀敌战功归于自己委派的元帅贰师将军,反而替一个叛徒说话,实在是胡说八道。因此斥责:“你这样替叛徒辩解,难道存心反对朝廷吗?”于是把司马迁关进监狱。司马迁被关押后,受到酷吏杜周的严刑审讯,但司马迁始终不屈服认罪。不久之后,有传闻说李陵在为匈奴练兵准备攻打汉朝,这似乎更加坐实了李陵已完全背叛汉国的罪行。汉武帝亦信以为真,判了为李陵辩护冤情的司马迁死刑。当时汉朝的刑法规定:如欲免死有两条路选择:一是交 50 万钱,二是接受腐刑。司马迁没有 50 万钱可交,本想一死了之,可想到父亲的嘱托和自己尚未完的《太史公书》书稿,以及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的时候写出《周易》、屈原被放逐的时候写出《离骚》、孙膑受刑被剜掉膝盖骨的时候写出《兵法》等名人名事,感到这些先古大贤都能在遭受极大困难的情况下写出名垂后世的大作,而自己也应该忍辱负重,完成父亲的遗愿。于是他选择了受辱而接受腐刑,但也从此失去了男性的生理功能。后来汉使者赴匈奴,了解到为匈奴练兵者是降将李绪而非李陵,但这时李陵全家已遭汉室屠门,而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也已受到了腐刑。受腐刑是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两年后,汉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并在不久后做了中书令,方得以有暇,寄心楮墨,于公元前 91 年完成了 52 万余字的《太史公书》。司马迁对自己之前生死之经历,在所写《报任安书》中,不仅向友人任安悲愤地控诉自己受到了超过所有刑罚、辱及人格的“最下腐刑”,还郑重阐述了自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表现了宁受屈辱也要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由上述冤屈之耻辱经历,我们很难想象司马迁还会在《太史公书》中写出“隐恶”的“虚美”之词。当然,以司马迁誓为写出流芳后世史书之执着,以及身处汉武帝刘彻刚愎自用下的政治环境,他也不会胆敢写出不符史实的诽谤之词。也许此言还不能完全说死,因为汉武帝在世期间《太史公书》并没有问世。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的最后说:该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也就是说,该书正本藏在了无人知晓的名山,而副本则在京城。“副在京师”的什么地方呢?实际上是保存在他的女婿——后任汉宣帝丞相的杨敞家中,而杨敞的儿子杨恽后来将此书稿献给了汉宣帝。由此可见,得以传世的《太史公书》(《史记》)应该是副本。就今天的认识而言,正本和副本的内容应该完全一致,因为不过就是一个备份而已。当然,对这一历史未知,或许还不能这样妄下定论,但司马迁遵父嘱而忠于史实的写作态度还是应该值得相信的。
为全面反映介绍西汉历史,东汉班固编撰了《汉书》。《汉书》对汉初历史人物的描述,除增加“惠帝纪”和将“项羽本纪”转入传记,以及不再区分“世家”和“列传”而均以“传”按卷排列外,其内容基本尊重《史记》对汉初人物和事件的记载。但为进一步增加史料的可信性,班固在叙事中较多引用了“诏曰”,这也是《汉书》与《史记》内容表现明显不同的地方。另外,如果说《汉书》中其他地方还有与《史记》有所不同,其表现最多的也不是正文,而是在后世历代版本的《汉书》中,先后增加了荀悦、应劭、颜师古等许多史学大家的大量“注释”。不过从这些方面,我们虽然看到的是两本书中相关内容的稍有不同,却更多看到的是后世史学家对《史记》的持续重视及研究成果,还有《史记》对后世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力。
上述所论,虽然是解析《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之缘由,但也并非完全认为《史记》无虚言及毫无瑕疵之处。且不说司马迁受君权神授迷信观念的窠臼,写了一些对刘邦神化的地方,而就其有关内容的不确切、不完整,甚至前后矛盾等问题而言,还是多有存在的。如对刘邦的介绍,其本纪虽然最为全面,但在后面介绍其他人物时,有时又会出现新的情节或前后不一的表述;又如《史记》中介绍的有些年份时间,在之后的《汉书》中并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呼应;特别是关于刘邦的名字和出生年份问题,因均记载不详,更是成为历代史学家一直追寻考证的问题;等等。
但是,白玉有瑕,不掩其美。我们不能完全用今天的行文修辞眼光,苛刻要求 2000 年前的这一史学新体例尽善尽美,而应该以十分客观的态度,认真分析探求《史记》的史学价值所在。不然鲁迅先生也不会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出于对司马迁著《史记》所作出伟大贡献的敬仰,和对上述些许模糊问题的发现以及史家一直存有的认识分歧,我产生了以今人档案的结构和内容形式对刘邦生平进行梳理归纳的念头,以使其事迹表现更为集中和清晰。我想,以《史记》为主要参考,以其他史书或传信为补充,再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分析,应该可以梳理出一份介绍刘邦身世及身边人的较详细档案。果如此,这也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