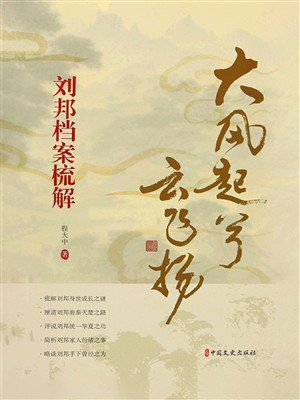一、姓名
汉朝开国皇帝,姓刘、名邦、字季,这是历代社会大众的广泛认知。因为自唐代以后,见之史书或文学作品的记载,均以“刘邦”作为汉高祖的通用姓名称谓,已成历史共识。但作为最早记载刘邦事迹的《史记》,以及后叙西汉全部历史的《汉书》之正史,都没有提到汉高祖的名为“邦”。那么,后世又如何产生或演化出“刘邦”这一被广泛称谓的姓名呢?
《史记·高祖本纪》这样介绍刘邦:“高祖,姓刘氏,字季。”其中没有说刘邦的名,但交代了高祖姓刘,字季。而《汉书·高帝纪》中的表述更为简单,仅指:“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居然连“字”都没有说。《史记》和《汉书》是反映西汉历史的最权威记载,其如此对汉高祖名字简单化处理,难免引起后世的诸多猜疑。
生活于东汉末年的秘书监、史学家荀悦,因汉献帝好典籍、常苦《汉书》文繁难读,乃遵其要求,按照《左传》编年纪事的体例,将 80 余万字的纪传体《汉书》,改编为“辞约事详,论辩多美”的 18 万余言编年体《汉纪》30 篇。其中明确指出了“汉高祖讳邦,字季”
 ,并解释“邦之字,曰国”。这是见之史书的第一次明确记载高祖的名为“邦”。虽然荀悦在书中并没有直接解释“邦”名的由来,但也说明了《史记》和《汉书》之所以没有提到高祖名“邦”,是因为“讳”的原因。
,并解释“邦之字,曰国”。这是见之史书的第一次明确记载高祖的名为“邦”。虽然荀悦在书中并没有直接解释“邦”名的由来,但也说明了《史记》和《汉书》之所以没有提到高祖名“邦”,是因为“讳”的原因。
西晋皇甫谧在其所著《帝王世纪》一书中采信了荀悦的观点。他说刘太公“生子邦,字季,是为汉高皇帝”。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亦附和荀悦的说辞。他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一书中说:“史记于高祖云字季,不书讳,余帝则讳与字皆不书。汉书本纪因之,马、班自以为汉臣故耳。”

名字是人或物的称号。在古代,人的“名字”指代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名”,一个是“字”。“名”通常在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而“字”则是男子至 20 岁举行冠礼(结发加冠)时取字,即“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至15 岁可以许嫁,则举行笄礼,并取“字”,即“女子十五笄而字”,所以女子在出嫁前被称为“待字闺中”。因此也可以说,“字”表示了一个人成年后的正式称谓,而“名”则是婴幼年时父亲所取的昵称。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亮”就是他幼时的名,“孔明”就是他成年后的字;东汉末年的大才女蔡文姬以“琰”为名,以“文姬”为字。另外,古人相互交往中,在不同的场合,“名”和“字”是各自表述的。对于非家庭成员或亲戚,称呼对方时,出于尊重只称其字,一般不直呼其名;而在向别人作自我介绍时,为示谦虚一般只说名,不表字。如诸葛亮通常就自称“亮”,而别人则称其为“孔明先生”。
古人的这种语言礼俗,早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先秦古籍《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公羊传·闵公元年》中讲得就更清楚了:“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即遇到君主、尊长或贤者时,不能直呼其名,也不能在书写的时候使用其名。所以,这些记载说明古时早已有了名讳之说,这也应该就是荀悦在《汉纪》中所说的“讳邦”的原因。
就上述礼法而言,汉高祖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其名为讳当应如此。但在比《汉书》更注重礼法的《后汉书》中,却将东汉历代皇帝的名讳一一写入卷首,而毫不避讳,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就史书对重要人物的介绍而言,其开篇还是应该需要将“名”和“字”都交代清楚,而后再通篇以字或职衔相称为合理,这样既符合史书记载的完整性,也能体现对人物的尊重。可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史记》或《汉书》原文中通篇没有讲到汉高祖名“邦”。但《史记》中又确实在多处贯穿了“以名为讳”的原则。如书中讲到一个本来名叫赵谈的人,司马迁为避开其父司马谈的名讳,把赵谈改为“赵通”;为避开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司马迁还把一个本名蒯彻的人写为“蒯通”。虽然赵谈和蒯彻在历史中都是不足为道的小人物而不可类比,但司马迁及班固毕竟还是没有直接指出汉高祖的名。
荀悦言“讳邦”,果然是汉高祖名“邦”吗?这也因此引发了后人对汉高祖“名”和“字”的探究。
探究一:汉高未名,或“季”既是“字”亦是“名”
此说的观点是:汉高祖本无名,或者“名”和“字”都是“季”,而“邦”字是汉立国后大臣们提出的。
最早表示此观点且尚能查到的历史文献,是唐代颜师古在《汉书》中所作的校勘注释,以及其后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的阐述。
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按:
邦之字曰国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颜师古这里是说“邦意为国,所以臣子们以邦代国以指高祖”。颜师古此解有些含混,他的确切意思应该是说汉高祖本无名,大臣们才以“邦”这个与“国”相通的字来作为汉高祖的名。
司马贞的表述比较清楚,他在《史记索隐·卷三》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按:《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
司马贞在此直接说到,他怀疑汉高祖即位前根本就是有字无名,或字即是名。而且他以东晋南朝时项岱说过的话为证,说汉高祖即位后才易名刘邦,因为避讳“邦”不避讳“季”,所以当时的汉将季布依然可以以季作为自己的姓。
司马贞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东汉末年荀悦所撰《汉纪》首谓汉高祖名邦,而当时通行的经颜师古校勘的《汉书》则不提汉高祖之名,但颜师古在《汉书叙例》“荀悦”条下,又说荀悦“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若依颜师古校勘为据,《汉书》本无,荀悦又依何本?是否存有荀悦自己杜撰或后人阑入的可能?
总之,这个因帝讳而不书的不寻常做法,确实让人不得不怀疑司马迁就是为掩饰汉高祖无名而为之,并为班固所继承。
探究二:“邦”是名,“季”是字,讳“名”说“字”不言“邦”
此说的观点是:汉高祖的名就是“邦”,但说名是忌讳,故《史记》与《汉书》均说字“季”而不说名“邦”。
最早持此说的记载,前面已经讲到,是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在《汉纪》中最早指出了“汉高祖讳邦,字季”。这里之所以“讳邦”,是因为汉高祖本就名“邦”。
南朝裴骃所著的《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其中记载:“《汉书音义》曰:‘讳邦。’”而《汉书音义》多被史家认为是由西晋臣瓒撰写。由此可见,古代持“讳邦”观点者大有人在。
假如我们赞同汉高祖本就名“邦”,应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史记·楚元王世家》载:
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而王次兄仲于代。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汉高祖一共有兄弟四人,大哥字伯,二哥字仲,四弟字游。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仅把刘邦三位兄弟的字都交代了,还特别点明了四弟刘游的名为“交”。那么刘伯和刘仲有没有名呢?刘伯去世早,其名无考,但刘仲的名确有记录在案。因为《汉书·高帝纪》中载:“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

结合前说“王次兄仲于代”,可以知道刘仲的名叫作“喜”。这说明汉高祖兄弟,除大哥刘伯之名无考外,二哥和四弟均有名有字。那么问题来了,难道唯独排序中间的汉高祖有字无名吗?这显然违背常理而难以圆说。如此说来,汉高祖以“邦”为名、以“季”为字,因而“讳邦”的观点似乎也是成立的。
后世对刘邦之名的取用与认识
仔细检阅史料,关于汉高祖的“邦”名,在后来有不同的认识和取用。
汉灵帝中平三年(186 年)刻立的《张迁碑》,其碑文中有“《诗》云旧国,其命维新”之句。实际上《诗经·大雅·文王》所云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张迁碑》改“邦”为“国”,这成为汉碑讳“邦”为“国”的孤证。但前此延熹元年(158 年)《郎中郑固碑》有“邦后珍玮,以为储举”语;后此初平元年(190 年)《圉令赵君碑》有“刊金石,示万邦”句,又都不避讳。这种前后不一之表述,显然让人难以判断适从。
“刘邦”作为汉高祖享誉后世的大名,后来在南朝梁代末年被首次使用出现。《梁书·世祖本纪》载:太清五年(551 年),侯景杀萧纲于建康台城,南梁群臣在江陵上表劝湘东王萧绎称帝。萧绎说侯景未灭,自己还不适合登大宝,并以周武王和汉高祖举例,且直呼其名:“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此时,刘邦之名虽正式公开使用并记载,但也并未解释汉高祖名邦的由来。并且,萧绎在太清、承圣(547—554)年间自撰的《金楼子·兴王篇》中,也是仅言“汉高祖名季,父名执嘉”,而再未出现“刘邦”之名。如果再仔细翻阅反映同时代历史的《全梁文》《梁史》《南史》《北史》等文献,也未发现刘季名邦的相关记述。萧绎一生著书甚多,在历代取得文学地位的帝王中,作为比肩“三曹”的“四萧”之佼佼者,他应该不会毫无根据地无中生有,其取处想来也应是源于荀悦之说,但为什么以后他又不再提及了呢?
直到唐朝,颜师古等人注释《汉书》、司马贞著《史记索隐》,引发人们的讨论与关注以后,汉高祖之名刘邦才开始为世人广泛认识并采用。但这并没有终止人们对刘邦之名由来的再认识,如前边讲到的清代王鸣盛就分析认为,汉高祖本有名,只是马、班讳之。他从因为马、班为汉臣以及史书体例的角度作出问答:
《史记》于高祖云字季,不书讳,余帝则讳与字皆书。《汉书》本纪因之,马、班自以为以臣故耳。其余各史则皆书讳某字某,沈约曾仕宋,而宋书亦皆书讳。夫史以纪实也,帝王之尊,当时为臣子者固不敢书其名字,若史而不书,后何观焉?各史不袭马、班是也。

王鸣盛的意思是,汉代其他帝王的名讳在史书中都有交代,后来各代史书中的帝王亦有名有字。如果因讳而不书其名,就不是纪实的史书了,后人怎么看呢?所以后世的史家不因袭马、班的这种做法。
在 2012 年首播的电视剧《楚汉传奇》中,汉高祖出场一直使用刘季这个名字。当他成为沛公后,萧何对他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县之令,不能再让人称呼刘季;当年诸侯在洛水边朝拜周天子,有人写诗称赞说“天子万年,安家定邦”,我觉得这个“邦”字很好,建议您改名为刘邦。这里不知编剧依何处史载说萧何为汉高祖取名为“邦”,要知道一百多年后,汉宣帝将自己的名字由刘病已改为刘询的时候,专门发了诏书布告天下,汉高祖岂能悄悄将名一改了之?但这也算是今人为汉高祖名“邦”出处的一种猜测或艺术性处理吧。
日本当代著名中国史专家佐竹靖彦,从西汉人扬雄编撰的《方言》一书中,发现有“膊,兄也”的记载,而“邦”和“膊”发音也很相近,即认为“刘邦”乃“刘兄”的意思。
 由于人们不能犯上直呼皇帝为刘兄,只好避讳不说亦不写。这又是今人一种新的判断认识。
由于人们不能犯上直呼皇帝为刘兄,只好避讳不说亦不写。这又是今人一种新的判断认识。
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在他的新著《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一书中,也未系统梳理刘邦其名的来龙去脉,而是仍然归因于避讳制度。他甚至这样含糊其词地说:
《高祖本纪》里高祖名字和生年的缺失,和这篇本纪里一再宣称的蛟龙、赤蛇、五彩云气等等,恰好形成一种反差很大的对比,并带上了一抹不易为人觉察的讽刺色调。

“汉高未名”更实际,约定俗成名刘邦
由此看来,我们还是回到“汉高未名”这一判断认识上来予以讨论,更为合理实际一些。
虽然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在读书识字很不容易的古代,给孩子起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也并非小户人家能够轻易办到的事情。小户人家生下孩子,多以排行或贱称敷衍应付,甚至几代无名无字的,也并不稀奇。即便以现在的农村习俗而论,以不分性别的子女排行,直呼为“二孩”“三妮”“四狗子”的也依然是屡见不鲜的常事。
就刘太公来说,他和刘媪只生有三个儿子,按照古代“伯、仲、叔、季”的排名,他们弟兄应该被依次称为“刘伯、刘仲、刘叔”,按今天的通俗话讲,就是“刘大、刘二、刘三”。比如三国时期的孙策、孙权兄弟,他们的字就分别叫“伯符”“仲谋”;司马懿有兄弟八人,其名排序亦先后为伯达、仲达、叔达、季达……另外,古人单以“伯、仲、叔、季”作字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夷吾,他的字就是仲;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范雎,其字是叔;先于汉高祖而和陈涉同时起义的另一首领吴广,字亦是叔;汉文帝时期的诤臣张释之,其字同汉高祖一样为季。
但问题是,古人虽然对兄弟如此排序,但作为老三的汉高祖是字“季”而非“叔”,又应该怎样解释呢?他为什么越过老三而被呼为老四的“刘季”?也许还有人认为古人多以“季”为“小”的意思,但这又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刘邦并非兄弟中的老小,因为在他之后还有一个弟弟刘交,所以此说并不成立。现在的问题是,“刘叔”去哪儿了?
其实汉高祖前面还有一个姐姐,史称“宣夫人”。《汉书》记载:“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由于史书中对宣夫人几乎没有记载,所以只能猜测她排行老三,或许名字里还有个近于“叔”字的三丫头称谓,这也许是刘邦被称为刘季的原因。只不过就家族传承和世俗习惯而言,女孩子一般不按兄弟排列为序。因此,是否刘邦前边还有一位早夭的三哥,还是刘太公打破常规之做法,此事还真是难以探析明白,而无法再予深究。
那时,处于乱世的沛县丰邑中阳里农民刘老汉和老婆刘媪生下汉高祖,没给起名设字,而是按乡村习惯排行称呼为刘季或刘四也极有可能。《史记·高祖本纪》开篇仅谓高祖“姓刘氏,字季”,并不言名,后文亦以刘季相称,直至汉高祖攻下沛县被推为首领,始称其为沛公这一楚国制度下的县令称谓。究其实,“季”就是按出生顺序排行,亦非父母专起的字,只是叫习惯了,人们按字给予称呼。多年后长安未央宫落成时,正值刘太公寿辰,汉高祖置酒大会群臣,在为父祝寿时仍自称“季”,呼二哥为“仲”。再看《汉书·高帝本纪》,开篇对刘邦的名和字均避而不提,而是直接称高祖。
《史记》《汉书》作为汉朝官修正史,无疑是关于汉高祖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但它们均回避了人物传记必须开宗明义清晰交代的名字,显然是确实不知道的无奈之举。
总之,汉高祖“邦”名之由来一直难以厘清,其称谓也只能按最早荀悦所说沿用,并为后世约定俗成。